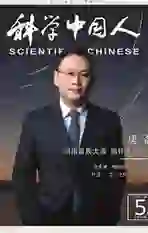张强弓:在“世界屋脊”上勇攀高峰
2021-10-12王艳敏
王艳敏
青藏高原,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屋脊”“第三极”。保护和建设好青藏高原对于地球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为了守护这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无数科学家将青春和热血倾洒,足迹遍布青藏高原上连绵不绝的山川。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张强弓就是其中一员。
“在青藏高原上研究工作的人,很难不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尽管高原自然环境恶劣,甚至有时候让人很难受,但每年还是想去走走、看看,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张强弓说道。
作为青藏高原年轻一代研究者,在前辈的指引下,张强弓也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高原探路人。十余年来,他已组织参与青藏高原地区野外科学考察数十次,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冰冻圈化学与环境研究。
“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我国西部地区在全世界中低纬度地区中拥有数量和面积最多的山地冰川,我们有48000多条冰川,面积超过5万平方千米,给我们冰川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张强弓说道。
自然资源独一无二的青藏高原,无疑也是众多科学家的科研殿堂。经过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努力,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环境变化的研究已处于国际第一方阵。在此基础上,我国科学家正积极推动以中国科学家主导,面向“三极”(南极、北极、青藏高原)协同研究的国际大科学计划。
“‘三极是全球变化的敏感区,是全球变化的指示器。推动‘三极研究计划,我们希望能从整体上研究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同时也为国际输入更多中国声音。”张强弓说道。
从地到天
回忆起来,张强弓其实从未想过进入冰川领域,在青藏高原上做研究,用他的话说,“这一切都是机缘巧合”。
2003年,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学前沿发展趋势,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藏高原所”)应运而生。时年12月2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复字〔2003〕165号文件《关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等单位机构编制的批复》,正式批准了青藏高原所的成立。2004年9月,从东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张强弓考入了青藏高原所,成为了首届研究生。
“当时青藏高原所刚刚成立,还没有招生权,是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代招的,录取之后再重新分配,所以我也是录取后被调剂做冰川研究的。”在初期建设阶段,青藏高原所组建了一支“站在高原、研究高原”的国际化、高水平研究队伍,张强弓的导师正是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当时刚从美国缅因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回国的康世昌研究员,其主要从事青藏高原的冰川学及冰芯气候环境记录研究。
“我的研究方向其实相当于经历了一个从地下到天上转变的过程。”张强弓介绍,地质专业主要是研究地球内部,到了青藏高原所之后,他转到了地理也就是地球表面冰川的研究,再往后又接触到大气化学方面的研究。“虽然从大的角度来讲都属于地球科学的范畴,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肯定是一个更加专业的方向,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去做青藏高原和冰川方面的研究。”张强弓说道。
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专业调剂,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特殊性注定了在这一领域做研究的人将承受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
早在2003年,导师康世昌就曾带队在西藏中南部的念青唐古拉山钻取了一支120多米长的冰芯,但大家觉得高原中部仅有一支冰芯,空间代表性不够。因此2005年,在导师的带领下,张强弓第一年进藏考察,并且直接走到了长江的源头——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峰,主峰海拔超过6000米。
第一次进藏研究就挑战这样的高度,对于当时刚读研究生的一群年轻人来说自然挑战颇巨。行进过程中不仅没有路,还有很多沼泽,每一次前进都格外艰难。经历了多天辗转,他们终于来到了冰川末端大概海拔5100米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搭建了营地,但之后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5100米海拔只是冰川末端,属于消融区,也就是每年积累的雪会小于消融的雪,要钻取冰芯必须在冰川的上部积累区下钻,才能获得完整的记录,而这段垂直海拔抬升不足1000米的旅途他们只能靠人力前行。
扛着沉重的设备,拖着早已麻木的双腿,他们在漫天冰雪中艰难地向选定的冰芯钻取点一步一挪地攀登前行。一天,他们从早上一直忙到傍晚,全身都已失去力气与知觉,以為可以收工休息的时候,没想到导师突然从冰川上跌跌撞撞翻滚下来,又累又带着激动地跟他们说:“我探到了一条路,咱们再把设备往上运一段吧!”
“我们当时一听真的崩溃了,野外还是很艰苦的。”张强弓笑着感叹。
不过,如果守得云开见月明,那这些艰苦与磨难也是有意义的。对于张强弓而言,第一次参加高原冰川考察的回报来得格外曲折与动魄惊心,他差点就因此耽误了毕业。
一波三折的雪冰研究
那次科考,在海拔5800米附近的地方,张强弓和团队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打钻的平坦区域,历经一个多星期,取出了一支147米长的冰芯,最后在牦牛的帮助下运回营地,之后又成功地运回到实验室,锯成了3000多块进行研究。在将样品水送到实验室后,他们得到了各种化学指标,只差一步就可以得到完整的历史记录,那就是年代。
冰川记录与自然及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冰川研究主要是想通过冰川的记录来反映气候环境的变迁。地球历史上一些重要的自然或人为事件,如火山爆发、核爆炸等都会在冰川中留下痕迹。要想确认冰川的年代通常需要找到核爆炸还有火山爆发等事件在冰芯中出现的信号。在他们的预想中,这个信号大概会在冰芯10~20米的地方出现,但反复找了许久,还是没有找到对应的数值。之后又花了整整两年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峰值的对应冰芯深度,然而,预期应该出现在20米左右地方的峰值,实际上在5米的地方就出现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的博士研究本来是想通过这支冰芯研究长江源头气候环境的历史变化,没想到跟预期的完全不一样。”为了顺利毕业,张强弓只得将博士论文进行了一个快速转化。
雪冰气候环境记录研究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现代过程,一个是历史记录。现代过程研究主要为历史记录重建提供基础。张强弓的博士论文本来以历史记录为重点,但当时,那块年代不明的冰芯不得不让他从历史记录转向了现代过程研究。在雪冰化学研究方面,他准确获取了珠峰海拔6500米至峰顶雪冰中数十个元素的含量和空间变化特征,分析指出珠峰雪冰元素含量与极区相当,受人类活动影响甚微,是北半球中低纬度大气环境本底的代表;首次全面阐明了冰川雪冰中典型重金屬汞的本底含量及其“冬高夏低”和“北高南低”的时空分布格局,给出了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大气汞沉降通量;特别是揭示了大气沉降颗粒物是控制雪冰中汞形态和含量分布的主控因素,由于颗粒态汞不易被还原和转化,可较好保存大气汞沉降信息,这些研究结果为冰芯历史记录的解译奠定了现代过程基础。
得益于扎实的功底与不懈努力,2009年,张强弓从青藏高原所博士顺利毕业,并获得2009年“中国科学院优秀毕业生”及“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之后一直留所工作至今。
从攻读博士学位到工作后的几年间,尽管科研方面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成果诞生,但张强弓却有些茫然。那块无法确认年代的冰芯一直横亘在他的心中,无法排除。
2014年,他将冰芯带到了世界上知名的核能、化工实验室——瑞士保罗希尔研究所,测试了冰芯中的一些放射性同位素,并将其与之前获得的相关信息进行研究。最后终于确定,格拉丹东这支冰芯的顶部对应的是1982年,但按理来说,这支冰芯的顶部应该是钻取时的2005年才对,为什么会是1982年?而且,这也代表着格拉丹东冰芯1982—2005年的记录都不见了,为什么会这样?
假如研究对象消失
“以往冰川连续记录了很长时间的人类活动历史,但最近几十年强烈的人类活动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快速减薄,所以最后我们发现,原来是强烈的人类活动把冰川近些年的记忆给抹除了。”张强弓说道。
冰川,就像一座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档案馆”,通过层层冰雪积累记录岁月的变迁。在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之前,冰川的积累区每年都会积累很多雪,一年又一年层层累积,如树之年轮一样形成非常明显的层理,在这个地方钻取冰芯可以获得完整的记录。研究人员不仅可以把这些冰融成水,测试里面代表气温波动的氢氧同位素比率,还可以测量水量,就能知道每年的降水量。同时,他们还能测试水中的各种化学指标,包括沙尘、离子、金属元素等,这些都是大气环境的指示,携带了远古时代大气成分的信息。在拥有世界上最大冰盖的南极地区,冰盖厚度超过3000米,科学家通过在南极钻探冰芯,然后将3000米长的冰芯从上到下排列,就可以看到百万年以来气温和大气成分的变化。但是现在,在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之下,地球上这一座座档案馆的资料正在流失,对于中低纬度的高山地区,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科学家预测,不远的未来还有更多的小冰川会消失……
“对于我来说,一个研究者的研究对象都不在了,还怎么继续工作呢?”在发现地球上的冰川正在加速消融这一不可阻挡的事实后,张强弓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他开始四处求索,冰川消退之后该如何进行研究。
有一次在翻看瑞士Stein冰川资料的时候,张强弓注意到冰川下面有一个湖,他突然想到,冰川退缩后,有没有可能冰川中的一些记忆转移到了湖中呢?后来,他果然从文献中查找到了Stein冰川和Stein湖之间的关系,里面记录了1970年代湖中污染物浓度出现了第一个峰值,这一峰值对应的正是欧洲大量工业排放的年代,第二个峰值出现在2000年以后。但那时欧美开始实施大气减排措施,污染物浓度应该下降,为什么反而上升呢?原来,冰川快速消融后,有些“记忆”转到了湖里。
得到这一发现后,张强弓顿时兴奋起来。“我又有了新的研究焦点,即便全球气候变暖,我的冰川研究还是要继续并且是可以持续的。”之后,他将这种想法和之前的资料汇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冰川和冰川湖所包含的信息是此消彼长的。冰川快速消融的情况下,冰川湖会扩大,也会接收到更多冰川带来的记忆。自此,他的研究也开始向冰川消融后对环境的影响这一领域转变。
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前人对高原冰川融水径流水文变化开展了诸多研究,但对冰川融水径流中化学组分的迁移过程及其对下游生态环境的影响缺乏系统认识。为此,近几年来,张强弓向这一领域展开了探索。
通过对高原内陆典型冰川和被补给湖泊“扎当冰川和纳木错”的持续系统观测研究,张强弓刻画了汞在冰川径流中的日变化特征和迁移过程,揭示了冰川消融对流域汞输出的控制和影响,发现高原冰川流域的汞产出率高于南北极,具有促进流域汞输出的强化效应。之后,他还对高原中南部数十个湖泊开展水化学系统调查,并深入研究了汞在高原水生态系统中的富集特征,发现高原野生鱼类和湖泊水生食物链具有显著的汞富集效应。
在此工作基础上,张强弓进一步建立了高山冰川影响区汞的分布和环境风险分区模型,综述展望了高原冰川流域汞循环及其环境效应研究,指出冰川消融是促进高山区域汞循环的活跃因子。他在Science发表的Letter文章“Melting Glaciers:Hidden Hazards”(《冰川消融是隐性灾害》),指出冰川消融释放活化微量有毒和营养元素对下游生态环境可产生长效和潜在影响,提出了冰川消融输出微量元素是隐性环境灾害的新观点。
这些研究深化了对山地冰川作用区和补给区元素循环的认识,被国内外多家刊物和媒体报道,并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19年发布的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 6(《全球环境展望-6》)引用作为全球冰川消融对环境产生影响的重要证据。
尽管这些年来在科研道路不断有新的想法与成果产生,但面对浩瀚无垠的“三极”研究,张强弓却始终觉得自己的攀登道路才刚刚开始。
站在巨人的肩膀远航
“这些年来,我国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在姚檀栋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带领下,一步步迈向世界地球科学的‘第三极,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发展迅速。冰冻圈研究也是类似,最早提出冰冻圈科学完整理论体系的就是以秦大河院士为代表的我国冰冻圈科学研究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的冰冻圈研究已在国际上占领高位。而现在,我深切地感知到我们正处于这两条线的交会处。”作为年轻一代青藏高原冰冻圈研究者,张强弓深有体会,“青藏高原与冰冻圈研究是我国科学家长期奋斗积累形成引领国际科学前沿的优势研究领域,我从事青藏高原冰冻圈科学研究,处在这两个特色优势研究的交会处,深感幸运而任重道远。”
近年来中国科学家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论文数量和被引用率稳居世界第一,在青藏高原环境变化的研究已处于国际上第一方阵。但青藏高原冰冻圈仅占全球一小部分,南北极的巨大冰蓋和季节性海冰动态变化在全球能量平衡中的驱动和反馈效应,是当前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协同开展青藏高原、南极、北极的“三极”气候与环境变化协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极是全球生态环境的重要屏障和关键纽带,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脆弱区。事实上,国家正在谋划从‘第三极出发,发起由中国人引领的‘三极大科学计划,这不仅是国家战略的需要,也是全球科学发展的趋势。站在国家层面,‘三极研究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帮助国家实现科技强国;站在国际角度,‘三极研究有利于全球环境保护,利在千秋。而作为我国青藏高原和冰冻圈这两大特色领域的青年学者,我们更应该主动思考并积极参与推进‘三极大科学计划,将我国的‘三极研究引向纵深和国际前沿。”张强弓说道。
为此,早在几年前,张强弓就已在这条道路上毅然前行。针对青藏高原大气污染以及全球山地冰芯消失的现象,他总结了利用山地冰川研究气候环境变化的优势,认为全球高山冰芯研究均面临冰川顶部减薄的挑战,并提出了应对冰芯记录消逝的策略方案,包括开展国际计划加快冰芯钻取,存储备份冰芯用于后续研究,实施新技术恢复解译已消失的最新冰芯记录等;他还指出近期“冰川消减—冰川湖扩张”的模态正在增强,提出加强冰川与冰川补给湖沉积物记录协同研究,以整体论思想认识区域环境变化的新思路……
然而,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张强弓深感青年学者才是“三极”研究的主力军和创新的动力源泉。2016年,张强弓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历任地学分会和北京分会理事。为此,在会员资助期间,他就积极发起创办“高极-三极”青年创新论坛,促进青年学者理解和把握“三极”研究前沿动态,加强跨地域、跨领域、跨学科间青年学者的交流合作。会议连续举办至今,已在国内外取得了良好反馈,有效促进了青年学者在“三极”研究领域的交流。2017年,他还获得了中国冰冻圈科学学会施雅风冰冻圈与环境青年科学家奖。
2020年,基于青藏高原冰冻圈化学与环境研究成果及对未来的发展规划,张强弓成功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但在他眼中,这只是科研的第一步。山峰有高度,科学无止境。站在“世界屋脊”,他将沿着前辈科学家的足迹,向着科学的高峰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