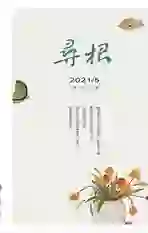“虎食人”与“人化虎”
2021-10-11陈熙罗雅文
陈熙 罗雅文



20世纪以来,巴蜀地区出土了大量带虎纹的铜戈。虎纹铜戈中特殊的一类是所谓的“人祠虎纹”或“虎食人纹”铜戈,如1975年四川峨眉山符溪出土了一件人虎纹青铜戈,铜戈正面有一个头发双结、跪坐绑缚着的人像。1972年,四川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村出土了一件人虎纹青铜戈,铜戈的正面有一个椎髻人头,反面有一个跪坐的人。此后宣汉进化村、渠县土溪镇、开县余家坝等地,也出土了类似的器物。一般认为,兵器上绘制这种图案乃是“厌胜”的象征,持有兵器的人可以借助神虎的力量战胜敌人或者鬼魅。如钱玉趾在《巴族蜀族彝族之虎考辨》一文中就认为,郫县铜戈是巴人铸造,戈上的单髻人是蜀人;峨眉铜戈是蜀人铸造,虎口之人是巴人,两种纹饰都象征着巴、蜀战胜对方的愿望。笔者认为,钱玉趾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巴蜀崇虎的因由
巴蜀地区出土众多虎形器物,除各地发现的人虎纹铜戈外,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还相继出土了金箔虎形器、铜龙虎尊、石虎等虎形器物。为何巴蜀地区如此崇拜老虎?
蓝勇在《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一文中认为,从仰韶到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经历了一个温暖期,此时期森林覆盖率高达90%,因而虎踪频现,重庆万州西南盐井沟村、沙坪坝区歌乐山、四川资阳雁江区黄鳝溪、筠连县政治乡等地相继出土了石器时代的虎类遗迹。在长期同虎的接触中,巴人了解到了虎的力量,进而将虎视为图腾乃至于祖先加以崇拜。蒙文通先生认为,《山海经》中的《大荒经》可能是巴人作品。《大荒西经》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西王母应为巴族所属氐羌系先民,具有明显的虎类特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巴族始祖廪君生于武落钟离山,“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廪君应当是巴人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的领袖,在传说中他可以化作白虎,具有神秘莫测的伟力。既然祖先或有虎形,或能化虎,巴人也就自认为是虎的后代了。《蛮书》卷十就称:“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
春秋战国时期,来自巴地的开明氏(鳖灵)取代了杜宇的统治,将崇虎风尚传到了蜀地。《蜀王本纪》记载,荆楚地区有一人名为鳖灵,死后尸体顺江而上到了蜀地,到了郫县地区后复活。蜀王杜宇令其治水,随后将王位禅让给鳖灵,鳖灵据此建立开明朝。所谓“荆”可能是湖北一带,即廪君所在的武落钟离山周边,也可能指的是川东巴地,此地在战国时曾被楚国攻占。无论是川东还是湖北,都是巴人所在地区,开明氏应当就是巴人分支。《山海经·海内西经》称昆仑有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这长得像虎的开明兽可能就是开明氏的图腾。开明入蜀,也将巴地崇拜虎的习俗带到了蜀地,因而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相继出土了金箔虎形器、铜龙虎尊、石虎等虎形器物,人虎纹铜戈在川渝地区也多有发现。
峨眉双结人虎纹铜戈的内涵
郫县和峨眉出土的两支人虎纹铜戈,纹饰上的人都跪坐捆绑,各被两个类似于牛角的物体包裹。钱玉趾认为峨眉铜戈上的双结人是巴人,郫县铜戈上的单结椎髻人是蜀人,类似于“牛角”的东西是一种枷锁或者牢笼,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华阳国志·巴志》载,巴人曾和汉王朝有过合作,世号“白虎复夷”或者“弜头虎子”,弜头,就是头发双结之意。从考古资料来看,这种“双结”頭饰曾出现在重庆冬笋坝等多个巴人遗址中,可见头发双结确实是巴人的特征,峨眉铜戈的发髻双结的人应该就是巴人。前文说到,开明氏源于巴地,入蜀后取代了望帝杜宇的统治,那么开明氏是否可能保持着巴人的双结发饰呢?如果保留着,那峨眉铜戈上的双结人还可能是开明氏统治集团。不过从文献记载来看,开明入蜀后并未保留巴式双结发饰。《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一带的夜郎、滇、邛等地,皆“魋结”,也就是说蜀地周围均是单结椎髻。刘渊林注解《文选》时,援引《蜀王本纪》称从蚕丛直到开明氏统治时期,蜀人都“椎髻左言”。三星堆的青铜人像,脑后均有一根垂直的辫发,而并无双结发髻。从上可见单结椎髻一直是蜀地居民及其周围夷人的特征,开明入蜀后就被蜀人同化,或许还通过“换辫易服”与巴人划清界限。(陈黎清:《四川峨眉县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6年11期)
峨眉铜戈上的人是巴人,又为何跪坐、捆绑,出现在蜀地的核心区域?研究巴蜀文化,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绕不开的,这个跪人的形象与金沙遗址的石跪人几乎一致。仔细看,铜戈上的人和石跪人,都是跪坐,都被捆绑,都有双结发髻,同峨眉铜戈上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有趣的是,金沙19号遗址发掘出跪坐人像时,旁边还出土了两件石虎,石虎的血盆大口正对着石人,这种摆放和峨眉铜戈中的人虎相对位置极其相似。同石人、石虎一起出土的还有三件石虎尾,据《金沙遗址》可知这些石虎尾可以插入石虎臀部,石虎尾呈135度的钝角,形状、弯折角度、相对大小等和铜戈跪坐人旁边的“牛角”可以说完全一致。所以,有理由认为,铜戈上的“牛角”实则就是“虎尾”,峨眉铜戈的纹饰当是对金沙19号遗址的复刻。
金沙19号遗址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出土的石人、石虎,多处涂有朱砂,朱砂为红色,代表着血液和光明,象征着生命与活力,同神秘的彼岸世界有关联,常常用于墓葬和祭祀活动中。老虎是自然界最为强大的存在,被巴人和开明氏认为是神灵和祖先,很显然金沙19号遗址为蜀王开明祭祀神灵和祖先的礼仪活动场所。根据《蜀王本纪》记载,开明之所以入蜀,是“死后”尸体顺江而上,可见他曾在巴地的战争中落败,他应该和巴人有血海深仇。《华阳国志》记载“巴、蜀世战争”,蜀人也和巴人频繁开战。19号坑中,巴人跪坐绑缚,其实就是蜀人和开明氏合谋对巴人进行的“诅咒”。《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开明氏毕竟出自巴地,更加崇虎而非崇鱼、鸟,因而其祭祀活动其实是巴氏的,即以真人祭祀先祖和虎神。双结石人或许还象征巴人中的贵族,那么这种祭祀活动或许还有“卧薪尝胆”的意味。
童恩正先生在《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研究》一文中就指出:“在武器和乐器上铸虎纹,无疑具有族蜀和巫术的含义。”开明入蜀后,蜀人也受其影响而崇拜虎,峨眉铜戈的纹饰是对开明氏祭祀活动的复刻,其持有者是蜀人,铜戈上的双结人是他们的对手巴人。峨眉铜戈中,虎的主体在戈“胡”部,也就是持戈者一方,仿佛虎神和先祖在庇佑。虎口朝向戈尖,头发双结的巴人乖乖地跪坐,象征敌人只能束手就擒。兵器上绘制此花纹,目的是“厌胜”,通过沟通天地神灵为自己作战,而削弱对手的战斗能力。当兵器嗜血之后,又达到了“人祀”先祖廪君、白虎的目的,使得持有者的力量进一步增强。
郫县椎髻人虎纹铜戈的内涵
既然峨眉铜戈的纹饰是为了“厌胜”,那么郫县铜戈的纹饰是否有同样的内涵?当然有可能。《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一带的夜郎、滇、邛等地,皆“魋结”,因此郫县铜戈可能也是刻画的战胜敌人的场景。不过郫县铜戈出土于蜀地的核心区域,单结人只是跪坐,双手并未捆绑,人也不在虎口之前,铜戈另一面还有一个形似王冠的物体……如此种种,说明单结椎髻人的身份可能并非其余蛮人,更可能是同样椎髻单结的蜀人。(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6年10期)
郫县铜戈中的纹饰是否也能找到对应的考古实物?确实可以找到类似的物品。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多件青铜跪人像和一具椎髻青铜人头像。这类青铜跪人和金沙石跪人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双手均未被绑缚,穿有整齐的衣服,这些人显然并非奴隶或战俘。既然三星堆一、二号坑是祭祀坑,青铜人又不是战俘和奴隶,那么必然是祭祀活动的另一主体——祭司。祭司在礼仪活动中需要身着整齐的法服,双手用于捧举供品或礼器,当然不能绑缚和裸体。郫县铜戈中的单结跪人,姿态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十分相似,均为跪坐、椎髻、双手自由,应当也是蜀人祭司阶层。铜戈的另一面,还有一个类似王冠的物体,应当就是祭司头部佩戴的法冠。
既然郫县铜戈上的人并非敌人,那么纹饰也定然不是为了“厌胜”,虎神也不可能吃掉“虎的传人”,那么铜戈上的人、虎又是何关系?从常理来看,铜戈花纹可能只是再现祭祀场景,不过笔者还有一个揣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巴氏先祖廪君的故事,廪君统一了巴氏,打败了盐水神女,在夷城稱王,死后“魂魄世为白虎”。在萨满教中,萨满巫师认为通过一系列祭祀仪式,身体可以转化为动物或半人半动物的形象,从而拥有超自然的法力。廪君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应当是集神权和王权于一体的首领,“廪君化虎”就是萨满巫师化为自然之灵的一个例子。既然开明氏源于巴地,自然也崇拜白虎和廪君,郫县铜戈可能描绘的就是开明氏巫师模仿廪君化虎的情形。
从神话传说中也可以看出,廪君后裔“化虎”并非个例。晋朝干宝《搜神记》卷十二载:“江汉之域,有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能化为虎。”可见廪君后人对“化虎”有深深的执念。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记载:“罗罗,乌蛮也。酋长死,以虎豹皮裹尸而焚……大德六年冬,京从脱脱平章平越嶲之叛,亲见射死一人,有尾长三寸许,询之土人,谓此等间或有之,年老往往化为虎云。”明代陈继儒《虎荟》卷三道:“罗罗,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从人类学调查中,也可以窥见巴蜀地区后裔对人化虎的深信不疑,至今,楚雄一些彝族巫师仍以为彝族经火化即可返祖化为虎。
总 结
峨眉铜戈和郫县铜戈的持有者都是蜀人,或者是“蜀化”的开明氏集团。峨眉铜戈上的纹饰是对金沙19号祭祀坑的复刻,戈上的人是蜀人和开明氏的共同敌人巴人,绘制“虎食巴人”是为了“厌胜”,兵器沾血后又达到了“人祠”的目的。郫县铜戈上的单结椎髻人,可以从三星堆遗址中找到原型,应当是开明氏巫师,花纹是“人化虎”之意,展现的是生命的升华。至于两铜戈上的“牛角”,笔者认为是“虎尾”,或许是作为沟通自然人和神虎中的某种介质。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