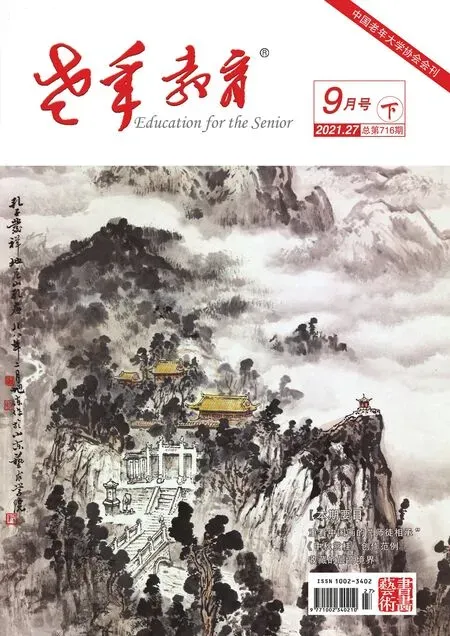重看中国画的“师徒相承”
2021-10-05□黄松
□ 黄 松
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中国书画及其“师承”关系亦发生了巨大变化。体制内美术学院教育体系的建立,使传统“师徒相承”的教育模式逐渐边缘化。然而,在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近几年师徒相承的美术教育正重新呈现出活力。
在古代,家传、交友构成难以超越的“师承”关系。古代画论中对中国画的“师承”关系多有记载,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说:“若不知师承传授,则未可议乎画。”在传统“师承”模式中,家族相传“子承父业”的模式孕育了诸如晋代王羲之、王献之,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等艺术家。尤其在古代“艺不外传”的规范下,通过父辈口传心授将一些外人很难理解的画理、画法常识传授给家庭内部成员。
除“家族相承”的模式外,“师徒相授”更是传统中国画教育中传承思想和艺术技巧的重要模式。学习的内容并非限于绘画技法,更包含品位、修养、境界、人品等精神文化内涵。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云:“凡画入门,必须名家指点……昔关仝从荆浩而仝胜之,李龙眠集顾、陆、张、吴而自辟户庭,巨然师董源,子瞻师与可,衡山师石田,道复师衡山。”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传统师承关系的延续有其必然性,主要体现在对技艺与思想的继承方面。
然而,“师承”并非只是跟着师父画。以沈周、文征明的师承关系为例,包括唐寅、祝允明、都穆及后继者,构筑起明代吴门一个博大的“朋友圈”。世交、姻亲、朋友、门徒关系,构成一张错综复杂而庞大的“师承”和“朋友”网络。他们近师师辈,上溯宋元,自成一格。

《溪山渔隐图》吴湖帆
至民国,名师未必出高徒,“明师”才能指方向。20世纪初,西学东渐,现代美术学院的雏形逐渐形成,徐悲鸿、刘海粟等人将西方美术教育学院体系引入中国,但中国传统“师承”方兴未艾。张大千的“大风堂”、吴湖帆的“梅景书屋”、冯超然的“嵩山草堂”,主要采取“师徒-自学”的模式。
不开课徒稿,直接给学生看古代真迹并有针对性、因材施教地借给学生作品带回家临摹,是“梅景书屋”的授业方式。看古画、鉴古画,以此提升学生的绘画技艺和眼界,这些古代流传下来的“师承”方式在“梅景书屋”得到延续。比起“梅景书屋”吴湖帆、“大风堂”张大千,“嵩山草堂”冯超然的名头似乎远不如前两位,但其弟子陆俨少却被广为知晓。对于学生与老师齐名,或者超过老师的情况,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徐建融归结为“名师”与“明师”的区别。而陆俨少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期间,更是培养了陈家泠、谷文达等不同艺术面貌的学生。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画教育日渐受西方学院教育影响。整个20世纪主导中国画教育的已经不再是师徒相承,而是学校教育,且基本上由西画家主持引领。尽管20世纪50年代后,学院教育主要以苏派素描的绘画方法“改造中国画”。但传统并未远去,中国画教育呈现出多元的形式,学生也表现出更开放的面貌。师徒式教学和美院教育以多种模式构建出的多元“师承”关系,在“师师父”“师古人”“师自然”中交错着多种可能性。
当下,中国画教育的现状则是学院西化、传承断代。21世纪以来,美术学院日渐成为中国画教育的主流。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人多以毕业学校判断“师承”关系,使私人教学呈现出边缘化趋势。
尽管如今的中国画教学更为宽泛,但在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下,书法、美术史、鉴定等曾为中国画创作服务的内容成为独立学科。这也造成中国画专业的学生普遍缺乏鉴赏力,甚至造成对传统中国画传承断代的后果,成为如今中国画教育不可回避和亟须解决的问题。正如郎绍君先生所言:“毫无疑问,师徒-自学模式不能取代学校教育,但学校教育应吸取师徒-自学模式的长处以改进自己。如推行兼有师徒制因素的工作室制、导师制等。对中国画教育来说,这也许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竹溪掬月图》冯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