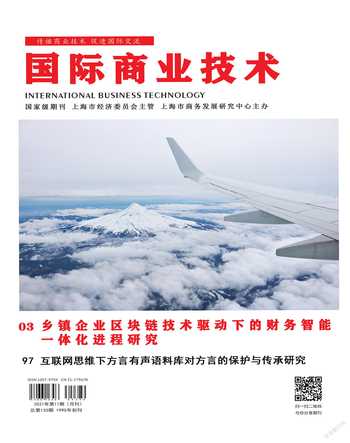经济危机理论与《资本论》在当代鲜活的生命力
2021-09-29陈文庆
【摘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始终伴随着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往往是资本主义世界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导火索,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生态环境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对此西方经济学家却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却显示出了鲜活的生命力。本文梳理了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经济危机理论,从原文出发探讨经济危机反复爆发的原因、金融危机导火索现象,并用《资本论》的思想精神探讨生态危机问题。
【关键词】《资本论》;经济危机理论;金融危机;生态危机
一、《資本论》揭示了经济危机反复爆发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经济危机。面对危机的反复爆发,西方经济学家自始至终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有关经济危机的理论,但《资本论》却揭示了经济危机反复爆发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的相对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两个角度探讨这一根本矛盾是如何导致经济危机反复爆发的。
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中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在劳动剥削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即使在诸如提高剥削程度、压低工资、压缩不变资本成本、增加股份资本等反作用下,利润率也会趋于下降,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①利润率下降会导致资本积累加速,同时资本的集中必然会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进一步提高,加速利润率下降,二者互为表里,最终会导致生产扩大与价值增值之间的冲突。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总结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在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向着绝对发展生产的趋势,另一方面其生产目的在于保有并无限制增值资本价值。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增值资本价值;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包含着降低利润率,贬值资本,从而发展劳动生产力。由此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在于资本本身,资本增值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只要这种生产方式存在,这一矛盾就会持续存在。③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积累引发的危机,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被描述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④,社会生产变得无序,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在此情况下资本主义采取抗衡措施只能一定程度上延缓矛盾,利润率的下降是必然的,因而危机也就会周期性的到来。
从剩余价值的实现来看,一方面现有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工资处于低水平,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有大量工人失业,这就导致整个工人阶级消费能力不足。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大量商品无法卖出就造成了生产的相对过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信用制度时指出,资本家生产资本无法转化为现实资本,原因在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有限,受工资和雇佣条件的影响,工人的消费能力是萎缩的,由此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一切现实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制的消费”。⑤资本主义国家对此采取的诸如开拓对外贸易、信用制度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扩大消费需求,但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剥削带来消费限制的根本矛盾,对外贸易和信用制度的链条一旦断裂,就会由金融风险引发国际范围的危机。
二、《资本论》提供了深刻认识金融危机的科学指南
当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但美国金融危机却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陷入泥潭、一蹶不振。当前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和本质是什么,马克思《资本论》提供了深刻认识的科学指南。
一些学者指出金融危机之所以是经济危机的先导,仅仅在于信用制度下过度的投机行动。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信用制度与投机行动中暗含了金融危机产生的种子,但根源仍然在于资本逐利造成的生产过剩。他说,“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⑥。
从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它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前面已经提到过为了扩大利润,资本家会加快资本积累、加速资本集中;为了促进剩余价值实现,缓解经济危机的破坏需要扩大消费需求。这些过程促进了信用制度的产生,一方面资本家突破了自身扩张资本的限制,另一方面突破了群众贫困造成的消费限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信用制度客观上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然而信用制度的产生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它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暴力爆发。⑦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资本扩张逐渐畸形,使得生产更加脱离市场需求,在扩张生产的同时营造出需求假象,使生产—消费矛盾隐秘并加剧。马克思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指出,货币危机的出现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⑧才会发生。由此看来,正是信用制度的出现才让货币危机出现成为可能,若是信用制度的某个环节突然发生问题,危机的爆发会更加深刻;而往往这种不测起源于生产过剩。
金融资本及股票交易更是加深了上述信用制度的不稳定性。信用制度出现后,金融投机资本和虚拟资本大量出现,形成了债券、股票及其他金融衍生品,更快的推进资本集中进程。这类金融产品是一种本身不存在价值的资本,在金融体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从而也就脱离了对生产—消费循环的注视。正是这些金融产品的出现加深了信用制度的不稳定性。马克思说,“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⑨,“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⑩。这也就是说,金融资本在其自身市场中的交易中很难发现矛盾,但它兑付为实体货币的过程格外惊险;金融产品膨胀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埋下兑付危机的种子,在此过程中若出现对实体经济信心的滑落(如,生产过剩),其贬值必然爆发金融危机,从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更大的影响。
从信用制度与全球贸易的关系来看,信用危机必然会波及全球范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信用制度也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金融危机发源地国家的资本输入地方及其贸易交流地方也都暗含了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发源地国家的生产过剩在国际贸易中会表现为进出口贸易均过剩,虚弱的全球信用链摇摇欲坠,加上发源地国家转嫁危机的需要,金融危机会迅速席卷资本主义世界;而同時随着资本输出地方的撤资,主要靠资本输入的地方实体经济也会惨遭不测。
三、《资本论》包含了正确理解生态危机的重要方法
随着工业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人类进入了工业和信息化时代,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但放眼世界,工业和信息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不禁让人们思考工业和信息化带来的生态破坏源自何处?虽然没有系统的阐述,但马克思《资本论》为我们理解当今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方法。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精神,生态环境的破坏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支配自然资源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这是资本主义转嫁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由此可以推及,即使个体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或者强制发展中国家遵守苛刻的环境规则,不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态危机也不可避免。
从生态危机的产生来看,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来的。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农业文明下人类要想收获就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人类将食物视作大自然的馈赠。然而工业文明开始之后,随着技术进步,水力、蒸汽动力、电力等动力来源逐渐更新,由此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也使人类不断地向自然索取。资本贪婪的属性使得资本家选择奴役自然的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的”⑪。人与自然的关系变为支配关系,自然资源成为了资本家获取价值财富的不变资本,为获得更高利润转嫁潜在的经济危机破坏,由此便埋下生态危机的种子。
从生态危机的本质来看,生态危机是资本掠夺自然资源价值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获得更多的资本。基于这种资本逻辑,资本家同自然资源的关系实际上也变为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自然资源被资本家视作榨取剩余价值的不变资本,因而也就不必考虑自然资源的恢复、生态的修复成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资本家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榨取剩余价值,就像贪婪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的肥力来提高产量一样。⑫虽然大自然有着自我修复能力,但是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索取过载必然带来生态破坏,资本不断地榨取自然的“剩余价值”,直至大自然自我修复能力的崩溃。竭泽而渔式的资源掠夺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发展,但资本的逻辑并不在乎。
资本为了转嫁生态危机的危害,不惜掠夺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资本扩张能力的增强,已发展地区自然的“剩余价值”趋于有限,加之民众对生活环境要求的提高,这种对自然资源的巧取豪夺转移到其他国家。依靠跨国企业形式,资本通过逐渐形成的全球资本链向外扩张,将生产环节、垃圾处理环节和资源消耗环节的企业迁至发展中国家,掠夺其生态环境资源,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崩溃。但人类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生态危机的危害并不仅仅影响所在国,发达国家也得承担生态危机的后果。即使再严格的国际环境法令,再高素质的人口,若不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也仍然会“剥削”自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李其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载《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3]王元璋,游泳:《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4]张亮,等:《理解马克思》,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1001571006。
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
作者简介
陈文庆(1998-),男,汉族,江西上饶人,江西财经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早期无产阶级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