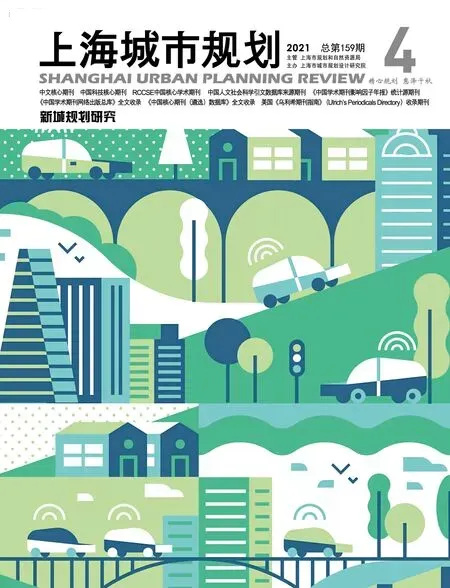规划书评
2021-09-27书评作者
书评作者:
李志刚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书籍作者:任雪飞
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年
21世纪是一个城市世纪。联合国在2014年宣布人类进入“城市时代”,全球城市化水平首次超过50%。2020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亦超过60%。事实上,过去30多年来,我国每年进城落脚的农民工规模在2 000万人以上。城市变得愈加重要,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和城市研究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城市的基础性研究也愈加重要。传统城市研究多围绕单个城市或区域展开,鲜有跨区域尤其是跨国的比较性研究。进入新世纪,“比较性城市研究”正成为新热点[1-3]。这是因为,传统的城市规划、城市理论建立在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实践基础之上,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地理环境为背景。然而,当代城市实践的热点“东进南移”,其发生之地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4]。城市知识的生产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热点向亚非拉诸国转移。传统城市理论与当代城市实践的空间错位成为当前城市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亟待开展针对主要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城市的系统性研究尤其是比较研究。Governing the Urban in China and India:Land Grabs,Slum Clearance,and the War on Air Pollution(《治理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征地、旧村改造与治理空气污染》)在202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正是这方面的成功尝试乃至典范。本书的作者任雪飞博士是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近年有诸多中国城市研究大著问世,是蜚声海内外的城市学者。本书同时被收入普林斯顿大学谢宇教授所主编的“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系列。
作为一本高水平学术专著,本书围绕土地、拆迁和环境治理等当代最重要的城市话题展开。全书共分7个章节,第1章是引言部分,系统呈现了全书的基本观点。第2章对中国和印度的城市概念予以对比,揭示两国城市内涵的差异。第3章则转向两个具体案例,分别是中国广东省的乌坎村和印度西孟加拉邦的辛古尔(Singur),围绕征地及其所引发的群体事件展开叙述。第4章的案例研究聚焦广州和孟买等特(超)大城市,主题是城中村改造和贫民窟改造。第5章则对比分析了北京和德里的空气污染治理。第6章讨论了历史维度下的两国城市治理及相关议题。第7章是全书的结论与讨论部分。这些内容主要基于作者2013—2016年在中印两国各地所做的实地调查,综合运用历史视角、比较视角和民族志(ethnographic)等分析方法,理论结合实证,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印两国城市治理上的差异与联系。任教授指出,中国城市研究历来强调中国城市的独特性、差异性。但从比较的视角出发,将中国城市现象置于广阔背景之下,则可带来诸多全新发现。据此,作者亦呼吁中国城市研究要由“基于地方的研究”转向“比较性的研究”。事实上,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研究并非只是案例呈现,它们恰是城市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5-7]。
具体而言,任教授的思考始于她在广州洗村所目睹的城管、街道的联合执法。对比而言,这种基层日常巡查在印度不仅少见,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想象,这种差异成为作者的切入点。传统上,学界对中印差异的解说中主要有两种观点:政府能力观、政治体制观。前者强调两国政府的能力差异,后者则强调两国差异化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任教授认为,中印差异的核心是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模式: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具决断力、执行力和动员力,对于地方事务的管理和干预力更强。相对而言,印度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尺度的地方政府的决策力和动员力较弱,对于地方事务的干预更多需要NGO、社会组织乃至政党等的参与和协作,在执行力上有较大局限。作者指出,中国的城市治理具有“地域逻辑”(territorial logic),存在诸多基于地域空间的制度,比如户籍制度、土地集体所有权等,当局及其基层组织具有很强的治理能力;相反,印度城市治理则是一种“结社逻辑”(associational logic),地方政府尤其是市政府没有实权,其土地所有权也相对复杂,其治理成效取决于政府、私人和社会组织的博弈与协作。这是一个贯穿全书的核心观点。通过各案例的深入实证,作者全面呈现了两种逻辑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与效能。
总体上,第1、2、6章是理论性章节,第3、4、5章是实证的章节。全书章节安排均衡有致,理论与实证内容的体量相得益彰,构成有机整体。就理论而言,作者对中印的城市概念做了精彩的分析和对比(第2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概念的精确界定和厘清无疑是比较研究的基础。事实上,城市的界定在各国有着很大差别。不同国家会以不同规模、密度、指标来界定城市。正因如此,近年一些学者们(Neil Brenner,任教授等)对联合国的“城市时代”的说法持批判态度,认为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方式相对粗放,忽略了各地具体的城市概念(人口统计)差异,忽视了各地城市实践的巨大差别[8]。为了把握城市特征及规律,近年学者们(地理学、规划学、地理信息科学、人口学、管理学等的学者们)无疑付出了很多努力。任教授则另辟蹊径,认为相对于精细化的城市边界描绘或人口统计,更重要的问题是城市身份的内涵,也就是成为城市居民的意义如何、对人们的影响如何。为此,任教授从历史维度详细分析了两国城市概念的演化及差别。相对而言,印度的城市人口的内涵比较稳定,而中国的城市人口的内涵则处于持续变动之中。也就是说,中国基层政府不断拓展其城市界定的范围,使得更多土地和资源被置于管理权限之下;印度的城市政府则因中央政府、本地社区等的博弈、协商而无法这样去做。作者指出,印度城市边界的划定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场域,乡村地区并不愿被吸纳或划定为城市地区。从城市地理学角度看,印度城市指的多是严格意义上的非农人口的高密度建成区,而中国的城市概念则往往同时包含建成区和周围的部分乡镇,实际是一个城市区域(city region)[9-11]。殊途同归的是,随着近年我国乡村振兴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加速推进,城市户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农业户口身份反倒有了一些优势,部分农民也不再一味地追求城市化。
实证部分是本书的精华。本书的第3、4、5章跨越了3组中印两国的大小城市,深入细致地探究几个核心领域:土地、拆迁、空气污染,它们也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工业化和土地开发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痛点和难点,也是涉及“维稳”的大问题。任教授认为,两国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不同的是尺度上的差异:中国是城市和村级政府,而印度则是区域级的地方政府(州政府)。通过对比分析广东的“乌坎事件”(2011年)和印度西孟加拉邦的“辛古尔事件”(2006年),发现两者均涉及招商引资、征地,出现开发争议下的群体性事件;不同的是前者具有“地域性”,无论是征地主体还是涉事群体均局限在乌坎村,村民们表达不满的对象主要是村委会和市政府;后者则是“结社性”的,征地主体涉及州政府,抗议者不仅包括本地居民,还包括诸多NGO、政党等各类组织。
第4章关注了广州城中村(冼村)和孟买贫民窟(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周边的贫民窟)的改造项目。任教授认为,虽然同是涉及土地开发的城市更新项目,两者也表现出明显差别:中国的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全程参与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印度的贫民窟改造则主要依托于开发商,自下而上的性质更加明显;而且,广州城中村改造中的村民往往获得大量补偿,印度的贫民窟则仅有少量合法居民能获得一定面积的安置房,原因当然在于前者拥有集体产权,后者则对其占用的土地并无产权可言。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在补偿获得机制上存在很大差别,广州城中村的补偿主要是在村集体的地域范围内,户口是关键;孟买的贫民窟的补偿则主要基于“结社政治学”(associational politics),得失取决于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与联合。以机场贫民窟为例,补偿取决于居民能否证明自己在商定的时间点在贫民窟住下,需要居民与住房组织进行谈判及达成共识。
第5章关注的是北京和德里的空气污染及其治理问题。任教授认为,传统研究强调中印环境治理上的分野在于“政府—市场”,前者更依靠政府,后者更依靠市场,但这种划分忽略了中印两国环境治理的实际进程。事实上,北京的环境治理同样具有“地域性”,空气污染的指标分解到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是一种有针对性的问责制。就德里而言,空气污染的控制并非政府牵头,而是建立在各方利益主体的协作上,NGO发挥着核心作用。作者发现,诸多NGO的动员能力(尤其是对印度高院的游说和动员)对于环境治理具有决定性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城市的环境治理有其主体也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等,而印度城市的环境治理则似乎缺乏责任主体。当然,更加广泛的公众参与是两个案例均面临的挑战。
这些案例表明,中印两国在城市治理上所采用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具有一定互补性的。中国的城市治理需要更多纳入“结社性”策略,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并发挥更大作用,这样也有利于减轻基层政府的治理压力。印度的城市治理则应更加具有“地域性”,尤其要赋予城市政府更多更大的权力,提升其治理能力和执行能力,从而提升治理成效。当然,“结社型”治理和“地域型”治理的划分也并非绝对。例如我国的城市治理虽以地方政府的主导为特征,但其中的“结社性”也是明显的:中国社会以“关系”著称;政府、部门的“条块”间普遍存在着博弈与协商;近年城市决策如国土空间规划的公众参与水平和强度也在持续提升[12]。
总体上,这是一本语言简洁、娓娓道来的学术大作,它为我们全面解析和认知中印两国的城市治理开辟了一条“比较研究”的新路。通过深入、细致和长期持续的努力,任雪飞教授阐明了两国城市治理的格局与特征,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在地现实、治理图景和历史脉络。不仅如此,围绕“地域性”和“结社性”特征,作者建立了一个清晰有力的分析框架,实现了对于中印城市治理体系的系统化解析。这些成绩的取得,也全面展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持之以恒的探索毅力,以及始终关注底层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