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丛林深处:马克思与韦伯现代性问题再探讨
2021-09-23周来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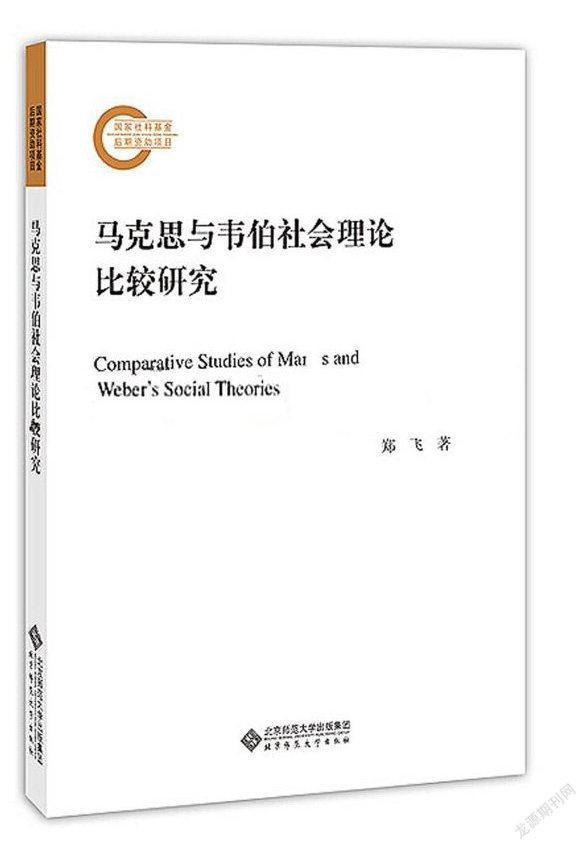
周来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马克思与韦伯有着诸多的理论关联,这种关联不仅源于前者对后者的深远影响,还源于两者都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都为批判理论和冲突社会学等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源泉”,而且源于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将两位思想巨人置入不同的比较视域中展开言说。他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创始人,一个被誉为“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他们都对资本、异化、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等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都将共同的关注点聚焦于现代性。现代性问题虽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它已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现代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众多,对马克思、韦伯任何一位思想家展开研究都是十分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在厘清两者理论的基础之上,置入比较学视野中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这是一件更为艰深且艰难的事情。而郑飞博士积十多年之功所著的《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不仅敢于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展开尝试,更是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著成了近年来这一研究领域鲜有的理论力作。该著不但有助于我们走近真实的马克思和韦伯,而且为我们走近他们所共同关注的架于社会理论之上的现代性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脚手架”。
首先,对比较性前提的独到探讨。比较学方法是近年来各学科普遍运用的研究方法,但在这种普遍的背后也往往存在着误用,存在着硬“比”硬“较”或是有“比”无“较”,存在着外在化、形式化倾向。而该著则建立在内在的、真实的比较学方法之上,把对现代性批判的深入探索作为马克思与韦伯比较研究的自觉前提。郑飞认为,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体系都是根植于对时代性问题的诊断,根植于现代性批判。马克思虽未直接使用过“现代性”一词,但他的整个理论是立足于对社会历史的深入考察,立足于对现代性理论的独特的、开拓性的阐释,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现代性批判。以研究现代性理论著称的贝斯特和科尔纳,将马克思誉为“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的社会理论家”。郑飞指出在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上,马克思不是先在地设定某种本质或规定性,而是从现代性问题最基本的物质规定性和观念规定性入手,从问题而非体系出发展开研究。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现象的反思深入到现代性的本质,指出现代性是建基于机器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货币—资本逻辑运动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虚幻形式”,其本质是一种“异化”。
而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危机、理性双重性等问题的深入分析,同样是围绕着现代性批判展开的。尽管在韦伯的著作中没有展现出一条如马克思那般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层透视与批判的清晰主线,但对“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现代的本质”的反思构成了韦伯整个理论框架的隐匿主线。韦伯将现代社会理解成合理化产物,并合理化构成了其分析现代性问题的主要维度。这一原则不仅贯穿于现代社会生活,而且还体现在商品生产过程之中,这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本质的判定。郑飞对马克思与韦伯之比较可能性的探讨是极具启发性、创见性的。特纳于1991年在为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韦伯文选》撰写新版序言时曾指出,马克思与韦伯“两人都是以批判的眼光来分析资本主义,也都属于更普遍层面上的對现代性现象的一种考察”。洛维特、吉登斯等同样断言应将现代性批判作为两者比较可能性的契合点。郑飞不仅极具洞见性地契入到这样一个比较的共同“问题域”,而且对域内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清晰的阐释,并在阐释基础上对两者之异同进行了深入分析。
其次,对现代性批判之存在论基础的深入挖掘。正如郑飞所指出的那样,面对复杂的现代性现象,马克思与韦伯分别从不同角度予以总体性把握。他们都力图兼顾物质层面与观念层面、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等的统一,“都是在这种总体性的关照下来提示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而绝非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因素的考察”。马克思从人类历史之一般和资本逻辑批判两个层面,也即是从构成人类社会存在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对现代性加以特殊阐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示现代性批判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基于存在论基础上所发动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从意识战场领域的“诸神之争”转向现实、实践的过程。也正是基于这种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传统哲学的变革,使马克思对哲学及现代性现象的理解获得了唯物主义的阐释。马克思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出发肯定了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地位,认为人类的其他活动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并在此基础上给予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精神活动等以唯物主义的说明。如果马克思仅仅肯定物质生活在人类中的基础性地位,那么就只是完成了对现代性现象的唯物主义阐释,而并未就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予以说明。而马克思恰恰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现代性存在之基础予以说明和揭示,“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其现代性批判的出场路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现实生活中最普遍的商品入手,通过对商品表征的揭示完整呈现出现代生活的实质与被遮蔽的本质。商品形式的奥秘恰恰在于,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物的商品却内含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背后所表征与隐含着的是金钱、货币,是西美尔意义上的“世俗的上帝”,是决定一切存在物比重的“特殊的以太”,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改变了现代社会的面貌,其秘密在流通领域、在对劳动的吸附,实质是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地揭示了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贯穿,澄清了现代性存在论的基础。
正如郑飞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原则是揭示现代存在论基础之前提,而这种存在论基础的澄清则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的。在笔者看来,某种意义上就致思理路而言,韦伯对资本主义及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考察则介于马克思与西美尔之间。韦伯从社会生活的诸多角度,从微观视域的合理化过程来揭示现代性的存在主义论基础。在其《经济与社会》《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等著作中,韦伯分别从文化论与制度论两大视角考察了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文化论与制度论彰显的是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两者并不具有高低、主次之分,而是强调“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每一种解释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强调应将两者完整、有机地结合。文化论侧重于精神、思想、观念等文化因素在现代性生成及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制度论则偏重制约现代社会生活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因素。当然,在此我们应看到,尽管马克思与韦伯在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考察中有诸多共同点,如二者都立足于对现代性的成因、表现、本质等给予总体性把握,而非将物质或精神中某一因素突显为决定性因素,但这种共同点并不能抹杀两者在研究路径与解决方案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基于对现实生活中诸要素不同地位的定位及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分歧一方面体现在展开形式之不同,马克思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展开,而韦伯则是以文化论与制度论两大主题展开;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理论的体系框架架构不同,马克思的理论架构是层级系统,在这个理论架构中物质生产方式是基础,而其他生产方式都是建基于此之上,而在韦伯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构架系统则是平行模式,各因素都是作为“理念型”而平行存在的。
再次,对现代性视域中意识形态批判的深入阐释。意识形态构成了当代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关注的焦点性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意识形态与现代性、现代社会间的重构与反重构等复杂关系。也正是基于此,英国学者大卫·麦克里兰指出,意识形态探讨的是我们“最基本的观念的基础和正确性”,是整个社会科学中最难把握、争论最为激烈的概念。而从现代性视域对意识形态问题给予系统性、深入性的关注,则非马克思莫属。正是由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概念得以广为流传。正如郑飞所言,意识形态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维度,将意识形态视为现代性社会存在的“观念副本”。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指出意识形态并非中性概念而是具有阶级性的,是以合理或合法的面具遮蔽真正的社会存在,遮蔽社会生活与交往方式的真相。意识形态掩盖和颠倒人们之间的真正关系,其功能在于为“现实”辩护,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持的是现存的阶级统治关系。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商品入手对意识形态形成的根源进行了考察。在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中认为,我们看作为一种“物”的商品的本质被假象遮蔽起来了,商品被赋予了某种神奇的魅力,人们像崇拜神一样崇拜商品。马克思从对商品的分析深入到对拜物教的批判,通过这一批判“马克思解开了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之谜”。在现代社会中,拜物教主要表现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副面孔,而三者之中资本拜物教则是“真理和归宿”。马克思通过对拜物教特别是资本拜物教的深入分析,通过“资本”批判揭露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根源,呈现出了“真实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真实”。
而韦伯通过现代性考察发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合理化原则,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构成其分析思想文化问题的基本架构。韦伯在分析为何在西方并且唯有西方文明走向了那样一条独特的资本主义道路中,指出音乐、建筑、印刷、大学、资本运算的理性化等现象与因素并非是西方所独有的。西方之所以走上了现代类型的资本主义,源于背后所隐藏着的发展“内因”,但这一内因的生成是无法用“理性主义”来解释的。这一内因便是以入世禁欲主义、责任伦理、天职观等为主要体现形式的“新教伦理”,新教伦理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隐秘内核,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价值支撑和精神力量。在这种分析中,韦伯从正面强调了作为新教伦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合理性内涵,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合理化的产物”。郑飞指出正是韦伯发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合理化原则,尽管他没有将这一理论系统化,但他所留下的这一理论遗产对日后的卢卡奇等影响深远。在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上,郑飞创见性地指出马克思与韦伯虽都承认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但在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独立性这一问题的理解却存在分歧。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存在,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隨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变迁。社会存在具有决定性,意识形态尽管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但却依附于社会存在。而韦伯则基于自身理论的“平行体系”,强调文化论与制度论、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间的非决定性和同等重要性,认为作为一种合理化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立领域,具有相对独立性。
最后,该著还对马克思与韦伯的异化理论、技术批判理论、效应史考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如在对如何解决异化问题的理解上,指出马克思对异化的超越是实践的超越。与之相比,韦伯对异化问题则更多是充满忧虑,深切意识到合理化的“吊诡”。“建立在专业官员制度和理性的法律之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形式合理性代替了传统的实质合理性,这种代替的进步性表现为可能会实现某种形式上的公平与正义,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铁笼”式的奴役。在这种合理化中,可能最终会导致“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韦伯语)。面对这样一种“铁笼”,韦伯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软弱无力的。韦伯指出人类“恶”的因子可能会从这“铁笼”中出走,而克服这“铁笼”的人类所依靠的将仅仅是意志而非理性。不但如此,对于这种意志是否能呈现出不间断的、长期的活跃性,韦伯同样“不抱什么希望”。又如在对技术批判问题的理解上,郑飞指出基于时代背景的差异,马克思对技术持一种辩证的态度,认为通过“生产-技术的内在超越”能克服现代性的局限,并创见性地指出,技术成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恰恰源于自身的矛盾性。韦伯则将现代技术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对技术持一种悲观态度,这种判定对日后的思想家特别是以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影响深远。
难能可贵的还在于郑飞是一位深度关切现实、关注我们脚下的土地,有着强烈担当意识、使命意识的学者。这一点我们从该著陷入沉思的艰深“结语”与充满家国情怀的“后记”中深深可见。尤其在“后记”中,郑飞对当前学界所推崇的“价值中立”原则进行了“痛心疾首”式的批判与深层反思,指出价值中立的过度化、无立场化使“‘恪守’价值中立的一些‘学者’日渐表现出远离现实的倾向”。这种倾向集中呈现为或是沉迷于象牙塔中的概念游戏,或是改头换面式的新瓶装旧酒,或是简单移植式的挟洋自重,或是拾洋人牙慧式的自诩多闻,而“这样的‘中国学术’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
无疑,该著是近年来现代性领域的一部佳作,是郑飞在这一问题上长期研读、耕耘、探讨、运思的结晶。该著以郑飞深厚的理论基础为研究前提,以明确的问题意识、独特的理论视角、真诚的现实关切、翔实的文献资料为研究基础,对马克思与韦伯所聚焦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思考。在笔者看来,该著无论就理论内容还是学术价值,已超越了对马克思与韦伯现代性理论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性研究,是中国年轻一代学人以中国话语表达中国观点、反思中国问题、阐释与解决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现代性难题的一种尝试性范本。基于这种深耕之上的可能性阐释与超拔,才能使之与国内学界关注此问题的学者共同将此问题的探讨不断地走进丛林深处。尽管在走进中可能会发现“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但他们会懂得“林中有路”,懂得“什么叫作在林中路上”。
(责任编辑:李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