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策略的“性别”
2021-09-23景欣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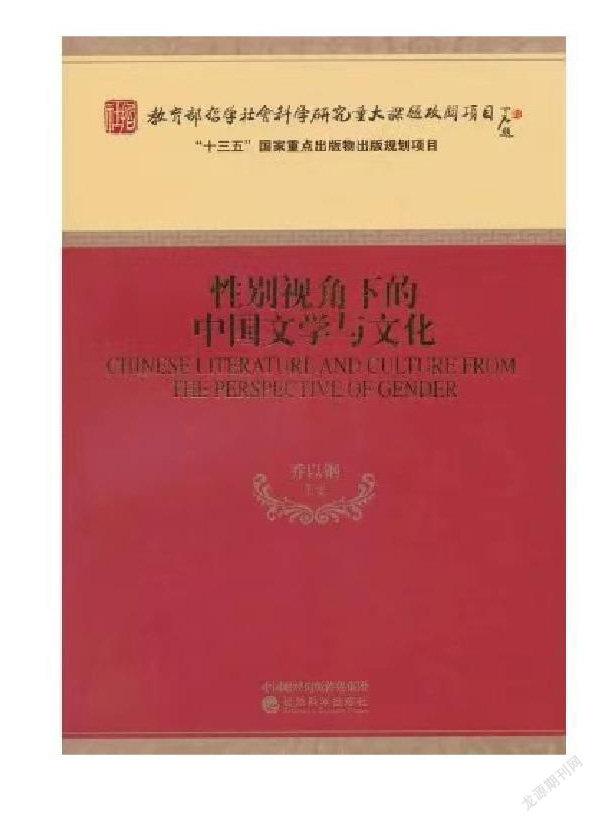
编者按:近年来,文学领域中的性别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女性文学研究论著。研究者们不仅开拓了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同时凭借本土的理论资源丰富了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与实践本身的内涵。在此过程中,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努力寻求进一步打开文學与文化现象新空间,努力打通文学研究与文化建设的密切关系。为此,本刊编辑部特约青年学者围绕乔以钢和林丹娅两位女性文学研究前辈的学术著作展开评论,期冀能为推进文学领域中的性别研究尽绵薄之力。
景欣悦,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女性形象谱系与现代中华文化建构整体研究”(19ZDA276)。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与社会文化的转型息息相关。晚清以降,中国被动开启现代化之路,传统的伦理秩序、道德文化、历史观念等遭遇冲击,缄默于历史的妇女问题为现代知识分子所关注,并被引入现代文明的建构之中。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1916)、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1927)、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1930)、黄人影的《当代中国女作家论》(1933),以及茅盾的《庐隐论》(1933)、《冰心论》(1934)等则是这一领域的初步实践。而当时的妇女运动同构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未形成独立的发展,本应具有主体属性的“女性”“倒置”为一种独特的“风景”①被发现。与之相应,与女性/性别相关的文学研究尚处于非自觉的前理论化状态。
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萌生了相对自觉的性别观念,开始了研究范式的探索和理论建设的尝试。在其发展的40年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女性文学研究处在社会文化转型后的探索期,多重思想资源杂糅并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伴随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与传播,女性文学研究集中于对传统性别文化及其运作机制的剖析和批判,流露出激进的理论锋芒。21世纪以来,强调两性差异以及男权批判的研究导向得到一定程度的纠偏,“性别”研究逐渐取代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空间得以扩展。
纵观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百年历史,其经历了从隶属于现代文明整体进程到回归女性本位再转入历史化性别研究的演变轨迹。在此过程中,将自觉的现代性别观念融入研究,确立性别研究的本土理论体系和独立品格成为当代中国女性/性别文学研究的重要旨归。这一方面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另一方面却因异轨的文化诉求引发了争议和讨论。如何推动性别理论的有效本土化?如何把握文学与性别的复杂关系?如何打破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乔以钢等所著的《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给予了积极而科学的回应。该书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结项成果,同时是南开大学乔以钢教授及其合作团队在2006—2016年间展开的中国女性/性别文学文化研究的总结。其将“性别”作为一种复义的研究策略纳入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之中,展开了卓有意义的探索。
一、性别研究的本土化实践
性别研究作为“舶来品”,自其开始进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就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尴尬和本土化的难题。早在1987年,女性主义理论方兴未艾之时便有研究者指出:“西方女性是在西方特有的政治、文化、妇女生态土壤上开放的文学之花,它们不是中国女性文学的楷模,更不会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归宿。”②此后,西方性别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度成为“热门”。与之相伴,异域理论与中国历史、现实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日渐突出,性别研究的本土化建设成为近年来学界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与提出“本土化”的研究意识相比,究竟如何展开合理有效的理论本土化实践却并非易事,建构新的性别理论更是一个长远的系统工程。
《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对于本土化问题有着明确的认知和判断,目的本身”。③这意味着,该书侧重践行本土化的过程,而非寻求一个本土化的结
果。故其所实践的理论建设不是基于民族认同的“民族化”“改造”,而是在客观评判和理性分析基础上的“本土化”或“在地化”尝试。例如书中“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一节系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叶嘉莹先生所撰。叶先生以西文文献为基础,梳理了后结构女性主义代表人物,露丝·依丽格瑞和海伦·西苏的性别观点,为其论述女性词人词作的“双性之美感”提供依据。但在分析中却并未完全承袭西方理论,“而只是想透过她们的一些光照,来反观中国传统中的一些女性词人之作品的美感特质”。④理性吸收外来理论的内在逻辑,加以学术操作而非立场性批判,可以说是性别理论本土化的前提,亦是该书提供的研究策略。
除了对西方理论采取放开、包容的态度外,性别理论本土化实践的另一面是充分尊重中国的本土经验、挖掘中华民族的传统性别文化资源。2003年,贺桂梅梳理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思想/理论资源,归纳为新启蒙主义话语、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话语三种资源。⑤将革命、启蒙等现代话语引入女性文学研究,正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语境深度观照的结果,推动了性别研究的本土化。但性别问题不仅涉及社会文化的变迁,亦与个体的生命体验有着深刻而紧密的缠绕。基于传统文化逻辑的性别意识是当代中国潜在的集体无意识,可视为女性文学研究的第四种思想资源。实际上,诸多性别问题的争论正是现代价值与传统观念之间的交锋与博弈。由此来看,探究中国传统性别文化的话语资源,索解其结构和内涵,既是性别理论本土化不应忽视的环节,亦能与当前的社会生活形成有效的“对话”,彰显性别研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
在探索中国古代的性别文化方面,该书不是口号化的倡导,而是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实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挖掘中国古代思想典籍中的性别文化与性别观念,例如道家的阴阳冲突与平衡、儒家的秩序实用主义等;二是将古代的文学作品、文化现象,以及人物原型等纳入到性别议题的讨论;三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进行学术史的整理和反思。凭借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中国文学内在的性别话语和文化传统得到了必要的观照和讨论。
近年来,女性主义批判的理论激情减弱,与之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进入了“瓶颈期”和“反思期”。学术资源的本土化不应仅仅是对全球化与差异性并存格局下滋生的“影响的焦虑”的反应,更应当付诸主动的、具体的、科学的实践。对于异域理论的包容态度和学理性运用,对于现实语境的观照和传统性别话语资源的探究,是《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所进行的理论本土化实践,亦为此后中国女性/性别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合理性、建设性的研究策略。
二、文学与文化的双向互文
性别研究并非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性别对文学产生意义通常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土壤、文化心理以及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从性别视角重审中国文学及其演变不能忽略其中的文化因素,单纯声讨文学中的男权文化,展开立场式的文化批判则容易忽视文学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格。而《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则试图通过文学与文化的双向互文,兼顾性别问题的文化因素和文学研究的审美维度。
该书虽以性别介入文学研究,但并未囿于封闭的文本世界,而是试图创建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动态理解机制。整体来看,研究不仅呈现了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发展的纵向演变,同时勾连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转型。从考察文学作品产生的文化语境,再到辨析其引发的社会文化思考,该书始终将文学与文化置于纵横交织的关系研究之中。书中“古代妇女创作的文化土壤及其感伤传统”一节在分析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探索了其诗文中的审美艺术特点。其中隐含的逻辑是,特定的文化土壤规范了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而其所形成的“感伤”风格则成为女性文学的一个文化传统,由此文学与文化形成了动态的互文性链条。此外,部分研究还重视传统文化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对现代性别观念形成的影响。例如“私奔”模式的古典叙事传统与鲁迅《伤逝》中性别书写关系的解读;又如通过梳理“木兰”故事的形变,剖析近代民族国家话语对这一形象的征用与收编等。这些研究以文史互证、古今对照的方式洞悉了文学产生的共时性文化,同时观照了千百年来积淀的历时性传统。
在扩展文学的性别文化空间的同时,该书坚守了文学的本体地位。一方面,文化问题产生于具体的文学作品。易言之,文学不是用以论证的材料,而是生成学术问题的“母体”,圈定了文化讨论的边界。另一方面,研究尝试从性别视角出发,探索文学的审美问题。这一研究思路看似陈旧、过时,但却是中国性别研究领域所忽视的内容,以及较难攻克的学术问题。长期以来,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常以两性差异为依据,解读文学的艺术特点,如男性文本的刚毅、恢弘,女性文本的柔美、细腻等。这一判断的背后可能存在性别本质主义的偏见,从而遮蔽文学作品的审美特质和丰富性,加重社会关于两性认知的刻板化和定型化。只有尊重文本事实,不做理念先行的概念分类,才能以性别为策略客观评价文学作品的艺术品质。如“‘五四女作家的女性观及其创作”一节肯定第一代女作家们在新旧文化冲突中彰显的社会文化意义,但也点明了其艺术层面的欠缺。另外,透过书中多个个案分析可知,男性作家同样可以细腻、敏感,如郁达夫;而女性作家也
可以书写关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历史题材,如宗璞。实际上,作为一种文化身份,性别很难说会直接作用于文学的艺术表达,但其与审美品格之间却常存在隐秘而复杂的纠缠。总体来说,该研究对文学的审美性有所涉猎,并未展开全面系统的探讨,但其所呈现的研究趋势,仍具启示意义。
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分野推动了研究的精细化和专业化,但也建造了无形的学科壁垒。受此影响,当前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意识还相对匮乏,而“性别”的引入不仅带来视角的更新,更意味着文学与性别及其相关的文化体系产生了关联。《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兼顾文化生态和文学本体的研究策略平衡了两者的关系,对学科分野存有一定的“破壁”意义。
三、文学文化现象的多元探析
长久以来,性别研究的一个基本结构性认知是男女两性的二元关系。这种结构的形成根植于人类的生物属性,强化于历史秩序的建构过程。波伏瓦在被誉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中,石破天惊地指出:“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性是他者”。⑥这一观点揭示了西方传统的罗格斯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强调女性重构主体的重要性,但却陷入了主体与他者的二元逻辑,并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性别理论建设。而作为文化身份的性别并非一个原子化的概念,它始终与其他身份相互规约、彼此渗透,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言:“性别的建构并不都是前后一贯或一致的,它与话语在种族、阶级、族群、性和地域等范畴所建构的身份形态交相作用。”⑦因此,将复杂的性别问题拆解为两性的秩序政治,显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简单化和片面化。
关于性别二元结构的反思,《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不是以后结构主义的对抗性思维消解性别,而是以中华文化经典如《周易》《礼记》等为依据,经过对传统文化的溯源揭示性别及其秩序逻辑的复杂。该书在承认宗法制度尊卑有序的前提下,认为在“上主而下从,男主而女从,嫡主而庶从”的关系准则中存在“相互补充为用”的实用主义哲学观,“而在‘上、‘男、‘嫡三个主导方面的交叉地带,留有很大的模糊空间,不是刚性的二元对立的绝对尊卑关系”。⑧这意味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性别不是单线结构,而是处在多重关系所编制的网状结构之中。于是,关于古典文学《天雨花》中性别意識的探析,便可从父女冲突、妻妾关系等多方面展开;而关于当代作家张洁文学创作中女性观的讨论也可由主体性矛盾、两性关系、代际关系等多角度切入。可见,中国传统性别文化内在秩序的复杂性为多元的性别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昭示出性别二元逻辑存在的局限。
除了关注性别内在结构的本土特征,该书在研究中还注重将性别与种族、族裔、阶级、年龄等文化身份相融合,对文学文本和文化现象展开多维度的分析和阐释。例如书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茫茫的草原》的解读就是从民族、性别、阶级三个不同的方面展开,进而挖掘其历史叙事生成的意识形态背景。此时,“性别”不再是审视文本的唯一视角,而是诸多视角之一。
性别研究的多元化策略不单能够全面、客观地把握研究对象,还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论意义。首先,一些此前未被重视的文学作品,如古典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得到了应有的关注,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版图;其次,从多角度辨析文本,有利于贴合文学产生的历史语境,避免单一性别视域造成的偏见或盲视;最后,文学中的性别表述蕴藏复杂的话语机制,而多元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洞察其背后盘综错杂的权力关系。
男女两性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构成我们对性别的基本认知,但不应将其本质化和绝对化。《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通过多资源、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反思了性别研究和社会认知中的二元思维,形成一种有“性别”而不惟“性别”的研究策略,促成了性别问题多元化理解的可能。
“性别”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而其作为“问题”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因为女性要打破传统格局争取权利,即基于两性的对抗。时至今日,关于女性/性别议题的讨论仍然容易陷入男女战争的逻辑框架。突破二元思维实现多元认知,实际上也是对于“人”本身所拥有的復合身份的尊重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性别文学研究的未来注定不会聚焦在两性的差异,而是致力于对有性别的“人”的人文关怀与文化反思。这也是所有人文学科研究的终极目的与归宿。
四、结语
《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在前言即开宗明义地写道:“在人类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认知事物的视角和方法起着重要作用,人们获得怎样的知识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视角和方法不同,认知的结构也会不同。一种新的学术概念的提出,往往意味着研究视角的拓展或研究方法的更新。‘性别这一范畴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引进和运用就是生动的例子。”⑨即是说,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引入“性别”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与文化。而研究最终所展现却不限于此,“性别”不仅是进入文学文本和文化现象的视角,更成为一种研究策略。所谓的“新”并不在“性别”本身,而在于如何将“性别”置于文学与文化中进行思辨与考察。从这个角度
而言,该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一次再解读,更在于为未来中国女性/性别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合理有效的研究范式和“更为复杂而有弹性的‘性别讨论空间”。⑩就理论资源的建设而言,该书秉持了开放包容、科学理性的态度,致力于实践外域理论的本土化。面对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该书积极推动文学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坚持文学本体的同时兼顾性别议题的特殊性,尽量克服文学研究的空洞化倾向。在认知观念层面,该书尝试打破传统性别研究中牢不可破的二元结构,弥合了女性主义理论所营造的两性对立以及社会场域中的性别成见,实现了性别研究的历史化、多元化和人性化。由此观之,该书所建构的研究范式恰好暗合了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关于未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愿景,那就是“包容性”“人性化”以及“冒险精神”。11总之,《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以“性别”作为研究策略的实践为此后相关工作的展开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文化史意义。
注释:
①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2页。
② 马婀如:《对“两个世界”观照中的新时期女性文学——兼论中国女作家文学视界的历史变化》,《当代文学思潮》1987年第5期。
③④⑧⑨ 乔以钢等:《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7,31,2,前言页。
⑤ 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⑥ 西蒙娜·徳·波伏瓦:《第二性》,郑克鲁译,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⑦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页。
⑩ 董丽敏:《性别:作为文学分析的方法——评〈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及相关系列丛书》,《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1期。
11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责任编辑:斯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