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的“结构意识”
2021-09-23肖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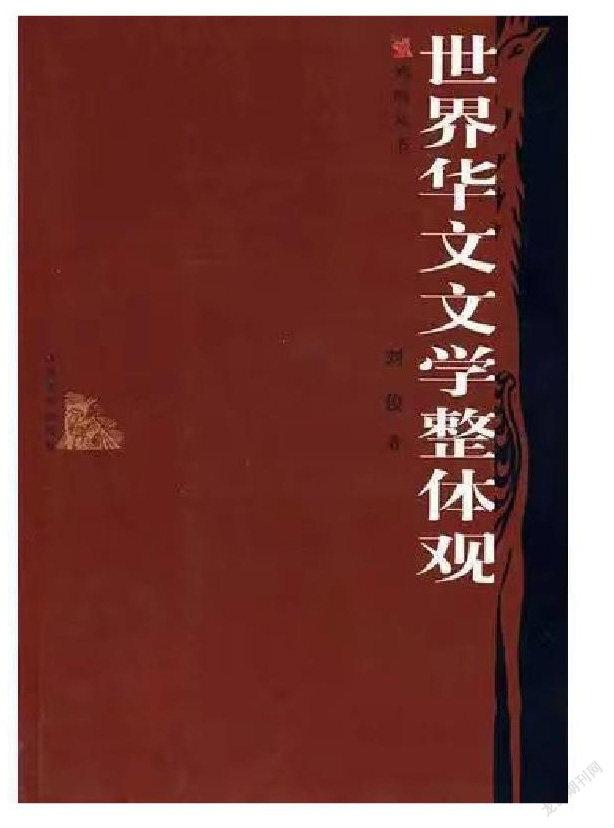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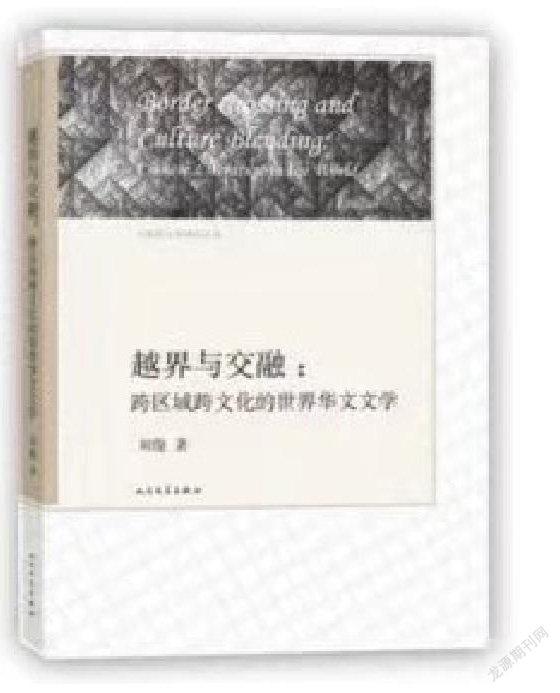

肖 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14ZDB 08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的共生态研究”(17BZW036);中央高校青年教师创新项目“中外文化互渗里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31511910301)。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伴随改革开放应运而生,四十年来顺应全球化的趋势,该学科的史料累积、理论建设、批评视野与研究范式已然具备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分庭抗礼的资格和规模,而后者也越来越难以涵盖、统筹、整编前者的发展势头和壮大潜力。“世界华文文学”要在学科建制上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量齐观,除了需要教育/学术体制推陈出新之外,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独当一面的研究“结构”是这门学科能自立门户的重要标志。一套卓有成效的“结构”突显的是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联,在重新厘定个案在一门学科中的位置的同时,拓展以往的研究领域,打散僵化的研究模式,在冲破區域疆界、跨越文化藩篱的重组过程中形成这门学科的“整体观”,以新角度、新方法、新问题构建一种别开生面的学术空间。
30多年来,刘俊教授孜孜以求的最大目标之一正是能开创这种学术空间的独特结构,尽量弥合中国大陆内地的现当代文学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之间的排异性,改变后者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里的附庸状态,以“越界交融”“复合互渗”的“结构意识”勘探包括中国大陆文学在内的世界华文文学共同体,也惟有在自成一体的结构当中,一位成熟的学者才能发出自己独树一帜的声音,显示自己别具一格的存在。
“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学科命名迄今尚未得到公认,争议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世界”与“华文”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世界”的空间性显示该学科的“跨区域”与“外部属性”,“华文”的族裔性则意味该学科的“跨文化”与“内部属性”。 用“跨区域跨文化”的思路重新认识近代以来华人以中国为根、散布世界各地的文学版图,是刘俊完成关于白先勇的博士论文之后,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一个极富象征性、影响力、历史感和多样化的个案研究出发,挺进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基础和背景,深入世界华文文学共同体时日渐成熟的整体观,由此改变“大陆文学中心主义”的僵化型态,构成一种结构性的颠覆,在全新的参照系的指引下,单一的中国本土视野察觉不了的问题才得以浮出地表。
现代文学为何“现代”,以及如何“现代”?历来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对于如此包罗万象、 与时俱进的开放型话题,局限于中国大陆本土疆域显然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非但不能一窥“现代”之全貌,甚至全然误解了“现代”的本质,而华人与华文的流变多样也难免于削足适履、生搬硬套的编排,沦为中国本土现代文学史论的陪衬与末流。
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首当其冲来自于和世界文学的同步态与错步态的相互影响,外国文化强势输入的同时,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被动或主动地去国离乡,从期盼落叶归根到乐于落地生根,从屈辱的单向“离散”到逐梦的双向“飞散”,全球华人的身份与心态、国籍与认同、血脉与信仰早应随环境的变迁与时代的更替而具体分别对待。有鉴于此, 包容四海、不离本源的“世界华文文学” 更能彰显“现代文学”求新求变的精髓所在。《打破三个“中心主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期待结构性调整》一文是刘俊的“结构意识”破旧立新的尝试。针对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于1985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刘俊提出带着历史局限和思维惯性的“大陆文学中心主义”“精英(雅)文学中心主义”和“新文学中心主义”构成的“整体观”显然画地自限、漏洞百出,只需把视野稍稍扩大,“改造民族灵魂”这一中国新文学的总主题就不再适用于曾受殖民统治的台港澳地区的文学。正因为此,陈思和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分期,强调战争对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莫大影响,如此才能将台港澳文学同等、有机地纳入“整体观”之中,真正实现结构性的突破。
循乎此,刘俊强调“世界华文文学是以华文为书写载体和创作媒介,在承认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源头是来自中国文学,同时也充分尊重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各自在地特殊性的前提下,统合中国之内和中国之外的所有华文创作的文学,所形成的一种跨区域、跨文化的文学共同体”。①如何观照、言说、绘制“跨区域跨文化”的文学共同体正是刘俊的结构性创新之所在,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简要论述刘俊在同质与异质、源头与支流的“互文结构”中所秉持的伦理关怀,以及在全球现代化进程、方式、结果千差万别的各版块华文文学的“类比结构”中,对现代的共性与个性的一贯追问,但由于各版块历史、现实语境的差异,跨区域跨文化的华文文学对现代性的追求必然呈现“同步态”“错步态”的关系,因此需要一种斜对称的方式使互文结构和类比结构达到平衡。
一、互文结构与伦理关怀
相较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他者”是世界华文文学里更显著的存在。这个后殖民理论里的核心概念,以客体、异己、国外、片段等特质构成了“本土”的对立面,“他者”与“本土”一方面显示了各自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在彼此参照中形成互文关系。在《“他者”的存在与“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一文中,刘俊指出美国华文文学里的“他者”是针对中国(跨地域)和美国(跨文化)的双重“他者”,借助他者的视角和他者的立场感同“他者”的意义,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坐标中提炼出美国华文文学里的五种“他者”存在和两类“身份”追寻,揭示弱势、边缘、少数的他者在充满偏见、顽固、无知、仇恨的环境中遭遇的人生悲剧和心灵痛苦,因此在平等的基础上正视差异、包容异己不仅是学术品格,更是伦理关怀,其源头正在于刘俊的首部专著《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悲悯已不再只是一种看取的角度和立足的制高点,它已内化为一种精神品格和情怀气质”。②
“自我”的形象建立在对“他者”的态度上,如何观照“他者”也就等于如何观照“自我”,由于与生俱来的视角和立场形成一个学者在协调“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时形成的洞见与不见, 身为中国汉族学者,刘俊对“中心”“边缘”“华语”“华人”这些“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里的关键词一直保持警醒。在《“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的生成、变异、发展及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论述中心》一文中,刘俊批驳了史书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的“逆向歧视”(站在海外立场对抗汉族中心主义),也指出王德威对大陆学界提出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否定实则透露出他不自觉的海外立场。③
无论站在何种立场,除非正视海外华人“由华入夷”的身份游移与困惑是中国本土卷入现代进程的产物,承认海外华人基于各自移民国所呈现的“他者”特殊性,否则何以认识中国本土“自我”的全貌。如果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过分夸大乃至敌对,否定他者的平等地位,其实无意中承认了他者的强大,反而暴露自我处境的不堪一击,最终不仅难以肯定自我的主体性,甚且消耗自我的合法性。“华夷之辨”这一与时俱变的议题本应对两者不作等级差序上的区别,但在权力运作下从来不乏自我、他者的优劣之分,回答“世界华文文学”里华夷辩证的难题尤其需要充满伦理关怀的新结构。刘俊在《“跨区域华文文学”论——界定“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新思路》一文里指出,当具有双重属性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给研究造成越来越大的困扰时,我们只有用“跨区域华文文学”取而代之才能回避模糊的边界带来的文化属性问题,尤其是本属中国的台港地区作家在海外落籍,更不提东南亚华人后裔作家移居、成名于台港地区后对东南亚故国华文文坛的影响,可见文化属性不再是一种本质,而是一种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的定位。
因此刘俊主张用“汉声文学”替代“华语语系文学”,以更务实、公正的态度承认各区域华文在形义同属一支的前提下只是音(方言)的千差万别而已,因此客观存在且绝无殖民、强迫色彩的“华语音系”比另有所图的“华语语系”更具包容性,它既明确海外华文文学源自于中国本土文学,也坦然承认海外华文文学虽然以华文为载体,但早已是外国文学,并不存在中国中心和中国性问题,由此澄清了“华语语系”因为偏见造成的歧义。“华语音系”承认华文的音的差异性造成华文文学的“分散”型态,也指出了华文的形义的同源性为华文文学带来的“聚合”潜力,因此跨区域跨文化的“跨”既是“分”的、静态的现实,也是“合”的、动态的势能。正是在这种“同异相生”的“分合”状态中显示出自我与他者的互文关系,进而衍生为刘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互文结构”,在华夷一贯混杂的语境中,华与夷、自我与他者随时存在着德里达的“好客论”里的主宾转换可能,以包容和悲悯为底蕴的“互文结构”才能让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打开新局。
二、类比结构与现代追问
无可否认中国的确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源头,而海外华文文学当然属于整体意义上的现代华文(或中文)文学,而且只有将所谓中州正韵之外的海外华文文学囊括在现代华文文学之内,才能真正发掘现代华文文学之所以现代、之所以是华文的最大公约数,也唯有如此才能描绘出现代华文文学的整体面貌。于是乎,刘俊以台港文学在殖民统治时期的“启蒙”为例,指出“台港澳文学的有机介入,可能会对建立在大陆文学基础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构成一种结构性的突破:原先在台港澳文学缺席的情况下很重要的问题,在有了台港澳文学的融入之后,可能不重要了或有所改变了,而原先不重要的问题却可能变得意味深长起来”。④
中国学者当然大多早已抛弃了“大中国心态”,但若真要全面认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必须以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华文文学为对象,告别单个区域的文学个案研究,通过“跨界整合”透视华文文学的集合状态,在承认各区域、文化的华文文学的差异基础上,思考能否超越这些外在条件,探究19世纪末以来的华文文学自传统向现代蜕变的共通元素,形成刘俊所说的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感和相似性:“虽然在题材、主题、人物、语言的词汇结构等方面有所差异,但在更为深层的文学观念、文学精神、美学追求、语言风格等方面,却有着相当明显的同构性和一致性。”⑤
《北美华文文学中的两大作家群比较研究》一文显示刘俊从中国源头(大陆、台湾地区)出发,考察源头在海外(美国、加拿大)的种种变貌,继而通过这些海外差异来回望源头,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类比结构中揭示现代华文文学的多样现代特征。此文将20世纪50至70年代在北美的台湾地区作家群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北美的大陆作家群纳入比较框架,提出两岸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各自特征和显著差异,在梳理20世纪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轨迹、内在理路和基本风貌的基础上,通过探讨造成北美两大华文作家群的特征差异的原因,提出两岸文学源头因为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和方式对各自文学场域的迥异影响,由此丰富了对现代华文文学的现代性认识。
将中国源头与海外支流并举分析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途径,即随时随地都带着“双重视野”——源头/支流、大陆(内地)/台港、中心/边缘、本土/海外——看待这門学科,既抓住普遍性也辨析特殊性,既宏观外在,也微观内在。借用语言学区分差异的研究模式,源自中国本土的华文是跨区域跨文化的华文作家共同使用的、必须遵守通用语法规则的语言,但在不同区域、文化版块里的华文作家使用的华文却会因为环境的变更而产生局部的差异。最明显的当然是现代汉语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的不同发音,尽管同属汉语,但这些语音差异却在各自的区域、文化系统中负载了不可一概而论的特殊意义。这也印证了刘俊用“汉声文学”取代“华语语系文学”的合理性。
呼应刘俊在解读北美华文文学里的“身份追寻”,身份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中越来越是一种“定位”而非“本质”,“双重视野”下的“类比结构” 既化约出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也保留了现象之间的特殊性,更有利于对开放的、游移的、混杂的、多变的现代性的追问。“类比结构”来自于人类学提出的“类比思维”,这种思维不看重现象与现象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不同现象在不同的类比之后会产生多样的类比关系,而不必在意严丝合缝的因果联系。说到底,人文学科毕竟有别于自然科学,“理性”固然重要,但在科学定理、实证公式之外还有更广大的认知范畴,建立在经验积累之上的想象和直觉正是人文学科的独特魅力。审美感受、精神分析、人性探索、历史反思……诸如此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当然无法落入程序化的操作。跨区域跨文化的华文文学为何、如何“复合互渗”“越界交融”固然有一定的规约,但最终仍取决于一位学者年深日久逐步获得的极具个性的眼界、才能和悟性,因此纳入“类比结构”的对象、方式和效果也反映出这位学者的成长过程,从刘俊先后出版的世界华文文学整体研究专著——《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跨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综论》《越界与交融: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复合互渗的世界华文文学》——清晰呈现了他层层开拓、步步深入的研究格局。
三、结语:结构中的斜对称
要突破现有研究格局,形成兼容并蓄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必然要在研究结构中使“跨区域跨文化”的华文文学达成有机的平衡,⑥但全球各版块的华文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方式、结果毕竟千差万别,互文、类比的结构观照虽然以同情的理解兼顾了不同现象的共性与个性,但对不同语境造成的不同现象之间的隔阂、龃龉甚至冲突毕竟不能视而不见,这就需要以“斜对称”的思路、方式来使结构更加公正与合理。
“斜对称”本是一个数学概念,最普遍、明显的体现在扑克牌花牌的图案设计中,至少是两人以上的游戏参与者彼此对坐后,无论从哪一方看桌上的花牌,都能清晰地辨认出图案中的角色,这说明“斜对称”成功化解了从任何角度、立场看问题带来的矛盾、对立甚至冲突。“斜对称”兼顾了“对称”和“不对称”,且在不同的角度、立场的观照下不至于引发歧义,这正适用于跨区域跨文化研究带来的“复合互渗、越界交融”。刘俊秉持“大陆现当代文学和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下的不同指向”的总体理念,所以当把“启蒙”扩展至中国大陆(内地)以外,不同语境下的启蒙者、被启蒙者、启蒙的内容和方式不再有唯一答案,而“斜对称”的研究思路使“启蒙”在互文、类比结构中不会因为单一的角度、立场而产生混淆,刘俊坚信这必将“改变已有的研究格局,改写某些结论”。⑦
注释:
① 刘俊:《越界与交融: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② 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台湾尔雅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③ 刘俊:《世界华文文学:历史·记忆·语系》,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161页。
④⑦ 刘俊:《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⑤ 刘俊:《“跨区域华文文学”论——界定“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新思路》,《复合互渗的世界华文文学》,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255页。
⑥ 肖画、刘俊:《兼容并蓄,守正出奇——刘俊教授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9年第1期,第68—74页。
(责任编辑:斯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