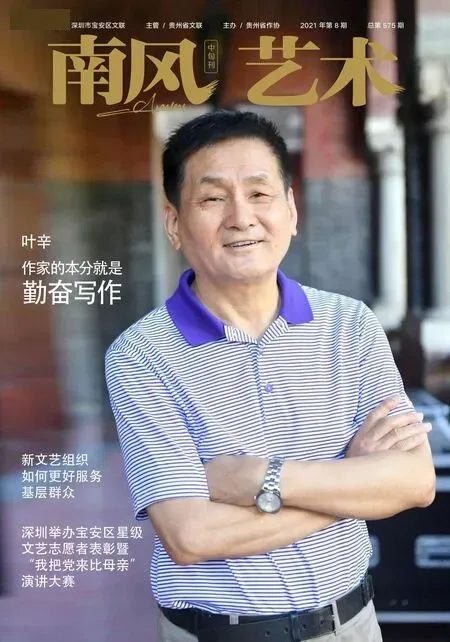傩 戏(外两篇)
2021-09-18徐建英
文/徐建英
良曲盯着家门前的大晒场,一看就是半天。几日后,他站在隔壁院的难生屋门前喊:“难生哥,封在自家巴掌大的地方,人快疯了,要不……咱哥俩把傩戏请起来?”
在院里闷着脑壳抽烟的难生听到喊声,顺着良曲手指的方向,看了看晒场角落那堆闯滩节后拆下的台料,沉思半响,“能成?”
“老祖宗留下的物什,怎就不成?”
“现这情况……”
“家门口请呢。里面套一层口罩,外面盖一层脸子壳壳,安全着。特殊时期,马角不请,五方小鬼用稻草扎,请六叔在台边打钹,我家二小子在屋门口敲鼓儿,咱老哥俩撑一出《镇钟馗》,准成!”
难生看着晒场周边密密匝匝闭着户门的人家,同意了。
傩戏名鬼戏,又称傩愿戏,是祭神、驱瘟避疫的祭祀活动。鄂傩戏,在原傩戏的基础上,另融入了湖北花鼓戏的精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湖村每年的闯滩节,难生和良曲都是堂角。

请钟馗的日子定在农历二月十二,惊蛰日。
老哥俩轮流把门前的大晒场清理干净,搭上简易的傩堂,公鸡黑狗乌鱼黄鳝甲鱼“五血”倒不难,这是鄂南请祭的常用物,两家备的养的一凑,齐了。蜈蚣地鳖蛇壳勾藤藿香金银花川贝茯苓等十二味镇邪、清肺止咳的中药就难着老哥俩了,别的还好说,难生闺女做村医,中药铺现成有。只是那味蜈蚣,两家人卸土墙翻阴沟直忙乎了多日,才找到一只小指头大小的红头蜈蚣,等把这些装入陶罐泡上酒,五帝钱又给卡着了,良曲一咬牙,把自家压房梁的那枚乾隆古钱给掀了下来。
按商定,难生做端公,良曲打先锋,打电话约六叔打钹子时,六叔在电话里泣不成声——他在省城的儿子早上送方舱医院了。
“难生哥,傩戏半台锣鼓半台戏,锣鼓开路,马角唱和,现在我们仅请出鼓和钹,打大钹的却退了,这……”良曲看着难生,一脸的沮丧。
“你老嫂子会些小钹,还有两日,我再提点几下,凑合吧。”
农历二月十二到了。
难生身着红袍,头戴着柳木做的竖眉獠牙傩面,手执方相走上临时搭的傩戏堂,良曲头戴青面,身穿兽皮衣饰,一手执金鞭,一手拖着稻草扎的麻衣小鬼跟在难生身后,难生嫂子和良曲二小子,一人怀小钹坐在台边,一个抱锣鼓坐在自家屋门口。
难生在堂案正中挂好钟馗神像,把轴联贴在钟馗像两侧,又将“秋官驱邪”四个大字粘在神像正上中,然后取过“五血”,在神像面部和手足各洒一圈,念起了钟馗诰:“……祛邪斩鬼大将军,终南铁面我神君,扫荡妖氛天尊至……”
念毕诰,难生用银针在神像的眼,口,鼻,喉咙,肺几处点刺,刺完,用蘸过十二药的方相点戳,口中念词:“天有金光,地有银光,日之黄光,月之射光。金光速现,速现金光,恒巫来开光。”
接着用两只海碗盛水,横一根筷子在两碗间,随后发令:“观我恒巫号,听我师郎令,日查三十六,夜查七十二,妖魔野鬼,魑魅魍魉,病邪远离……”难生手执方相在傩戏堂上边舞边唱。
唱毕,难生持方相斩断碗上的筷子,端起水,沿着戏台旋转,边转,边浇水入地,同时念:“……天地日月斗南开,全生丽水福庆来,瘟疫病灾今日散,福佑善神入庭来,今我恒巫听神令,水碗一扣瘟疫脱。起!”将另一碗水泼向麻衣小鬼身上。
水落地,六叔屋门前传来“咚”的一声悠长大钹声。难生一怔。是六叔,他红肿着双眼站在自家屋前,手里的大钹随即“咚咚锵”“咚咚锵”合上了难生嫂子和良曲二小子的两番鼓钹。
难生心一悸,手里的方相转得更快了。
远处,有板鼓声聚上了;东面叫锣发出清脆的声音;西边的中钹和次钹也合了过来;南角的尺板和木鱼声丝丝入堂;堂北的号头也亮了……一时间,十番锣鼓从湖村的四面八方响起,和着傩堂的步奏。
接着高腔、平腔、花鼓腔、山歌腔,阵阵楚腔传来。银脸的四大天将,花脸的关索,黑脸的城隍,粉脸的和合二仙与小娘子接腔而出……闯滩节上的十二舞神戴着脸子壳壳一人两米的距离立在大晒场四周。
难生眼一红,感觉周身的血脉偾张,手里舞动的方相越转越快,嘴里的唱念加急了几分。旁边的良曲手执金鞭舞动起来,边舞边指傩堂边的那一排麻衣小鬼:“吾是先锋太白将,钟公派我打先锋,一打东方木精鬼……”
“二打南方火灾殃!”
“三打西方金精怪!!”
四周阵阵和音响起。
一帧帧脸子壳壳从晒台边的各处户门窗口探出来,齐声唱念:“四打北方水灾殃,五打中央土精鬼,土精邪鬼土内藏,五路瘟疫都打尽……都打尽!无病无灾出屋门。"
齐齐整整的楚腔,在一片“咚咚锵”的锣鼓钹声中,在傩堂外的大晒场边合着鼓点,在麻衣小鬼倒地的声响中,踩着三角形的舞步在跳,和着难生和良曲嘹亮的声音,冲向傩堂,冲上了云宵……
皮影
“看牛皮(皮影),熬眼皮,摸黑回家撞鼓皮,老婆挨眉捏闷脾……”
沔阳皮影戏在江汉平原一带久负盛誉,让陈皮没想到的是,背井离乡时隔三十年,他还能亲眼目睹皮影子成戏的全过程。
父亲老陈头今年七十,陈皮一早与父亲约好,春节回湖村过,只是没想到刚落家,一场突来的疫情,路封了。如果能一早预知这些,或许陈皮会选择留在花都,厂子里一摊子事,从封城的第一天起,他的手机铃声就不停在响。
父亲老陈头倒是安心,铺天盖地的封城信息传来,他却蹲进东厢房的角落里捣鼓那几只大木箱。老陈头老了,老了的老陈头习惯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搬出他的木箱子,翻开一张张叠卷的皮影子,边晾晒,边抚摸,如同抚摸那些折叠在皮影里的旧光阴,偶尔还有老陈头的叹息,“哎,不中,都不中啦!”
封城的第二天,老陈头在封村前出了村,黄昏返家的时候,他的嘴边扣了一个天蓝色的口罩,在陈皮惊讶的目光中,把半张新鲜的黑牛皮浸泡在水盆中。几天后,陈皮帮老陈头起过盆,将浸泡过的牛皮晾上木架,他的电话又响了,陈皮边接电话,边看老陈头一点一点地割牛皮,去碎皮边角,用刮刀剔牛皮里的肉渣,等老陈头翻过牛皮刮外面的牛毛时,陈皮已经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
老陈头一整天一整天的刮牛皮,陈皮一整天一整天地接电话,或对着笔记本电脑里的视频指指点点。老陈头那张饭桌大小的牛皮经过他不停的刮皮、浸泡,逐渐变得光滑透亮,被老陈头展开钉在木板挂在背阴处。陈皮电话里的大吼大叫声,也慢慢变成笑逐颜开。
每隔几日,老陈头便会取下木板上的牛皮,用圆木棒在皮子上来回推磨,整张皮子变得越来越平整越来越光滑了,老陈头又把皮子一分为二,分别在两张皮子上描影。描完影,从东厢角取来十几把大大小小的刻刀,逐一过了水,上水石打磨。

江汉平原一带的皮影匠,对刀路、刀型都颇有讲究,不同的刀路要用不同的刀型,老陈头先用钢针顺着描过影的线条扎,接着将牛皮绑进一块硬木板上,凿头形凿帽形,雕侧影,打眼眉儿,挑鼻尖子,每下去一个凿刀,都会比对一番。
天晴的时日,陈皮晃着腿,叼着香烟,靠在紫縢椅上晒春阳,其间不时会拿起手机,吩咐厂里的主管几句,脸上挂满春风。下雨的时候,遇着陈皮不忙,他会上来帮帮老陈头,对着老陈头手里的活指点:“这鼻尖儿,蛮好了。还有这,也行了。玩耍儿的小皮影,不用这般过细的,蛮讲究做吗?”
通常这时候,老陈头眯着眼睛看陈皮,“说嘛呢?做啥都得有讲究。这鼻梁太挺,就少了一点乖巧伶俐劲,懂不?这额头,还不够圆润,也显得妩媚有余而柔美不足。”
陈皮笑,“哈,您老还懂审美呢。”
“皮影子仿的都是戏剧人物,刻皮影讲的就是繁而不乱,密而不杂,哪处该涂染,哪处要镂空,眉弯弯,眼线线,樱桃小口一点点,笔笔都含糊不得,若布的局不合理,人物就难逼真,不逼真,戏就砸吧了,你小子不懂!”
讲完这些,老陈头不再理会陈皮,将红黑绿等几色颜料分别熔进碎皮子熬好的皮胶中,在小火里一边温,一边往皮影的两面上色,待色变干,又一层层的刷桐油,待这些做完,一男一女两副惟妙惟肖的皮影子也告成了。
老陈头选了一个晴日,在家门口置了一张方桌,方桌上架上一块白纱布,白纱布的底水边是老陈头自己手描的水草幕,他将一男一女两副皮影子紧贴在水草幕上,先提起那副男影,轻咳了两声后,男影的手缓缓抬起,男腔随之而出——
“近来好鱼价,清早把湖下,哪知天气陡变化,雷电又交加,倾盆大雨隆……”是《大汉皇帝陈友谅》。年轻时的老陈头,曾领着年幼的陈皮,带着这出皮影戏,一口楚腔走遍江汉平原。
屏幕后,老陈头的手转向了那副女影,丝丝入扣的女音同时传了出来:“狂风掀巨浪,啊呀呀,沷进了仓……”
陈皮突地有了去帮帮父亲提线的想法。
“只顾把鱼捕,难道我,陈普才夫妻就要命丧于此吗?”屏幕后的声音又换成了男音。在陈皮走向幕后的瞬间,他怔了。他看到父亲老陈头手里提着男影,鼻梁上架着一副白色的口罩,那是他的工厂生产的口罩,是他在封城前匆匆塞在包里带回的样品,最近工厂火热在生产。
“这……前面有一个土滩,待我抱妻上岸想办法哟!”看到陈皮,老陈头口罩里的声音停了停,仅仅片刻,他的声音又响起:“荒野产子遭险,无数水鸟筑屏棚,不见风雨电轰,雨过天晴现彩虹……”声音随着老陈头手中提线的变动,时高时低,时男时女,女低音似溪流入谷,苍老的男中音厚实略带苍凉。
看着偻腰专注的父亲,陈皮怔在那儿半天没动。
等他豁然回醒,一把摘下了老陈头戴在嘴边的口罩,在老陈头错愕的目光中,陈皮半跑着冲进了内屋,拔掉了正在充电的手机,哆嗦着手拔通了工厂主管的电话。
招魂
楚人好巫,自古就有招魂习俗。听村里老一辈人说,战国时的三闾大夫屈原有一年坐船过潘河,却在船上病了,一连多日重病不起,村里有位九十岁的老人试着去潘河为其招魂,第二天屈原的病全好了。后来屈原写的《楚辞》中就有一章《招魂》,村里老辈人说,那就是根据湖村招魂的习俗而来。
群发在外做了多年生意,回到湖村后就病了。
开始他只是说胸闷乏力,汪娴陪着上省城医院,求了专家,折腾了仪器,查来查去,也查不出所以然。
汪娴急得不行,听得哪儿有治胸闷乏力的偏方,哪儿有郎中专治疑难杂症,立即脚不点地奔过去,可群发的病全无好转。
汪娴没招了,群发有气无力地出主意:要不……你……找爹,给我招魂。
在汪娴小时候,娘为她喊过魂。
但小孩喊魂和大人招魂却各不相同。大人招魂,相对繁琐些。
有一年三叔在南拢凹干活回家病了,爷爷挨家挨户去讨米,然后把家中的水缸填满水,放了一把作镇邪之用的剪刀在缸里,奶奶抱了三叔的内衣,手持圆镜拿着百家米由瓦梯走上屋顶,仰面朝天门持镜朝东喊:东方有鬼崽啊莫留哟——
喊完将手讨得的百家米朝东洒一把。
然后顺次各喊一句,将讨得的百家米朝各方洒一把。
四个方位喊完,再仰头面朝天门,圆镜朝三叔失了魂的南拢凹喊:东南西北都莫去,崽在南拢凹吓了回哟——
喊一句,丢下一把米,再由瓦梯走下屋顶。据说这些扔下的百家米,会落地成兵,从镜子里照出的镜路上,把人的魂收回家。
汪娴听完眼一亮。但招魂还有一说,得家中长辈出面喊才有效,比如父母,再或岳父岳母。群发年幼失父,青年丧母,自已的爹娘倒是健在,但是……汪娴一想到爹,眼神随即黯淡下来。
当年汪娴和群发谈恋爱,汪娴的爹娘大力反对,特别是爹,嫌群发家弟妹多负担重,嫌群发个头矮怕汪娴嫁了会吃苦……汪娴不管不顾,娘以绝交恐吓,汪娴还是不理,偷偷拿着户口簿与群发领了结婚证,请了几位要好的朋友摆桌酒席就正式住进了群发家。孩子出生后,群发去给汪娴爹娘报喜,硬生生吃了个闭门羹。从此汪娴倔着不回娘家了,任群发怎么劝也不听。
看着床上气息如丝的群发,汪娴咬咬牙还是出了门。
站在阔别多年的娘家门口,远远见娘在院子里忙碌,爹在树下抽旱烟,汪娴站在门口,红着眼睛看着娘叫了声:娘!看着爹,怯怯地喊了一声:爹!娘看到汪娴一怔,眼睛发红,脚向女儿挪。你站着!她说绝交就绝交?她愿来往就来往?爹一喝,娘的脚就停了,哭着转身向内跑。
爹磕磕烟灰,闷声问:这是哪家闺女?走错门了吧?汪娴把手中拎的贵重礼品放在门边,怯怯地说:爹,这是群发让我拎来孝敬您的。
群发是哪个?你又是哪个?老汉我不认识!又一脚抛开地上的礼品:发财了,了不起啦?这些你拿走!老汉我不稀罕。转身进了屋。
爹,群发重病,您晓得的,他爹娘早不在了……爹一怔,又砰地一声关了门。汪娴哭着一路跑回家。群发看着汪娴红红的眼睛,喘着气说:娴子……再去,咱们结婚时没尊重两老意见,爹还气着……
汪娴说:你又不是不知咱那爹,这些年,你哪次去,不是被他撵了回来?
群发说:娴子,再跑一趟吧,爹只是……那口气没放下……
傍晚时汪娴萎着头回来,她哭着说:门一天都锁着,照面不给打。要不,还是我去化百家米,请族里的长辈来试试?
万万不行……
群发话刚落,一个佝偻的背影进了厨房,接着一个苍老的男音在屋顶响起来:群发,我的儿啊,东方妖魔多作怪,崽啊你早回莫作留哟——
群发,我的儿啊,浙江人多车多你莫留啊,娴子和伢崽在屋里等你回哟——
汪娴听着这熟悉的喊声大滴的眼泪从眼眶滚出来,连日来窝在床上的群发掀开被,挣扎着想下床,这时一个人影进了屋,一把按住他,说:儿啊,保重身体最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