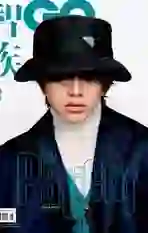大象远行
2021-09-16
生死自负
云低,犬吠,风热。远处的苞谷刚开始抽穗,和橡胶叶一起低语。
采访进行不下去了。
6月18日下午,坐在我旁边的是西双版纳勐腊县管护局副局长陈萌,他51岁,皮肤黝黑。我们本来要一起去勐腊乡下见大象地面监测员,可在一条宽不足10米、名叫“九分场”的乡间小道上,被拦了下来——前方草丛里,有11头象。于是,我们就近坐在石头上聊起了天。
下午5点左右,陈萌的电话响了。不到1分钟,他挂掉电话,面露难色,转达上意:“要你们单位马上提供一个(带公章的)人身安全保证书。”内容是,出现生死安全问题,与当地政府无关。
我能理解他的难处,很多年前,当地曾有记者遭大象攻击而死。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亚洲象研究专家张立统计,2019年,大象在分布区造成14人死亡。可我一时拿不到公章,场面有点尴尬。
一头大象打破了尴尬,它从草丛中冲了出来。像所有人一样,陈萌和我立即撒腿就跑。
那一刻,众生平等,不管你是局长、记者、村民,是男是女,面对大象,第一反应都是“跑”。
一只不明所以的黄狗汪汪直叫。陈萌怕把大象吸引过来:“嘘,哪家的狗,别让它叫。”待场面稍微缓和,我们轻踮脚步,悄悄绕进旁边一座居民平房,爬上蓄水池,近观距离不到30米的大象。树叶荫蔽之下,大象的皮肤呈灰棕色,背部宽广。另一头象,用头撞击着平房的钢铁门,“砰!砰!”。
这于我而言的惊险半小时,已然成为了西双版纳乡民与大象相处的日常。据西双版纳州国家级保护区管护局统计,当地约300多头亚洲象,已有约三分之二都走出了保护区,散落在人们生活的乡镇。西双版纳景洪市管护局副局长查伟忿忿又无奈,他管辖下的景洪市景讷乡并非在保护区内,但大象常来“做客”,“给面子的话,40多头,不给面子,80多头。”
据西双版纳州国家级保护区管护局统计,当地约300多头亚洲象,已有约三分之二都走出了保护区,散落在人们生活的乡镇。
6月25日,象群格外“不给面子”地来访了。在景讷乡659.6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80多头大象徘徊。
当天零点22分,景讷乡弯山角村,月色皎洁。国有林小道静谧幽深,我正跟随无人机大象监测员蔡明飞夫妇开车前往下一个村庄监象。又是一个电话。对方寥寥几句,蔡明飞一脚刹车,降下车速。原来,就在刚刚,村里的智能广播响起,提醒大象正在靠近村庄。蔡明飞在村里的朋友听到预警,估算他正往这条路上开,提醒他别和大象撞上了。
我们恰恰和象不期而遇。两头小公象刚穿过马路进入草丛,在蔡明飞妻子手电筒的照耀下,小象白得像玉,悠哉自若。我们小心地缓慢驶过,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轻柔许多。
这套预警系统从2019年11月开始建设,迄今,已有579台红外相机、181套智能广播分布在西双版纳12个乡镇、38个村委会、115个村小组。约四米高的红外相机拍到大象照片,传输到云平台服务中心,经过物种识别确定为亚洲象后,形成预警信息发布,整个过程仅需12秒。
系统虽智能,但也只能起到提醒作用,无法限制大象的行踪。“我们现在累计的预警数量是5362次,影像数据是114万张。”西双版纳州管护局科研所工程师谭栩吉6月11日说道。这意味着,不到两年,人类生活的边界已被大象踏入5362次。
大象进村已属寻常,但这个夏天,15头大象“放飞自我”,离家远行。这次,他们不再安心于只在保护区附近徘徊,而是离开西双版纳,一路北上。浩浩荡荡500公里,途经普洱、玉溪、红河州,靠近昆明。直到7月,尚未归来。
因為其中一头象的鼻子偏短,这群象被人们亲昵地称为“断鼻家族”。他们的行踪牵动人心。为了拍到大象,一家媒体的记者在山林里住了三天两夜,一出山直奔澡堂。直播博主们也闻风而动,见不到象,他们甚至沿路直播大象留下的粪便。
7月7日,脱离北移象群独自活动32天的独象被麻醉送回西双版纳,回归山林。而其他的大象还在红河州继续游荡。
“你有你的家,我有我的家?”
若端视一头亚洲象,便可知造物主对其是何其宠幸。一头成年亚洲象身高2.5米,长6米左右,四肢粗壮,体重4 ~ 5吨,皮肤厚达3厘米,像干涸的树皮,不易被利刺扎伤,就连睾丸都被精巧地隐于腹腔内,可防止意外伤害或猛兽进攻。他们跑得够快,每小时达24千米,游得还久,可连续游泳5 ~ 6小时。除此之外,寿命足够长,一般能活60 ~ 70岁,最长能活到120 ~ 130岁。
曾经,他们在陆地上几乎没有天敌,老虎也不敢轻易挑衅。更难能可贵的是,大象是生物链中最“善良”的那一类强者。他们在行进中推倒枯败的树枝,让低矮的植物也能重见阳光。走过之处,在地面上形成象道,为小动物们“开疆辟土”。他们每周产生1吨的粪便,很多未经消化的种子藏身其中,随着大象迁移播撒到森林角落,而粪便本身也成为昆虫们的家。
然而,当大自然中传统的强者遇到人类,注定要节节败退。
4000年前,大象曾出现在北京附近,3000年前,分布在黄河以北。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发掘出亚洲象化石,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关于象的记载。那是人类早期和象相处留下的印迹。
可随着人口增加,“农民和大象对栖息地直接争夺”,历史学家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一书中写道:“农民为保护庄稼,免遭大象踩踏侵吞,与大象搏斗。”
在和人类的冲突中,大象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中原大地消失。自周朝初年,由黄河流域南迁;到了唐代,退至长江以南;宋代,越过南岭。18世纪后,除了云南西南部,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找不到亚洲象的踪迹了。
尽管如此,几十年前,亚洲象在云南尚有喘息之隙。西双版纳在20世纪50年代才有20万人口,地广人稀,“人和象并不冲突。”生态人类学家尹绍亭说。
1971年,上海动物园想引进一头象,在有关部门批准下,进入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捕象。纪录片《捕象记》中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记录了这次抓捕行动。解说的声音高亢兴奋:“用麻醉枪捕象终于成功了!”捕象途中,其他珍贵物种也难逃厄运。凿开大犀鸟孵蛋的洞,“这是捕捉它们的最好机会……它终究斗不过好猎手!”
“跟发展阶段和人的意识水平有关系,以前一般把野生动物只看作可利用资源。”绿色和平森林与海洋项目经理潘文婧说。
最后,以5头成年野象的生命为代价,一头幼象被捕获。它被运回上海,取名“版纳”,成为动物园里的“明星”。2017年11月24日14时30分,离开故土46年后,53岁的版纳倒地昏迷,再也没有醒来。
这次捕猎行动成为一次转折性事件。亚洲象专家陈明勇、吴兆录等人撰写的《中国亚洲象研究》中写道:“原本,少数民族在精神和力量上都不敢捕杀亚洲象,可这次开了杀戒后,为不法分子带了坏头,猎杀野象事件逐渐多了起来。捕象队走后几年,仅勐养一带就有10余头野象被非法猎杀而死。”
从飞机上俯瞰版纳,山峦层叠,满眼葱绿。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张锡炎说:“其实触目可见很多都是橡胶林。”
据20世纪70年代调查,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内当时只剩下101头野象。若照此下去,亚洲象很快就会和渡渡鸟、旅鸽一样,从大自然中灭绝谢幕,只留下几具标本和一个名字。
人类也意识到,不能这样下去了,大象也要拥有一个安全的家园。1958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成立,最初的总面积只有5.72公顷,后来陆续扩大到24.25万公顷。西双版纳原林草局局长、65岁的曹孟良还记得:1979年,西双版纳州林业局专门成立自然保护科,当时他23岁。“春节过了我被分到这个科室,3月我们就参加了扩大自然保护区(工作)。”
他们找来全州的地图,“重点看哪个地方是野生动物比较集中、森林植被比较好的,就划出来。”曹孟良说,扩大保护区并不仅是为了保护大象,而是保护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如勐仑保护区更强调石灰山的植被特殊性,“上为森林、下为石林”,而曼稿则是“勐海唯一剩下的一片面积较大、遭人为破坏不甚严重的原始森林”。
他们拎着红色油漆桶进入山林,以明显的道路、山脊、河流为界,划出新的保护区边界,最后划出了24.25万公顷。“按当时来讲,我们认为是能足够保护好西双版纳的生物多样性了。”曹孟良说。
他还富有感情地念了一首自己写给大象的诗——
《我想对你说》(节选)
你有你的家,我有我的家,
你会来我家,我不能去你家。
诗中大象的家,指的就是自然保护区。然而,保护区成立60多年后,“你有你的家,我有我的家”则愈发显示出是一种一厢情愿。大象并不知道人类已经给他们的生活划定边界,他们频繁地走出保护区,踏足周边人类居住区。“具体它是怎么想的,无法跟它沟通,我们也不知道。”西双版纳國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说。
“怎么听不到鸟叫?”
走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告庄街头,总有穿着白衬衫的房产中介热情招呼:“看房吗? 25万一套。”印着芭蕉叶的蓝绿色传单上,字里行间描述着对美好生活的想象,“雨林度假”“神奇乐土”“旅居天堂”。一只灰色的大象也出现在传单上,成为必不可少的卖点。
刚到西双版纳的我,也曾为此心动,面朝雨林,四季如夏。可一位当地人泼了一盆冷水,甩出一句:“主城周围,哪有什么雨林?全是橡胶林。”
从飞机上俯瞰版纳,山峦层叠,满眼葱绿。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张锡炎说:“其实触目可见很多都是橡胶林。”若在12月份前后到三月底四月初,橡胶林叶落枯黄,山上大片斑秃,和恒久常绿的雨林,形成鲜明对比。
47岁的张锡炎总是穿件印着小象的白T恤。他带着远道而来的朋友爬上村庄房顶,分享分辨雨林和橡胶林的方法。“一层一层有规则摞上去的是橡胶林,”他用手划过眼前的一大片,然后指着远处那一小撮,“一簇杂乱的是雨林。”
据绿色和平提供的数据,2000年到2018年,西双版纳全州亚洲象适宜栖息地(乔木林和灌木林)面积减少了40.68%,变成了农田、茶地和橡胶林。据《消费日报》报道,2021年西双版纳橡胶林面积已达447万亩。然而,橡胶林被称为“绿色荒漠”“抽水机”,很少能长出大象爱吃的食物,也不适宜大象栖息。张锡炎曾经带一个朋友进入橡胶林,对方问,“怎么听不到鸟叫啊?”
在这次大象出走事件中,橡胶林成了外界批评的焦点之一。6月16日,我把橡胶林的问题抛给州林草局局长朱洪进,他回答:“我们一定要历史地、客观地、科学地、发展地看待这些问题。”
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农垦局编写的《中国天然橡胶五十年》载,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会议指出:“橡胶为主要战略资源,美帝国主义对我进行经济封锁,为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自给。”同年,开始对开辟云南植胶区进行筹划。后来,当地陆续开辟农场,接收湖南支边青年和省内移民种橡胶。“为了发展橡胶事业,我们西双版纳也是做出了贡献的。”朱洪进说。
改革开放后,政府继续鼓励发展民营种植橡胶,帮助当地脱贫。
基诺山坐落于西双版纳的版图中央,43岁的阿明家就在山里的巴飘寨。他们经历过贫穷的时光,“一年吃一顿肉,一块八一包的春城烟都买不起”。
2005年,市场经济进入山林,胶价上涨,每公斤达30多元。阿明记得,那一年,整个村58户没有一户不种橡胶,村干部带头放火烧山,开辟的!2000多亩橡胶林,原本全是大森林。按照生长规律,橡胶本该种在海拔800米以下,可盲目扩张下,800米以上的地方也能看到大量种植的橡胶林,有的地方甚至种到了山顶。
这样的情况不止在基诺山,也发生在西双版纳各个角落。潘文婧当时在保护区旁的村寨走访,调查大象和人相处的情况,那里原本都是森林,等她两个月后重访,山已经变得光秃秃的,“大象也不去了”。
橡胶改变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带给人观念的冲击。早种上胶的山民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批,当地人李红军记得,当时每到晚上,那些家里富起来的小孩儿,衣服口袋塞着一沓一沓的红色钞票,开着摩托车飙车,从山上一冲而下。
巴飘老寨本有两棵大榕树,被供奉为神树。财富让神灵退却,“山有主、树有魂”的朴素信仰不再,年轻一代把其中一棵砍掉卖了,腾出地方种橡胶。不久以后,村里就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山体滑坡,千百年来从未出现过。
橡胶的价格并不稳定。到了2011年左右,胶价回落,在2018年左右,胶价一度只有每公斤六七元,去年稍涨了点,但也只到每公斤9元。阿明家去年一年割胶只能收入3万元。
要赚到这点钱也并不容易。6月15日,我住进阿明家,第二日跟着他去割橡胶。阿明和妻子先则总是9点多睡,次日凌晨2点起。我们换上胶鞋,坐上皮卡,在阴凉的山风中出了巴飘寨,摇晃地往林子里前行。
一路寂静,我们到达山的东面,前面就是橡胶地了。虽然点着蚊香,可蚊子还是成群地往我的脸上糊,先则却像没感觉到,只是专心地割胶。
在树干距离地面15米高处挂一个瓷碗,先则熟练地先抽出一条干胶,用刀顺着划痕的方向往上割一圈,白色的胶水迅速凝结,滴落在瓷碗里。她动作熟练,割一棵只要10秒,一排割完,我们扒开杂草丛,往下走割下一排,橡胶林里黑暗寂静,只听见猫头鹰的声音。
大约割了两小时,下起了雨,先则有点懊恼,“阿明估计要怪我了。”出发前他们有过争吵,阿明听到了变色龙的声音,觉得会下雨不愿上山,但先则觉得不会,“多割一天,就多一天的钱。”
山路泥泞,我们全身湿透才爬到车里,都冻得够呛。阿明发动车子,可车轮空转,烂泥横飞,只能等天亮雨停了再走。今年的雨季来得早,从5月到8月,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一场大雨,就意味着我们今晚割的所有橡胶,都会被雨水冲走,分文无收,本来熬夜一晚,“可以赚200的”。
车里,阿明点了一根烟,小火苗在黑暗中闪烁,他和先则都很沉默。雨水敲打着车窗。我问先则:“种橡胶这么累,熬了一夜,一分钱都没有,会觉得委屈吗?”
“不委屈,我们一直是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的。”她说。
任由外界热火朝天地讨论,当地人顾不上理会,为生活而忙碌着。我了解到,版纳温泉村发生过一起因割胶而被大象伤害的命案。这是一个悲伤往复的故事,大象因橡胶失去栖息地,而胶民因大象而死。
第二天,温泉村小组长杨则汉特意打来电话:“记者,你能不能到中央反映,因为大象我们大半年割不了胶,完全没有收入。”
两难
“不要一味指责西双版纳的人怎么怎么样,西双版纳的老百姓也想环境好,但他也要发展,不种这个他吃什么,他啃叶子去啊?”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秘书长张锡炎说。
事实上,当地政府和民间力量也已经意识到橡胶的问题,尝试推动退胶还林。2010年,在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主导下,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成立。基金会从2017年开始筹划“雨林修复”项目,引导村民退出自家不适宜种植橡胶、茶叶等单一经济作物的高海拔地块。
阿明就是加入“退胶还林”的其中一戶,他把老寨那些不出胶的橡胶林都砍了,和基金会签订了10年植树管理合同,免费领取经济性树苗。他来负责养护已种植的树苗,每年除草10次,每年每棵树苗会收到基金会10元的管理费。
截至2020年底,基金会已推进了三年的雨林修复项目,共种植了2万余棵树,修复面积约323亩,存活18424棵,三年累计发放管理费305160元。
往年,基金会发放的树苗由西双版纳林草局免费提供。一棵苗根据品种和大小不同,少则十几二十元,多则几十上百元,单是树苗就耗资将近百万元。可是今年,“由于云南省为期#年的经济林木推广项目结束,进入验收阶段,西双版纳林草局没有了这笔预算,今年暂时没有免费树苗给我们,”张锡炎在“小象计划”公众号中写道,“基金会必须得自己想办法解决。”
事实上,当地政府和民间力量也已经意识到橡胶的问题,尝试推动退胶还林。2010年,在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主导下,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成立。基金会从2017年开始筹划“雨林修复”项目。
在一场“各怀心事”的饭局上,州林草局局长朱洪进和张锡炎曾经深聊。朱洪进想推进热带雨林修复示范工作,缺钱,听说对方是个基金会,“我以为从他们那里可以挖点钱。”可聊了不一会儿,张锡炎说资金不够,朱洪进才发现,原来对方也想找他要钱,“我一听说都是没钱的,”算了算了,朱洪进心凉了一半,“要靠政府拿钱、拿资金,说个老实话,我们地方政府太穷了。”
6月18日下午,我和陈萌坐下休息时,不远处的11头大象上空,飞着一架无人机。为了监测大象,这样的热成像无人机勐腊县配了)台,一个乡镇&台,选的是便宜的,一台也要$万多元。“这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配上的,”陈萌说,“根本就不够用。一块电池最多就飞20分钟,每一台都配了四块电池了。山上没地方充电怎么办?”他也想配上&"块,“一块电池一千多块钱,我们没钱啊。”
大象监测员人手也紧缺,整个勐腊县只有14名野象监测员,大象出现时,监测员要24小时工作不间歇。有三个乡镇没有监测员,象来的时候只能从别的村紧急借调。当地没钱请更多的监测员,因为发不出工资,“财政没钱啊。”陈萌说。
景洪市管护局副局长查伟不明白,外出北上这15头象为何要600人监测,他说:“我们这儿,两个人,看9群。”
当地不是没想过发展其他产业创收,但同样面临两难的困境。陈萌说:“我们勐腊县土地面积(约)1029万亩,但是森林就占到800多万亩。”他犯难,“我要招商引资搞一个开发区、工业园区是不是要土地?随便什么地一看都是国有林、都是保护区,不能动,”他说,“勐腊县的支柱产业就是橡胶。”
35岁的金辉是景讷乡松山岭寨的监象员,在大象不出现时,他还有另一份工作——保险勘探员。大象踏入农田,吃庄稼,当地政府和保险公司会合作赔偿。6月24日一早,金辉去勘探了前一晚被大象踩踏的秧苗。5月育秧,水稻秧苗刚长到20公分,被毁意味着这户农家错过了这一季的收成,按照市场价,&#亩地的收成价值5万元左右,但最终这家人只能获赔600元。金辉也很无奈,去年10月,自己家的苞谷地也被踩,一亩地赔400元,可市场价格能卖1000元。
“实际上这样叫补偿,而不叫赔偿。”陈萌也觉得不公。
当地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委屈。“大象到一个地方横冲直撞,吃庄稼,当然现在外界人感觉这点儿破坏不算什么,可经常这样怎么受得了?”尹绍亭为当地人感到委屈,不能因为大象“萌得可爱,憨态可掬”,就对当地老百姓“他们的生存、愿望和发展毫不关心”。
“西双版纳就有老百姓说,保护大象你拿去保护去,为什么你大城市不拿走,你放在我这儿,我这庄稼损失你赔我吗?外界大家都看象,象多可爱啊,它进你家去试试?”张锡炎说道。!
在勐腊,6月15日,我临时参加了一个上级部门组织的、几十人的媒体团,当地林草局在农家乐招待了一顿饭。有鸡、有鱼,还有当地特色的粥饭。
2020年,勐腊县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77元,平均每月1064.75#元。我们这顿饭由勐腊县林草局买单,六桌共计1500元左右,相当于当地人一个多月的平均工资,我有些愧疚。
丛林的智慧
20世纪80年代以前,保护区内有100多个自然村,2000多户山民,日常生产主要是刀耕火种。人们在森林里将树木焚烧后形成肥料投入土地,种植农作物获取食粮,时而轮歇迁移。!
后来,“刀耕火种”被外界认为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是“落后、愚昧”的象征,逐渐被淘汰,原住民也被要求陆续迁出保护区。
几十年过去了,大家慢慢发现,传统的刀耕火种后,能够促进林下草本和幼树的生长,这恰恰是大象喜欢的食物。资料显示:大象每日要进食150千克,它喜欢吃植物的嫩枝、树叶和茎秆等。
原住民迁出后,保护区森林覆盖率一路狂飙,从20世纪80年代的88%,到了如今的93%。“森林郁闭度大了,林下草本禾本科长势不旺,间接导致大象食物减少。”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所工程师王巧燕说。森林覆盖率过高,食物减少,正是外界猜测大象不断离开保护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来者总是不自觉地以俯视的姿态来打量雨林,用所谓的“先进”标准去衡量和评判,最终被实践证明:不尊重丛林的智慧,终要付出代价。“我们都需要不断地学习、适应,不断地纠正我们过去的错误,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尹绍亭说。
2013年,张锡炎问一位基诺山的小伙子:“你觉得你们最值钱的是什么?”对方答:“橡胶、茶叶,如果还能砍的话,森林里的大树砍下来卖钱。”
小伙子的父亲是基诺族文化传承人。原来山地民族的文化是在雨林中孕育的,和自然息息相关,你问山民什么时候出生,他会告诉你“山里白花盛开的时候”;打铁节、新米节都是雨林里最真实的呼吸。可小伙子却是在橡胶林中长大,所有的时间被橡胶规训,那些浪漫而富有诗意的节日,变成了何时“出胶”“割胶”。
“我們经常把丛林法则等同于弱肉强食,”张锡炎说,“可真正的丛林法则,是相互依存而共生。”
基诺族口口相传的古老歌曲、舞蹈在慢慢消失。尹绍亭非常痛心,“橡胶是外来的,我们的传统文化跟它不相容,是割裂的,”他说,“假如几十年以后,我们不再种植橡胶,森林恢复再生,而我们的山地文化怎么恢复?怎么再生?难了。”
6月的西双版纳是一座旅游城市,大金塔下,穿着傣族盛装的姑娘们笑意盎然。熙熙攘攘的夜市,不时冒出一句东北话。当地有走入雨林的活动,这本是体验雨林的最好机会,可不少从一线城市来的游客“却从来没有走进过当地人的生活”。他们甚至要求,能否让山民背着桌子进山,“雨林里铺上白桌布,戴上白手套,然后在那里以雨林为背景,进行一场野生的享受。”一位对接客户的旅游从业者说。
6月26日,我跟着基诺族的猎人进入基诺山。林荫层叠,泥土松软,我们溯溪而上。雨林重新定义了“强大”和“弱小”。几个人手拉手怀抱不住的大树,经过雷击雨蚀和藤蔓缠绕,会枯残倒下,依然倔强昂着头的,是从树缝中钻出来的菌菇和看似弱不禁风的小草
行走久了口渴,猎人随机砍下野芭蕉,剥开芭蕉芯,溢出满腔清甜,这也是大象最爱吃的食物之一。此刻,我们和大象都平等地受到雨林的滋养。“我们经常把丛林法则等同于弱肉强食,”张锡炎说,“可真正的丛林法则,是相互依存而共生。”
我们从大城市来,看似离文明很近,却离自然很远。下雨了,我感到寸步难行,但猎人却能独自一人在雨林里待上十几天。以前他们进山打猎,打到野猪,一定会和其他猎人分食,然后彼此帮衬着走出山林。
“我们本就是林子里出来的去了毛的猴子,你所有的自大、傲慢、无知,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强加的。”张锡炎说。可山民们却对自然有着最朴素的生态观,山有灵,樹有魂,要敬畏和互助。
有一次,张锡炎在河边喝酒,听到一个在西双版纳居住了20年的外地人感叹西双版纳现在环境越来越差。张锡炎反问“你来这儿20多年,你为这个城市做过什么事情?你为这个城市变得更好,或者不让它变得更差,做了什么?”面对外界对西双版纳的指责,张锡炎也想问,“你为大象和雨林做过什么?”
北上昆明的大象还在远方。朱洪进想好了,若是归来,要给大象“表彰,记一等功”,因为是大象让大家关注到西双版纳,“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我们的同志回家。”
尹绍亭反而觉得,大象的去向“顺其自然”,这件事带给人类启示:“回去还是不回去,都有它的意义。”
6月18日那天,我最终还是没能见到勐腊县的监象员。半小时后,追我和陈萌的象群向深山行去,危机终于解除。从早上堵到黄昏的九分场路重新畅通,村民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附近勐满岔河小学的学生放学了,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三三两两地回家。
我们生而为人,与大象相处,恒常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