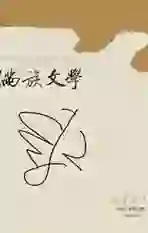何谓“先锋”,“先锋”何为?
2021-09-15李德南
李德南
2015年,《南方文坛》杂志推出了“先锋文学三十年”专辑,《文艺争鸣》杂志推出了“先锋文学研究三十年专辑”,不少高校和其他刊物也举办了相应的活动。比如11月2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杂志社共同主办的“通向世界性与现代性之路——纪念先锋文学30年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在这些活动以及相关的论述中,1985年时常被视为先锋文学的起点。这种认知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虽然在1985年之前,王蒙还有刘索拉、徐星等人已经着力于文学的变革,尤其是叙事层面的变革,但是,确实是从1985年开始,小说在创作方面才显示出革命性的突破。
在约亨·舒尔特-扎塞看来,“人们对先锋派的理解方式可以分为哲学上和历史上的两种。这些方式具有相互对立的人类学的、社会的与哲学的含义。一种是从似乎是无穷无尽地变化着的凝结与分解,再现与生活,形而上的封闭与解构,一般与特殊,量与质的对立出发;而另一种则是从对大众传媒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为了统治的需要而毁灭和剥夺个人‘语言的历史观察出发的。”①对先锋派进行哲学上的理解,多是从先锋派的运思方式出发,强调的是先锋派本身的特点;对先锋派进行历史上的理解,则主要是强调先锋派的产生和形成有其具体的历史性,意味着要将之放在历史的、文化政治学的视野中进行观察。这两者,实际上又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只有综合哲学的和历史的理解,形成重叠的视野,才能对先锋派给出完整而准确的理解。
约亨·舒尔特-扎塞是在《现代主义理论还是先锋派理论》一文中提出上述观点的,这是他为比格尔《先锋派理论》一书英译本所写的序言。在约亨·舒尔特-扎塞看来,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强调认识理论和认识事物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语境,要对之进行具体化的认识。这种历史化的诉求,确实是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所着重强调的。比格尔曾指出,“审美理论家们也许会竭其所能,以求获得超历史的知识,但当人们回顾这些理论时,就很容易发现它们清楚地带有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痕迹。”②具体到先锋派,“先锋派实践并不是凭空创造出认识艺术作品的普遍有效性范畴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可能性是以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发展为历史先决条件的。”③约亨·舒尔特-扎塞和比格尔的这些观点无疑有其洞见,也是我们理解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时想要坚持的方法论原则。
一、先锋派:一个概念的历史
要说明何谓先锋派,有必要先对这个概念进行历史化的梳理。这里不妨先谈谈它在西方的状况。目前对先锋派这个概念进行梳理的、值得重视的观点,首先来自卡林内斯库。卡林内斯库曾经把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视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并对这五副面孔进行了历史化的描绘。按照卡林内斯库的梳理,先锋这个词在法语中有悠久的历史。它首先是一个军事术语,至少在中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意指军队中的先行部队。然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先锋这个词获得了它的比喻意义,用以表示政治、文学艺术和宗教方面的进步立场。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在其最初的政治意义和次生的文化意义上,先锋隐喻已为社会乌托邦分子、各种改革家和激进新闻工作者使用,却还极少为文学或艺术界人士使用。在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先锋派一词仍保有其广泛的政治含义,并开始用于指称一小群新进作家和艺术家,这些作家和艺术家把针对社会形式的批判精神转移至艺术形式的领域。随后,它在法国继续稳步发展,在其他拉丁国家也获得发展。在20世纪文学批评中,先锋派这个概念成了一个重要的术语工具;但也是在20世纪,这个概念遭遇了它的危机,引来广泛的论争。“二战后,与这种论争的出现同时发生的是,先锋派艺术出乎意料地在公众中取得广泛成功,先锋派的概念本身也相应地变成一个被广泛使用(和滥用)的广告标语。长期以来先锋派有限的声名完全是靠触犯众怒而获得的,轉眼间它却变成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化神话之一。它的唐突冒犯和出言不逊现在只是被认为有趣,它启示般的呼号则变成了惬意而无害的陈词滥调。有讽刺意味的是,先锋派发现自己在一种出乎意外的巨大成功中走向失败。”④在20世纪60年代,先锋派的终结或先锋派文学之死成为一个热议的论题,甚至很多人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卡林内斯库不但详细地梳理先锋派这个词的历史,还对它和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概念、思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厘清。在中国,先锋文学或先锋派小说,情形也同样复杂。如吴义勤所指出的,“什么是‘先锋?怎样的‘先锋?这是至今都难以说清的问题。事实上,长期以来,‘先锋小说正是作为一个其具体所指和含义被悬置了的空洞能指被谈论的。虽然,在通常和普遍的意义上,‘先锋小说指的是1985年以后马原、洪峰、苏童、余华、格非、北村、吕新、孙甘露、叶兆言、潘军、杨争光等一批作家的写作。”⑤在《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元小说因素》一文中,陈虹则指出:
尽管“先锋派”(avant-garde)在西方文化中有特定内涵,但我们仍倾向于把中国当代文学中有明显创新意识和革新意识的一批作家叫作“先锋派”,当然这个称呼毫不含有价值判断,“先锋派”只是时间向量上的一个点而已。“先锋派”出现于1985年左右,主要包括马原、残雪、洪峰(他们又被称为新潮作家),格非、余华、孙甘露、苏童等(他们又被称为后新潮作家)。
其实,看似随手拈来的“先锋派”这个称谓大有深意。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新时期文学中其他较著名的文学流派或思潮,就会发现,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等无一不概括和指称着某一类小说的内容或主题。而“先锋派”却不然,它不再直指小说内容,而只是暗示了某一类作家的先锋意识。这种先锋意识当然不是在内容题旨上,而更多表现在形式上的革新和创新。⑥
陈虹的这段话,对先锋派的构成成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较好的概括。这种认知,虽然不能说是人们对先锋文学的共识,却也是很多人都接受和认同的。需要注意的是,先锋派这个概念或命名与当时的创作并不是完全同步的,而是稍显滞后。那时候,人们更多是以“探索小说”“新潮小说”“实验小说”“现代派”等对之进行命名和归纳。1988年,李劼发表了《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钟山》1988年第5期),张颐武发表了《人:困惑与追问之中——实验小说的意义》(《文艺争鸣》1988年第5期),南帆则发表了《先锋文学和大众文学》(《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3期),这些都是当年批评家从宏观上谈论先锋文学的文章。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先锋小说或先锋派的命名并没有获得共识。
这种命名的含混或交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先锋派文学尚在建构的过程当中。包括作家创作、读者接受、批评家阐释等,都还处在过程当中。从批评家阐释的角度而言,当时很多批评家也还在一个观念生成或调整的阶段。从文学社会学的层面而言,当时的文化政治内部则还存在复杂的博弈。这些不同的命名,从一开始带着各种不同的历史目的、美学立场和文学观。先锋文学后来能从诸多命名中脱颖而出,既是各种力量博弈后的产物,也是顺应了历史时势的结果。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先锋派文学这一名称较早得到运用是在1988年。《文学评论》和《钟山》编辑部1988年10月召开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使用了这一说法。南帆在《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在九十年代后,陈晓明、张颐武等批评家则密集地使用先锋派小说这一概念,并对很多相关作家作品进行了具有先锋色彩的解读。先锋派或先锋小说,在后来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并逐渐取代了其它的命名,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概念。
在对先锋派这一概念进行厘定之后,还有待进一步追问的是,先锋派有着怎样的、内在的运思逻辑或精神逻辑。
按照卡林内斯库的看法,“从词源学上说,任何名副其实的先锋派(社会的、政治的或文化的)的存在及其有意义的活动,都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1)其代表人物被认为或自认为具有超前于自身时代的可能性(没有一种进步的或至少是目标定向的历史哲学,这显然是不可能的);(2)需要进行一场艰苦斗争的观念,这场斗争所针对的敌人象征着停滞的力量、过去的专制和旧的思维形式与方式,传统把它们如镣铐一般加在我们身上,阻止我们前进。”⑦卡林内斯库还指出,“历史地看,先锋派通过加剧现代性的某些构成要素、通过把它们变成革命精神的基石而发其端绪。因此,在十九世纪的前半期乃至稍后的时期,先锋派的概念——既指政治上的也指文化上的——只是现代性的一种激进化和高度乌托邦化了的说法。”⑧从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观念出发,先锋派往往崇尚新,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认为新就意味着进步,新占有着价值上的优先性。甚至,会有一种价值的断裂,“一边是绝对意义,另一边是绝对无意义”⑨。这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价值断裂:新的意味着绝对意义,旧的意味着“绝对无意义”。相应地,先锋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也把创造新的思想、新的艺术和新的文学,作为一种内在追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来用以称呼军事领域的先行部队的先锋,获得了它的隱喻意义:一种基于线性时间的,在思想、文学和艺术领域里存在的、进步主义的价值立场。
卡林内斯库的论述,主要以西方文学中的先锋派作为考察对象。而在中国,先锋派也显示出类似的立场。在吴义勤看来,“在中国的文学语境中,‘先锋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内涵稳定、所指明确的范畴,而是对于所有那些试图挣脱旧的文学图式和文学形态的文学努力的肯定与期待。它是一个假定性、期待性的乌托邦化的命名,但它又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命名,它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的最高荣誉,代表了我们对于‘纯文学的最高想象与冲动……”⑩吴义勤还强调,在思想逻辑和精神逻辑方面,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先锋派和西方文学史中的先锋派有相通的地方:“从精神层面来说,‘先锋主要是指一种不断创新求变的思维方式和反叛的艺术精神。对于意识形态话语、习见的艺术规则、占统治地位的审美趣味以及主流的文学秩序的反叛应该是其核心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先锋小说与西方文学史上的所谓先锋派有相似之处,反对偶像崇拜、强烈的革命色彩、弑父意识和挑衅性,使其在新时期小说中有着惊世骇俗的‘另类意味。从审美思潮层面来说,对于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的关系的颠覆,语言和形式的崇拜,非道德主义、非理性主义、非本质主义、非历史主义的文学观与世界观,也都带来了中国文学面貌的根本改变。”11西方文学中的先锋派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先锋派,各有它们的历史,各有它们的使命,但也有着共同的立场和精神。
二、文化热与翻译热:
先锋小说显在的精神资源
如今回头重看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会发现,它在八十年代的兴起,是文学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层面的因素合力形成的结果。文化热和翻译热,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为先锋小说的形成提供了相应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
这里不妨先对当时的文化热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大概是从1985年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都显得异常活跃,生机勃勃。那时候的中国,从高中学生到大学的知名教授,从工人到政府官员,不同阶层的人,都有巨大的求知热情,阅读则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甚至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时尚——与此相应,有的后来颇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正是从工厂中走出的,有的官员则成为著名学者。人们以读书会、读书小组的形式,或是结成社团或知识共同体,踊跃地针对各种问题进行讨论,文化热和翻译热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人们对文化的参与热情是类似的,文化热的内部构成却是复杂的,是各种思想、观念的荟萃与对话,并非铁板一块。譬如张旭东在《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一书中就认为,“文化热”存在着三个流派:开始阶段的科学主义或“走向未来派”,由中国文化书院的新儒家和作为独特个案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李泽厚所构成的“中国文化派”,还有“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为中心的新一代学人。
文化热内部的思想来源存在着差异,知识人的追求和目标也有所不同,其中,求新求变的追求是有力量的。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兴起,有着不同的历史语境、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却都受一种线性时间概念的影响,都表现出一种求新求变的冲动。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80年代的文献当中,任何标有‘西方或不如说‘当代西方的东西都有市场,并且一流的书商会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或把诺曼(Nouveau Raman)和《百年孤独》放在一起,所有这一切在那个时期都有极大的市场价值和适用性。”12基于同样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那时候,文学的变革,最终会这么激进地求新求变。这是先锋小说兴起的很重要的思想背景。
还需要注意的是,要考察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兴起,不能不关注当时的翻译热。从晚清以来,翻译对中国文学与中国学术的影响是巨大的。林纾的翻译对文学革命的影响、苏俄文论翻译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和延安工农兵文艺的影响,还有翻译对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张爱玲、钱钟书、冯至、李健吾等人创作的启发都不容忽视。要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因素,翻译是重要的视角。进入当代以后,苏联文学的翻译对“十七年文学”有巨大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紧接着,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翻译,尤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再次成为新时期文学兴起和获得新质的重要力量。先锋小说的兴起,也与八十年代的翻译热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文革”结束以后,过去长期坚持的“阶级斗争”的主张被放弃了,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解放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在这样一种意愿下,精英知识分子翻译、引进西方的思想著作和文学作品,甚至包括过去曾有禁忌性质的著作与作品。虽然在某些特殊时期会有反弹,但是就整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而言,谋求思想解放与“再度启蒙”终归是一种无法阻挡的潮流。在经历了长期的文化封锁与文化禁锢以后,外国文学的翻译与引进的步伐也明显加快,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派文学”的翻译与引进。在八十年代初,袁可嘉、郑克鲁等编选的八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袂推出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还有外国文学出版社的“荒诞派戏剧”等丛书,让中国作家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多种风格的文学作品。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垮掉派文学、新小说、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100多年的西方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各种形式的“主义”,在短短几年里都进入了中国作家的视野。在理论方面,弗洛依德、现象学、存在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学说,也先后被介绍到中国。那时候,阅读这些思想著作和理论著作,成为一种时代的风潮。
作家们对这些著作的阅读,在那个年代,还谈不上融会贯通,甚至会脱离理论所产生的语境,缺乏历史化的认知。可是这种观念上的冲击是巨大的,直接改变了很多人对思想、文学和人生的认知。这些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使得作家与读者眼界大开,更成为文学变革的重要资源和推动力量。在那时候,对外国文学和理论,也包括对外国哲学的阅读,甚至可能成為年轻作家实现创作转变的重要契机。在1984年之前,莫言就开始进行长时间的文学探索,为了寻找感人的故事而长时间地看文件、翻阅报纸,对不同行业的人进行访问。这些可以为他增加新的写作素材,却不一定能提供新的方法,因此,效果和预期还有很大的距离。直到他读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才慨叹:“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这种别样的可能,使得莫言可以进行更为大胆的尝试和探索。余华的写作也同样如此。余华早期的写作明显带有现实主义的痕迹,受川端康成的影响也很大,而在1986年,在读了《卡夫卡小说选》后,他产生了和莫言阅读《百年孤独》类似的震惊体验:“在我即将沦为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又比如史铁生,阅读史铁生的作品,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都不难发现,他的运思方式和以海德格尔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现象学具有鲜明的家族相似色彩。他在写作中所涉及的对“我”、对“世界”、对“我”与“世界”的关系的阐释,对宗教和文学等的理解,都有显而易见的现象学意蕴。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等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重要著作,正是在八十年代开始翻译成中文并引起广泛阅读的。诸如此类的个案,其实还有不少。
三、传统文化和古典精神:
先锋小说隐在的精神资源
谈到先锋作家的精神资源,除了高能见度的、外来的影响,还有来自本土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后者是不容易辨别的,甚至近乎透明,因而时常被忽视。如今回头重看,可以发现,传统文化和古典精神,实际上也是先锋文学兴起的一条隐秘的精神线索。
就地域而论,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其实萌芽于西藏。在1982到1985年间,马原、扎西达娃在西藏拉萨开始进行小说创作并在《西藏文学》上写过不少相关文章。此外洪峰在吉林,余华、孙甘露、格非、叶兆言、苏童等作家,则主要在南方,尤其是集中在江浙地区。考察先锋文学的兴起,地域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在《如何理解“先锋小说”》中,程光炜就指出,“先锋小说”的发生和上海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时“先锋作家”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江浙和西藏等地,显然,就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发生过的一样,它的“文学中心”无疑在上海。据统计,仅1985到1987年间,《上海文学》发表了三十篇左右的“先锋小说”,这还不包括另一文学重镇《收获》上的小说,差不多占据着同类作品刊发量的“半壁江山”。另外,“新潮批评家”一多半出自上海,例如吴亮、程德培、李劼、蔡翔、周介人、殷国明、许子东、夏中义、王晓明、陈思和、毛时安等。正如作家王安忆描绘的,那时上海的生活景象是:“灯光将街市照成白昼,再有霓虹灯在其间穿行,光和色都是溅出来的”,“你看那红男绿女,就像水底的鱼一样,徜徉在夜晚的街市。他们进出于饭店、酒楼、咖啡座、保龄球馆、歌舞厅,以及各种专卖店,或是在街头磁卡电话亭里谈笑风生”,这“才是海上繁华梦的开场”。而当时北京和大多数内地城市,各大商场夜晚七点钟前已经熄灯关门,很多地方还是“黑灯瞎火”的情形。某种程度上,城市的功能结构对这座城市的文学特征和生产方式有显著的影响。所以,无论从杂志、批评家还是作为现代大都市标志的生活氛围,上海在推动和培育“先锋小说”的区位优势上,要比其他城市处在更领先的位置。这些简单材料让人知道,即使在1980年代,上海的文化特色仍然是西洋文化、市场文化与本土市民文化的复杂混合体,消费文化不仅构成这座城市的处世哲学和文化心理,也渗透到文学领域,使其具有了先锋性的历史面孔。13
程光炜的这一观点,对于理解“先锋小说”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尤其是他注意到了“先锋小说”在兴起和形成层面的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为人们理解先锋小说的兴起提供了知识社会学和文学社会学的视角。这些作家都以现代城市上海为中介,共同受到异域文学与思想的影响,各自也受到不同的本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滋养。这里不妨举个例子。1986年,扎西达娃曾谈到不少批评家用“魔幻现实主义”一词来概括当时发表于《西藏文学》的作家及其作品。扎西达娃对此的态度是:“在6月号的作品中作者们原没想过团结在这个词的旗帜下,这本身是拉美的东西。当然,我们的确从拉美文学中吸取了成功的经验,但拉美文学并非是我们学习的唯一路子。就我个人而言,美国文学影响较之更大。这次座谈会,被人抓辫子也在‘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上,这是编辑在编后自己加上的。所以后来被某些人指责说‘魔幻是拉美的而不是西藏的。对于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和文学现象,本不应由作家自己封冠,这是评论家的事。我们的意思是评论家们评介作品时,可以把我们的作品与拉美文学现象作比较,但不应该看成是拉美文学的附庸品。事实上也是如此,《隐秘岁月》从构思到情节以及某些观念,完全是西藏古老民族中本身的东西。”14
扎西达娃的这封信,是写给程永新的。考察先锋小说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注意到作家的创作,注意到批评家的阐释和建构,还有必要注意到编辑的作用。从编辑的角度而言,像程永新还有李陀、朱伟,等等,都对先锋小说思潮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针对扎西达娃信中的看法,程永新曾这样评议道:“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拉美文学崛起之际,博尔赫斯的智性作家小说在东西方知识界得到重视,马尔克斯的一本《百年孤独》在世界范围内风靡一时。于是,中国西部高地上默默实践的文学新军恐怕就很难从大师的光环下突围,他们的作品写得再有新意,人们也还是要冠之以‘魔幻的帽子,归入拉美一路。扎西达娃正是为他及他的文友们的努力而作一辩。”15这种“努力一辩”,不乏事实的成分。在翻译热之下,魔幻现实主义确实很容易成为人们阐释西藏文学的框架。但实际上,注意到更切身的周围世界的、也是更为隐匿的影响,对于理解先锋派作家写作的来龙去脉也非常重要。影响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需要有一种复杂的思维予以求解。
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除了扎西达娃,在其他先锋作家身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在韩松刚看来,“先锋小说最早的源头应该可以追溯到1984年马原《拉萨河的女神》的发表,随后洪峰、残雪等人的小说写作,逐渐使得这一文学潮流为人所关注。但先锋小说真正开始产生影响力,是莫言、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作家的出现及其作品的逐渐流行,而其中影响力持续时间较长并引起更多关注的是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一批出生于江南地区的先锋作家。当然,先锋作家群在江南的崛起并不是有意为之的文学安排,更不是冥冥之中的偶然与巧合,而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人文地理所孕育的一场文学风暴。”16
在江南文化等地域文化的影响下,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先锋作家在1980年代的创作中就已经蕴含着中国古典精神的气息。甚至可以说,他们后来在写作上的后先锋转向,一早就埋下了种子。从先锋到后先锋的转折,实际上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是一个突然的转折。实际上,最早期的先锋小说也包含着古典的元素,比如格非的《迷舟》(《收获》1987年6期),余华的《世事如烟》(《收获》1988年第5期)、《难逃劫数》(《收获》1988年第6期)。这些作品,起码在语言和意象的經营上,带有非常古典的气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曾被视为后先锋写作的代表作品,放在格非的写作脉络中,一方面可以看到调整的痕迹——尤其是和《欲望的旗帜》相比较,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格非写作固有的一些特点,比如对古典意象的重视。苏童的写作也同样如此。在《无边的挑战》这一关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影响卓著的论著中,陈晓明主要是对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进行开掘。不过,他也并不认为中国先锋小说的形成完全是受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在谈到苏童的写作时,他曾认为苏童等作家作品中有着来自地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记忆,一种“复古的共同记忆”:“例如,《妻妾成群》的那种典雅精致、沉静疏淡的风格,那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态度,沟通了古典主义文化的传统记忆……由审美态度无意识触及的文化记忆。尽管先锋小说的叙述人经常用现代的叙事话语讲述那些古旧的故事,然而,古典性的故事要素与文化代码完全吞没消解了话语的现代性特征,话语讲述的年代透视出纯净的古典时代的风格,而讲述人的精神气质和美学趣味则重现了古代士大夫文人的文化风范。”17
“任何真正的先锋派运动(老的或新的)都有一种最终否定自身的深刻的内在倾向。象征性地说,当再也没有什么好破坏时,先锋派迫于自己的一贯性会走向自杀。”18先锋小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转折,实际上正是因为走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阶段。但先锋小说作家却并没有选择卡林内斯库所说的“走向自杀”的路途,而是选择了自我拯救。从先锋走向后先锋,走向对曾经的先锋道路的反思,便是自我拯救的措施。自我拯救的方法大概有两种:一是对曾经的美学极端主义倾向进行纠偏。二是将过去就有的却被遮蔽和压抑的一些美学经验进行放大。正如王一川在评价苏童的创作时所指出的:“尽管苏童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并有意或无意中注意摹仿,但当他用中国语言来写作的时候,这种语言本身所‘蕴涵或‘携带的中国传统就被释放了出来,使读者可以感受到中国古典式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或人物交感等意味,甚至也不难发现宋词式婉约、感伤等特色。也许可以这样比较:贾平凹的隐喻形象使中国传统处在明言层次,而西方影响被置于隐言层次;而苏童这里恰好倒过来了,西方影响在明言层次,而中国传统在隐言层次。”19
在写作中,莫言曾受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启发,但他的写作,也始终扎根于中国的大地,扎根于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传统。2012年12月7日,莫言在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中,曾谈到,个人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在叙事上有过形形色色的尝试,最终却回归了传统。这种回归,不是单纯的借用,而是一种创造性运用。他的《檀香刑》和《生死疲劳》等作品,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的叙事技艺,并且在这种借鉴和继承中融入了个人的创造。除了文学内部的继承与借鉴,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也对莫言的小说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莫言甚至认为,“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20这一点,他除了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中谈到,在其他场合也多次谈到。
不单是苏童和莫言,余华的写作也是如此。在《古典爱情》中,余华曾对才子佳人小说进行了戏仿,在《鲜血梅花》中则对武侠小说进行了戏仿。通过形式上的戏仿,余华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解构态度。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则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法进行了借鉴。正如余华所说的:“我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我的祖辈们长眠于此,这才是左右我写作的根本力量。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传统给了我生命和成长,而西方文学教会了我工作的方法。”21作为先锋小说的重要代表,余华并不是简单地借鉴西方而拒绝自身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在《活着》当中,在福贵等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中那种坚韧、忍耐的价值观念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人物的行动和性格。
可以说,如果没有受到西方文学、西方文化的影响,先锋小说的文学革命是无从发生的。同样,如果只是受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和自身的文学传统、文化传统截然断裂,那么先锋文学就会完全成为对西方先锋文学的模仿,先锋文学也不可能出现从先锋到后先锋的转折。
四、先锋小说的再评估——从思想资源的角度来看
如今看来,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发生的先锋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表现主义、心理主义、未来主义、新小说派、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还有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学说的引入,使得当时的先锋作家致力于进行各种形色的文体实验,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先锋小说的叙事革命成果,已经为今天大多数的青年作家所继承,他们借此迅速地完成了诗学或叙事艺术的基本积累,继而开始进行个人化写作风格的建构,也由此向着新的未知之域挺进。
与此同时,在今天回望先锋文学,也不能忽视先锋文学所存在的问题。通过系统的考察,程光炜曾提出这样一个对于先锋小说具有总结性质的观点:“当年存在的‘先锋小说,实际正是八十年代中国的‘城市改革所催生,并由上海都市文化、众多‘探索小说‘新潮小说‘超越历史假定主题,以及马原、余华小说奇异故事等纷纷参与其中的非常丰富而多质的先锋实验。但‘城市改革的多元文化主张,并没有真正促成‘先锋小说向着多样性的方向发展,形成百舸争流的文学流派,相反它最后却被树为一尊。这种一派独大的文学现象,有可能会在文学史撰写、教育和传播中长期地存在。虽然我在文章中力图‘还原它文学生态的驳杂性,呈现当时人们对它不同的甚至分歧很大的理解,然而它的‘历史形象早已经被固定化,要想‘改写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认识到,‘今天的当代文学史,事实上被塑造成了一部以‘先锋趣味‘先锋标准为中心而在许多研究者那里不容置疑的文学史。它已经相当深入地渗透到目前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观念之中,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支配着今天与明天的文学。”22这一看法,不能不让人想起卡林内斯库曾经指出的:“先锋派是或者说应该是有意识地走在时代前面。这种意识不仅给先锋派的代表人物加上了一种使命感,而且赋予他们以领导者的特权与责任。”23对先锋文学的批评或研究,也理应在特权和责任之间形成张力,致力解决其内在矛盾。张力的形成,离不开对其问题的分析。
陈晓明曾指出,先锋小说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先锋小说一直专注于个人化经验的发掘,因而它在感觉、故事、话语和风格等方面才能如此别具一格。然而单纯在个人化经验中走极端,其结果则是在幻觉的奇怪空间和语言的歧途永无止境地循环、重复和自我消解,其个人经验除了怪异之外,应有更深广的意义。因此,当代小说在发掘个人化经验的同时,有必要强化历史意识——对历史的理性意识。事实上,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乃至米兰·昆德拉所创造的非常个人化的经验,始终蕴涵着深邃的历史意识在其中。余华较成功且有内涵的作品如《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往事与刑罚》等中出现的‘算命先生‘老中医‘刑罚专家预示着余华把独特的个人化经验融合到历史意识(或历史无意识)中去。然而,余华后来并没有深入发掘这种‘历史意识,他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之所以徒具怪异的感觉,其欠缺正在于此。”24陈晓明的这一分析和论断,可以说是切中先锋小说要害的。有待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看来,它其实也与先锋文学所接受的精神资源有直接的关系。
在《评法国现代派小说》中,叶甫尼娜把存在主义视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八十年代先锋派作家在接受西方文化时,也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萨特热、海德格尔热的流行,使得不少小说家倾向于认可萨特式和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历史观,对萨特、海德格尔的热爱,在当时有社会语境作为支撑。往往不难体会人生中荒诞的一面,还有被抛的痛感和孤独感。这和存在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此外,它有存在论上的依据,也部分地改变了人们对人之存在结构的认识。不管是海德格尔还是萨特,都倾向于认定个体存在具有“优先权”,也就是每个人所关心的首先都是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方式。每个人总是以自身的存在作为出发点,然后构造起具有个人色彩的“世界”——有别于客观的物理世界。总是先有我,然后才有属于我的世界;个人和世界的照面,总是以“我”为圆心。人的存在是多种多样的,与之相关的世界也是色彩斑斓的。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的学说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对个人及其感觉偏差的认知与肯定,里面更有一种“当下即是”、我为我自己立法的味道。应该说,他们对人之存在结构的理解与把握,有值得我们重视的一面。新时期以来,个人经验在小说叙事里的复活,也与类似的认识作为支撑有关。可是,仅仅从此一维度来把握人之存在特性,也是有局限的——它很可能会无限地放大个人经验的重要性,无限地放大个人的主体性与合法性。它的局限,又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的局限同出一辙。如蒂里希所指出的,海德格尔“把人从一切真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让人自己獨立,把人置于人的孤立状态之中,从这全部的故事之中他创造出一个抽象概念,即历史性概念,或者说,‘具有历史的能力的概念。这一概念使人成为人。但是这一观念恰好否定了与历史的一切具体联系。”25
作为存在主义基本方法的现象学,很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排除掉所有的社会、历史、政治的因素,把个人意识绝对化,使之成为本体论的存在。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历史观便有其值得我们重视的一面,因为“马克思并不从孤独的个人处立言,而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与‘存在本身历史地建立关联上立言,这种与存在本身的历史关联,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正在产生的社会。”26他从一种社会、历史的大视野中理解人之存在的思路值得我们参照。今天,我们回头重新评估先锋小说的作用和局限,也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示。
结语
在今天回望先锋文学,还有必要注意的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已经成了新世纪小说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尤其是70后、80后和90后这几代作家,有不少正是通过阅读先锋文學而开始文学创作的。正是通过对中国当代先锋作家的阅读,以及相关的“作家中的作家”的作品的阅读,使得他们迅速地完成了诗学积累,获得了一种基本的方法,可以开始他们的文学探索和创造。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已然构成一个文学的“小传统”,是文学传统中的重要环节。
在当下,新现实的不断涌现,文学语境和文化环境的变化,都给文学变革提出了要求。先锋写作并未过时,相反,我们需要有和新现实与未来相匹配的先锋文学。在对先锋文学进行回顾和反思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有展望和期待。未来的先锋文学将会关注什么样的主题,又有着怎么样的形式?我们期待着新一代先锋作家的赋形与实践。
参考文献:
①[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页。
②[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9页。
③[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4页。
④[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端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0页。
⑤吴义勤:《秩序的“他者”——再谈“先锋小说”的发生学意义》,《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⑥陈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元小说元素》,《文艺评论》1992年第6期。
⑦[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端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1-132页。
⑧[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端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3页。
⑨[德]鲍里斯·格罗伊斯:《论新:文化档案库与世俗世界之间的价值交换》,潘律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xvi页。
⑩吴义勤:《秩序的“他者”——再谈“先锋小说”的发生学意义》,《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11吴义勤:《秩序的“他者”——再谈“先锋小说”的发生学意义》,《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12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崔向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5页。
13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收入李建周编:《先锋小说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59页。
14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15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16韩松刚:《先锋小说的古典精神与复古倾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1期。
17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喔年版,第327页。
18[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端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4页。
19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44-145页。
20莫言:《讲故事的人——在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讲故事的人》,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259页。
21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227-228页。
22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收入李建周编:《先锋小说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79页。
23[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端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12页。
24陈晓明:《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
25[美]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11页。
26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域的开启》,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6页。
【责任编辑】邹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