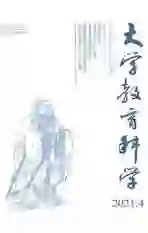信息不对称理论视域下新高考改革的困境及突破
2021-09-14张善超李宝庆
张善超 李宝庆
摘要: 高考是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承担着实现教育公平、人才培养和为国选才的使命。为推动高中学校落实素质教育、实现学生个性与全面发展,国家于2014年拉开了新高考改革的帷幕。由于新高考改革信息质量不对称、高校和学生信息处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改革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驱动,新高考改革遭遇了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偏差、选考科学性不足、利己行为等困境。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视角研究发现,多级委托—代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损耗”、信息不完整条件下学生与高校的“逆向选择”、契约精神与约束制度弱化下的“道德困境”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此,拓宽改革信息的传递渠道与交流平台、释放有效招考信息与筛选信号、建构完善的监督预警机制与弘扬契约精神,是改革突破上述困境的有效之策。
关键词:新高考;信息不对称;认知偏差;逆向选择;道德困境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21)04-0070-08
一、引言
高考制度是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高考是人才选拔与培养的重要环节,关系着社会正义的提升、社会和谐的实现[1]和人才强国的建设[2]。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颁布拉开了新高考改革的帷幕。随着2017年6月上海、浙江首批新高考改革的平稳落地和第二、三批实验省市相继开启新高考改革,陈宝生部长指出,“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已经在上海和浙江试点,经评估取得了成功”[3],“‘四梁八柱的改革方案已基本建立”[4]。然而,为什么在各大媒体广泛宣传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仍有研究发现,有受众对高职考试招生方式、农村专项招生计划、“强基计划”、平行志愿填报方式等改革措施不了解,且普通高中或者低收入家庭的家长对高考改革举措不了解的比例更高[5]?为什么在改革相关部门三令五申强调高中要严格落实新课程方案、学生要按照兴趣确定选考科目的背景下,某些高中仍用“田忌赛马”的策略应对新高考?为什么选考会出现一度令社会震惊的“理科萎缩”现象?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认知偏差、逆向选择、道德困境等视角为我们解开上述谜团提供了新的可能。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其产生是为了消除传统经济学的信息完全对称假设与现实交易中交易双方信息不完全对称相矛盾的困境。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交易中当市场的一方无法监测和监督市场另一方行为或无法获知另一方行为的完全信息,抑或监测和监督的成本高昂时,交易双方掌握信息的不对称状态[6](P6-10)。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在不同阶层分布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表现为不同主体掌握信息数量、质量、时空的不对称。20世纪80~90年代,经过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詹姆斯·莫里斯的共同努力,信息不对称理论已日趋成熟且因为其极强的解释力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教育、管理等领域。信息不对称理论主要包括逆向选择、委托—代理模型、道德困境等。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在论文《次品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中提出了旧汽车(柠檬)市场模型。他认为在旧汽车市场上,买方由于不知道二手汽车的质量,往往根据市场的平均价格购买二手汽车;卖方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利用买方的信息劣势,将更为劣质的汽车以市场平均价格卖给买方,导致市场上出现劣等二手汽车取代相对较好二手汽车的现象。阿克尔洛夫将其称为逆向选择,并进一步指出逆向选择的存在必然导致市场效率低下甚至崩溃。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莫里斯以三篇题为《关于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的笔记》《道德风险理论与不可观测行为》《组织内激励和权威的最优结构》的论文奠定了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委托—代理模型和道德困境理论。委托—代理模型能够有效解释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市场风险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在该模型中,莫里斯认为交易双方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与代理关系。其中代理人是指交易中信息占优势的一方,而委托人则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代理人往往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通过隐匿行动、目标差异等方式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来增加自身利益,进而引发道德困境。他进一步解释,逆向选择是委托人与代理人在达成协议前由于彼此间信息不对称进行博弈的结果。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下新高考改革困境的多元表征
迈克尔·富兰认为教育改革必定“充满着似是而非和相矛盾的现象,以及通常注意不到的因素”[7],即教育改革必定遭遇诸多阻力与困境。具体而言,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新高考改革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以下困境。
(一)信息质量不对称下利益相关者对改革的认知偏差
信息质量不对称是指信息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分布不均。信息质量的不对称通常表现为信息拥有量不足的一方对另一方可能一无所知[8](P28)。换言之,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个体所掌握的信息不论是在数量或是质量方面都是不对称的。恰是这种不对称性使得信息接收者难以全面正确认识信息推送者的意图。新高考改革之初,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将新高考改革的总体要求、改革意义、价值追求、改革具体内容等通过新闻媒体做了大量宣传。例如,《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就详细介绍了新高考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招生计划分配方式、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改革招生录取机制等”。《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则对新高考改革的原则、目标、成绩使用等进行了更加具体详细的规定。上海、浙江、北京、山东、湖南、重庆等省市也都已将本省市新高考改革方案通过电视、报纸、发布会等向社会公布。按理说,受众不难全面正确认识新高考。然而,在新高考改革实施过程中,由于改革信息内容多样、受众群体选择性接收改革信息且信息获取能力有限,不同利益相关者所获得的改革信息并不完全等同于信息发送者所要传达的全部信息,结果出现某些利益相关者对考试改革目标、内容等知之甚少的现象。例如,在国家、省级教育部门对改革广泛宣传、提前公布招生简章的背景下,對新高考非常了解的学生仅10%[9],对高校招生非常了解、较了解的仅24.1%[10]。对高校某些具体“录取规则”,80%的家长表示不知道[11],甚至还有高中校长说“综合素质评价和升学有关系吗?”[12]在改革信息质量不对称的情况下,某些利益相关者会基于自己非理性偏好去质疑、否定、歪曲新高考改革。例如,有人认为“此次高考改革有一项措施存在方向性失误”[13],多次选考的改革信息被学生理解为自己能否胜出取决于跟他同时报考这门科目学生的能力,导致学生去琢磨其他学生都报考了哪些科目,据此选择同科“考伴”相对较弱的科目[14]。可见,在改革信息质量不对称的情境下,利益相关者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片面认识新高考改革的现象。
(二)信息处理能力有限性下高校与学生选考科学性不足
信息处理能力是指个体获取、分析、处理信息并形成策略的能力。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个体的信息处理能力具有有限性。具体表现为,当个体不能获取全部信息或科学处理信息的时候,往往会依据原有思维及观念,根据片面化的信息做出自认为于己有利的决策[15](P36-40)。《國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改革就是要“促进学生发展学科兴趣与个性特长,科学选拔各类人才”。为了实现科学选考与招生这一目标,《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指出“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的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由学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要将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所有科目成绩提供给招生高校使用”。《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则指出“高校可以根据专业需要,确定招生要求,包括选考科目范围、综合素质评价使用等”。可见,学生按照个人兴趣、特长确定选考科目,高校按照专业特点制定选考要求是新高考选考的科学体现。但在信息处理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学生、高校往往会做出不“科学”的选考决策。例如学生作出科学选考需要了解自己的兴趣、特长、各科成绩发展趋势、高校性质、专业排名、近几年报录比、专业师资、就业情况等大量信息。然而,由于缺乏收集、分析上述信息的经验、能力、技术,高中生只能根据现有成绩的好坏、自己的感觉、家长意愿来进行选考决策。新高考改革研究课题组调研发现,有60%甚至更多学生的志愿是由老师、家长包办或主导[16]。潘昆峰、刘佳辰等研究指出,中学生由于获得的信息不充分,往往会作出与自身能力和愿望不匹配的专业选择[17]。同样,高校科学提出选考方案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办学特色、专业定位,掌握其他高校同类专业的名额及选考要求、该专业三至四年后的就业需求、当年可能报考该专业的大致人数及其成绩与综合素质状况等信息。但事实上,高校在极短的时间与现有技术条件下很难获取相应的信息。张红霞调研发现,学生综合素质档案中的内容,还不足以满足高校招生的需要,高校招生部门在具体执行落实这一要求时大多一筹莫展[18]。因此,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招生名额、获取更多财政拨款等压力下,不少高校因顾虑到生源问题不敢提出选考要求[19]。如2017年在上海招生的高校共有专业(类)1 096个,其中没有提出科目要求的有655个[20]。又如某师范学校数学系的选考科目居然是物理、化学、历史三选一[21]。概言之,学生与高校信息处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选考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三)利益驱动下利益相关者的利己行为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委托人难以收集代理人全部信息或在对其不能进行有效监督的条件下,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利用信息优势做出“搭便车”、隐瞒真相、疏于管理等投机行为使另一方利益受损[22]。换言之,投机行为、利己行为是委托人与代理人在信息不对称作用下面临的又一困境。《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新高考改革要“确保公平公正,确保考试招生工作高效、有序实施”。可见,公平有序是新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与基本要求。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要求,“严格落实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严禁压缩课程授课时间;要根据本《意见》,制定本省(区、市)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具体办法”。《北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试行)》强调,“学生选考做到随教、随考、随清。高等院校可根据办学特色和定位,以及不同学科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分专业(类)自主提出指定选考科目”。由此可知,地方政府、高校、高中、学生都是实现上述“契约”的代理人。然而,地方政府、高校、高中、学生都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即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诉求、高校对优质生源的需求、高中对升学率的追求、考生对名校的渴望。他们在利益驱动下会通过隐瞒某些信息、“搭便车”等方式来为自己谋利。例如,有的地方政府利用新高考改革的某些制度设计来维护本地考生的利益:国家要求各省市对转入考生的等级考试科目进行认定,但是某些省市的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都明确指出外省转入考生等级科目成绩不予认定。又如为了实现升学目标,高中学校及考生往往采取“田忌赛马”、多次重复选考等方式打压对手:上海某中学就强行要求全体学生在高二阶段必须选择生物、地理等级考试,这样到了高三阶段只需选择一门课程,可以把大多数时间花在语数外等科目上面[23]。再如,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很多高校会采取更换校名或挂靠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办法来吸引优质生源,2017年浙江646分考生被挂靠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独立院校录取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下新高考改革困境的原因探析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市场主体间信息的不完整必然导致认识偏差,而交易双方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进行博弈必然导致逆向选择、道德风险[8](P29)。由此可知,多级委托—代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损耗”、信息不完整情境下学生与高校的“逆向选择”、契约精神与约束制度弱化作用下利益相关者的“道德困境”是导致改革遭遇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多级委托—代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 损耗”
信息传递损耗模型认为,委托—代理层级的数值越大,信息在各层级环节传递过程中的丢失量也就越大,即出现信息损耗现象。信息损耗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信息接收者对信息的理解发生偏移[24](63-67)。可见,信息在多级委托—代理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损耗现象,传递渠道越长,受众接收到的信息就越少,结果导致受众难以掌握全部信息进行理性判断。事实上,新高考改革的利益相关者对改革的认识偏差也是源于信息传递渠道过长导致的信息传递损耗。以学生及家长对新高考改革的认知偏差为例,他们获得新高考改革的信息大都来源于班主任,班主任获知的新高考信息通常来自学校,学校的新高考信息来自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的信息来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获得的信息来自教育部。也就是说,国家要将新高考信息传递给学生及家长要经历至少四级信息传递链,形成了三对委托—代理关系。其中,省级、市县级、学校既为上级传递新高考改革信息的代理人,又是下级信息接收部门的委托人。由于每一级传递链在解读与理解新高改革信息时难以完全一致,因而当新高考改革信息经过这条传递链到达学生及其家长时必然蕴涵着信息不对称[24](P63-67)。在不能及时、全面掌握改革信息的条件下,学生及家长必然难以全面认识新高考改革的价值与本质。同样,多级委托—代理模式传递改革信息的方式致使高中校长及广大教师也难以及时、全面获取改革信息。比如针对“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的传达,浙江一位负责学校各种文件往来的教师就说到:“上级如果下发关于新高考的文件,我肯定第一个收到,再转给校长。可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收到过这个文件。”[25]综上所述,委托—代理层级的过多使得新高考改革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发生损耗,进而导致处于代理链低端的学生、教师、家长等难以及时而全面地获取改革信息。
(二)信息不完整条件下学生与高校的“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拥有不对等信息的双方进行交易时,拥有信息较少或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由于没有掌握全部信息而不能进行理性决策的行为。赫伯特·西蒙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逆向选择是人们无法完全按照“效率最大化”和“选择最优化”原则理性指导自己而做出的行動[26]。可见,逆向选择是互动双方在不能够掌握彼此完整信息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或不理性的选择。实际上,新高考改革所遭遇的学生选考与高校招生的科学性不足本质上是彼此间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基于委托—代理模型来审视学生的非理性选考,假定选考所要求的科目为商品的话,学生是委托人,高校则是代理人:虽然学生会提前知道心仪高校A专业要求的选考科目,且自己很喜欢其中的科目,但是他并不知道本次选考科目难易程度、选考该科目的人数以及和他一同报考该校A专业的人数等关键信息。当没有掌握这些信息的时候,为了更有把握考上该校A专业,他必然会采取“非理性”选择,即放弃自己喜欢且难度较大的科目而选择容易得分的科目来获取更好的成绩。这种结果必然使得越来越多的优质考生被那些通过逆向选择的考生用高分排挤出去,导致高校最终招录的学生并不适合所报专业。再如,高校的非理性确定选考科目同样是其在不能完全掌握考生信息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基于委托—代理模型,高校在招生过程中是委托人,而学生则是代理人。由于高校制定专业选考要求是在学生选考之前,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报考自己学校A专业的考生人数,以及学生学习程度如何,但学校又必须完成国家下达的招生任务,假如学校将A专业限选科目定为物理一门的话,那么学校则要承担A专业难以完成招生任务的风险。正如某高校招生部门负责人担忧的,“分数线越往下走,学物理的被前面的招生单位都选完了,学校再选人难度可能就大一点”[27]。因而,他们只能采取三选一或者不限选的策略来规避招生风险。高校放低选考条件的后果就是很多不符合专业要求的考生进入该专业,导致高校教育资源浪费,教学效率低下,难以培养优秀人才。正如清华大学浙江招生组组长崔凯所说,学生在高中阶段过早放弃物理、化学等科目,会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出现学习跟不上的问题[28]。总而言之,在不能全面掌握招考、报考信息的情况下,学生、高校都只能根据现有条件在选考、指定选考科目过程中去“理性”地逆向选择。也恰恰是这种“理性”选择,使得新高考改革遭遇选考科学性不足的困境。
(三)契约精神与约束制度弱化作用下的 “道德困境”
道德困境是指委托人和代理人签订合同后,代理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而且并不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后果[15](P36-40)。代理人通常利用约束制度弱化、信息优势、隐匿信息等方式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6](P6-10)。事实上,新高考改革中的“道德困境”正是利益相关者在约束制度弱化条件下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所导致。其一,内在契约精神弱化诱发道德困境。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契约关系建立后,代理人必须严格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代理人一旦发现不认真履约比认真履约能够收获更大的收益,那么他们就可能利用信息优势选择隐匿自身行为来获取更大的利益。以普通高中投机行为为例,作为实施素质教育代理人的高中必然要遵照与国家的契约,认真落实改革要求。但是高中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当他们发现按照改革要求实施课程与教学改革可能会降低升学率,而大搞“田忌赛马”二次选考等可能换来更高的升学率,那么在相关监督与问责机制不完善、行政部门难以获取学校落实改革信息的条件下,他们就会顶着“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帽子大搞应试教育。如浙江某高中发现分数与课时是否上完并无绝对关联时,通过“排兵布阵”使高二某班40人选考化学,10人获得满分,90分以上27人,全班平均分为96分[29]。其二,外在约束制度弱化诱发道德困境。委托—代理理论认为,道德困境是由于委托人无法监测和监督市场另一方的行为,或无法获知另一方行动的完全信息所致[6](P6-10)。也就是说,新高考制度设计的不完善是其遭遇“道德困境”的又一原因。例如,作为新高考改革委托人的国家委托高校规范招生,但是国家只要求高校向社会公布选考科目、招生计划,确定招生政策和规则,至于关键信息如高校性质、专业简介、专业师资、就业现状与前景等信息却未无详细要求。因而,一些高校通过隐匿信息(更换校名、挂靠名校等)的方式来诱导处于信息劣势的考生,使新高考科学招生面临道德困境。又如,改革要求建立监督制度来保障高中落实新课程改革与走班教学:浙江出台的《普通高中学校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指南》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对高中课程、教学进行监督。然而,该文件仅仅规定了监督原则、监督方法、建构哪些制度及保障机制,对于具体谁来监督、监督哪些内容、谁对监督负责、对监督不力如何问责等并未明确指出,使得监督效果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正是监督机制的相对薄弱助长了某些高中的投机行为。
四、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下新高考改革困境的规避之策
信息论创始人申农认为,当人们获得完全信息时,风险就不存在[8](P31)。因此,通过多种途径,增加新高考改革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对称是规避上述困境的有效之策。
(一)拓宽改革信息的传递渠道与交流平台
新高考改革认知偏差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改革信息传递的委托—代理链条级数过多,使得信息在到达受众群体前遭到严重损耗。因而,化解人们对改革的认知偏差就需要健全新高考改革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渠道。其一,拓宽新高考改革信息传递渠道,降低信息损耗。托马斯·戴伊认为,新闻媒介的真正功能在于它们能够决定将要被决定的事[30]。特别是信息源如果具有权威性、专业性、知名度高等特征,新闻媒介传播的内容信息信誉度就高,受众的接受效果就好[31](P111)。换言之,大众传媒(特别是权威媒介)扮演着政策宣传者的角色,对已经出台的政策进行准确、全面的宣传与解释,能够促动受众客观全面地理解政策内容,真心接受与支持政策内容[32]。因此,国家可以借助权威信息传递平台同步地、全面地、经常地将新高考改革信息传递给受众。其二,建构信息交流平台,确保信息被正确理解。美国信息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强调信息的有效传播基于两端传播主体的对等性[31](P118)。换言之,只有信息的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进行平等互动,才可以使接收者更准确地了解信息。因此,国家可搭建新高考改革利益相关者间的沟通平台,方便他们获取改革的全部信息。一方面,可通过选择有影响力的媒介对利益相关者传达改革信息。如各级政府在自己的网站开辟新高考咨询板块,开通新高考改革微信公众号、QQ号,邀请新高考改革专家进校园、社区、家长学校宣讲等。这种面对面的及时沟通能够打消改革利益相关者的疑虑与困惑,使他们正确认识与肯定新高考改革。另一方面,新高考改革决策者可以邀请执行者、受众参与到改革政策的制定与修订过程中,使他们对改革的价值取向、内容达成共识。同时,改革决策者也要参与到地方改革政策制定、执行与宣传的过程中,促使改革执行者能够精准落实改革要求、受众群体能够最大限度地接受改革政策。
(二)释放有效招考信息,发送筛选信号
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中“逆向选择”的规避研究,斯彭斯认为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能够将关键“信号(信息)”传递给在信息上处于劣势的个体[3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信号筛选理论认为,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委托人)首先以某种方式给出区分不同类型的市场信号以求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借此来弥补或解决自己在交易中所处的信息劣势状况[34]。换言之,信息优势一方向劣势一方主动提供相关信息以及信息劣势一方采取适当方式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是突破逆向选择的有效途径。在新高考改革中,应对逆向选择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方面:其一,释放有效招考信息。在改革过程中,掌握最全面的选考信息、高校招考信息的无疑是省级考试招生部门与高校。因而,为了避免学生在不知道某次选考科目人数、难度等信息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省级招生考试部门及高校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网络及印发选考信息手册等方式,提供每一科目历次的选考人数、考试难度分析、历年考生人数等信息,为学生科学选考提供依据。例如,省级招生考试部门可以采集面向本省市招生高校的关键信息做成数据库,供学生查询,为他们的科学选考提供参考。又如,高校招生部门、各学院可组织教师走进高中校园,就本校历史、办学层次、专业设置、师资与就业等情况进行宣讲,现场回答学生及家长的咨询,规避学生选考的逆向选择。其二,发送关键筛选信号。在招录环节,海量的考生信息与极短的录取时间,特别是某些考生的投机行为,使得高校很难从所有考生中高效地筛选、录取适合的考生。因而,这就需要具有该方面信息优势的学生、高中、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向高校发出有效筛选信号来提高招录的科学性。例如,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建构学生成长数据库。该数据库采集的信息指标至少包含学业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社会实践、竞赛获奖等内容。其中,教师需做好学生平时成长数据的输入工作,学校需做好数据审核工作。在录取环节,数据库可为每位学生生成一份包含综合素质、兴趣特长、内在潜质的可视化报告。当高校输入某些关于学生素质的关键词,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就可对报考考生自动甄别与排序,进而提升招录的科学性。
(三)建构完善的监督预警机制,弘扬契约精神
针对如何化解由制度与契约精神弱化引发的道德困境,迈克尔·斯彭斯一针见血指出“要靠制度保障”[8](P110)。因而,规避新高考改革的道德困境就是要建构健全的制度对委托人进行约束。其一,建构完善的监督预警机制。阿罗认为道德困境的规避可以由市场的一方通过预警和监督市场另一方来实现[6](P6-10)。国家应建立全方位的新高考改革预警与监督机制来规避道德困境。例如,国家可以在各省市建立专门的新高考改革信息办公室、新高考改革巡查或督查组等搜集关于各省市新高考改革的一手信息,以便在第一时间发现改革中存在的道德困境,进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另外,国家还应建立完善的监督制度。除建立自上而下的预警制度之外,国家还应该建构自下而上的监督平台,如开通专门举报新高考改革中地方行政部门、高校、高中等违规违纪行为的信息平台。此举不仅能够节省国家监督成本,而且还能提高监督效率。其二,弘扬契约精神。首先,作为新高考改革委托人的中央政府要对作为改革代理人的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高校、高中进行培训,旨在使其认真落实新高考改革政策,提升其履行新高考改革使命的责任感和契约精神。在契约精神的驱动下,高中会自觉落实课程标准规定的所有课程、实施走班教学,高校会自觉根据专业特点科学提出选考要求,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则会自觉按照国家要求落实改革方案。其次,面对制度弱化造成的新高考改革道德困境,国家要完善优化新高考改革的各项制度。一方面,细化新高考改革的各项规定,来规避某些利益相关者因试图隐匿信息而引发的道德困境。例如,国家可以在新高考改革方案中完善与细化高校科学制定选考科目的具体措施,并要求高校向社会、考生公布更多的关键信息(学校性质、办学层次、培养方案、师资配置、就业率及就业前景等)。另一方面,建立与新高考改革相匹配的激励机制和处罚机制。这样既能顾及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又能够打击利益相关者的“不道德”行为。例如,国家、地方政府可以对认真落实新高考改革要求的高中學校适当给予招生名额倾斜、经费支持、荣誉奖励等措施,以激励它们更好落实素质教育,推进新课程改革与走班教学,而对于未认真落实新高考要求的高中学校,可给予责任人相应的处罚,如批评、降职、解聘等。高中只要认识到认真落实新高考改革比依靠“田忌赛马”等投机方式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而又可避免处罚,就会自觉落实新高考改革的各项要求。
参考文献
[1] 袁卫.美国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政策改革:背景、争议与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21(02):118-127.
[2] 孙立新,叶长胜.习近平关于终身教育论述的思想探源、内涵价值及实践推进[J].大学教育科学,2021(02):26-33.
[3] 新华网.陈宝生:从2018年起将有17个省份开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进程[EB/OL].(2018-03-16)[2021-03-17].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
2018-03/16/c_1122545332.htm.
[4] 中国新闻网.陈宝生:这五年是人民对教育获得感不断增强的五年[EB/OL].(2017-10-22)[2021-03-17].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7/10-22/
8357916.shtml.
[5] 王新凤.增强高考改革的满意度与获得感[N].中国教育报,2021-05-21(06).
[6] 赵超,贺华.信息不对称理论下政府公信力影响机理探析[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
[7] [加]迈克·富兰.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M].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加拿大多伦多国际学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2.
[8] 向鹏成.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9] 杨德军,黄晓玲,朱传世,范佳午.北京市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年级学生选课调查及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18(06):15-23.
[10] 张雨强,顾慧,张中宁.普通高中生高考选考科目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5所高中首批选考学生为例[J].教育学报,2018(04):29-38.
[11] 于乐.高考必读:这些“录取规则”,80%家长都不知道![EB/OL].(2017-05-03)[2021-03-17].http://www.sohu.com/a/138003943_599821.
[12] 王萍.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阻抗与消解[J].课程·教材·教法,2017(07):93-99.
[13] 赵俊芳,刘艳红.高考改革社会风险评估与规避机制刍议——基于权力监督与公共政策价值分析的视角[J].大学教育科学,2019(01):53-59.
[14] 柯政.高考改革需要更加重视科学学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03):13-24.
[15] 辛琳.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J].嘉兴学院学报,2001(05).
[16] 新高考改革研究课题组.沪浙新高考改革近四年,效果怎么样[N].光明日报,2017-07-13(07).
[17] 潘昆峰,刘佳辰,何章立.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选考的“理科萎缩”现象探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7(08):31-36.
[18] 张红霞.综合素质档案在高校招生中的“初筛”构想与风险分析[J].全球教育展望,2017(10):92-101.
[19] 鄭若玲,孔苓兰.“双一流”学科选考科目制定的现状及建议——基于2019年浙江省高考选考科目的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19(01):60-67.
[20] 周凯,王烨捷.上海37所高校公布2017年高考选考科目要求[N].中国青年报,2015-02-04(01).
[21] 吴育人.新高考改革:物理为什么受冷落[EB/OL].(2017-10-02)[2021-03-16].http://learning.sohu.com/20171002/n515803771.shtml.
[22] 杨跃.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困境及其突围——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7(02):6-12.
[23] 施华.关于改进和完善目前“3+3”高考模式的建议[EB/OL].(2017-08-15)[2021-03-17].http://www.shszx.gov.cn/node2/node5368/node5376/node5388/u1ai99551.html.
[24] 樊亚峤.信息不对称与课程政策执行[J].教育发展研究,2009(12).
[25] 高逸平.最近家长圈里流传的“浙江省高考改革方案”是真的吗?[EB/OL].(2014-04-15)[2021-03-17].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c149a20102eb6w.html.
[26] 赵敏,冷望星,宁燕.决策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规避之策——基于政府与公众视角的分析[J].领导科学,2017(04):34-35.
[27] 环球网.浙江、上海公布“新高考”方案:浙沪各具特点[EB/OL].(2017-03-20)[2021-03-17].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7/03-19/8177790.shtml.
[28] 陆文琳.新高考改革后高校怎样挑学生?清华北大这么说[EB/OL].(2015-12-20)[2021-03-16].http://www.zjol.com.cn/05zjol/system/2015/12/20/020960303.shtml.
[29] 刘博超.浙江高考改革是场闹剧?新高考方案改变了什么?[EB/OL].(2016-11-30)[2018-10-10].http://edu.qq.com/a/20161130/017833.htm.
[30] 刘水云.大众传媒对教育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影响——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为例[J].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14(12):182-194.
[31] 任艳妮.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D].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32] 陈堂发.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传媒在政府政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78-190.
[33] 杨利娟.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J].北方经济,2009(05):20-22.
[34] 施先旺,李志刚,刘拯.分析师预测与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研究——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02):39-48.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of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s: Analysis based o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
ZHANG Shan-chao LI Bao-qing
Abstrac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the basic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which undertakes the mission of realizing educational equity, talent training, and talent selection for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high schools, China launched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s in 2014. Due to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quality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s, the limi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bility of colleges and students, and the interest driven of the reform stakeholders,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encounters the dilemma of cognitive bias, lack of scientificity and self-interest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the "information loss" in the process of multi-level principal-agent communication, the "adverse selection" between examine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the "moral dilemma" under the weakening of contract spirit and restraint system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above dilemma. Therefore, it is feasible to broaden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channels and exchange platform, release the effective recruitment information and screening indications, construct a perfect supervision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agreement to avoid the risks.
Key words: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 cognitive biases; adverse selection; moral dilemma
(責任编辑 黄建新)
收稿日期:2021-03-17
基金项目:2020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教师教学关键能力建构及本土化培育策略研究”(20YBQ037)。
作者简介:张善超(1986-),男,河南新乡人,教育学博士,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教育评价、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长沙,410082。李宝庆,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重庆,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