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声歌、西曲歌艺术特征初探
2021-09-13刘晓
刘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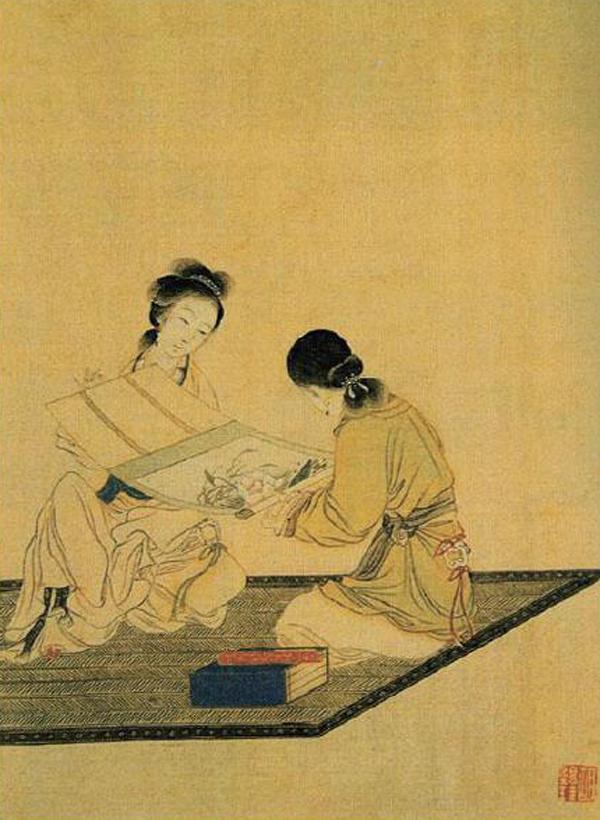


摘要:吴声歌、西曲歌是南朝民歌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称为南朝民歌最为出色的部分。吴声歌、西曲歌的产生与当时南北朝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及民歌创作者消沉的心态等密不可分。吴歌西曲中双关隐语手法的独特作用与其五言四句的短小体制使其语言呈清新流丽的特色,艺术特征鲜明,对后世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民歌史上颇具一格。
关键词:吴声歌;西曲歌;社会环境;双关;爱情
南北朝时期,民歌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学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南朝民歌发源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富有浓厚的水乡气息,大多保存在宋代文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中,吴声歌和西曲歌在南朝民歌中占有独特地位,题材内容多种多样,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吸引着人们。吴声歌曲中《子夜歌》《子夜四时歌》《懊侬歌》和《读曲歌》最为引人注目,它们通过运用清新自然的语言反映江南女子在爱情问题上的种种思绪,真实再现了南朝的社会图景。而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西曲歌,以《三洲歌》《莫愁乐》《襄阳乐》和《那呵滩》等为代表的作品都十分感人,在清幽美丽的环境中诉说着一段段人间故事。
一、吴声歌、西曲歌产生的主客观条件
分裂动荡的南北朝时期,社会矛盾重重,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内心痛苦不堪,大多数人通过民歌吐露心声,作不平之鸣。民歌是南朝那个特殊年代特有的表达情感的方式。“吴歌西曲产生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的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又特殊的时代。”[1]地处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南朝,以其独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孕育了色彩鲜明的吴声歌和西曲歌,成为当时民歌的主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民歌除《诗经》外的另一个源头。它们自刘宋时期就从民间发展起来,并随着音乐文化的繁荣在梁代进入鼎盛时期,它的传播也从民间传播到了宫廷,在民间的蓬勃发展激发了帝王、文人的创作热情,逐渐成为宫廷娱乐音乐的主要样式。
(一)南朝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
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动荡的时期,国家分裂,平民百姓流离失所,战火纷纷,众多的边关将士与亲人分离,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终日生活在沉重的迷茫与痛苦之中。分裂对峙的时代大环境下,吴声歌西曲歌脱颖而出,并在孝武帝大明前后在民间引起文人关注,到了“刘宋时期则发展迅速,一大批吴歌新声曲调在刘宋开始为文人所注意并进入宫廷音乐系统”[2]131。其后的梁武帝潇衍更是开创了“博学多通”“笃好文章”文学风气,帝王及文人等的认可、加入使得它们传播得更加广泛迅速,而某些南朝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纵情声色的需要,让乐府机构大量采集此类民歌,吴歌西曲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逐渐发展成宫廷娱乐音乐的主流,也成为当时民间文学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南朝地处长江中下游流域,“商业非常发达,吴歌西曲反映城市商人生活的诗歌占有很大分量”[3],而且那里多水乡景色,山清水秀,诗意盎然,朦胧中有着缠绵悱恻。吴声歌指在以扬州建业为中心的吴地民歌,西曲歌主要在以江陵为中心的地区发展,处在江南的中心,如画的风景,富饶的物产,孕育了色彩鲜明的吴歌与西曲。吴声歌与西曲歌中的很多佳作都带有江南韵味。《子夜四时歌》中的“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两句写出了春天江南地区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盛况,而且描述了吴地人的多情,男女间情思的描写深深地埋在吴声歌中;而西曲歌中的《三洲歌》“风流不暂停,三山隐行舟”也是有着独特的江南韵味,勾勒出了风儿推着小舟慢慢前行,直至消失在山水间的具体画面,给人一种缠绵隐逸的感觉,而“风流”二字的运用也使得民歌的主题更加明显。不论是吴歌还是西曲都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蕴藏着化不开的浓情,并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生根发芽。
(二)民歌创作者普遍的精神消沉状态
“歌诗合为事而作。”吴声歌、西曲歌亦是创作者们为“事”写的,“吴歌西曲,以‘情见长”[4]。战乱的年代,人们流离失所,内心遭受着巨大的恐惧、煎熬,高昂的斗志渐渐磨灭,取而代之的是消沉的状态,创作者们在这种状态下創作的吴歌西曲必然有着悠长的愁思。《子夜歌》便是创作者心情低迷的写照,特别是“今夕已欢别,合会在何时?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两句,写了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用简洁的语言描写了作者迷茫痛苦的心境。吴声歌西曲歌生于乱世,创作者精神消沉,这必会反映在作品中,或多或少,或明显或隐蔽,歌写事,事藏于歌中。创作者普遍的精神消沉状态使得吴声歌、西曲歌中弥漫着一种柔和的气息。作品大多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对于日常生活中琐碎小事的描写很多,注重刻画细节,以小见大,从小处着手,但饱含着强大的力量。由于创作者普遍处于精神消沉状态,作品中的落寞是避不开的,也正是因为创作者普遍的精神消沉,让吴歌西曲有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并传承下去。
二、吴声歌、西曲歌清新流丽的语言特色
吴歌西曲语言的表现形式多样,在运用了大量修辞手法的同时,句式和体制方面也十分精妙。比喻和双关手法是吴声歌与西曲歌使用最普遍、也最成功的一种修辞手法。大量的比喻让吴歌西曲的呈现更加形象生动,作品内容更加真实可感,也进一步为其增添了浪漫气息;双关隐语的丰富运用是吴声歌西曲歌显著的艺术特征,内敛含蓄的创作者们用这种隐逸趣味的方式挥毫泼墨,不管是同音同字的双关,还是同音异字的双关,都蕴藏着真挚的情感。此外,吴声歌、西曲歌的句式创作也十分精妙,多为五言四句的短小体制,这使得吴歌西曲更加精炼、准确,营造了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开创中国诗歌形式中五言四句的先河。
(一)双关隐语的隐逸情感
吴声歌和西曲歌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双声、叠韵、夸张、叠字、比喻、拟人、双关等一系列修辞手法在吴歌西曲中都有展现,正是这些修辞手法的相互融合塑造了吴歌西曲独特的艺术特征。双关隐语是吴歌西曲区别于之前文学作品的地方,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双关手法十分少见,双关也可以说是在吴歌西曲中渐渐发展起来的,此后双关手法被文人们重视起来并广泛应用在多种文体中。
双关隐语的大量使用,是吴声歌和西曲歌尤其是吴声歌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当时其他文学形式所不具备的。在吴歌西曲中,双关隐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区别于之前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并且在作者抒发情感时发挥着巨大作用,经常带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埋藏着作者的隐逸情感。作品的感情最能吸引人,而含蓄隐逸的情感最能打开读者的联想与想象,双关隐语使得吴声歌西曲歌表情达意的力量迸发出来,在柔美中增添了一种隐秘的力量。吴歌《子夜歌》中的“我念欢的的,子行由豫情。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5]65一段双关隐语的使用历来为人们赞颂,这其中的“芙蓉”二字与“莲”是同义词,而“见莲不分明”中的“莲”又是“怜”字的双关语。“怜”是怜爱的意思,句中的“莲”除了指莲花,也双关怜爱之意,这种隐逸的情感表达方式,显得含蓄委婉,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在西曲中双关也很常见,比较富有代表性的是在《作蚕丝》中“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两句,它运用了两处双关,“怀丝”双关“怀思”,并以蚕丝的“缠绵”双关爱情的“缠绵”,通过蚕丝来表达主人公缠绵的爱,这是一位女子的深情表白,她以春蚕自喻,温婉隐秘地表达了她对爱情的执着。
双关隐语的表达手法具体可分为同音异字的双关和同音同字的双关两種。正如《子夜歌》与《作蚕丝》两部作品,“莲”与“怜”“怀丝”与“怀思”便是同音异字的双关,而《作蚕丝》中用蚕丝的“缠绵”双关爱情的“缠绵”则是同音同字的双关。同音异字的双关和同音同字的双关都有着巨大的力量,都推动着民歌情感的不断递进,是作者抒发美好情感的一种方式,透过双关隐语可以挖掘创作者内心更深层次的情感,使吴歌西曲中的感情更加缠绵悱恻。吴声歌和西曲歌被双关隐语修饰的内涵更加丰富,意味深长,含蓄委婉中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在当时的各类文学作品中别具风格、独树一帜。
(二)五言四句的短小体制
每一种文学样式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体制。体制、句式是作品的一种模式,甚至会成为某类作品必须要遵从的一种形式。吴歌西曲大都是五言四句的短小体制,有的也会夹杂几个长句、短句或者是四字句,但主要以五言四句的形式为主,即使是长句也不会太长,“吴声西曲多四句一曲,一曲下若干首”[6],短小精炼也就成为了吴歌西曲的主要体制形式特征。吴声歌中的《长乐佳》就是典型的五言四句的体制,“红罗复斗帐,四角垂朱裆。玉枕龙须席,郎眠何处床”,字字精雕细琢,言言当行本色,用简洁明了的话语抒写缠绵的情谊,留下了悠长的情思,言有尽而意无穷。西曲歌中的《莫愁乐》《襄阳乐》《青阳渡》《来罗》等都是五言四句的体制,比如《来罗》中写道的“郁金黄花标,下有同心草。草生日已长,人生日就老”,在西曲歌五言四句的体制中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它用简洁凝练的语言表达了意义深刻的人生哲理,增强了它的哲理意味。吴声歌、西曲歌创造性地运用了五言四句的短小体制,文字虽然简短,但其中蕴含的情感却愈发浓重,用简明的语言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吴声歌、西曲歌
独特的艺术特征对后世的影响
南朝时期的吴声歌、西曲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以及多种文学样式的形成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南朝文人模拟乐府民歌蔚然成风,其中不少就是模仿吴歌西曲中的民歌。如谢灵运、鲍照等诗人的文集中,都有相当数量的乐府歌辞。下及唐代诗人李白、李贺等都受南朝乐府情歌的影响”[7],尤其是对文人五言诗和民间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歌西曲的艺术特征一直为世人所称道,它的修辞、体制、男女间爱情描写等都具有独特的风格,有些一直被沿袭至今,在中国文学史上、民歌史上独树一帜。
吴声歌、西曲歌五言四句的短小体制简洁精炼,清新自然,而中国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也是从此开始的。南朝后的文人诗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吴歌西曲的影子,最明显的是文人诗的体制也是五言四句,是从吴歌西曲中衍生而来并加入了后人的许多智慧。而且吴歌西曲的押韵也在其中得到了体现,文人诗的押韵在继承吴歌西曲押韵的同时也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押韵方式,使得它的结构更加完整。后代文人诗的创作者如李白、李商隐和刘禹锡等也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吴歌西曲的影响。此外,文人诗中婚姻爱情题材的诗歌也受吴歌西曲的影响比较大,吴歌西曲之后文人诗也多以爱情诗为主。作者们对爱情诗的理解在吴歌西曲的影响下不断加深,爱情的描写角度也渐渐被拓宽,爱情诗在当时风靡一时。吴歌西曲也是一种民间文学,它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文学样式,首先在民间发展起来而后才渐渐进入文人将相的视野最终进入宫廷,它反映了南朝时期民间的一些风俗习惯,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再现了南朝的现实生活。吴歌西曲通过对南朝民间生活的描写,壮大了民间文学的阵营,丰富了民间文学的样式。
参考文献:
[1]朱金涛.南朝吴声歌曲与西曲歌之综合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
[2]吴大顺.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辞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31.
[3]翟景运.南朝皇族与吴声西曲的创作与传播[J].东方丛刊,2009(1):145-158.
[4]李华颖.从民间传统到文人创作:吴歌西曲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0.
[5]余冠英.乐府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65.
[6]李博昊.论词体文学演进中对吴声西曲的容受[J].江苏社会科学,2012(3):197-201.
[7]张中秋.明清古诗选本之“吴声西曲”考论[J].中州大学学报,2008(5):6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