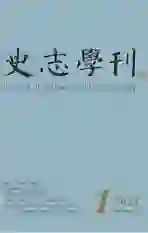司马光家庭美德教育思想研究
2021-09-10张迎春
张迎春
摘 要 司马光家训非常重视家庭美德教育。在其“正家而天下定”的家庭美德教育目的指导下,司马光把“治家莫如礼”作为家庭美德建设的核心;把德教为先、教子义方,父慈子孝、爱而不溺,约束心性、崇俭戒奢,蒙以养正、诗书传家等作为家庭美德教育内容。其家庭美德教育具有注重儒家思想熏陶、强调以惩罚辅助家庭教化、家长要率先垂范和将“圣贤”人格作为立家的人格范式等特点。司马光家庭美德教育思想的启示是:进行家庭建设要注意教化形式的多样化;家长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要通过家国同构,厚植家国情怀等。
关键词 司马光 家训 家庭美德
司马光在家训领域的代表作主要是《家范》《居家杂仪》和《训俭示康》,这些家训著作凝聚着司马光的治家智慧。在其家训中,司马光对家庭建设、子女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周详的分析与论述,体现了其家庭美德教育思想的超越时代的特征。本文拟对司马光家训的家庭美德教育思想进行研究,以期对中国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一、“正家而天下定”——家庭美德教育的目的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结构模式,强调“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正如孟子所描述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司马光继承了这种“家国一体”的政治观念。他认为进行家庭美德教育有两个目的:其一,“正家”。使家族成员各尽本分,使宗族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加强家族的凝聚力。其二,“天下定”。促进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最终巩固社会统治。
在司马光看来,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本分和职责。他引用《周易·家人》观点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彖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认为男子应该主外,女子应该主内,这是天地大义。“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认为无论是哪个家庭,父母都应是严正的君长。如果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能各尽其责,那么长幼尊卑就会各得其所,这样家庭建设就会步入正轨了。家道端正了,天下就安定了。 “正家而天下定矣”,正是司马光要建立的社会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建立离不开每个家庭成员遵守规范、恪守本分、约束自己。
二、“治家莫如礼”——家庭美德建设的核心
司马光奉行“治家莫如礼”“故治家者必以为先”。认为治家必须把“礼”放在首位,“礼”是家庭建设的核心。
司马光在《家范》卷一《治家》中引用齐国晏婴的话阐述了“礼”的内容。晏婴认为:“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司马光对此的解释是:“君令而不违, 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夫治家莫如礼。”“礼”被看作是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即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尊卑有等、长幼有序的封建人伦纲常关系。
司马光认为,治家之“礼”要从爱父母开始推及爱兄弟、爱祖宗,从爱家人推及爱亲戚、爱百姓,这样就会形成人对宗族、婚姻的依附,从而保护自己,保护家庭,保护宗族,进而保护国家。他指出:“是故圣人教之以礼,使之知父子兄弟之亲,爱其父,则知爱其兄弟矣;爱其祖,则知爱其宗族矣。如枝叶之附于根干,手足之系于身首,不可离也。”[1]学习礼,可以使人懂得个人、家庭与宗族是互相依存的,就如同枝叶对于树干、四肢对于身体,是须臾不可离的。《孝经·圣治章》曾经有“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的论断,认为爱人敬人要从敬爱自己的父母开始,这样推及兄弟、朋友以至于天下,符合这样的顺序才是正确而合理的。毫无疑问,这是司马光关于“礼”的思想的重要来源。
司马光特别重视“礼”的建设[2](P136-141),主要是因为:首先,北宋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为了重建封建宗法秩序,恢复久已涣散的伦常,加强集权统治,宋代统治者必须复兴儒学,强调伦理纲常。作为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司马光清晰地认识到加强“礼”的建设,可以使家族成员明确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建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长幼尊卑各得其所的社会秩序,这是实现“正家道”并完成教化天下目的的有效途径。其次,进入宋代以后,“庶人”队伍逐渐扩大,传统的宗法制度遇到挑战,只有积极推行“礼下庶人”,才可以强化对“庶人”的管理和约束,重建宗族制度,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居家杂仪》这部简明扼要、规范严格的封建家庭礼法读本就是司马光在对古礼进行修正的基础上,赋予其时代内涵修撰而成。该篇细致、严格规定了居家生活的礼节,涉及家庭成员的角色定位、行为准则、惩戒方式和对子女教育方法,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子女构建“父慈子孝”的社会关系。
为了让子女能学到“礼”的规范和要求,司马光把治家中的榜样、典范的人和事例收集起来,写成《家范》,供后代学习、效仿。正如他所说:“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降及后世,爰自卿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为人法者,今采集以为《家范》。”[1]这正是《家范》被历代推崇为家教范本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家庭美德教育思想的内容
(一)德教为先,教子义方
司马光认为,要对子女进行“礼”的教育,就要“教子义方”。所谓“义方”,就是做人行事的规范,“教子义方”就是对子女进行伦理教化。他借石碏之语说“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他又说“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1]。他认為用正确的礼法对孩子进行教导和约束,可以避免孩子误入歧途。人之所以会产生骄傲、奢侈、淫荡、逸乐这些不良品德都是由于宠爱和物质给予过多所致。
司马光认为教导孩子要注意“夫爱之,当教之使成人”。要处理好爱和教之间的关系,要爱而有教。他认为,历史上因为只爱不教使孩子陷于危亡状态的家长不在少数。他说:“自古知爱子不知教,使至于危辱乱亡者,可胜数哉!夫爱之,当教之使成人。爱之而使陷于危辱乱亡,乌在其能爱子也?”[1]从历史角度警示人们对孩子不能只知疼爱不知教育,否则只能害人害己。
司马光主张教导孩子要注意“宠禄过也”,要处理好“遗之以德”与“遗之以财”的关系。他认为,人所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是必不可少的,但一定“勿求多余”, 否则就会成为人生拖累。他明确说明积累财富留给子孙后代的行为是十分愚蠢的,为子孙积攒过多的物质遗产将会后患无穷。《家范》卷二《祖》中,他强调“若其不贤耶,虽积金满堂,奚益哉”“多以遗子孙,吾见其愚之甚也”。“圣贤之人”要“遗子孙以德以礼”“遗子孙以廉以俭” 。
司马光发现人到老年因为对孩子有无限热爱,都会想着为子孙后代谋利益,但能真的对子孙有益处的,却是极少的。“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2]。如果尽一切努力为子孙积攒土地、房产、粮食、金银财宝,“田畴连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麦盈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施施然,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2],企图使子孙后代吃不完、花不尽。然而结果却是“而子孙于时岁之间,奢靡游荡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娱;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虐之也”[2]。积累的物质财富很快就被子孙挥霍殆尽,甚至还不念祖辈的好,反而埋怨、虐待祖辈,“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2]。因此,在司马光看来,聚敛资财遗子孙,只能养成子孙骄奢淫逸、不思进取,结果只能是贻害子孙。
司马光认为要教育好孩子就必须对失德者进行严厉谴责, “则为人而怠于德,是忘其祖也,岂不重哉”[3],认为后辈骄奢淫逸、挥霍浪费,是忘记祖宗、辱没祖宗的行为。
(二)父慈子孝,爱而不溺
中国很早就有“父慈子孝”的家庭美德。《管子·形势解》中有“慈者,父母之高行也”的论断。《礼记·大学》强调“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强调“父慈子孝”。在这里“慈”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爱,二是教。既包括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也包括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主张对其进行良好品行的教育。司马光继承了古代先贤关于“慈”的认识,对“慈”进行了全面的阐发和论述。
司马光认为爱孩子就应该慈爱有度、爱而不溺,使他顺利成长,这是对“慈”的基本要求。只爱不教是溺爱,溺爱会让孩子陷进危亡、羞辱和惑乱之中。他说“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1],他认为爱孩子就要做到慈爱有度,爱而不溺 。他举例论证说“梁元帝时有一学士, 聪敏有才,为父所宠,失于教义”“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语不择,为周逖抽肠衅鼓云”[1]。告诫人们,一味溺爱却不知教导子女,只知宣扬子女的长处,对子女的过错百般掩饰的做法,到头来反而是贻害了孩子。他告诫人们“慈母败子”。对子女,“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1]。
司马光认为爱孩子就要威严有慈,教子有方。由于父母对子女的爱是自然的、无私的,这就导致父母对孩子的爱常常当着孩子的面过分表现出来。父母应将这份爱掩藏起来,在子女面前表现出严肃的样子,即“父子之严”。他说“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要“常以严庄莅之,不以辞色悦之也”[1]。这样的话“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1]。因为父亲对于子女的关系不庄重、不慎重,就会导致孩子的不恭敬、不孝顺。
司马光认为爱孩子要以孝义为先、大义凛然,当孩子遇到生死大义的关头要舍生取义。为人母亲,她不仅要抚养儿子平安长大,还应当培养他的孝义品德,即“非徒鞠育其身使不罹水火”“又当养其德使不入于邪恶,乃可谓之慈矣”[1]。爱孩子就要督促训导,矫枉处罚。为了教导孩子成才,可以用“楚挞惨其肌肤”“汤药针艾救之”这些惩罚方法。“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于呵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耳。当以疾病为谕,安得不用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于骨肉乎?诚不得已也!” [1]
司马光认为父母于孩子施以慈爱是自然的,儿女对父母尽以孝心则是必须的。“不孝不慈,其罪均也”[1],认为不慈和不孝都是不道德的。从物质上侍奉、赡养父母,这是孝最基本含义。《尔雅》说“善事父母曰孝”,司马光继承了这一思想。司马光对孝子侍奉父母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提出基本要求。“子事父母,鸡初鸣而起,左右佩服,以适父母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卒,受巾。問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2]要对父母问寒问暖,了解父母的身体状况,及时为父母解除病痛。要随时询问父母的所需,满足父母的要求,不仅要周到、细致,而且要态度温和。
《居家杂仪》中,司马光引用《礼记·内则》的观点提出:“凡人事父母,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终养之。”认为孝子赡养老人,就是要满足父母生活需要,要用好的饮食尽心地奉养他,让他能够安居,使他心情愉快,不违背他的心愿。总之,“事父母,能竭其力”,就达到了养亲的标准。
司马光引用孔子的话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强调对于父母来说,除了物质的供养之外,还要做到敬重父母。
敬重父母就要懂得他们的感受,不能让父母替自己担心着急,要让他们开心快乐。《家范》开篇就引用《孝经》中的理论,强调孝子敬养父母就要做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要时时刻刻考虑父母的感受。《居家杂仪》要求“凡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就是为了避免父母为自己担心。“凡子事父母,父母所爱,亦当爱之;所敬,亦当敬之”,则主要是强调让父母处在开心快乐的状态。
敬重父母就要注意顺从他们。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强调:“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记而佩之,时省而速行之。事毕则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则和色柔声,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许,然后改之。若不许,苟于事无大害者,亦当曲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己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况未必是乎!” 凡是父母命令自己做的事,就必须不折不扣地去完成,并要把事情的结果及时向父母禀报。即使父母吩咐的事情是有错,做子女的也不能自作主张,否则就称不上孝顺。
敬重父母还要注意及时提醒劝谏他们。父母也会犯错,但父母犯错提醒劝谏时要注意气色和悦,态度恭顺,声音轻柔。《居家杂仪》认为“凡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即便是劝谏不成,也不必着急怨恨,要做到态度柔顺,要不急不怨。“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不悦,与其得罪於乡党州闾,宁熟谏。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三)崇俭戒奢,约束心性
《论语·里仁》篇,孔子曾有“以约失之者鲜矣”的论断,认为因为俭约而导致犯错误的事情是比较少见的。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司马光秉承了孔子的这一观点,认为要保证家庭或家族的长久兴盛,就必须提倡节俭,崇俭戒奢。
《居家杂仪》的开篇里,司马光就强调治家的原则在于“量入为出”“禁止奢侈”。他说:“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费,禁止奢华,常稍存盈馀,以备不虞。”
司马光生活的时代,“众人皆以奢靡为荣”,讲排场、比阔气成为了一种风尚。“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甚至当差的大都穿士人的衣服,农夫穿丝织品做的鞋,人们对物品的使用超过了它的功能所在,导致了物品的严重浪费,司马光很为之痛心。在《训俭示康》一文中他感叹:“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嗟乎!风俗颓敝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认为节俭还是奢侈,这关系到人生的成败得失,应教育孩子崇尚节俭。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认为减少欲望是修养内心最好的办法,因为寡欲可以滋养仁义礼等伦理规范,“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1]。司马光继承了孟子的这一思想,进一步阐发了欲望的多寡在修身与节俭之间的作用。他认为节俭之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过多的物欲,自然就可以减少外在的物质利益对道德本心的诱惑。精神上的寡欲可以变成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节俭和节用行为。《训俭示康》认为:“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在日常生活中秉承寡欲,就意味着不过多索取,就可以在心理上加强对物欲的控制,因而就可以约束自己不违法、不背德。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引用御孙的观点,他认为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各种好品德的共有特点,奢侈是各种罪恶中的大罪。司马光告诫孩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强调要成为一个有德之人,就要把生活节俭、克制欲望、不贪慕奢华当作修身的内容,并能发扬光大。他告诫司马康“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强调不仅仅是自身实行节俭,还应当用节俭来教导子孙,使他们了解前辈的作风,将节俭作为家训世代相传,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好家庭美德建设,最终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四)蒙以养正,诗书传家
中国自古就有“养正于蒙”的传统,主张孩子的教育要及早进行。司马光继承了先贤的这一思想。在《家范》卷三《父》中,他对西汉时期贾谊“赤子而教”和《颜氏家训》中“教妇初来,教儿婴孩”大加赞赏。《家范》卷三《母》中他列举了周文王之母重视胎教的例子,之后评论说“彼其子尚未生也,故已教之,况已生乎”,强调教导孩子要从他们幼年时及早进行。他深刻揭露批评当时流行的社会现象:“人之爱其子者,多曰:‘儿幼未有知耳,俟其长而教之。’”认为这如同“犹养恶木之萌芽”,如同种了一棵刚长芽的坏树,等它长得粗大后再去砍伐,如同鸟放走了再去捕捉,松了缰绳把马放走再去追逐,这是贻误时机,终将劳而无功。
《居家杂仪》中,司马光参照《礼记·内则》设计了一套教子规程。他说:“子能食,饲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万福、安置。稍有知,则教之以恭敬尊长。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六岁,教之数与方名。男子始习书字,女子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自七岁以下,谓之孺子,早寝晏起,食无时。八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以谦让。男子诵《尚书》,女子不出中门。九岁,男子诵《春秋》及诸史,始之为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十岁,男子出就外傅,宿于外……”
司马光给孩子设计的教育内容丰富而完整,包括道德教育、生活和文化知识教育、礼仪教育等诸多方面。他强调要恭敬尊长、教之以谦让,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要读《春秋》及诸史,通晓其中的“义理”,并强调“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肯定“养正以蒙”并不反对用“诃责”的办法。
司马光认为女子必须接受教育,这是女子遵守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些礼仪德行的基础。《家范》卷六《女》中司马光说:“凡人,不学则不知礼义。不知礼义,则善恶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识也。于是乎有身为暴乱而不自知其非也,祸辱将及而不知其危也。然则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根据司马光的认识,首先强调人人都必须接受教育,不论男女。否则就不会懂得礼仪德行,这样是很危险的。马光所处时代,盛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不必才明绝艺”的观念,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司马光在引用曹大家《女戒》中的一段话略窥一斑:“今之君子徒知训其男,检其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教乎?”可见女子是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的。司马光对女子接受教育持肯定态度,并大加提倡。他认为,女子要读书,特别是要读儒家经典,这样的话就会在遇到杀身之祸时保全自己。提倡女子读书在当时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
四、司马光家训家庭美德教育思想的特点
(一)把家训作为古代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载体
司马光把家庭看作家族子弟品格养成的重要场所,其家训就带有传播社会主流规范的意蕴。在其家训中,无论是勉励子孙为学修养还是立身处世,都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子弟进行熏陶的理念。
首先,给家族子弟进行教育时所选的内容完全是儒家经典,如《易上》《易下》《礼记》《孝经》《大学》《论语》《孟子》等,内容闳阔精微。
其次,家族子弟必须遵守的行为礼仪都是按照儒家所宣传的纲常礼教设计的。《家范》中涉及了祖、父、母等18种家庭成员的行为礼仪;《居家杂仪》作为一部简明实用封建大家庭的居家日常礼节范式,都是宣传儒家封建纲常礼教的,体现了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理念 。
第三,家庭教育实践中司马光援引的先贤古训,撰集的旧闻故事,提供效仿的典范,均是宣传儒家的纲常礼教。如曾子、颜之推的治家之道,太任的胎教之道、孟母三迁的教子典范等,都是通过儒家思想纠正防范家族子弟的不良傾向的。
以上这些都是有效实现儒家主流价值观向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的重要形式。通过这些形式司马光家训实现了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对家族子弟的不良思想倾向的预防和纠正,有效促进了人们对古代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
(二)强调以惩罚辅助家庭教化
一般来说,家训与法规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法规是刚性的话,那么家训则柔中带刚,多是在宗族内部起着规范效应。司马光在教导家族子弟的过程中,以《家范》作为法则,“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杂采史事可为法则者”“修己型家”。其治家之“礼”同时具有“法”的性质,“礼”与“法”结合 ,不仅要求家族子弟遵守《家范》规定的各种礼节和伦理纲常,同时也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居家杂仪》中规定,“凡子妇,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后怒之;若不可怒,然后笞之;屡笞而终不改,子放妇出。” 认为凡是有子女不孝顺父母的,要先教育他们;如果教育不起作用,父母就应当发怒;如果发怒也没有起作用,就笞挞他们。如果还无济于事,就要把他们赶出家门。注重劝导性教育与强制性处罚相辅相成。
《家范》卷五《子下》中强调,当子女劝谏父母,如果父母不乐意,“不悦而笞挞之流血”,即使这样,“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对其“苛虐于骨肉”“楚挞惨其肌肤”。这些处罚措施层层递进,既有身体上的惩罚,也有精神上的处罚。这种以惩罚辅助家庭教化的方式在当时对约束家族子弟、促进家庭和谐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提倡家长要率先垂范
司马光非常重视家长率先垂范的作用。与以往中国传统家庭片面要求家族子弟必须完全尊从家长不同,他主张不仅要用家训规范家族子弟的行为,也要用道德规范约束家长的行为。要求家长用实际行动遵守礼法,管理家政,教导子女,以此起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作用。
《居家杂仪》开篇司马光就对家长提出要求:“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由于父母和子女有着天然的联系,又朝夕相处,如果父母身体力行,既可以对子女起到较好的教导作用,也可以给家长以有力的约束和有效的监督。
在《家范》卷三《母》中,司马光列举了诸多母教典范。如晋陶侃“以一坩鲊遗母”,母封鲊责曰:“尔以官物遗我,乃增吾忧耳。”陶侃借工作之便,将一些腌鱼送给母亲,母亲不接受,还责备了他。又如唐朝太子少保李景让的母亲郑氏,“早寡,家贫,亲教诸子。久雨,宅后古墙颓陷,得钱满缸”。但“家贫”的郑氏却亟命奴婢“掩之”,因为“诸子学业有成”才是她的心愿。司马光对此进行了评论:“此唯患其子名不立也。”认为做母亲的只需要担心孩子不能立名就可以。
(四)以“圣人、君子”人格范式作为立家之范
司马光是通过汇集历代贤良在治家、教子方面的名言和道德故事的方式,对他的家人、子弟进行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和治家教育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家范》是一部中华古代贤良名士治家方略、治家理念的集粹。它将古代圣贤君子树为典范,使之成为家人子孙立家的人格范式,以供家人、子弟学习效法,使家族子弟在修养自己、约束自己,树立良好人格形象时有了可参考榜样。据粗略统计,仅在《家范》卷一《治家》篇中,就列举了古代的贤良名士十余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家训是非常重视利用圣贤和君子的人格形象来教育影响子女的。
五、司马光家庭美德教育思想现代启示
司马光家训的家庭美德教育的内容,在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对古代价值观的培育起了重要的作用[1](P27-3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古代核心价值观在性质上的相同之处是同为意识形态教育,二者在价值旨归上共同指向教化人心,司马光家训蕴含的家庭美德教育的内容可以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注重采用多样化的教化形式
司马光在对家族子孙进行教化活动时,运用儒家治家格言警句、历史人物典型事例介绍、道德故事以及自己的议论和阐释等多种形式,传播家族规范以及社会主流价值,使其家训更为丰富多样、活泼生动、贴近生活。这种润物无声的教化方式,可以让孩子在幼年时期就被植入家庭美德教化的内容,使他们的内心世界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性,并促进其道德修养的改善和道德境界的提升。这种家庭美德教化的形式,可以成为公民个体提升自身道德修养和建构家庭美德伦理的基本遵循。
(二)家长的言传身教、熏育感化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强调“无言而教”的教育理念。司马光非常重视家长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认为家长谨守礼法、言行一致,在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维护和构建家庭成员之间和睦关系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新时代家庭教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通过家国同构,厚植家国情怀
司马光家训非常重视家长的教化主体作用,强调家长要有修身养德、齐家治国的志向与情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国情怀。按照司马光家训的逻辑,家国情怀是在自然情感向政治情感转化、由血缘伦理向政治伦理转化过程中形成的[3](P94-96)。基于此,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就要强调家长在家庭美德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这是通过家庭美德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所在。(责编:沈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