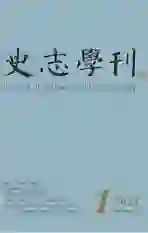论湖广总督张之洞与继任总督赵尔巽之冲突
2021-09-10史展
史展
摘 要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奉旨进京并任军机大臣前后,继任总督的人选问题颇费周折。尽管张之洞中意的继任者是吕海寰,但继任湖广总督的却是赵尔巽。张之洞本希望继任总督能“萧规曹随”,以便继续对湖北施加影响。后因赵尔巽在湖北军政和财政领域频繁安插亲信,张之洞对其日益不满,故借机上奏将其调离。张、赵冲突的背后是张之洞对经营了近二十年的湖北大本营这一政治资源的重视及控制,其根源在于晚清以降的地方主义。
关键词 张之洞 赵尔巽 湖广总督 督抚专政 晚清地方主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上谕令湖广总督(简称“鄂督”)张之洞入京觐见,慈禧太后有意召张氏入军机处(简称“入枢”)。不久后军机处变动,军机大臣林绍年出任河南巡抚,张之洞和袁世凯同时担任军机大臣,可谓丁未政潮后政局的一大变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入京后,继任者是其亲信杨士骧,而张之洞入京前后,继任鄂督人选一事纠葛颇多,最后由非张氏亲信的赵尔巽继任。后因赵尔巽在湖北安插亲信和有所更张,致使张之洞日益不满并上奏将其调离。实际上,张之洞希望继任鄂督能“萧规曹随”和遵守成规,以便其继续对湖北施加影响。以往相关研究对此有所忽视,如:李细珠教授结合丁未政局,探究了张之洞入枢前后对政局的观察、入枢的态度以及具体反应,不过对继任鄂督的问题着墨不多[1](P297-304);谢未渊关注到张之洞拟保吕海寰继任鄂督,却未深入探讨[2](P14);张浩威注意到赵尔巽调离鄂督与张之洞有很大关系,但未详究其因[3](P49-50)。本文结合张之洞入枢的政局背景,详细梳理张之洞与继任鄂督赵尔巽之间冲突的过程,重新审视冲突的背后原因,即张之洞对经营多年的湖北的重视和控制,以此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力和地位,揭示并阐释导致冲突的背后根源——晚清的地方主义。
一、张之洞入枢与继任鄂督人选
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以来,丁未政潮中的瞿鸿禨和岑春煊一方逐渐失利,七月初军机大臣林绍年又出任河南巡抚,使得军机处发生变动,慈禧太后也借此先后召总督张之洞和袁世凯进京。同时经营湖北近二十载的张之洞也在斟酌鄂督的继任问题。与袁世凯入枢后由其亲信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不同,张之洞入枢前后,关于继任鄂督人选的周折颇多。
(一)丁未政潮后张之洞入枢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初一日慈禧太后驻跸颐和园乐寿堂,光绪帝驻跸颐和园玉澜堂[1](P473、474)。据盛宣怀在京坐探陶湘的密报,初二日下午慈禧太后借口“初一夜电灯出险”召见领班军机大臣庆王奕劻、军机大臣世续和电灯总办,而光绪帝并不在场。名为电灯事而实涉及枢府,但其中“所议甚密”。关于此次密议,坐探陶湘仅探知:“慈圣议政府,领袖首举岑,慈摇首;继言雪公,慈又默然;终言曲江,慈脱口而言曰:‘此人大可。’又云:‘甚妥。’即时廷召曲江。”[2](P64)其中“慈”指慈禧太后,“政府”指军机处,“领袖”指奕劻[3],“岑”指岑春煊,“雪公”指袁世凯[4],“曲江”指张之洞[5]。据同日军机处电传上谕,召张之洞迅速来京陛见,并有面询事宜[6](P178)。慈禧太后召见张之洞,是借进京面询之机打算召张之洞入枢。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军机大臣除奕劻、世续和资历较浅的林绍年和醇亲王载沣外,还有资历较深的鹿传霖。关于召张之洞入枢之事,鹿传霖甚至是从世续处探知的。可见此次奏对并未召见军机大臣且资历较老的鹿传霖,背后原因值得玩味:鹿、张两人为姻亲,鹿传霖为张之洞姊丈,慈禧太后担心张之洞入枢以及鄂督的继任人选等事,会经鹿传霖走漏风声,故此举实有避嫌之意。初四日,在天津的坐探张寿龄密告张之洞:“上意拟招中堂入枢,恐难辞。”同日在京坐探齐耀珊亦告知张之洞:“军机未放人,佥谓慈圣眷注中堂也。”初十日,军机大臣鹿传霖将从世续口中所探的“慈圣微露召公入枢意”密告張之洞[7](P299-300)。这更加证明了陶湘所言非虚。
早在七月初三日,身在天津的袁世凯便已得知相关消息,且致电两江总督端方:“闻召南皮已定议,日内即发表。代者为次珊,恐未易辞也。”[8](P394)次珊即赵尔巽[9]。此时袁世凯已提前得知内定赵尔巽继任鄂督。揆诸慈禧太后召见奕劻和世续商议军机大臣事,既然涉及张之洞入枢一事,自然也就会考虑鄂督由谁继任。时在场大臣只有奕劻和世续,且奕劻已提议张之洞入枢,想必慈禧太后也会顺便询问继任鄂督的人选。事后奕劻便将赵尔巽出任鄂督的消息透露给袁世凯,后袁氏于初三日再电告端方。不久后,张之洞已经得知入京的消息,却“深惧入内棘手,且不肯脱离汉皋,一面迟迟乎行,一面拉雪公”[10](P64)。鉴于瞿鸿禨在政潮中的遭遇及此前自己入枢败北的经历,张之洞谨慎行事并试探政敌袁世凯。袁世凯曾在致端方的电报中感叹道:“近来事话,非宣示不能作定也。”[11](P369)自丁未瞿、岑败北后,草木皆兵,不仅是张之洞,连袁世凯也谨小慎微,称病观望。关于张之洞观望的政治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张之洞担心此次进京入枢再遭失败,故以待入枢谕旨下达后方可动身,以求稳妥;另一方面则是张之洞正在考虑继任鄂督的人选问题。张之洞经营湖北多年,视之为大本营,是决不会轻易将湖北之事托付给不信任者。
(二)继任鄂督的人选问题
据坐探陶湘观察,张之洞观望之举的背后原因是“湖北事不便遽易生手”[12](P65),实际上是在考虑鄂督的继任人选。当鹿传霖从世续处探得慈禧太后表露出要召张之洞入枢的意愿后,初十日便致电张之洞,并建议继任鄂督人选:“鄙见宜择替人,如举不避亲,浙抚当可遵守成规,请密筹备。”[1](P300)从此处可以获取两个信息:一是鹿传霖在得知张之洞入枢后,主动向其提议继任鄂督人选,也是在迎合张之洞的心思。与将要离任的总督私下商议继任总督人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晚清的地方主义色彩,即身处督抚专权之政治生态中的张之洞难免染指继任总督人选。二是鹿传霖所举荐的继任者是浙抚张曾敭,此人系张之洞同族侄曾孙。张曾敭为官政绩平平,若继任鄂督,必如鹿传霖所言能“遵守成规”,这想必也暗合张之洞的心意。荐举族亲张曾敭本就容易招引非议,更不遂人愿的是因秋瑾案而身处舆论的风口浪尖,为官谨慎的张之洞不免考虑其他人选。据陶湘密报,张之洞心目中已有人选:“拟保莱州督武昌。”“莱州”即吕海寰。时任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的吕海寰虽与袁世凯交恶,却与张之洞关系匪浅,况且张之洞此时并无其他合适人选,吕海寰确为最佳人选。然事与愿违,清廷任命赵尔巽继任鄂督。张之洞的观望使得袁世凯捷足先登:“今竟放天水,则可征曲江手段远不如雪公。”[2](P65)“竟放天水”指的是七月二十八日赵尔巽调任鄂督[3](P177)。前文提及,尽管内定赵尔巽继任鄂督,不过尚未宣示,仍有回旋的余地。由于张之洞犹豫观望,没有即刻起身入京,一定程度上也错失了面奏继任鄂督的最佳时机。既然袁世凯得知清廷有意任命赵尔巽出任鄂督,便会在入京后的面奏中保荐并非张之洞亲信的赵尔巽。据《梦蕉亭杂记》载:后来张之洞对继任赵尔巽感到不满,散值后向袁世凯抱怨,时陈夔龙亦在侧,袁世凯只好嘱托回乡扫墓的陈夔龙路过武昌时传话给赵尔巽:“文襄所办兴学、练兵、理财、用人各大端,极宜萧规曹随,不可妄行更易。”[4](P117、118)由上观之,赵尔巽出任鄂督极有可能经过了袁世凯的举荐,不然张之洞不会平白无故地向袁氏抱怨,袁氏也不会委托陈夔龙传话给赵尔巽。此时报端也刊载袁氏曾向奕劻保荐过赵尔巽[5]。赵尔巽并非袁氏亲信,袁氏保荐赵尔巽出任鄂督不过是顺应圣意的折衷之策。总之,袁世凯在赵尔巽出任鄂督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此外,高阳先生认为:“湖广总督出缺时,四川总督亦缺人未补,由赵尔巽之弟赵尔丰以川滇边务大臣护理,此时以赵尔巽调补;赵尔巽可能想为赵尔丰制造真除的机会,不愿赴任,遂改调湖广。”[6](P245)实际上,在张之洞入枢以致鄂督出缺前,清廷早已于三月二十一日下令将赵尔巽调往四川任总督,在此期间其一直没有到任。关于赵尔巽一直不愿赴任川督一事,与其谋求新职有密切关系。光绪三十三年二月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因病去世后,尚书一职空缺,故离任奉天的赵尔巽有谋求邮传部尚书之举动。此时亦传言清廷内定赵尔巽为邮传部尚书,但尚未宣布。留京期间,赵尔巽在谋求邮传部未果后,又有调任度支部尚书之传闻。无论赵尔巽是否谋求邮传部或度支部尚书,仅以其留京之举观之,定有谋求新职之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赵尔巽与后任徐世昌之间就奉天交接事宜产生过不小的矛盾。赵尔巽原为盛京将军,后因东三省改制裁撤盛京将军,由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主政东三省。当赵尔巽离开奉天,与后任徐世昌交接时,曾交给后者六百多万白银。后赵尔巽入京扬言:“政府亦以为既有六百数十万,似亦可不借外债。”然徐世昌予以否认:“止有二百万,尚短四百数十万。”[7](P52、61、67)于是徐世昌挟私报复,上奏弹劾奉天财政局,将赵尔巽的亲信奉天财政局总办史念祖、会办叶景葵和金还等十九名人员一并弹劾[1],并勒令叶景葵、金还等赴奉天清厘交代。愤愤不平的赵尔巽将此事告知袁世凯:“我确有六百数十万,且可将我解回奉,与后任清算。”关于赵尔巽的辩解,由陶湘给盛宣怀的密报中所提及的“群称其糊涂,刻已调两湖,然亦受影响矣”[2](P67),可知赵尔巽调任湖广,多少也受到此事的牵连。正如《大公报》中的评论所言:“赵尔巽曷为而得湖广?有排之者。”[3]赵尔巽是在京城谋求邮传部尚书等未果后,才接受了鄂督的任命。
当赵尔巽职掌湖北成为定局后,张之洞也准备启程进京。八月初一日子时,张之洞急电赵尔巽,除恭喜荣调湖广外,并询问其是否陛见和“何日起节来鄂”,“亟思详谈,是否在京晤面”[4](P737)。初二日,張之洞从武昌启程北上,后路过河南郾城时再次致电赵尔巽,并告知自己的行程,又因“拟请教之事甚多”,故希望赵尔巽在京暂住数日以便前去请教[5](P1)。可见事先张之洞并未预料到赵尔巽会出任鄂督,所以事后急切希望能与之在京会面,想必所谈事宜不外乎鄂督交接之事。后赵尔巽于九月初三日出京入鄂,抵达武昌[6],开始执掌湖广。
二、继任鄂督赵尔巽频繁安插亲信
对赵尔巽而言,继任鄂督并非出自本愿,但并不妨碍其走马上任。作为清末颇具能力的封疆大吏,赵尔巽在东三省的改革有声有色,此次在湖北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有所更张,在财政和军队领域频频安插亲信。
(一)起用被弹劾的亲信任职湖北
上文提及在奉天财政局案中遭到弹劾的史念祖、叶景葵和金还等人,均系赵尔巽亲信。在赵尔巽任盛京将军时,史念祖为奉天财政局督办,后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所弹劾而罢官,而赵尔巽极力为之开脱。叶景葵和金还曾为奉天财政局会办,皆为赵尔巽亲信。赵尔巽抚晋时,招叶景葵为内书记,并委任金还。后赵尔巽调任湘抚,奏调金还委充文案,叶景葵也跟随赴湘。赵尔巽升盛京将军,调叶景葵为总办文案,金还委充文案总办。
任鄂督后不久,赵尔巽便上奏起用被罢职的亲信史念祖、叶景葵和金还等人:“奉省此次被议人员,其中不乏可用之才,前经奴才面奏,蒙恩准调往湖北差委毋庸赴奉等因……俟檄调各员到鄂后,再行分别奏留,谨附片陈明。”[7]此奏折中所言“面奏”在赵尔巽调任鄂督后尚在京师期间,为八月初一日到九月初二日之间。在奉天财政局被参后仅一月左右,赵尔巽便上奏清廷,希冀起用被弹劾的亲信并调往湖北,奉天财政局参案中的二十位被参人员,除了史念祖已经加恩外,叶景葵、金还、周肇祥等九员“先后到省,委充各差,数月以来,益矢慎勤,无渝初志,分理数绩,深资臂助”[8]。相关事件也见诸报章:“闻赵次帅到湖广任所,再为奏调史绳之都护襄办鄂省事宜。”[1]可见赵尔巽多次想起用被弹劾的史念祖,并希望将其调往湖北。另据顾廷龙的《叶公揆初行状》:“嗣尔巽总督湖广,复折简相招,(叶景葵)先至郑州省亲,南下至汉阳,维格邀寓铁厂,导观新式炼铁炉,讨论相得。”[2](P544)可见赵尔巽的确任用了被弹劾罢职的财政官员叶景葵。
此外,赵尔巽还上奏将革职的好友朱钟琪“调湖北差委补用”[3]。朱钟琪不仅是赵尔巽的胞弟赵尔萃的把兄弟,还是叶景葵的岳父。据《叶公揆初行状》记载:光绪壬辰年正月,叶景葵“续娶朱夫人”,“夫人父朱钟琪,与庚及赵尔萃为义兄弟,同官济南”[4](P542)。可见朱钟琪与赵尔巽、叶景葵之间关系相当密切,非同一般。赵尔巽将朱钟琪调往湖北委用,显然也是在安插亲信。
(二)在军队中安插亲信黄忠浩
在湖北新军中,张之洞最信任的是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到达武昌后仅十日,赵尔巽便任用亲信黄忠浩,甚至危及张彪的地位:“鄂督赵尔巽奏调狼山镇总兵黄忠浩到鄂差遣,拟畀以陆军第八镇统制之任,以继张彪后。时黄就医在汉,赵督谕其即回皖交代,迅速来鄂。”[5]黄忠浩早年曾追随张之洞,后“因其军中颇多自立军骨干”而遭到株连。张之洞为摆脱干系,下令将所募兵勇驱散,并调黄忠浩驻湖北新堤以戴罪立功。此后,黄忠浩逐渐追随赵尔巽。当赵尔巽任湖南巡抚时,黄忠浩应赵尔巽邀请总理全省营务,并一度担任湖南教育会会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当赵尔巽离鄂督川时,黄忠浩去职回湘。同年又应赵尔巽邀,担任“四川兵备、教练两处总办,兼督练公所总参议”,并升任四川提督。宣统三年(1911),当赵尔巽离川赴奉时,黄忠浩再次回湘[6](P561、562)。由上可知,黄忠浩多年追随赵尔巽,确为其亲信。可见在督鄂后不久,赵尔巽便打算调任亲信并安插于军队之中。
实际上,黄忠浩并未代替张彪担任新军第八镇统制,而是“领湖北全省巡防军兼统荆襄水师”[7](P562)。后来赵尔巽仍试图继续委黄忠浩以重任:“湖广总督赵制军电告陆军部铁尚书云:湖北陆军定额两镇,除张彪统辖业有成效外,拟再添练一镇,以符定额,并电请以前奏调之总兵黄忠浩为全军统制。”[8]可见赵尔巽在鄂督任上,计划在原有一镇新军的基础上再添练一镇,并打算任命亲信黄忠浩担任此镇新军的统制,这必定会导致湖北军政格局产生巨大变动。
由此可见,赵尔巽并非如慈禧太后所希望的那样,步张之洞之后尘,效萧规之曹随:“二十六日湖广总督赵尔巽请训出京,奉皇太后训谕云:鄂省当水陆交冲之区,匪党潜滋,外轮络绎,安内和外均为重要,所有一切新政事宜,均按照张之洞规画办理云云。”[9]而是有所更张,“赵尔巽之督两湖不过数月,方思有所更张,不欲以萧规曹随者贻讥当世”[10]。至少在财政和军队领域,赵尔巽皆有所动作,频繁安插亲信。
三、张之洞的不满与赵尔巽离鄂
赵尔巽在湖北频繁安插亲信,致使前任鄂督张之洞对赵尔巽在湖北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因赵氏并非张之洞所中意的鄂督人选,入枢后的张之洞便上奏将赵氏调离湖北。
(一)张之洞对赵尔巽的不满
张之洞历来注重士兵的文化素质,但在他离开湖北后不久,就有协统王得胜、刘温玉等人禀告赵尔巽,请求以后湖北“添招新兵,不用读书人”。对于此事,张之洞在致张彪的电报中表示“殊属可骇”[1](P52)。受史料所限,尚不知赵尔巽是否同意此建议。不过,从对此事巨大反应和希望张彪速来电报可以看出,离开湖北四个月后的张之洞仍注意湖北之事,故其对赵尔巽调任财政人员和军事将领的举动就更为关注了。上文提及,在京之时张之洞曾与赵尔巽会面:“新任鄂督赵次帅日昨与张相国面唔,谈议许久。相国询及次帅启程之日期,次帅答以约在节后。又闻相国谈及史都护,曾云史某颇有胆量,惜无学术以济之,故动辄得咎云。”[2]“史都护”即史念祖。张之洞用人一向很注重官员的品行与出身,故其对出身行伍且数次被参的史念祖印象不佳亦在情理之中。且因自立军一事,张之洞对黄忠浩也存有争议。然而赵尔巽却试图调用史念祖和黄忠浩等人,可想而知张之洞对赵尔巽的不满并非空穴来风。据胡思敬在《国闻备乘》所言:“赵尔巽初莅任,易一财政局总办,之洞以未先关白,大怒。”[3](P112)当然,胡思敬所言赵尔巽易财政局总办一事,尚无史料证明为何人。如前文所述,赵尔巽的确有所更改:面奏原奉天财政局被参人员调赴湖北差委,并获得清廷恩准[4],又在军队中安插亲信黄忠浩,调用财政人员朱钟琪等。不言而喻,以上举动均会引起张之洞的不满。
在此期间,赵尔巽的另一举动也会加重张之洞的不满。清末清廷铸造银元,有一两和七钱二分之争。参与论争的张之洞一直主张铸造一两银币作为通国货币,并多次力争。此时赵尔巽明确支持七钱二分方案,反对张之洞的主张:“查各省已铸之银元,七钱二分者也。户部银行及各省官钱局发行之钞票,亦七钱二分者也。今改铸一两,银元如收回另铸,既恐无此财力,若流行市面,则有两种银币,断无此制……以上各节,系以七钱二分与一两者相比,利弊较然,所有铸造银主币之重量,拟请以七钱二分为断……大学士张之洞会奏,主持一两之说。若廷议照准,似须俟中国度量权衡画一以后,方可施行。”[5](P363-366)可见赵尔巽针对的是张之洞的方案,此举必会遭到张之洞的反对与不满。
据《梦蕉亭杂记》记载:陈夔龙由江苏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后并来京陛见,时“文襄适以鄂督内召入直枢廷,与继任某制军臭味差池,颇思易人而治。”此时同在京师的张之洞曾三次会见陈夔龙,委婉地表示希望陈夔龙担任鄂督,又流露出对继任鄂督赵尔巽的不满。尤其在第二次见面时,袁世凯也在场,“文襄拂然对项城曰:君言我所办湖北新政,后任决不敢改作。试观今日鄂督所陈奏各节,其意何居?且其奏调各员,均非其选,不恤将我廿余年经营缔造诸政策,一力推翻。”关于张之洞希望陈能接任鄂督一事,而陈夔龙是“漫而应之”,并匆匆乘京汉火车而去[1](P117、118)。《梦蕉亭杂记》可信度较高,何况陈夔龙正是当事者。据陈夔龙所言,赵尔巽不仅调用自己的亲信,且将张之洞在湖北经营之政策一力推翻。可见张之洞不满赵尔巽并非事出无因,也不是朝夕之事。
(二)赵尔巽离鄂与陈夔龙督鄂
即便是已经离开湖北,张之洞仍重视曾职掌近二十载的湖北,此举背后涉及晚清的地方主义。未做到“萧规曹随”的赵尔巽在湖北难以长久立足:“(朝廷)所用之人无非为人择地,而无丝毫为地方谋公益之心。其甚者如赵尔巽之督两湖不过数月,方思有所更张,不欲以萧规曹随者贻讥当世,则迁调之惟恐不速。”[2]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也言及此事:张之洞对赵尔巽不满,将其“迁四川而改用陈夔龙”[3](P112)。
赵尔巽本非张之洞中意的鄂督人选,加之其在湖北频繁任用亲信,张之洞已经不满于赵尔巽的种种作为,甚至希望“易人而治”。此时赵尔巽胞弟赵尔丰的上奏恰好为张之洞提供了一个契机。时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上奏清廷:“藏与川相为表里,一切筹兵、筹饷,责在川督。总督与边务大臣休戚相关,源源接济,藏事自易奏效,否则无从办理。”赵尔丰意在清廷任命与自己关系密切和休戚与共的川督,而新任川督陈夔龙与赵尔丰并不熟识。时西藏边境危机加深,故张之洞抓住时机,希望将赵尔巽与陈夔龙互调,并上奏力陈:“边务大臣之意,恐川督非所素识,不肯为力。查鄂督与该大臣系胞兄弟,合办川藏事宜,公义私情,更责无旁贷。不如将鄂川两督,互相调补。”[1](P118)而张之洞之所以能将赵尔巽调离湖北,原因是此时张之洞身为枢臣,便于面陈地方事宜。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四日,清廷降旨令鄂督赵尔巽调补川督,鄂督由陈夔龙调补[4](P23)。继赵尔巽之后任鄂督的是陈夔龙。
关于张之洞为何希望陈夔龙出任鄂督,原因有二:一方面是不满于赵尔巽在督鄂期间培植私人的行为,前文业已详述。另一方面则是张之洞确无合适人选。陈夔龙言及自己出任鄂督并一直到张之洞去世,这是出于张之洞对其的欣赏[1](P117-119)。陈夔龙所言虽有夸大之嫌,不过张之洞希望陈氏出任鄂督的原因也值得探究。揆诸常理,陈夔龙与张之洞并无特殊关系,按理说张之洞不应该推荐陈夔龙出任鄂督。观之陈夔龙,其能力逊于赵尔巽,且幕僚亲信较少,即使出任鄂督,也决不会像赵尔巽那般大量安插亲信,更不会对以往政策有大的改动,正如后来陈夔龙所云:“余承乏二载,萧规在望,有愧曹随。”[1](P105、106)前文提及,鹿传霖在向張之洞推荐张曾敭继任鄂督时,将“遵守成规”作为择人标准之一,也是在揣度张之洞的心理,而陈夔龙确是“遵守成规”之人。此外,陈夔龙兄长陈夔麟为张之洞亲信。综合考虑,较赵尔巽而言,如果陈夔龙出任鄂督,张之洞更易继续对湖北施加影响。
實际上,在陈夔龙督鄂期间,张之洞仍然插手湖北军政。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正值陈夔龙任鄂督期间,逢安徽新军兵变,鄂军越境镇压。身在京师的张之洞时刻关注此事,并致电陈夔龙:“皖省叛兵已窜入内地,江岸防卫、安庆城守,皆非所急。鄂军越境剿贼,自应合马、步队,全力追踪痛击,方能一鼓荡平此股,剿灭他股,匪徒自不能起。若鄂省劳师费财,专代皖省弹压省城,殊为不值。鄙意亟宜迅饬王得胜统率全军并马队赶赴桐、舒一带,奋勇追剿。此时匪势尚炽,须速派数营助之。弹药一切,源源接济,尤为紧要。此事乃鄂军名誉所关,于中原大局安危,尤有关系。闻叛兵在安庆劫得库存枪两千支、弹四万颗,沿途裹胁。若不速灭,必致燎原。机不可失,盼我公成此全功。务祈裁酌速办,并发张统制阅看,至祷至祷。近日情形请电示。”[1](P9682)张之洞认为鄂军越境镇压兵变,需要一鼓作气,若专代皖省弹压省城则劳师费财,故其希望陈夔龙按照自己的计划去镇压,并请陈夔龙将计划并发自己的亲信张彪阅看,又不忘叮嘱电示最近情形。在入枢一年后,张之洞仍然关注湖北新军,为陈夔龙筹谋划策的背后是试图对湖北军政施加影响。此外,陈夔龙就军队武器管理人员的任用,主动询求张之洞的意见:“新购兵舰鱼雷,须得妥员管理……公夹袋多才,祈示一二,以便委用。”[2](P555)
在财政方面,张之洞经营湖北多年,离任时在财政上留下不少亏空,后来陈夔龙在鄂督任上,极力为之弥补。正如身为张之洞幕僚的张曾畴所言:“鄂中积亏,太邱总算一笔勾销。”[3](P38)其中“太邱”指陈夔龙。此外,张之洞时刻关注湖北财政人员的保荐与任用:“高道松如,办理鄂省财政,成绩最伟。筱帅此次保荐鄂员,似应特列荐剡,方昭公道……筱帅想早有同心。”[4](P104)“筱帅”指陈夔龙。“早有同心”也从侧面反映出陈夔龙举荐或任用的湖北财政官员暗合张之洞之意。由是观之,与赵尔巽相较,张之洞更希望陈夔龙出任鄂督,并非没有原因。较赵尔巽而言,陈夔龙更为遵守成规,张之洞便更易遥控多年经营的政治资本——湖北。
余论:冲突背后的晚清地方主义
晚清以降的地方主义,实有二源:一是咸同军兴后,在镇压太平天国等起义过程中,督抚逐渐专权,尤其是用人权、财政权和军事权,致使出现罗尔纲先生所谓“督抚专政”以及“外重内轻”之权力格局[5](P208-228)。由是观之,关于张、赵之冲突,并非私人恩怨所致,其根源是晚清的地方主义,即“督抚专政”。二是清末清廷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督抚对新军的控制和影响。当督抚缺乏对新军的节制时,新军将领的权力遂不断扩张,同时新军中革命思潮更易萌发扩散,致使督抚在军事方面多处于无权地位,而中央集权有名无实,收效甚微。正如李细珠教授所谓清末“内外皆轻”之权力格局[6](P399-411)。此背后为晚清权力格局由咸同至庚子的“外重内轻”到清末十年的“内外皆轻”之转变。“民初北洋军阀并非清末地方督抚,而多为清末新军将领”[6](P410),民国初年之军阀割据,其源头之一为清末新军,并非“督抚专政”。清末新军的地方主义,亦受晚清以来“督抚专政”之政治生态的影响,二者虽有不同,但并非完全割裂。在“内外皆轻”格局下,清廷中央和督抚都无法真正控制新军,给了以清末新军势力为代表的地方主义崛起的机会。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民初军阀割据还有另一源头,即晚清的革命党。
由上可知,“督抚专政”是张、赵冲突背后的根源。观二者之冲突,可知入枢后的张之洞对经营多年的湖北不愿轻易放手,仍视其为政治大本营,时刻关注并试图施加影响。若从后来张之洞奏请将赵尔巽调离鄂督来看,入枢后的张之洞对湖北还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在进京之前,作为地方大员,张之洞虽由清廷中央任命,但其权力更多地来源于地方,即对湖北地方上行政、财政和军事等方面的控制,然此又植根于晚清督抚专权和地方主义。当张之洞被任命为中央大员后,希冀借助继续控制和影响湖北,以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实际上,这与袁世凯希望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由亲信杨士骧继任如出一辙,袁世凯也将直隶和北洋视作大本营,希望继续施以影响,尤其是干涉直隶的新军和财政。后袁世凯得偿所愿,其亲信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正如时人胡思敬所言,“袁世凯内召,亏公帑甚多,保杨士骧为直隶总督,一切授意行之。每岁北洋供其经费,不下百万。张之洞于湖北亦然……津、鄂为袁、张外府”,可谓“狡兔之窟”[1](P112、113)。可见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张之洞,离任时均在财政上留下不少亏空,需要继任者帮其弥补,甚至供应经费,故张之洞对赵尔巽改弦之举十分不满。后来,直到陈夔龙任鄂督时,才弥补了张之洞留下的亏空。此外,在处理继任者的问题上,与袁世凯相比,张之洞还是略逊一筹。原因是清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已形成派系,并与奕劻勾结,上下其手,而身膺疆寄二十余载的张之洞,虽不乏门生故吏,却没有形成如同湘系、淮系和北洋系之类的派系。袁世凯始终遥控着北洋和直隶,即便是回籍养疴,其始终也与北洋出身的亲信保持密切联系,成为其在辛亥年得以复出的政治资本。反观张之洞,即便后来上奏将赵尔巽调离湖北,由陈夔龙补调鄂督,不过陈夔龙仍非其亲信,可见其对湖北的控制和影响有限。质言之,即便是“督抚专政”,其程度也不尽一致,袁世凯对直隶的影响远深于张之洞对湖北的影响。(责编:高生记)
Abstract In July of thirty-third year of Guangxu, after Governor Zhang Zhidong entered Beijing and became Minister of Military Aircraft, the selection of the new governor of Huguang was tortuous. Zhang Zhidong's preferred successor was Lv Haihuan, but it was Zhao Erxun in the end. Zhang Zhidong hopes the successor will follow in his footsteps, who will continue to exert influence in Hubei. Because Zhao Erxun frequently placed close relatives in Hubei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fields, Zhang Zhidong became increasingly dissatisfied with them, so he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transfer Zhao Erxun from the governor of Huguang. Behind the conflict between Zhang Zhidong and Zhao Erxun is that Zhang Zhidong's concern, control and influence on the Hubei which is the base camp has operated for nearly 20 years.The influence of loc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Zhang Zhidong Zhao Erxun the Governor of Huguang Governors authoritarian Localism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