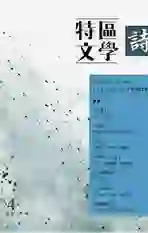写作
2021-09-10海男
海男
首先,写作这件事,并非是任何人可以热爱上的职业,也不可能是像你们想象中那样神秘。写作者的命运都是从生命中的某一天开始的,在我与农艺师的母亲居住在永胜县三川坝时,我的写作就已经开始了。但我所生活的时代,几乎看不到工业文明的影响,永胜是横断山脉中间的区境,是祖国版图中不可割离的云壤,是我的出生地、二十六岁之前的成长地。我除了从课本上、十岁以后偶遇的书籍阅读之外,在那个时期,更多的是对于自然世界和成长地外部世界的阅读和感悟,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写作早在我七岁那一年就开始了。因为,之前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只有七岁以后的生活直到今天,仍然像一部我自编自导的电影,清晰如眼前的波浪,而镜头中的主演者就是我自己。
七岁那一年我在干什么?我们居住在当时的金官公社大院内,门外有一条小河流,不宽不窄,是明代洪武年间的移民们开拓的,用此河流来灌溉良田。一条河流从五百年前穿越在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其神性中的流水使我在七岁那一年,寻找到了戏嬉的场景。我和小哥哥们经常赤脚到小河中去游玩,河水不深,刚到足踝,所以,这是一条不会危及到我们生命安全的河流。我用手去捕捉河水中的鱼虾,让它们在我手掌心中游动,再松开手指,让它们游回到卵石青苔之间去……我从那时刻就已经开始写作了,我看到了水的晶莹、鱼虾们的欢娱和自由状态。这条微不足道的河流后来竟然消失了,若干年以后,当我再次返回三川坝时,迫不及待去寻访这条河流……它消失了,在小镇的建设中消失了,因而,它成为了我的记忆。幸亏世间有记忆,否则这个世界会失去更多抚慰灵魂的东西。
七岁之后,我在假期时会陪同母亲去下乡,母亲将蚕桑养殖带到了这座坝子,所以,每一座村庄都是母亲下乡的路线。母亲戴着宽边草帽,穿着蓝色的确良衬衣,是那个时代的美人。我跟在母亲身后往前走,小鸟们在低矮的天空之上列队飞行,我几乎可以听得见它们拍击翅膀的声音。我想,我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作了,我倾听着小鳥的声音往前走时,感觉到了空气中有鸟翼的味道,这味道与田野上的庄稼融为一体。通往村庄的路会遇到许多扛着锄头、担着篮子的农人。母亲似乎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打招呼时我感觉到一种音韵,就像小鸟的叫声那样动人……因此,我相信,从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写作了。准确地说,是在时间的游移中为写作这件事在做准备。
金沙江短经永胜境内的区域是灼热的,岸上金黄色的沙岸线很漫长,在七岁时,记忆中有一桩死亡的事件:江岸之上的山坡是父母下放劳动改造的五七干校,当父母在喂猪放羊时,我们这群孩子就像一群狂野的山羊散布在山坡的橄榄树下,并以此制作出一幕幕游戏,男孩子喜欢爬到高高的橄榄树上,并晃动着树枝摇下了许多已经成熟的橄榄;女孩子则在地上拾起了橄榄并馈赠给那些干活的大人们。那一天,我们顺着铺满砾石的小路突然往江边走去……这件事是必然要呈现的,因为好几天以前一个女人失踪了。那是一个略带轻微精神病的女人。那一天,在热风扑面而来的金沙江畔,我们在江岸沙滩上发现了一具女尸,她的面目已被江水浸泡得像一只乳白色的气球。死亡突如其来,仿佛雷电击中了我们的小身体,我们掉转头就往山坡上奔跑……从那一天开始,死亡太早地在我身体中投下令人恐惧或不安的暗影。因此,我相信,从那天目睹到死亡时,我就已经开始写作了。
法国小说家尤瑟纳尔曾说过:书中所有经历死亡和悲伤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写作者是使用语言来呈现另一个世界的。人这一生面临着两个主题,那就是生与死的碰撞。而在这主题之下演化而来的均由时间所提供的场景,生活无法脱离场景,场景构成了每个人生活的世界。生命无法脱离与他人的关系,也正是他人给我们带来了叙事中的欢乐和悲伤。
记得在滇西永胜县的十七岁的我,是县城中无数彷徨少女中的一员,有着那个年龄特定的符号:像一朵微微绽放的花蕾,散发出一生中最美的气息。尽管如此,在那个黄昏,我却已经伸手把窗帘拉上,以此抵制来自二十米之外站在另一道窗户前,那个总是想窥视我的男人的目光。我在合上窗帘之后就坐在书桌前翻开了一本之前已经准备好的笔记本。事实上,之前我就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钢笔、墨水、笔记本,只是缺少勇气而已。终于,我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上了一个短篇小说的名字,然后顺着笔记本的横栏开始写上了分行的文字……在那一时刻,我发现再也听不到外面杂乱无序的声音了,也看不到窗帘外面那个站在窗口窥伺我的男人暧昧的影子了。我第一次开始了用语言建立了一个世界,它就是我写作中的小世界。
写作,必须迎来自己的一场仪式,这仪式是由写作者自己主持的,从一开始就是由自己主持,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这场仪式需要时间机缘,即灵魂出窍以后弥漫出来的一阵气息,恰巧你身置其中,不写是不可能的,只有写下第一行文字,才会延续像宇宙星宿中那些潜伏或飞翔之翼中的语词。是的,语词就是曾经绽放在你面前的一朵花的绚丽或凋亡的过程;语词就是呈现在你面前的西红柿、果酱、葡萄烈酒的味道;语词就是生死之界中关于地狱和天堂的划分和距离……语词是非常鲜活的故事以及深陷其中的人们玄妙的传说。
我写作已经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犹如梦境,留下来的只是一本本书上的痕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永胜小县城开始了写作,我待在那间只有八平方的房间中给自己平静地沏一杯茶水。写作者在开始写作之前永远需要一杯水或者一杯咖啡,我喜欢当时从烟酒茶店里买来的像方块砖形的云南茶叶。那时候的茶叶没有包装,它是裸露的,七十到八十年代的所有成形的食物饮品均将以裸露呈现在眼前:纯白色的棒棒糖是裸露的;制成方块砖的云南茶叶是裸露的;手工坊中熬制出来的红糖是祼露的;盐巴、白酒没有包装袋、没有器皿也是裸露的……这是一种停滞在贫瘠时间中的裸露。
写作之前为自己沏一杯茶水的习惯一直从八十年代延续到了今天。褐色的茶水滋养着干燥的咽喉,或许是语言的缘故,只有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书桌上,似乎才会诞生故事。所以,我写了三十多年的文字,同时也喝了三十多年的茶水。多年以后,我的足迹终于来到了云南的茶山,从保山的昌宁到永平茶山,再到临昌的风庆、双江、永德,再到普洱西双版纳的古茶山。我拜谒了在各种海拔中生长的上千年的古茶树,我从树上摘下一片绿色的茶叶放在嘴里轻轻地咀嚼着,一种生涩之后的甜香味使我品尝到了喜悦……啊,喜悦,犹如文字中缔造出的那个属于写作者的世界。
除了茶饮之外,酒也是必须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我写作跨文本散文《男人传》《女人传》《爱情传》《乡村传》的时间,也是写作时间中,为了写作生活得更为自我而纯粹的时间。在一个个写作之外的黄昏,也是我颓废感伤的时辰,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给每一间房屋都插上了玫瑰、康乃馨、百合花。通常来说,写作的房间里是必须有鲜花相伴的。在永胜写作时,我书桌上就有了花瓶,里面有四季中轮回绽放中的鲜花,从花枝中绽放的暗香使我饱受着美意的滋养。尽管如此,花瓶中无论是多么鲜艳的花朵,七八天以后就会凋亡了,我目睹了全部的残枝,默默地将它们送走,再洗干净花瓶,换上新的即将绽放的鲜花。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一个女人,如果想写作的话,除了拥有一间独立自主的房间外,书桌上一定要有你喜欢的鲜花相伴。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因为亲自插放花瓶中的鲜花,我感知到了从绚丽到枯萎的过程。啊,时间,我莫名的忧伤开始在写作中寻找到了另一些延续故事的词汇,同时还寻找到了那些仿佛从波涛中汇集到我耳边的旋律。
酒,装在瓶子里的红酒,并非是一些无生命特征的东西。喜欢上红酒,是因为我曾沿着德饮县域梅里雪山脚下的澜沧江来到了茨中村。澜沧江是除了金沙江之外,令我生命踪迹迷失其中的另外一条江。在神圣的梅里雪山脚下,澜沧江流速很缓慢,它就在你身边,而高空中的碧壤却总是会飞翔着一只或几十只黑色的兀鹫。来自地理中每一局部的现实,在我看来都是一幅画卷,它会使你敞开了触碰那幅图像的生命中的激情。没有深情燃烧的人是不适宜写作的,激情就是挟持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力量。
沿着澜沧江的羊肠小路我们寻找到了传说中的茨中教堂,它坐落在一座干燥而温暖的山坡上。云南的每一座山坡都可以搜寻到通往村舍的小路,而我们就是在那个沿澜沧江行走的午后,倾听到了神意的召唤,从而寻找到了那条通往茨中村的小路。往山坡上走去,就倾听到了来自茨中教堂的声音……山坡上种满了荞麦和葡萄树。一个拥有传说的地方,必然会诞生与传说相联系的现状。早就听说,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在百年以前沿着澜沧江行走后来到了茨中村,之后,便在这座山坡上筑造了教堂,并移植来了法国的葡萄苗,种植在茨中村的后花园中,开始酿制了红色的葡萄酒……传说是迷人的,同时也是被时间所阻隔的。在茨中村的教堂后院,我们发现了生长中的葡萄树,同时也发现了酿酒的地窖……在茨中村的村民家里,我们喝到了他们自酿的葡萄酒。之后,我就喜欢上了在写作的空隙中,给自己倒一杯红色的葡萄酒。简言之,无论是茶水、鲜花、葡萄酒,它都是我生命旅遇中的秘使,它们来到了我身边,是为了陪伴我将写作进行下去。
写作者要经历许多事、许多人、更要走许多路,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这是传统赋予写作者的说法。不错,生活的体验对写作者们来说非常重要,但为什么那些经历了众多故事的人无法成为作家呢?除了宿命之外,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写作者,他们绝对是游离于芸芸众生的另一群人。写作者与芸芸众生的区别在于,在一个俗世者看到一朵花的凋亡时,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一堆尸体而已,而写作者却从一朵玫瑰的凋零声中,倾听到了黑夜中一朵花正在秘密轮回转世的场景……
那么,如何去解决写作与现实的冲突矛盾,这或许是一个写作者终生所面对的困境之一。逃避现实是不可能的,当花瓶中的鲜花凋零以后,你必须去收拾落在书桌上的残枝,它们会使你黯然神伤。写作者不仅仅是一个人,每个写作者身边都有亲眷和社会的关系……通常来说,从写作者走出书屋的那刻开始,与你相遇的就是现实,剥离开现实是不可能的,除非你逃到没有人烟的沙漠上去写作。然而,如果真的当你来到了没有人间烟尘的沙漠写作,用不了三天,你就会因缺少水或食物,还有外在的恐惧而丧命。
写作者可以在各种旅途中写作,他们写大海,未见过海洋者,在大海出现前,曾无数次梦见过海洋的面貌,而他们一旦走近大海时,却显示出了难以言喻的安静。海洋和陆地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写作者所沉迷的纽带和距离。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生活在云南,因为高山阻隔,没有海岸线,云南却有诸多仙境般的湖泊,并将湖泊称为海。他们写孤寂,这是众多写作者们所面临的问题,写作就像一个人孤寂的旅途,延续在路上的是疲惫的影幻和手中的旅行箱。
一个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写作者,其内心已经熔炼出了三种东西。其一,他们从一开始就与语词相伴。在选择语词时,就像雀鸟在飞行中选择着在哪一座屋檐和树上筑建巢穴。这一只只巢穴就是写作者隐藏自我、呈现语词的小世界;其二,每个写作者都有一座来自黑暗的城堡,他们在其中编织着时间的密码,写一本书,意味着永不止境的在编织密码的过程中消失自己的影子;其三,写作是一条充满苦役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选择了写作,就像选择了流亡自己灵与肉的命运,他们更多的是在漫天飞舞着沙尘暴的天宇之间,去会见自己命中寻找的那个神。
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从事写作这项职业。很多人感觉到作家生活在没有人间烟火的地方。而恰恰相反,作家所置身的世界,是活生生的生活现场。作家是这样一类人,哪怕待在书房中写作时远离着外面的世界,而他们写下的每一个语词,都是呼啸而来的一场风暴。我曾在四壁林立中写作,每个字逼近笔端时,魂灵已来到了面前,写作就是与无数外在的、陌生的灵魂们相遇。在各种寒冷、温暖的气候中写作,作家在写作中所耗尽的光阴,经因那些文字的存在,而虚释了现实。
一个写作者从年少时写作,终有一天將会老去……此刻,瓶中的红玫瑰花又已经换了新颜。玫瑰花的绽放,陪同我又来到了语境中:生命因其渺茫,从而获得了大海以上的陆地,因而有触觉眼眸幻影,从而与万灵厮守,与自己的身体朝夕相处。介于两者之间,心灵获得了光阴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