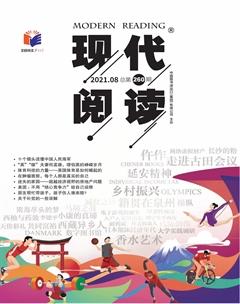1924年,列宁逝世前后
2021-09-10
1923年5月中旬,列宁在医生的陪同下来到位于莫斯科东南的哥尔克,住进一所可以看到村子的房子里。入夏时列宁的身体好转了,他可以独立上下台阶,去公园,试着拄杖行走,用左手写字。
10月18日,农业展览会闭幕前夕,列宁要求回莫斯科。他在克里姆林宫上楼来到住所,翻了翻藏书。第二天挑选了几本书和笔记本,去了人民委员会驻地和自己的办公室,在克里姆林宫院子里走了走。
1924年1月的头几天,列宁口授了给“大婶”——亚·米·卡尔梅柯娃的信,妻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信中补笔说,列宁“几乎完全好了,感觉身体不错……但还不能工作”。1月7日在大厅为附近的孩子们举办了枞树晚会,列宁也来到他们身边。但1月20日早上他没下楼来吃早饭,不想去散步,说眼睛不舒服。
米·约·阿韦尔巴赫教授不止一次给列宁会过诊,他认为从神经学角度看,列宁的眼睛完全正常,如果不算左眼先天视力差的话。他告诉亲属们,早上的不适很可能是轻度头晕引起的。
这些天待在哥爾克的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弗·戈·索凌回忆起1月21日这一天的情况:“是的,比平常略差,但仅此而已。没什么可担心的。12时(或更晚)一位大夫说,情况明显好转,‘老头这会儿睡着‘到春天一定医好他”。1月21日17时30分,列宁的状况急剧恶化,呼吸断断续续。18时50分,列宁因呼吸中枢麻痹去世。
在哥尔克管理电影放映设备的伊·尼·
哈巴罗夫描述了这一时刻:“1月21日,星期一,傍晚,我被叫到屋子里去,我以为是要谈放影片的事。走上二楼,我见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她说:‘列宁已经离开我们了……我立即意识到,世界上发生了极大的灾难。”
列宁的亲属和党中央委员晚上很晚赶到哥尔克。雕塑家谢·德·梅尔库罗夫从列宁脸上拓下石膏面模,并制作了手臂的石膏模制件。1月22日早6时,电台广播了列宁逝世的消息。
从这一天起,苏联开始了递交入党申请书的群众性活动。截止到1924年5月中旬,俄共(布)新增党员24.16万人,主要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党员人数增至78万人,每10名工人中就有一名共产党员。
1月23日一大早,亲属们、莫斯科代表团和全俄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团、附近村庄的农民到哥尔克向列宁告别。灵柩按军队礼仪移出门外,大约有5000人汇入护送灵柩的队伍。13时灵车抵达萨拉托夫(今帕韦列茨)车站,队列从那里向停放灵柩的工会大厦行进。数十万莫斯科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职员,以及来自苏联各地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汇集到这里与列宁告别。
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月26日决定将列宁去世的那一天定为苏联全国哀悼日,满足彼得格勒人民关于把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的请求,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以及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哈尔科夫、梯弗利斯、明斯克和塔什干建立列宁纪念碑。
1月27日早晨,出殡行列从圆柱大厅走向红场。一队队的莫斯科人和赶来的各代表团在列宁灵柩前通过,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
电台向世界转播了列宁葬礼的实况。在正在举行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遥远的广州,孙中山在哀辞中说:“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拏。君遘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同轨并辙……亘古如生,永怀贤哲。”
第二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给伊·费·阿尔曼德的女儿因娜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因诺奇卡:昨天我们安葬了列宁……灵柩停放在工会大厦,那儿一切都很好,庄严肃穆,不同往常。人们(有75万人)日日夜夜在灵柩前通过,瞻仰伊里奇的遗容,泣不成声……”
哥尔克的电影放映员哈巴罗夫在1924年整个冬天走遍了多莫杰多沃乡的每个村子,放映影片《列宁逝世》:“在人们的脸上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真诚的眼泪!不仅是妇女,连老大爷都放声大哭——列宁是大家都感到亲切的人。人民对列宁的爱是无穷无尽的。”
(摘自中央编译出版社《列宁生平画传:事件与回忆》 编写: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译者: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