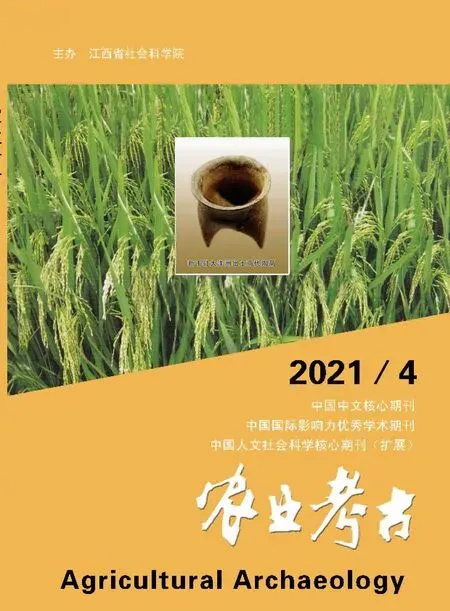本草考古:出土医药文书的历史文化考察
——以植物药为中心
2021-09-09郭幼为
王 微 郭幼为
本草考古是以考古出土的药物或药物相关遗存为研究对象,探索古代先民与药物的相互关系,复原和重建人类利用药物的历史。从广义上来讲,本草考古的目的是复原古代药物及其相关领域的文化历史,重建药物使用的生活方式,复原药物文化发展进程。出土的医药文书是本草考古的重要方面[1]。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陆续出土了一批简帛医药文书,其中有药物记载的就有二十种之多。张显成先生说,“简帛方剂、本草类文书主要存在于‘马王堆医书’‘武威医简’‘阜阳汉简’‘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其中以‘马王堆医书’中的方剂文书内容最多,其次是‘武威医简’”[2](P2)。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对出土的医药文书中药学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文字释读”“医理考证”和“临床验证”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3]。特别是对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却谷食气》《十问》等)①、《武威汉代医简》②中的药学成就,学界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张显成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便以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杂禁方》等六种)、《武威汉代医简》、阜阳汉简《万物》《居延医简》《敦煌医简》等十种简帛医书、本草文书为底本,对其中药物按“已知名”与“异名”两大类名称进行了详尽而系统的研究,“共得药名717个,凡1236见,表示420味药物”[2](P6)。21世纪以来,马继兴先生对出土亡佚古医籍进行了翔实的研究,并总结了马王堆出土医书中的药学成就[4]。张雷将里耶秦简医方、周家台秦简医方等11种秦汉简医方收集整理并结集出版,全面解读秦汉医方[5]。中国古代药物一般由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组成,其中植物药所占比重最大③,所分的小类别也最为细致,一般分为“草部”“谷部”(又称“谷豆部”)、“菜部”“果部”“木部”等五部分。比如《五十二病方》中可录出药名243种,其中植物占比达42.4%[6];阜阳汉简《万物》中所载药物不少于110种,其中保存有药名可考者约90种,其中植物药有41种[7],占比达45.6%;马继兴先生对马王堆古医书中现存的药名总数初步统计为394种,而植物类共180种,其中木类药62种、草类药87种、谷 类 药19种、菜 类 药12种[4](P278-279),占 比45.7%;《武威汉代医简》记载了100种药物,其中植物药为61种,占比达61%[8]。而为我们所熟知的传世本草典籍《神农本草经》中共有365味药,其中有草部、谷部、木部等植物药物270味,占比高达73.9%。出土文书和传世文书中有如此众多植物药,难怪有学者说,“关于药物学著作何以称之为‘本草’的问题,一般认为是由于药物的总体构成中,以植物药居多,故称之为‘本草’”[9](P128)。郑金生先生也将药、本草、植物药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统属[10](P7、P8)即中国传统药物为本草,而本草的命名很大程度是因为其中植物药占的种类最多。基于此,本文在参考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五十二病方》等十五种出土医药文书为参考底本,对其中占比最多的植物药进行考察并做一些浅陋拙见,一窥当时药物、药方形成背后的社会文化因子,进而来寻绎先民治病施药的经验信息,探寻秦汉及以前的中医药发展轨迹。
一、传承:医药文书之间互有影响,方药渊源迹象明显
对十五种出土医药文书中的植物药进行排列组合,求同存异后发现,共有59种植物药出现在至少两种出土医药文书中,其中3次以上的有25种:1.蜀椒7见;2.乌喙7见;3.桔梗7见;4.桂6见;5.细辛6见;6.姜6见;7.人参6见;8.厚朴5见;9.甘草5见;10.半夏5见;11.附子5见;12.黄芩4见;13.茯苓4见;14.皂荚3见;15.茱萸3见;16.白术3见;17.白芷3见;18.麦门冬3见;19.防风3见;20.菱3见;21.芍药3见;22.葶苈3见;23.菥蓂子3见;24.藁木3见;25.泽泻3见。如此多植物药出现在至少两方以上,可以说明医药简帛是同一时期著作或其之间存在着方药渊源。比如《里耶秦简医方》中有治令金伤毋痛方,所采用的植物药分别是辛夷、甘草和白术[5](P11)。而在《五十二病方》中亦有令金伤毋痛方(方名一样),所采用的植物药分别是辛夷、甘草和荠、术(所用药物基本一样)[2](P372)。还有《五十二病方》用甘草、桂、姜、椒进行配伍来治“诸伤”[2](P371),而在《武威汉简医方》中亦用姜、甘草、桂等配伍组成“治金疮止痛方”[5](P203-204),如表1。

表1
又如,在《里耶秦简(壹)医方》中有“病暴心痛方”,该方用菌桂等植物药来治心痛[5](P8)。在《武威汉简医方》亦有用桂来配伍成“治心腹大积上下如虫状大痛方”[5](P187)的记录④。而在《周家台秦简医方》有“去黑子方”[5](P52),其中含有稾(藁)本、桑木等植物药。在《武威汉简医方》有“治妇人膏药方”,其中的药物虽然增多但藁本(藁草)却得到了承继[5](P303、P315)。
上述情况的集中出现或可证明,《里耶秦简医方》《周家台秦简医方》《五十二病方》《武威汉简医方》等秦汉时期的简帛医书之间存在着方药渊源和用药方法理念的传承。而学者王兴伊也在考察张家界古人堤出土木牍医方“治赤谷方”和武威汉代医简的“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二方时发现,“治赤谷方”是《备急千金方》中“华佗赤散方”“赤散方”的祖方;“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是《备急千金方》中“青散”《外台秘要》中“麻黄散”的祖方[11]。这些都说明出土医药文书与传世医药典籍之间也存在着方药渊源和用药理念的传承。
二、交流:药物跨区域流动,地区间药物药方交流频繁
一些药物在不同区域的出土医药文书中出现,可推测医药文书的所在地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药(方)交流。比如在《敦煌汉简》中一些常用的植物药非当地所产,可能是朝廷中央运送过来的,药物的来源是中央辖下的所有地区[12]。“生东海池泽”[13](P170)的海藻和“生西番和昆仑”[14](P139)的阿魏也出现在该简之 中[5](P331、P356),或 可 说 明 当 时 敦 煌 与 我 国 其 他 地区甚至中国以外地区存在着广泛的药物交流。在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既有荆楚地产的厚朴、半夏、乌头、石韦等,也有产于巴蜀的蜀椒;产于西北的甘草;产于今华北地区的黄芪、防风、枣、牛膝等,则说明了当时药物或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地域交流[6]。
说麻黄和人参的传布则不仅仅只涉及药物交流了。《武威汉简》和《张家界古人堤汉代简牍医方》中出现的麻黄,学者王兴伊认为其或是在西域与洛阳大规模交流的背景下,自西域楼兰传入洛阳[15]。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麻黄的传布继而做出更为详细的考证,涉及药用植物的宗教崇拜、民族迁徙等问题[11]。由此看出,麻黄的传布涉及到药用植物的宗教崇拜、民族迁徙、汉朝时诏书颁布的验方制度等问题,它是在药用植物的宗教崇拜、民族迁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从西域楼兰传入中原,后又传到了南方地区。与麻黄情况类似,人参似乎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叶明柱等在《隋以前人参考》一文中曾言最早记录人参的文书是《神农本草经》,而成书于西汉初期的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老官山出土的《六十病方》、简书《万物》中则没有人参的记录。但我们在其他出土医药文书中找到了人参的记录,如表2:

表2
从表2可见,人参多出现在北方的出土医药文书中,而在南方则只在《张家界古人堤汉代简牍医方》的“赤散方”中有。如前述王兴伊所考证的麻黄恰恰也在“赤散方”中出现。麻黄是在药物崇拜的宗教背景下由楼兰传入到今湖南张家界地区。那么人参是否也具有相似的性质呢?前述叶明柱、叶平曾言,“人参虽位列上品,但仅作药物及墓葬神药,不作服食之品”[16]。余欣也曾对丝路遗物所见人形方术进行探姬,认为那些多用桃木做成的人形,“被用来替代死者领受罪厄罚谪,替生者解除殃祸注咎,同时还可以起到辟邪禳祓的功能,保护墓葬或建筑”[17](P138)。“参”字前冠以“人”字很有可能是因其似人形而成为墓葬神药被用来替代死者领受罪厄罚谪,替生者解除殃祸注咎。总之,麻黄、人参等药物已超越其本身的药用价值而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因具有了驱邪避灾的“神效”而被广泛传布。
三、观念流变:“药食同源”观念由来已久、“毒药”由“药之凶毒者”向“百药之长”过渡
医药简帛中多次出现花椒(蜀椒、秦椒、椒)(7见)、桂(6见)、姜(6见)等食材,且这些食材在医方中并不是充当调味的作用,而是作为主药来治病驱疾,见表3。

表3
从表3可见,在《五十二病方》中即有用桂、姜与椒来治疗外伤与疽病的复方剂;在《杂疗方》中三者又成为了壮阳药的有效成分。而在北方的医简中三者又成为治久咳(《武威汉简医方》《敦煌汉简医方》)、治雁声(《武威汉简医方》)的有效药物,甚至在一些兽药中也会用到姜、桂来治疗动物的一些疾病(《敦煌汉简医方》)。不只是调味品,还有一些农产品(谷、豆、菜、果等)入药,亦可以看出先民很早就注意到食疗的重要性。湖南农学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曾对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进行鉴定,共鉴定出17种农产品,涉及谷豆、瓜果、蔬菜、麻等四类[18](P1-18),其中有八种农产品在马王堆出土的简帛医书中能找到记录,见次页表4。

表4
诚如薛爱华所说,“正如我们无法在远东文明中的化妆品与药物之间划分出一条严格而固定的界线一样,任何想要在食品与药物之间,或者是在调味品与香料之间做出明确区分的企图都是徒劳的……”[19](P353)桂、姜、蜀椒等调味品和稻麦黍等农产品在治疗疾病中凸显的重要作用可证明薛氏所言不虚,反映了古代先民们善于就地取材,用一些食物、调味品来治病驱疾,这或是中国古代药食同源理念的渊薮和滥觞。
医药简帛中一些辛热有毒植物如乌喙、附子也多次出现在简帛医药文书中。比如乌喙在《五十二病方》(10见)、《养生方》(12见)等出土医药文书中就频繁出现,用来治疗金伤、臊者(体臭)、牡痔、疽、痂、痈、干骚等疾病。余欣便言,“附子和乌头在中国医学中有极为悠久的应用历史,时间的下限至少可以划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在今湖南地区有用乌喙制成毒箭的记录,该箭射人还是射兽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是当地一定有毒乌喙箭伤人的事件发生,所以也就有了用芍药、杞本(枸杞根)、叔(大豆)、蘼芜本(芎蓉穷 根)治箭毒的方剂现世[2](P376)。“乌头毒箭确曾早在汉代就已经在狩猎和战争中被广泛使用,以致成为医家所要对付的主要创伤之一”。这种毒箭到了唐代,通过唐军与阿拉伯军队的交战,被传播到了阿拉伯地区[17](P208)。
如前所述,与乌喙毒性相当的附子亦在北方地区的出土医简中多次出现。见表5。

表5
由表5可见,在《武威汉简医方》中附子用来医治行解解腹、大风、痹手足臃肿、痂及炙疮及马鞍等疾病。杨凯、于赓哲曾对附子进行了长时间段的考察(先秦至唐)并指出,“在上古、中古时期,药物同毒物界限模糊,有时混为一谈。在一定条件下,药物与毒物之间可以转化”[20]。从出土医药文书中频繁使用乌头、附子来看,在秦汉时期先民已经将附子、乌头的药用价值和炮制方法挖掘出来,也掌握了克制乌头、附子毒性的方法,附子、乌头等毒物在两汉时期便“改过自新”,由“药之凶毒者”变为“百药之长”。
四、结语
在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而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总书记又强调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实质上是为开展本草考古指明了方向。本草考古是系统研究考古出土药物或药物相关遗存的新方向,是考古学与本草学的交叉领域。大量药物、药简、简帛医药文书或药物相关遗迹(遗存)相继现世⑤,为开展本草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1]。出土医药简帛文书中包含的药物有数百种,其中植物药的品种和使用频率当属最多。从辑录的药物药方来看,植物药已达上百种,一些复方中的植物品种就有数种,这“证明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本草学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且也早已具备了编写本草学著作的强大物质基础”[4](P307)。从古至今,人类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观念都与药、药方紧密联系,对其中为数众多的植物药进行考察,可以明了古人治病驱疾、处方施药的经验源头,找到秦汉及以前药学史发展的蛛丝马迹,进而可以管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结构变化,对于重视和保护我国中草药文化也大有助益。
注释:
①马继兴先生说《五十二病方》等六种帛简书中有药物的记载,其他八种医书均无药物名称。见马继兴《马王堆出土医书中的药学成就》,选自氏著《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这六种帛简书中,《五十二病方》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研究也最为充分。见张雷《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出土37年来国内外研究现状》,载《中医文献杂志》2010年第6期。
②学界关于武威汉代医简研究的详细情况参见:张延昌《武威汉代医简出土后的研究现状》,载《甘肃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30年来武威汉代医简研究进展》,载《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武威汉代医简出土后的研究现状》,载《甘肃科技》2002年第9期;《武威汉代医简出土30年来出版著作发表论文题录》,载《简牍学研究》2004年版;《武威汉代医简注解》,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③在《神农本草经》未出现之前,记录药物的著作中似乎只有《山海经》记录的植物药要少于其他种类药物:动物性药76种(兽类19种,鸟类27种,鱼龟类30种),植物性药54种(木本24种,草本30种),矿物药及其他7种。但这恰恰说明《山海经》的成书时代要早于《五十二病方》《内经》等书,反映了渔猎时代生活的特点。进入农耕时代后,植物药再没有少于其他类别的药物了。关于山海经中的药物学研究可参看,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编辑《〈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④这种用桂治心痛的亦可从出土药物一窥端倪,南京药学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医研究院、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医中药研究组等四家单位曾对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药物(姜、桂等9种)进行鉴定后推测道,“据尸体病理解剖,发现有冠心病、胆石症等病变,死者生前可能会出现心腹冷痛、风头痛等症候,推论这些药物可能为生前疗疾所用”。可以想见,马王堆的墓主生前可能用桂来治疗心腹冷痛。见,南京药学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医研究院、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医中药研究组《药物鉴定报告》,选自《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42页。
⑤详细内容参见,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写作小组《从西安南郊出土的医药文物看唐代医药物学的发展》,载《文物》1972第6期;耿鉴庭《西安南郊唐代窖藏里的医药文物》,载《文物》1972年第6期;马继兴《解放后出土文物在医学史上的科学价值》,载《文物》1978年第l期;吴德铎《何家村出土医药文物补证》,载《考古》1982年第5期;戴应新《解放后考古发现的医药资料考述》,载《考古》1983年第2期;文化部古文书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万物〉》,载《文物》1988年第4期;刘丽仙《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药物鉴定研究》,载《考古》1989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