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在它的波澜中诞生,在它的深渊中轮回
2021-09-08段义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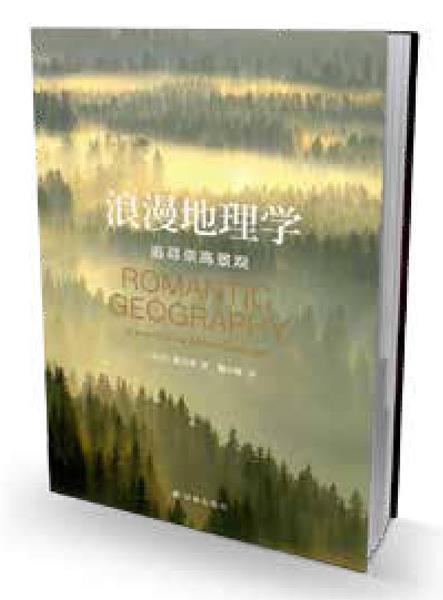
書名:浪漫地理学
作者:[美国]段义孚
译者:陆小璇
定价:59.00元
出版年月:2021年8月
字数:110千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第三日,上帝将天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当这也做成时,上帝看这是好的。“地要产生新鲜的菜蔬……事就这样成了。”而水呢?“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事就这样成了;但那万灵之中也包括海怪利维坦。显然上帝钟爱陆地,因为他把伊甸园立在那里,而在园中他创造了最美好的生物——亚当和夏娃。而海,却仍不令上帝感兴趣。直到20世纪的浪漫想象中,海仍是那样原始,那样无休止地躁动,那样残暴又含混无序;文明在它的波澜中诞生,又在它的深渊中轮回。对于《启示录》的作者而言,时间尽头的理想世界是抽离了任何流体和生物的领域——一座没有植物的几何晶状城市,一个“不再有海”的世界。
海洋像动物一样,有它的情绪
即使到了18世纪,人们也不愿去海里冒险。两位远古时代的航海者——奥德修斯和伊阿宋——也不愿如此。奥德修斯只一心想要回家,而且如果不是遭到波塞冬那个独眼巨人怪物之父的憎恨,奥德修斯大可以更早回到家乡。与此类似,伊阿宋也并不是个航海者:他只是想寻找遥远国度的金羊毛。尔后,基督教把朝圣之旅变成了精神生活的自然象征,但水域中却从来没有救赎的意义,即使到达圣地的旅行必须穿过水域。在但丁的笔下,奥德修斯虽因展开寻找美德与智慧的航程变成航海英雄,但他情愿放弃家庭的做法使其蒙羞。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从未自愿出海冒险——那是难于忍受的苦难,通向重生的死亡,一次为建造永恒之城的审判。
减少对海洋的恐惧的办法,就是缩减它的尺度。制图师们从古希腊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事。的确,哥伦布对向西航行到达陆地的时间的乐观估计,是以制图师低估了将要跨越的大洋的面积为前提的。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人们总有夸张陆地面积的倾向。海洋的范围在18世纪末最终得到确定。尽管它确有边界,而远方的地平线也并没有想象的那般遥远,然而海洋在人的心理层面上仍能唤起浩瀚的感觉。能唤起这浩瀚的是未知,而未知使人感到失控和威胁。
眼见为实,但海面上有什么可以观察的吗?除了经验丰富的水手,它对于其他人而言就是一片空白的布。海洋的深度同样加剧了海的未知性。水域的深度是陆域所没有的;人可溺死于水中,而陆地则支撑着他。海洋到底有多深?直到19世纪,才出现了一些严谨的测量尝试。与此同时,人的想象亦变得漫无边际。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第一幕,第四场)中表达了这种意向,他让克拉伦斯在梦中陷入“大海汹涌的浪涛里”。

科幻作家凡尔纳在小说《海底两万里》中描写了不少海底怪兽,其中最恐怖、最令人厌恶的则是巨型食肉章鱼。
主啊,我仿佛觉得那就是淹死的痛苦!我耳里的波涛声多么可怕!我眼里的死亡景象多么狰狞!我好像看到了成千条凄凉的沉船,上千个被鱼群咬食的尸体。海底下到处是一锭锭的黄金、巨大的船锚、成堆成堆的珍珠、不计其数的宝石,还有价值连城的首饰。有的躺在死人的头骨里,有的躺在曾是眼睛的窟窿里。宝石似乎在嘲弄着眼眶,一闪一闪地跟滑腻的海底眉来眼去,逗弄着四散在各处的死人骨殖。
海洋有它的情绪,就像动物一样。它可以不可思议地平静。大西洋中部的海面可以持续几天甚至几周如镜面般平静。在过去,航船到了这里便静止了。人们期望借助一阵轻风使船开动,于是把货物和奴隶纷纷抛入水中。甲板上也无比寂静,以至于忧虑的水手可以听见他们自己的心跳。神秘的平静是海面的一种极端情绪。而在另一个极端,大海亦会咆哮——它的浪会像愤怒的野兽般摧毁一切。海也可以变得狡猾,把航船诱进它致命的大漩涡。大漩涡是当猛烈的洋流遇到强大的潮汐时生成的水体涡流现象。其强大的下拉力足以吞噬小型船只。但在想象的世界里,漩涡变身为一只猛兽。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不得不在靠近大漩涡卡律布狄斯航行与靠近六首怪物斯库拉航行之间做出选择。在《大洋图》(Carta Marina,1539年)中,漩涡被描述成靠近挪威海岸盘绕的长蛇。然而没有什么可以比拟两位19世纪作家埃德加 · 爱伦 · 坡和儒勒 · 凡尔纳的想象力。以下是坡的文字:
突然 —— 突然一下子 —— 就成了个清清楚楚、确确实实的圆形漩涡,直径有半英里开外。涡圈是宽宽一道闪闪发亮的浪花,浪花却一点都不漏进那巨型漏斗的口里,极目望去,只见这个漏斗的内部是圈滑溜溜、亮闪闪、黑黝黝的水墙,同水平线构成45度左右的斜角,速度飞快地转啊转地直打晃,晃里晃荡,翻来滚去,转得人头昏眼花,而且还向四面八方发出可怕的声音,半若喊叫,半若咆哮,连气势磅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也从没向苍天这么哀号过呢。
爱伦 · 坡描绘了一个咆哮的海恶魔。被其吞噬即是永远地消失,或是被撕成碎片再吐出来。海洋无垠而充满恶兆,因此人们在想象中用奇异的生物把它填满。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荷马、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都丰富了这些传说。中世纪的制图师,正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也在已知世界的边缘绘上怪异的野兽。这些对海洋的想象延续至19世纪的事实令人感到意外——在人们对海洋的实际大小已经有所了解,并且原始的海洋探索技术已经出现的时候,这些神怪论实在有些过时了。
海洋的深邃、黑暗和寒冷远超想象
人们或许曾认为,海的神秘會伴随着更多知识的获得而降低。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是因为海洋实际的深邃、黑暗和寒冷程度远远超越曾经的想象,它更加令人感到疏离。关于海洋及其访客的作品总是很畅销。儒勒 · 凡尔纳的小说《海底两万里》(1869—1870年)的流行,反映了其同时代人对掺杂着现实的幻想故事的强烈反响。对深海的热衷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时代。1964年,迪士尼公司把凡尔纳的小说拍成了电影。
凡尔纳的文学造诣使其得以生动地描述神秘的水中世界。他笔下的海怪包括“一个绵延的生物,有细长的身形,偶尔发出磷光,而又比鲸鱼巨大且敏捷得多”;以及那75英尺长的抹香鲸,它硕大的头颅占了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一,而它的大颚中有25颗巨大的獠牙。但其中最恐怖而令人厌恶的则是巨型食肉章鱼。它有八只长有吸盘的触角,靠虹吸作用强烈地喷吐海水推动其前进。那巨大的章鱼想用它挥舞的触须摧毁“鹦鹉螺号”。当潜水艇终于浮出水面时:
其中的一个船员站在中央扶梯的最后几级阶梯上,松开了舱盖的螺栓。但是,螺母刚松开,舱盖就被极其猛烈地打开了,显然是被章鱼触角上的吸盘给掀开的。一根长长的触角随即像蛇一样,从舱口探了进来。
那些触角从船的侧面摸爬上来,而当船员们用斧子和它们搏斗时,那怪物喷出了一股黑色的液体,然后就消失了。同时,那些被砍断的触角“在满是血与墨的甲板上蠕动着”。
在这本书的最后,“鹦鹉螺号”和它的船长被卷进了挪威海岸附近的漩涡。他们命运未卜。但这都是虚构,是促使人产生些许愉悦的颤抖的文字。在“泰坦尼克号”的命运中,现实超乎虚构。是的,“泰坦尼克号”没有被卷入漩涡;1912年4月15日,它因在纽芬兰外海撞上冰山而淹没。然而,从目击者的记录以及三部围绕这一灾难的电影的视觉刻画来看,这艘船在倾斜了45度将要跌入深渊之时,就好像被什么吞噬了一般。这正证明了在人与自然无休止的争斗中,人造的“泰坦”无法与海洋,即希腊神话中的“泰坦”抗衡。大约1 500名乘客身亡,他们的骸骨被困在瓦解了的钢铁巨匣中,长眠于距海面2.5英里的深渊之中。
“泰坦尼克号”的命运显示了从秩序到混乱可以多么简单和迅速,好像它们之间只有薄薄的隔层。我们不禁要问:在今天的世界,去哪里寻找那最纤薄的分隔,那呈现着秩序与混乱、文明与原始两个极端间最强烈对比的地方?因为飞行变得如此普遍,人们或许会想到飞机内部与外部空间的分隔。在飞机里,我可以平静地坐在柔软舒适的椅子上读一份杂志,偶尔瞥一眼舷窗,欣赏壮丽的天空和被夕阳照耀的朵朵白云。此时微微感到的紧张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如果飞机爆炸而我被甩入高空,剧烈的寒冷会瞬间置我于死地——即使这极度的寒冷并非怪兽,因为空中旅行和高空未被古代神话提及。
然而,在一艘大船上横跨大洋的经验提供了更高层级的对比。船内是文明,甚至可以说是“过度的文明”,因为船上的社会有比陆地上更精密的分层,船长就好似圣王;人们比在陆地上更频繁地身着正装,在水晶吊灯照亮的高屋顶下享用晚餐。晚上从远处看去,这艘船就像闪耀的宝石在漆黑的海面上平静地移动。若有旅客靠在栏杆上望向这海面,如果他或她哪怕有一点想象力,都会为这深邃的恐怖与其中必然出没的诡异生物战栗。还有哪个自然/文化分隔比这更加绝对吗——一面是人们悠闲散步的甲板、维也纳的华尔兹和社交时的闲谈,另一面是阴暗、潮湿、冰冷的未知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