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的力量
2021-09-08殷建坤
殷建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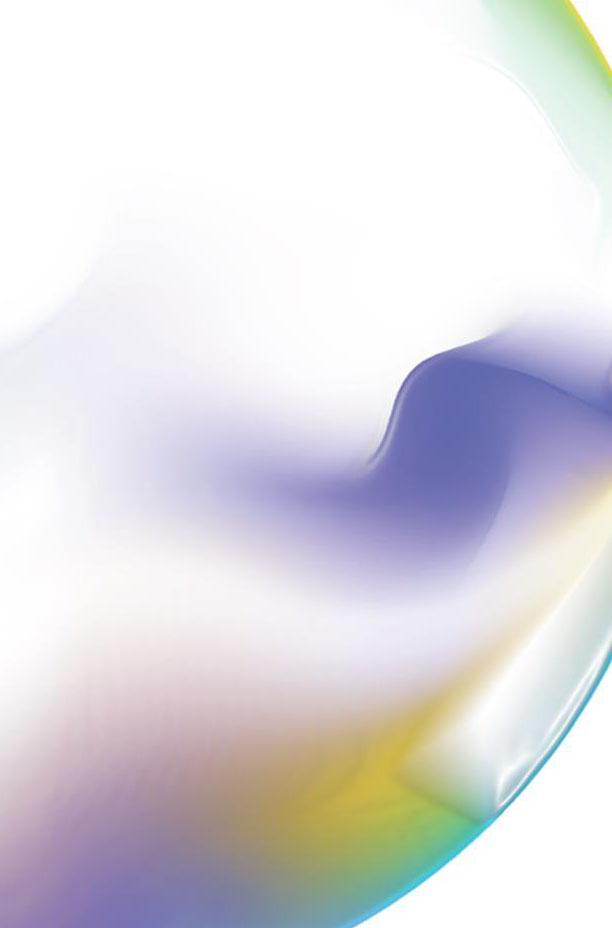
老师说
鲁迅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孔乙己》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
这段文字综合运用了神态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细节描写,表现了孔乙己善良的一面,刻画了孔乙己这样一个深受科举制度毒害却以读过书为荣,虽然经济上已经沦落为与“短衣帮”一样甚至还不如短衣帮,却要依靠一件“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来维护残存的尊严的形象。如果把这段描写稍作修改,这样来写:
孔乙己显出极兴奋的样子,将两个指头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
或者这样修改:
孔乙己显出极兴奋的样子,将两个巴掌拍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
那还是孔乙己么?
肯定不是。这就是细节的力量。“长指甲”三个字将孔乙己虽然已经贫困不堪,却要顽强地维护自己读书人的尊严,却又好喝懒做的特点很好地表现了出来。
所谓细节,就是细小的情节,它往往具有巨大的力量。在生活中,“细节决定成败”;在文学作品中,成功的细节具有细腻深刻、含蓄生动、极具表现力的作用,用来塑造人物形象,可以使之个性化、典型化。
人物的细节
大作家们都很注重细节描写。莫泊桑在《项链》中这样描写还完债后的女主角:
路瓦栽夫人现在显得老了。她成了一个穷苦人家的粗壮耐劳的妇女了。她胡乱地挽着头发,歪斜地系着裙子,露着一双通红的手,高声大气地说着话,用大桶的水刷洗地板。
正是“胡乱地挽着头发,歪斜地系着裙子”和这双“通红的手”,突出了路瓦栽夫人贫苦人家的身份。
鲁迅在《故乡》里也借助“手”来写闰土:
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少年闰土的手“红活圆实”,中年闰土的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作为细节的手的变化,反映了闰土的变化——昔日的小英雄,今天的木偶人,揭露了残酷的社会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戕害。
事物的细节
细节描写,也可以是描写一件不起眼的“物”。契诃夫《变色龙》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写:
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提着小包,穿过市场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一个火红色头发的巡警,端着一个筛子,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
好一个“筛子”!军警宪兵本应该维护社会治安,维护公平正义,但他们出门执法却要带着一个“筛子”!那个时代,军警宪兵横行、老百姓的自由和财产得不到保障的黑暗现实,就通过这个“筛子”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再如吴敬梓笔下的严监生。小说有这样一段叙述: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如何刻画“吝啬鬼”的形象?他临死之际,放心不下的不是家人,不是朋友,不是其他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或物,仅仅是多点了一根灯芯!这样的人不是吝啬鬼谁还是呢?这样的举动不能表现“吝啬”,还有什么能够表现吝啬呢?
动作的细节
细节描写,还可以是描写一个或者一组动作,借助细微的动作,来表现人物心理,表达人物情感。孙犁《荷花淀》中有这样一段精彩描写: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像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手指震动”,表现的是内心的“震动”,女人听说男人就要到大部队上去,心中既有肯定,又有不舍与不安。男人到大部队可以更好地打鬼子,自然很好,所以女人低下头来说了一句:“你总是很积极的。”但战争毕竟是残酷的,牺牲随时会降临,因此心中又有不舍与不安,毕竟参军的目的不是牺牲,而是赶走侵略者,恢复和平宁静的幸福生活。
细节描写的方法
著名学者王鼎钧说,好的描写可以使我们对久已熟悉的事物有新的感受,好的描写可以使我们对陌生的事物恍如親历亲见。这句话用在细节描写上尤为恰当。
与之相反,如果没有了细节描写,文章的感染力就大打折扣,有学生在《最美的礼物》一文中,把父亲在自己模拟考试失利后的谆谆教诲当作礼物(考试失利,从材料来说有点陈旧;父亲的教诲当作礼物,却不乏新颖)他这样写:
父亲在电话里说:“没关系,这次考不好,还有下一次。你要好好努力,肯定能考上高中的。我们在外面做生意,也很辛苦,早起晚归,都是很不容易的。今年特别难,生意很不好,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我听了,感到很羞愧。
这段文字真实,但是缺乏感染力,为什么?缺乏了细节。父亲的文化程度是什么?最爱用哪些词语?父亲说话的语速、语气怎样?父亲说话的腔调如何?父亲的人生经历如何?他的沧桑、艰难怎样体现在说话之中?我听父亲的话,只是一个“羞愧”?有没有想起父亲的艰辛?想起父亲忙碌的身影?如果多一些细节描写,就有了感染力。
怎样才能将细节描写得生动形象?
一、细心观察,找到生活中最能打动你的那一个“点”,用特写镜头凸显其特征。
鲁迅《故乡》有这样一段文字: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
到了家门口,作者观察的“镜头”没有对准整个老屋,没有对准大门,没有对准飞檐翘角,而是对准了瓦楞间抖动着的枯草的断茎,以此来烘托故乡的衰败,渲染自己从千里之外回到故乡时的悲凉。
写人也可以这样。《台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那时已经是深秋,露水很大,雾也很大,父亲浮在雾里。父亲头发上像是飘了一层细雨,每一根细发都艰难地挑着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随着父亲踏黃泥的节奏一起一伏。晃破了便滚到额头上,额头上一会儿就滚满了黄豆大的露珠。
这段文字既写出了父亲劳动时舞蹈一般的优美姿态,又借头发上和额头上的露珠,写出父亲造屋过程中的艰辛。
二、细化人物动作,用慢镜头拉长动作过程。
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这样描写临刑前画圆(签字画押)的过程: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是怎样画圆的?作者用一连串的动作,把一个本不长的动作过程拉长了,人们就像欣赏慢镜头一样完整地看清了他画圆的过程,也就看清了他内心的愚昧麻木。
三、学会提问,更加具体地凸显人物行为特征。
《我的叔叔于勒》中有这样一段吃牡蛎的描写:
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牡蛎壳扔到海里。
为了突出吃法“文雅”,用了连续的动作描写,但仅有动作描写依然不能细致生动地表现这些“准贵族”的“文雅”,于是采取“提问”的方法,细化描写。怎样的手帕?小巧的手帕。头怎样向前伸?稍向前伸。怎么动?微微一动。“小巧”“稍”“微微”等词语就是在提问之后得到的答案,在描写时辅以这样一些词语,就更加细致,更有表现力了。
再如,有同学这样写上学快要迟到时的动作:
天啊!要迟到了。我踹开被子,从床上跳下来,拽过校服,蹬上鞋子,蹿进洗手间,抽出牙刷,涂上牙膏,在嘴里戳了几下,扯下毛巾,在脸上抹了几下,冲出了屋子。
这个片段也用了一连串的动作,拉长了动作的时间,表现了“我”快要迟到时的忙乱。但细细品味一下就会发现,“细”得还不够、还不准。
这时,运用提问法,尝试在动词前面加上修饰语,就可以把这种忙乱表现得更加具体生动。
比如说,“我踹开被子”,是怎么踹的呢?“我”又是怎样蹿进洗手间的呢?经过提问之后这样修改:
天啊!要迟到了。我一脚踹开被子,慌忙跳下床来,一把扯过校服,蹬上鞋子,三步并作两步蹿进洗手间,抽出牙刷,随意涂上牙膏,在嘴里胡乱地戳了几下,然后飞快地扯下毛巾,在脸上匆忙抹了几下,火急火燎地冲出了屋子。
这样,忙乱就更加细致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敲黑板
有人说,写文章就如钓鱼,读者就是那“鱼”,细节描写就是那鱼钩上的饵,能够直击读者之心。好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在细枝末节之中,被触动,被感动,进而感受到了纷繁复杂的世界背后最真切、最微妙、最直击人心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