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轻生者的网络“树洞”
2021-09-07毛亚楠
毛亚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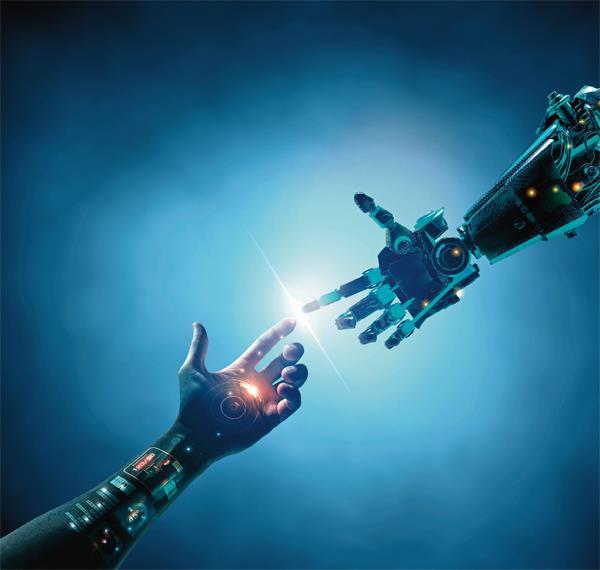
就像现实中有人会将不能言说之事说给一个树洞听,在网络上,也藏着无数人隐秘的苦楚。2016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发现了网络上也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树洞”。当时他所在的计算网络心理实验室正在进行一项网络心理的研究,主要通过用户的网络行为去了解他们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变化,包括可能的自杀行为和自杀风险。一个叫“走饭”的微博用户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走饭”微博的评论区里,聚集了数量庞大、危险程度不一的求死讯息。
“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这是“走饭”最后一条微博信息,她已于2012年3月17日因抑郁自杀。在当时,抑郁症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走饭”一事曝出后,社会各界围绕这一精神疾病的讨论多了起来。人们争相转发她的这条微博,前来留言的人也越来越多,从此,这条微博的评论区下演变为互联网上一个承载情绪的“树洞”,到如今,“树洞”已有超过100万条的评论、11.3万条的转发,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天几千条的速度继续上涨。
在朱廷劭看来,网络树洞之所以形成,源于留言者们对现实的失望,而“停摆”微博之下无疑是个可以无条件容纳他们失意情绪的场所,不仅如此,有时还会收到同病之人的暖意。朱廷劭便想,如果说前来取暖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有没有可能他们也在等待搭救?因为据朱廷劭的研究团队调研发现,“在网络上表达绝望情绪的人,有79%认为获得求助‘并非没有必要,但‘从未寻求过帮助的人占据50%以上,尚有超过60%的人从没有接触过自杀预防的相关知识”。
“是不是可以通过分析自杀者的微博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试着找到那些有自杀意念却还没有实施的人,及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帮助呢?”——这是朱廷劭的初衷。计算机出身的他很快想到了AI,“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网络上的信息做及时自动的识别,我们能很快找到有自杀风险的人群,这种效率是人工标注不可比的”,朱廷劭向《方圆》表示。
当年春天的那个下午,通过微博账号“心理地图PsyMap”,朱廷劭向AI在微博筛选出来的4222个有明显自杀倾向的对象发送了私信。私信是这样写的,“你现在还好吗,情绪状态怎么样……”并附上了24小时自杀求助电话。整个下午他都在不安中度过,不知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用AI 筛选自杀意念
朱廷劭的本、硕、博学的都是计算机专业,1999年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博士毕业后,他又去了加拿大的阿爾伯塔大学继续深造。阿尔伯塔大学是加拿大人工智能领域排名前三的学校,值得一提的是,阿尔法狗(AlphaGo)、阿尔法零(AlphaZero)的主创人员就是此学校AI组毕业的。
在加拿大,朱廷劭主要研究推荐系统,“通过对人浏览网页时的行为分析了解他的信息需求,然后从全网找到能够满足他需求的内容”。因为里面涉及对人的行为分析,后来他逐渐接触了心理学。2012年来到中科院心理所后,朱廷劭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最新的计算机技术运用到心理学领域。
在朱廷劭看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心理学的研究打开了全新大门,“首先它能很好地规避心理学研究中极易受到主试和被试自身期待或动机影响的弊端,因为一个人的网络痕迹是不会骗人的,如今人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现象都能够被电子化记录成大数据保存下来,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对用户的人格特质或者行为进行判断。而一旦有了这些生态化的行为数据,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对人们心理指标的自动识别”。
具体到在互联网上寻找到那些自杀意念者们,用人工智能筛选出他们的前提是要找出自杀用户和无自杀倾向用户在社交行为、语言使用上的差别。通过朱廷劭团队的对比研究,这种差异性被总结,“这样人群的微博一般互动更少、更加关注自我,在情绪上有更多负面表达,他们说的内容和死亡、宗教相关的较多,和工作相关的比较少”。
归纳出有自杀倾向用户的可识别模式后,便可利用机器学习建立自杀意念识别模型。朱廷劭说,为保证其精确度,他们会对每一条微博给出一个预测标注,按照不同的层级分成1、2、3级,1就是有自杀意念;2是有自杀意念,同时有自杀计划;3是不仅有自杀计划,还有自杀的实施。
朱廷劭办公室一台站立式机位前,电脑屏幕上能看到自杀识别的模型,它每隔一段时间会自动抓取一次“走饭”微博下的评论,输出的界面类似一个文本文件,每句话前都有一个数字,朱廷劭说,“比如这句,‘从前我只是晚上才会想到死亡,最近就算有阳光的时候都会觉得要活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这个就是有自杀意念了,所以是1,一旦数字是1,模型就会自动向该用户发送事先编好的私信”。
但也有特殊的情况,中文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有时也增加机器识别的难度,比如“饭饭,我很快就要看到你了”,这话在日常语境下没人会想到和自杀有关,但若出现在“走饭”评论区,其中之义便再明了不过。所以为了避免出现机器误发私信的情况,朱廷劭团队里还设有专门的把关人,用来阅读并标注AI筛选出来的结果。朱廷劭说,这个模型仍需要不断的优化,目前精准度在85%以上。
比起人,更相信机器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自杀是全球15至29岁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年轻人缘何成为自杀高发群体?这与发展快速、压力巨大的社会生活不无关系。据最新版《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2020)》显示,“18岁至34岁青年期的焦虑平均水平要高于成人期的其他年龄段”,这提示人们需要绝对重视青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与干预。
2019年,一份名为《失控的想象——社交媒体时代青少年自杀现象研究》的调研报告如此描述互联网时代同龄人与长辈之间的代际鸿沟——“在绝大多数家庭,尤其是小孩尚处于学习阶段,控制媒介使用时间和频率是家长的必修功课,从而使得代际之间的信息流动急剧减少,部分青少年与虚拟空间中群体交往大于与父母或教师之间的交往。不但如此,青少年对虚拟空间中信息的信任度也大于对家庭成员或教师的信任度”。
“比起人来说,他们更相信机器”,这也是朱廷劭在一次采访中提到的。“所以当他们在网上讲自杀,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只是为了博取别人关注而已,我们做过一个研究,研究显示在网络上表达自杀意念的人有一半以上真的会去尝试自杀。这提醒我们,他们在网上并不只是说说而已。”朱廷劭说。
他向《方圆》回忆了5年前收到的第一次反馈,“当时的感觉是,松了口气”。有300多人直接回复了私信,仅有个位数的回复很负面。“谢谢你,你是第一个这么问我的人”,有人这样回复道。有人正走在湖边,被这条私信拦下,发现还有暖意可留恋。还有人已经自杀死亡了,但他的亲人回复了并表达了感谢。这给了朱廷劭做此事的信心,“很多时候情绪的爆发只是没找到出口,而如果帮他们一起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结果或许会不同”。
他同时表示非常理解那些回复负面信息的用户,“毕竟投向用户的关切注视如果处理不当,也有可能被当成是可怖的监视”。但其实,朱廷劭说,隐私保护是他们这个“自杀干预系统”上线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因为有“前车之鉴”。
2014年,英国慈善机构Samaritans曾和twitter合作推出了一款相似的心理危机干预技术Samaritans Radar,这个应用会扫描用户关注的所有好友,一旦用户发布了负面情绪的表达,它便会通知到用户的twitter好友那里。该应用在它的广告片中声称可以让人们及时发现身边需要帮助的朋友,但其却在上线十天之后被永久关闭,因为此举让众多推特用户感到隐私被侵犯了。
2017年,Facebook 也通过机器学习系统加人工审核的方式,发布了他们的自杀预防工具,他们在 Instagram 上对超过 80 万条此内容进行了介入,有时还会把心理健康内容发给创建自杀内容的个人,或在危急情况下向用户所在的地方当局发出警报。但这同样触动了用户在隐私方面的神经。
相较于上述两者,同样都是主动扫描用户,朱廷劭团队研发的“自杀干预系统”的呈现方式则要低调得多。为了更好地保护微博上有自杀意念用户的隐私和尊严,该团队通过微博账号“心理地图PsyMap”,用微博私信的方式同AI筛选出来的每个用户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据朱廷劭说,由于私信属于一对一的邮件系统,在系统前台根本看不到交互,他们的官微还差点因为日活量太少被关闭,但其实,仅去年一年他们的后台已有超过20万条的交互。
真正的帮助
既然联系上了,就要想到如何能带来真正的帮助。
曾经接收到过这个系统发来私信的刘丹(化名)告诉《方圆》,她之所以点开了这条微博私信链接,原因首先是觉得它可靠。“他们会先介绍背景,再推送问卷,并提供可选择的干预方式。让人既能了解自己现在怎么样,又能知道该怎么办。”
据朱廷劭介绍,这份私信的形成是经其团队前期大量的调研、访谈,并组织专家进行讨论后设计而成。“里面提供的全国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汇总的服务质量是可以得到保证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了一些科学的心理测评量表和自助干预项目。心理测量不同于网上的娱乐测试,是通过专业的手段让他们知道自己当前的情况究竟如何。而自助干预服务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不愿意跟人讲话,而是愿意跟机器交流。这个属于认知行为疗法,在目前被认为是最具有明确程序化的一个自助干预系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带领团队开发了“在线自杀主动预防”系统。(来源:资料图片)
同时,他们也招募志愿者,因为这需要非常专业的交流,朱廷劭团队的志愿者都是国家二级或三级心理咨询师。作为团队早期志愿者之一,刘明明向《方圆》简单介绍了志愿者的工作。“每天18点到22点都有志愿者值班在线,一般情况是用户通过私信回复我们,志愿者就会跟进,我们首先会表示关心,然后询问情况、了解问题,并且进行检测,包括对测试结果进行反馈解释,再之后我们会利用问题解决疗法去帮助他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
朱廷劭强调,为了保证干预的专业性,志愿者会被要求用统一的账号进行交流回复。在未收到回复的情况下,就连私信发出的次数也经过深思熟虑,“不能每次都发,否则就形成骚扰。我们通常讲事不过三,但又觉得可能很多人不看,所以就定了发5次”。一位收到私信的用户曾如此感谢,“我现在还好,谢谢你多次注意到我的情绪。我从不相信会有官方号会如此执着,一开始我也警惕,现在却觉得大千世界不乏温情”。
也有用户感激的同时透露出担忧,认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被窥视,志愿者就会跟对方保证,“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会报警,但如果你要自杀,请告诉我们”。
来不及沟通的時刻也有。刘明明记得有一次值班,AI检测到一个用户的微博状态是“当晚0点要服用安眠药自杀”。当时距离0点只剩几个小时,所有人半夜起来商量对策。他们先是联系上对方确认状态,得知对方当时是一个人在外地一个宾馆里,由于对方无论如何都不肯提供自己的手机联系方式和具体位置,志愿者最后只争取到让其把手机伸向窗外,拍了张照。最后当地警方通过志愿者提供的那张照片,成功找到了那个人。
事后那人去了医院疗养,恢复了一段后继续跟志愿者们保持着联系,他还表示,那次事件虽没有直接解决他生活中的处境,但志愿者帮他找到了其他身边的积极关系,至少让他认识到,除了死亡这种解决方法之外,或许还有其他道路可走。
刘明明觉得,他们通过AI技术进行自杀干预,“转介的效果其实要比干预的效果意义要大”,“是我们发现了他可能会需要帮助,所以我们给他推的第一条推送其实不是说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而是说,我现在是一个专业的身份,我告诉你,你现在如果有一些不开心的想法,你可以通过这些资源找到专业的机构,去接受更加专业长期的辅导。而如果你现在连打电话的勇气也没有,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带你分析一下,现在怎么做对你来说是最好的”。
“我们更重要的,是桥梁作用。”刘明明说。
边界与伦理
2017年7月以来,该团队已累计向2万多位有自杀意念的用户推送了心理危机干预资源,准确率高达92.2%。但他们从不总结“成功率”,更无从得知救过多少人。
“这正是做自杀研究与其他研究不一样的地方”,朱廷劭告诉《方圆》,“我们没办法做比较,也就没有什么所谓‘救助成功率之说。因为即使这一次干预成功了,我们不敢保证会不会有下一次。毕竟有过一次自杀行为的人下一次自杀的可能性要高于其他人,当然也会有不再自杀的情况。所以这些都是不能被总结的。我们能做的也只是长期追踪他们,或者对干预前后他们的认知状态做一个比较,总之,技术干预自杀,不能夸大效果。”
由此表明他对技术介入自杀干预的警惕。朱廷劭一直认为,即便自己研发的系统对于自杀表达语言的分析准确率已经达到了85%,但自杀表达反映出的问题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对于主动进行自杀干预,从技术到人工上都必须非常小心,否则很容易对轻生者造成二次伤害。
“自杀干预不是一个好心就能办好事的事情,过于激进,有可能会起到相反作用。”他们的研究团队曾根据30名已确认自杀死亡的微博用户的公开数据进行过分析,发现自杀死亡用户在自杀之前,在社交网络上的表达是有清晰的逻辑结构的,并不是人们常常认为的“一时冲动”。“在一个深思熟虑的人面前跟他讲大道理,他肯定是听不进去的,甚至有可能使其之后以更隐秘的方式采取自杀行动”,所以朱廷劭认为,做自杀干预,除了保护用户的隐私之外,更重要的是尊重。
所以,做这件事情的成就感就在于,保证隐私和尊重前提下的再干预,“我们得承认做这个事情的有限性,AI技术的介入只能提高自杀干预的时效性,但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自杀这个问题,是很难做到的。在中国,很多自杀者并非因为精神疾病死亡,而是因为社会问题,比如家庭矛盾、经济困难等。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从专业的角度提供一些技术手段和方法思路,让他能多个选择。我们救不了所有自杀的人,但只要能够有人觉得这个方案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就可以了,不管这个有用是对一个人还是几个人,这是我们继续往下做的动力。”朱廷劭说。
但这毕竟是份每天都能接收到负能量的工作,朱廷劭团队里的志愿者人员的流动性还是很大的,据朱廷劭说,目前人数是10位。该项目强调志愿者用统一官方账号与用户进行交流,不支持线下交流,私下联系,除了保证专业性之外,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志愿者自身。
“即便是具备三级以上心理咨询师证书,遇到紧急危机干预的情况,对志愿者的心理还是会造成影响的,需要通过心理督导师以‘再干预的方式去疏导。”刘明明说。
为此,朱廷劭团队经常同其他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預机构进行合作,定期前来指导志愿者的工作,避免“负负得负”的发生。
提到那几年的志愿者工作,刘明明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她说,这相当于一个能帮她看到世间百态的窗口,让她了解到每个人生活都各有各的难处和希望。并且,她也意识到,当自己帮助了那些用户重新审视自己的想法和生活的同时,她自己也用同样的技巧调整化解了对方给自己带来的负面输入,“环境都是不变的,但你可以用另外一种视角,调试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她记得自己曾经看过的一句话,“想死的人太多,有时候遇见高崖湖水,也就死了;有时候遇到花遇到雪,也就算了”。是花,也是雪,这就是她对这段经历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