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文赋的回归与转向
2021-08-31叶露
叶露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文赋”是赋体演变到宋代的产物。元祝尧《古赋辨体·宋体》谓“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1](P61),又在扬雄《长杨赋》后注云:“如《子虚》《上林》,首尾同是文,而其中犹是赋。至子云此赋,则自首至尾纯是文,赋之体鲜矣。厥后唐末宋时诸公以文为赋,岂非滥觞于此。”[1](P47)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首尾是子虚、乌有、亡是公的对话辩难,故用散语,而且中间也以三人的对话连接,其“假设问对”乃是构篇的框架。扬雄《长杨赋》也是假设子墨客卿和翰林主人的问对构篇,但其前四段都是二人的对话议论,第五段也大半如此。扬雄此赋相较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的巨丽铺陈,确实是以散语论事为主,名物和形容铺陈遽减,祝尧言其“赋之体鲜矣”,即是批评其违背了赋尚铺陈的体制特点。唐人提倡“古文”,宋人赋作受其影响,完全变成了“以文为赋”,则可以说是铺陈的丧失。祝尧对于这种现象是持批评态度的,在他之后,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故今分为四体:一曰古赋,二曰俳赋,三曰文赋,四曰律赋。”[2](P101)至此,宋赋已被确指为“文赋”,在一体之赋的定义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代学者对宋代文赋亦有所讨论,如曾枣庄称“文赋是继俳赋、律赋之后的一种新兴赋体”[3],郭建勋指出宋代文赋多用散文句法,押韵自由或不押韵,以才学议论为主[4]。尽管学界对宋代文赋的研究已较充分,但从句式等角度来分析,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
从祝尧以来,学界一直将“以文为赋”视为文赋写作的重要特征。事实上,相对于《诗》语整饬而言,赋体初为散语,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文为赋”可以说是赋体自身的回归。班固《两都赋序》谓“赋者,古诗之流也”[1](P489),但赋异于《诗》,最为根本的区别就是散语的运用。赋体散语不同于《诗》之四言整齐一律及重章叠句的咏唱,中国诗凭借“汉语单音独字形成节奏并由此产生稳定的句式,进而固定为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和七言诸体”[5](P113)。《诗》主四言,由两个双音形成2-2节奏,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6](P22),句读必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会断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除了节奏的平衡感带来诗歌本身的韵律美之外,《诗》之句式对称、稳固、整齐,更容易规范诗体,形成模本,易于和音律合拍,弦歌而唱。节奏的平衡与音律合拍,适合《诗》章“优而婉”[7](P1402)的歌唱。为了契合固定句式,按照启功先生的说法,《诗》语多“缺头短尾,脱榫硬接”,盖“四字一句……实出无奈”[8](P4)。例如《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6](P595)“昔我往”意义已足,加语助词“矣”凑足四言,而且延长声气,“思”字也有同样功效,“但以虚字衬贴,叠字形容,语句反复,重章迭唱,敷衍一篇,实义为寡,唯以歌咏为功”[5](P170)。又如《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6](P228)为凑足四言,将“尔卜筮体无咎言”拉长为“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将“以尔车来我贿迁”拉长为“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这表明《诗》四言具有很强的形式规范作用。
赋源于《骚》,“屈《骚》在《诗》外别立一体,宋赋承之,去情叙物,开启汉赋”[9]。《离骚》长篇巨制,在结构上明显异于《诗》四言的短制歌唱,而且散语句式为后来骚体赋沿用。《离骚》散语相对于《诗》四言整齐的重章叠句,则是长短参差,没有固定的字数和句数,并“以句中虚字连接更多的字词形成复杂结构的长句,并以句尾虚字加强情感的表达和咏叹的效果,实质上乃是借助虚字以使散语长句成为韵语,较之《诗》语四言的拘限具有情感表达和名物容纳的更大空间”[10],例如“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11](P12),上句句尾“兮”字用以延长声气,加强感叹的效果,句中虚字“其”“以”连接形容的语词或句法成分,与《诗》四言整齐一律的句式限定显然不同。
宋玉继承屈原《离骚》的名物和形容铺陈而弃情叙物,开创赋体。其《风赋》《高唐赋》已肇汉大赋之端,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铺陈为主,不仅异于《诗》语,也不再是《骚》语拖着“兮”字和虚字连接的散语长句,如《高唐赋》中一段:
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盘岸巑岏,裖陈硙硙。磐石险峻,倾崎崖隤。岩岖参差,纵横相追。陬互横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积,重叠增益。状若砥柱,在巫山下。仰视山巅,肃何芊芊,炫耀虹蜺。俯视崝嵘,窐寥窈冥,不见其底,虚闻松声。[12](P73)
尽管多用四言,但与《诗》四言两句一意不同。《诗》语如《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为一句,形成一个完整的语意单位,一句句意已足,所以接下另说“匪来贸丝,来即我谋”,换成另外一个完整的语义单位,尽管上下两个语意单位之间具有意义上的联系,但中间存在顿断,《诗》即依靠四言两句一韵一意的形式规范“诗人”的写作。而宋玉此赋自始至“状若砥柱”,都是“登高远望”的情状,铺写山石之态,千奇百怪,目不暇接,不可顿断,本质上是四言短句在一个整体散句中的一顺铺陈,各个四言短句之间,没有句意的顿断,而是连续承递的铺写。这种四言一顺铺陈的散语长句与《离骚》两句一意的长句铺陈也不相同,它不再是《骚》语两句结合而以上句句尾“兮”字延长声气,而是截为若干四言短句,其组合形成的长句比《骚》语两句结合的长句要长得多,可以容纳更多的名物和形容描写。《高唐赋》使用这种散语,使篇中名物大幅增多,从托物抒情变为直接呈现名物,并增加了大量形容描写,惟以铺采摛文为事。
汉大赋将宋玉开创的散语铺陈发挥到极致,乃是出于“苞括宇宙,总览人物”[13](P12)的需要,往往具有十分富丽的名物和形容铺陈,其描写空间越大,越需要散语的延展。汉大赋虚设问答多为散语,主客对答之间的四言一顺铺陈也是散语。兹以司马相如《上林赋》为例:

这是亡是公对子虚和乌有的陈词,段首四句为对话散语,接下来便是对“天子之上林”的铺陈,现代标点往往在“紫渊径其北”后断句,但其后“荡荡兮八川分流”本是包括丹水、紫渊、灞、浐、泾、渭等,显然在此不可断句;又或以“经营乎其内”为断,同理亦为不可;或在“过乎泱漭之野”断之,但接下“汩乎混流”一段正是对前面叙述的描写,直到“衍溢陂池”,都是描写水势,一气贯注,滔滔汩汩,无论在其中何处句读,似乎都阻断了文意。实际上,自“左苍梧”至此,虽间有稍长句式,用以叙述,或三言振作声气,但大多还是四言,重在形容描写,总合起来,只是一句。接下一段写鳞甲飞鸟及水下奇物,也是一个长句的一顺铺陈。在一顺的语势中,用于描写的语词之间并不构成现代语法学所谓主、谓、宾、定、状、补的关系,而是形容词的一顺铺排和不断堆积,名物的铺陈则多以四字句所包含的两个双节结构直接呈现,也不存在各种句法结构的关系。惟其如此,才不可顿断,十分典型地显示了汉大赋散语长句的一顺铺排,具有名物和形容铺陈的巨大空间。
二
汉大赋承接宋玉赋,成为一代文学之盛。《离骚》等楚辞则在汉代演化为骚体赋,仍以抒情为主,句式因承楚辞上下两句的结构而渐趋整饬。至东汉张衡《归田赋》,如“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等语,已经脱落楚辞句尾“兮”字,变成流畅的六言联对,其对四言的运用则已是相当成熟的骈偶句式,如“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六朝抒情小赋多用属对,如刘宋谢庄《月赋》“擅扶光于东沼,嗣若英于西冥”“聆皋禽之夕闻,听朔管之秋引”,对偶十分工整,但于平仄声律尚未规范。及至唐代律赋,则如近体律诗一样严格遵守平仄格律了。
实际上,六朝骈赋以及唐代律赋的联对结构,乃是一个相对自足的语意单位,尤其是在律赋中,这种联对结构还起到构篇的作用。律赋题目琐细,篇幅短小,试赋更是限以八韵,拘于平仄,这都局限了赋体铺陈的特点。律赋多用联对,如唐懿宗咸通间王棨的《缀珠为烛赋》:“出宝箧以规圆,呈姿璀璨;入雕笼而艳发,香照荧煌。”[14](P8020)这是六四联对。王棨《秋夜七里滩闻渔歌赋》:“此时游子,只添歧路之愁;何处逸人,顿起江湖之趣。”[14](P8018)则是四六联对。六朝骈赋多用四四、六六联对,唐代律赋沿袭之,且又多四六、六四联对,这成为了唐代律赋的典型句型。这种联对结构由上四六或六四,对下四六或六四,上下之间构成字句、平仄和语意的对应,在对应中形成相对自足的语意空间,一联写完,下一联重起,转到另一语意结构。律赋一韵即由若干四四、六六、四六、六四等联对组成,间以三言或六言以上者,如砌砖般堆成一段或一韵。一篇,则由数韵构成。联对结构乃是律赋的基本单位,联对结构之间的语意间断导致赋文铺陈的停顿,再也不是大赋四言一顺、滚滚而出、滔滔不绝的铺陈,极大地缩减了铺陈的空间,这是从六朝骈赋到唐代律赋对汉大赋散语一顺的破弃,反映了赋体的重要演变。
唐代律赋是六朝骈赋的进一步演变。骈偶只是一种语体,用于无韵之文,则为骈文;用于有韵而铺陈之作,则称骈赋。六朝骈文深刻影响了唐代四六文的写作,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正因骈体流行,中唐韩愈等人遂以“古文运动”矫救其弊,提倡秦汉散文,反对六朝骈俪。由于六朝骈赋及唐代律赋都用骈语,所以“古文运动”反对骈文,亦必影响赋体创作,改变骈俪的造语习惯,从而促进了文赋的产生。赋发展至宋演化为文赋一体,无疑与唐宋古文运动有密切关联。刘培谓“文赋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文体”[15],许结则谓“宋人以文为赋同于以文为诗,均密契于自中唐迄北宋相继两朝的古文革新运动”,进而指出:
以文为诗或为赋皆为当时文学思潮发展之大势所趋,在中唐韩柳古文运动摧激下,赋体虽未如诗体变化之显,然韩愈之类文之赋,杨敬之《华山赋》、杜牧《阿房宫赋》已兼采散文句法(如杜赋前半用律后半用散)。至宋代,不仅骈赋、律赋逐渐走向散文化,即连承袭晚唐的四六俪语亦多以文体为之,注入散文的气势,参以散文的议论,为纯粹的新文赋的出现铺展了道路。[16]
近来,胡建升在《宋赋研究:权力与形式》中也认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给‘以文为赋’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赋予了‘以文为赋’新的内涵,也使‘以文为赋’成为宋赋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和艺术特征”[17](P227)。
文赋破除骈赋和律赋的联对结构而使用散语,确实是回到了赋体之本。但宋代“以文为赋”之“文”与汉大赋四言一顺的散语之“文”是不同的,当然更与拖着“兮”字和句中用虚字连接的骚体不同。关于汉大赋的来源,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论曰: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18](P116)
实际上,《诗》并非赋源。除了《离骚》及楚辞,赋的确还受到《庄子》《战国策》的影响:在主题表达上,不是紧扣题目的集中论说,而是挥洒自如、天马行空的任意遨游;在语言叙述上,也不是精炼的文法和字斟句酌的讲求,而是重视洋洋洒洒的铺排和一气贯注的气势。
影响“以文为赋”的唐宋古文和影响汉大赋的古文是有很大不同的。不同于《庄子》的汪洋恣肆而“荒唐谬悠”,不同于《战国策》的纵横谈说而“恢廓声势”,也不同于汉代史传的详赡繁富,唐宋古文“以文载道”的理念要求古文写作应当具有突出的中心思想和强烈的主体意识,因此很多古文篇幅短小精悍,结构有序严谨,章法层次森然,造语注重说理的气势、长短的搭配,气足而理盛,表现手法则以叙议为主,就事议论,夹叙夹议。至宋代古文,更是以议论说理为本。韩愈《杂说》中的《马说》一篇,即是唐代古文创作的典范: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是在唐代“古文运动”背景下精心构撰的短制精品。首先,作者的创作意识强烈。它体现了一种道义的担当,具有十分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并非一时的情绪之作。其次,主体意识十分明确。世人“真不知马”,唯我独知;执策者亦不惜马,而我欲振臂呼之,所以“抗颜而为师”[20](P871),乃为天下说之。再次,篇幅精短,结构严谨。第一段首句点明论点,干净利落,谓世人不识马,则千里马只能“祇辱于奴隶人之手”;次段写食马者使之不饱,则不能千里;第三段归结为治马者并不识马。全文简当精准,只就论点展开简短的演说,逻辑层层推进,十分严密,无隙可乘,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最后,语言精炼。弃斥骈偶,散行使气,多用判断句表明论点的正确性,长短错落,参差有致,短者三字,如“食不饱,力不足”,干脆有力,长者则压缩复句于一个单句之中,间不容发,体现出古文家对语言的精审提炼。这种简略却具有针对性和战斗性的古文在秦汉论理和史传文学中是难以见到的。韩愈的其他古文如《原道》《师说》《送孟东野序》《毛颖传》等也多是如此。
宋代散文上承中唐“古文运动”。《宋史·文苑传序》云:“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21](P12997)欧阳修自述其从小倾心韩愈之文,“见其言深厚而雄博”,谓“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22](P1927),又认为古文写作要贴近社会现实,反映与作家关系密切的身边百事,不能“弃百事不关于心”[22](P1177)。较诸韩愈古文的奇崛不平,欧阳修散文更趋平和,行文更为顺畅。欧阳修的文学追求也体现在他的文赋创作上,并引领了一时风尚。铃木虎雄认为欧阳修是宋代“文赋开山之功者”[23](P265),他与梅尧臣都是诗文改革者,二人对文赋的贡献相当,而在创作实践上,梅尧臣的文赋创作还要早于欧阳修。梅尧臣的《红鹦鹉赋》作于明道元年(1032):
相国彭城公尹洛之二年,客有献红鹦鹉,笼之甚固,复以重环系其足,遂感而赋云:蹄而毛,翼而羽,以形以色,别类而聚,或啸或呼,远人而处。在鸟能言,有曰鹦鹉。产乎西陇之层峦,巢于乔木之危端。其性惠,其貌安。与禽兽异,为笼槛观。吾谓此鸟,曾不若尺鷃之翻翻,复有异于是者,故得以粗论。吾昔窥尔族,喙丹而绿;今览尔躯,体具而朱。何天生尔之乖耶!俾尔为尔类,尚或弗取,况尔殊尔众,不其甚矣!何者?徒欲谨其守,固其枢,加以坚鏁,置以深庐。虽使饮琼乳、啄彫胡以充饥渴,铸南金、饰明珠以为开闭,又奚得于鸟鸢之与鸡雏?吾是知异不如常,慧不如愚,已乎已乎。[24](P2945)
不妨比较汉末祢衡的《鹦鹉赋》: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故其嬉游高峻,栖跱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觜,绿衣翠衿。采采丽容,咬咬好音。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24](P391)
祢赋体物而抒情,铺张笔墨,写鹦鹉聪慧丽姿,却遭网罗捕获,最终离群丧侣,借以表达作者不为明君赏识、空负绝世之才的愤懑。鹦鹉乃是作者的自比,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这类咏物赋因仍骚体赋的比兴寄托,只是体制短小,以抒情为要,名物形容逊之。句式则以骈偶为常,如“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觜,绿衣翠衿”,“飞”对“翔”,“不”对“必”,“妄集”对“择林”,“绀趾”对“绿衣”,“丹觜”对“翠衿”,或单字对单字,或偏正词汇对偏正词汇,十分整齐。
梅赋虽以咏鸟为题,却通过红鹦鹉禀赋奇特而遭遇牢笼,来说明“吾是知异不如常,慧不如愚”的“粗论”。抒情并非主要目的,“吾”与“尔”(红鹦鹉)是观察和被观察的关系,在叙事中完成“道理”的阐发才是本赋的主旨。在结构上,梅赋层层设问,先写鹦鹉之形性,次叹红鹦鹉“体具而朱”之“乖”而被囚牢笼,最后顺势推出结论,夹叙夹议,叙议结合,突出主题。在句式上,梅赋前半虽有骈语,但从“吾谓此鸟曾不若尺鷃之翻翻”开始,即用“古文”奇句单行,虽以“赋”名篇,但已受到“古文”行文的影响,文气一脉贯通,更注意一己之意的顺畅表达,从而打破骈赋和律赋的偶对规范,更像一篇用“古文”散语写作的议论文。以“古文”之气势为赋,即以单行之气势运偶语,以散文之气势驭韵语,这成为文赋造语的基本特点。梅尧臣在北宋初期写作文赋,并非典型,至欧阳修的《秋声赋》和苏轼的《赤壁赋》,方成为宋代文赋的名篇。不过,通过梅尧臣赋可以大致看出文赋三个方面的特点,即句式以“古文”散语为主,表现手法则以叙议为本,题旨则是一篇一论。
三
事实上,宋人对于古赋,更倾向于学习楚辞,而非汉代逞辞大赋。从北宋晁补之的《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到朱熹的《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都体现了宋人对以《骚》为代表的楚辞之景仰。《离骚》铺陈华瞻,采撷瑰丽,鸿篇巨制,同时“跌宕怪神、怨怼激发”[25](P5),贾谊因承其骚动之情,穷蹙申诉,创立骚赋;枚乘踵武宋玉,沿袭其凭虚之体,铺采名物,衍为大赋。两者各绪其义,开一代文学,而宋人所作文赋,恰恰于二者优长之处,都有欠缺。文赋以叙议为本,略于抒情,不尚铺张,其承载的名物既寡,又囿于说理,渐渐丧失赋之本色。
苏轼《滟滪堆赋》作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其逞才之情态在赋序中显露无疑:“世以瞿塘峡口滟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于此石。”然而作者力排俗议:“以余观之,盖有功于斯人者……因为之赋,以待好事者试观而思之。”与大赋作者铺排文字、罗列名物式的逞才不同,此赋“以理服人”,所逞者乃是“学理”之才。试与左思《三都赋》中关于吴都的一段山泽描写比较,二者在名物铺排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观乎滟滪之崔嵬,然后知其所以开峡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忽峡口之逼窄兮,纳万顷于一杯。方其未知有峡也,而战乎滟滪之下,喧豗震掉,尽力以与石斗,勃乎若万骑之西来。忽孤城之当道,钩援临冲,毕至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于是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滟滪堆赋》)[24](P3120)
显然,苏赋驭散文之气,倡思理之风,名物描写缺少丰盈感。其渲染滟滪之崔嵬、波涛之浩荡,只有“浩漫漫”“喧豗震掉”“滔滔汩汩”等寥寥数语。相较《三都赋》对山势险峻、河海奔涌的全方位描写,如“嵬嶷峣屼”“巊溟郁岪”“溃渱泮汗”“滇淼漫”“磈磈”“滮滮涆涆”“濆薄沸腾”“寂寥长迈”“濞焉汹汹”“隐焉礚礚”“歊雾漨浡”“云蒸昏昧”“泓澄奫潫”“澒溶沆瀁”,显得“词穷”很多。从赋体本质要义来说,“只以四字为读,直接呈现名物,无需句法结构,形成绵密复沓的铺陈效果”[26],而从文赋需要说理的角度上讲,却需要句法结构形成逻辑顺序,故而苏赋中有“而观乎”“然后知”“所以”“而”“固”“方其”“于是”等连词不断顺接,理固然通畅明白了许多,却也失去了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形容叠加,气势减弱了很多。
刘勰说:“至孝武之世,则相如撰《篇》。及宣、成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颂》,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臧否大半。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27](P623-624)作家重视文字音韵在赋中的运用,他们搜肠刮肚,创新求奇,“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27](P494)。大赋作者普遍创作艰辛,斟酌用词。司马相如为创作大赋,通《尔雅》,著《凡将篇》,可以说是一位文字训诂学的专家,其《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等俨然是生僻文字的罗列,称其佶屈聱牙,亦不为过。宋人雅好读书,学问丰赡,王观国《学林》、王楙《野客丛书》、王质《诗总闻》、姚宽《西溪丛语》等笔记中都有关于赋作字词的探讨,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
扬雄《反骚》云:“有周氏之婵嫣兮,或鼻祖于汾隅。”注:“鼻,始也。”余以为未尽其义。雄《方言》云:“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也。梁、益谓鼻为初。”或谓始祖为鼻祖者,其义如此。[28](P195)
由此可见,宋人对于字义的用功与推敲毫不弱于前人。但在创作时,宋人却去掉了考究字词的“学问”,转而追求文风之畅达。不得不说,名物的缺省让句子的表述功能更加通畅。欧阳修是平易文风的倡导者,在其知贡举时,更借选拨人才的机会改变当时艰深险怪的文风。据陈振孙《刘状元东归集》提要载:“辉,嘉祐四年进士第一人,《尧舜性仁赋》至今人所传诵。始在场屋有声,文体奇涩,欧公恶之,下第。及是在殿庐得其赋,大喜,既唱名,乃辉也,公为之愕然。盖与前所试文如出二人手,可谓速化矣。”[29](P500)故而沈括赞赏欧阳修云:“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30](P344)可见在主考官倡导下,连场屋应试都可以迅速出现顺畅平实之风,何况赋家自作。苏轼就认为:“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31](P1532)提倡“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31](P1418)。文赋与大赋虽同为散体赋,也都崇尚以学为赋,最终却表现出了巨大差别:大赋以文字为学,文赋以思理为学。
苏轼《滟滪堆赋》为了说明江浪冲击滟滪堆时的惊心动魄的力量,运用了贴切生动的比喻:滔天的江水似乎是不可一世的千军万马,骄横跋扈,目空一切,而滟滪堆恰似沉稳勇敢、独当一面的将军,沉着应对,不急不迫,短兵交接之下,顿时杀声震天,惊涛如雷的江浪人仰马翻,徒耗力气,最终倒戈偃旗,逃遁东流。唯其如此,才能显示出滟滪堆的功劳,也才能凸显赋家说理的目的。而《三都赋》只为展示魏蜀吴三都之盛状,所谓“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故而以直接描写、罗列名物为本,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也正是由于平易文风的流行,宋赋一改以往大赋考据名物、艰涩难读的面貌,兴起了“押几个韵者耳”的新风尚。可资创作的题材也越来越多,纪行赋、咏物赋、感怀赋等不一而足,无论写作何种题材,名物铺陈已不那么重要,赋题变小,体制变短,语言更通俗化和口语化。如苏轼《黠鼠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24](P3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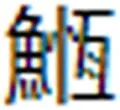
四
自来不乏对宋人文赋的批评,即便是欧阳修的《秋声赋》与苏轼的《赤壁赋》,也未能获免。清李调元《赋话》评曰:“《秋声》《赤壁》,宋赋之最擅名者,其原出于《阿房》《华山》诸篇,而奇变远弗之逮,殊觉剽而不留。陈后山所谓一片之文,押几个韵者耳。朱子亦云:‘宋朝文章之盛,前世莫不推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与眉山苏公,相继迭起,各以文擅名一世。独于楚人之赋,有未数数然者。’”[1](P107)“楚人之赋”即骚体赋,其言是谓宋人作赋无复屈原“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故不能“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1](P528)。不过,朱熹所批评的欧阳修,却是骚体赋的崇尚者。在欧赋24篇中,《病暑赋》《憎苍蝇赋》《红鹦鹉赋》《述梦赋》《啄木辞》《哭女师》6篇均为骚体赋,占25%;考虑到律赋是北宋中期的科考文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创作,而欧作11篇属之,若除去律赋不计,则骚体赋占比46%,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欧阳修的骚体赋缺乏“美人香草”的名物铺陈和形容描写,大多是枯燥的议论,确有“一片之文,押几个韵者耳”之嫌,反不如《秋声》文赋一篇,辉映文坛,为宋代文赋在赋史上独立一宗奠定了基础。
朱熹批评文赋议论过多,缺乏名物描写,是谓理胜其辞。元代祝尧《古赋辨体》已经指出:“赋之为体固尚辞,然其于辞也,必本之于情而达之于理。文之为体每尚理,然其于理也,多略乎其辞而昧乎其情。故以赋为赋,则自然有情、有辞而有理。以文为赋,则有理矣而未必有辞,有辞矣而未必有情,此等之作,虽名曰赋,乃是有韵之文,并与赋之本义失之。”[1](P47)明徐师曾《文章明辨序说》更为明确地指出:“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丽矣!”[2](P101)汉大赋藻丽夸饰,就是名物和描写的巨丽铺陈,其实在《离骚》等楚辞作品中即已如此,只不过《离骚》等楚辞篇章大多是托物抒情,蕴含着丰满的情感。汉大赋弃情叙物,以物为主;六朝骈赋亦多体物描写,将主体情感融入到物态的描写之中。宋人文赋却以议论说理为要,情、物并失,或有以抒情为主者,也多直接抒情,名物及其描写是相当缺乏的。
但也应当看到,宋人文赋议论说理,乃是在此前赋体写物抒情之后别立一体,不同往代。兹举欧阳修《秋声赋》和苏轼《赤壁赋》为例,其略云:
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物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秋声赋》)[22](P478)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赤壁赋》)[24](P3122-3123)
两赋虽主理趣,但也可以从中感受到充沛的文气、深沉的情感和磊落的胸襟。“百忧感其心,万物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非情致深邃、体察细腻不能至此。只是这样的抒情被统摄于全篇的议论和说理之中,显得纡徐婉转而深挚平和,似乎情是浅显的、其次的,哲理才是重点和本质。苏轼“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等,同样也是抒情,但已融入空灵虚静的绵邈之思中,读者所感受到的,不是读《骚》之后的掩涕长叹,而是通于天地阴阳与人生思辨的体悟,在情感的共鸣之外获得深沉的思索。
《全宋文》中收赋1480余篇,可算文赋的大约200余篇[17](P11)。宋代文赋在数量上虽然不如律赋、骚体赋,但多出自大家,且颇多精品。如苏辙《墨竹赋》,以散化骈,说理精当,其云:
与可听然而笑曰: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隐乎崇山之阳,庐乎修竹之林。视听漠然,无槩乎予心。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观竹之变也多矣。若夫风止雨霁,山空日出。猗猗其长,森乎满谷,叶如翠羽,筠如苍玉。澹乎自持,凄兮欲滴。蝉鸣鸟噪,人响寂历。忽依风而长啸,眇掩冉以终日。笋含箨而将坠,根得土而横逸。绝涧谷而蔓延,散子孙乎千亿。至若藂薄之馀,斤斧所施。山石荦埆,荆棘生之。蹇将抽而莫达,纷既折而犹持。气虽伤而益壮,身以病而增奇。凄风号怒乎隙穴,飞雪凝冱乎陂池。悲众木之无赖,虽百围而莫支。犹复苍然于既寒之后,凛乎无可怜之姿。追松柏以自偶,窃仁人之所为。此则竹之所以为竹也。始也余见而悦之,今也悦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笔之在手,与纸之在前。勃然而兴,而修竹森然。虽天造之无朕,亦何以异于兹焉?客曰:盖予闻之: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万物一理也,其所从为之者异尔。况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与可曰:唯唯。[24](P3154)
此赋是宋代文赋中的佳篇,多有体物描写之语,其沿用汉大赋主客问对,总体上以散语为主,间或参以六朝骈赋偶对,但却不是四六、六四紧紧相连,而是以说理运气,一顺而出,从而化解骈赋联对的板滞,轻松自如,摇曳生姿。这是以“物我两忘,合乎大道”的“理”为旨归,全篇情辞飞越,笔墨生辉,既有古文散句之疏宕,又兼俪藻偶对之清朗,绝不是专攻理趣、木质无文的刻板之作。
宋代文赋还有较为特殊之处,便是一篇之中包容各类赋体特点。比如孔武仲的《憎蝇赋》,其开篇为“方盛夏之滔滔兮,气蕴蕴以熏心”,这是运用了骚体赋的标志性“兮”字句。接下来却是“而是时也,有曰蝇者,或形小于乌豆,或衣蓝而冠赭,其来无端,其聚而积”,这就是散文化的句法了。其后,赋中又频见“浮瓜于泉,沉李于水,清尘埃以洒扫,洁槃箸以湔洗”等对偶工整、骈俪整饬的四六句。最后又云:“盖与生以终始,非有时而去来,舍此不思,而惟蝇是责,则我亦褊矣,何异拔剑而逐之哉!”[24](P3147-3148)则分明是一篇以蝇为议论之由头、自我警醒、思理精妙的文赋。
晁补之《北渚亭赋》的句式杂糅得更为明显,前段有骚体赋中常见的“兮”字句,纡徐宛转,中间一段四言居多,骈雅藻俪,具有骈赋特色,然而赋作后半段启用主客问答模式,同时运以铺陈手法。一篇之中各体兼备,也难怪苏轼认为“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己意微箴之”[31](P1532)。此中微词是说晁补之的辞赋缺少畅达文脉,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宋代文赋的创制,不是完全抛弃以往赋体的写作传统,而是杂取诸体,运以己意,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意识。
最后,再略举宋代文赋之作,如叶清臣《风异赋》,梅尧臣《灵乌赋》《乞巧赋》《鸤鸠赋》《鱼琴赋》《矮石榴树子赋》《雨赋》《击瓯赋》《针口鱼赋》,苏轼《后赤壁赋》《天庆观乳泉赋》《秋阳赋》《后杞菊赋》,黄庭坚《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东坡居士墨戏赋》《刘明仲墨竹赋》,张耒《秋风赋》《卯饮赋》《哀伯牙赋》,李之仪《闲居赋》,沈与求《客游玄都赋》,杨简《广居赋》,杨万里《浯溪赋》《糟蟹赋》《月晕赋》《交难赋》《压波堂赋》《清虚子此君轩赋》《海鰌赋》等,都各有特色。虽然其中有的作品也杂有咏物叙事,有的糅合情感,但基本上名物缺省,铺陈减弱,仍是以理取胜。文赋“尚理”确是其主要特点,它虽拓宽了赋的书写内容,却失去了赋体铺陈的本质,从而造成了赋学在宋代的重要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