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派”电影人全昌根的民族主义电影风格成因探究
2021-08-28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100876
乔 宁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 100876)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不仅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也是很多“朝鲜半岛”独立运动人士和文化先驱者的流亡地和避难所。上海的国际都市地位、先进的文化、开放的氛围,尤其是繁荣的上海电影文化产业备受亚洲文化人士的瞩目。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被称为“上海派”的电影人群体,在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将作品与足迹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变迁史上。这些朝鲜半岛电影人为什么会选择来中国、最后又是怎样离开的?他们的上海电影征程对他们的电影人生有着怎样的影响?他们为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怎样的贡献?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对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相关的资料进行了梳理考证。据笔者查阅的资料显示,张东天在《在对方的镜头里找回自我——1949年以前韩中电影文化交流史初探》一文中对中国与朝鲜半岛早期的电影交流做了探讨;许珍在《跨国电影合作中的民族身份与国族想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电影交流史》一文中对李庆孙、郑基铎、全昌根等南下上海的朝鲜族电影人进行了表述;林吉安在《韩国“流亡影人“郑基铎”与二十世纪二三十现代中国电影》一文中对集编、导、演于一身的电影人郑基铎进行了细致梳理和评述。而这一派别的其他电影人相对于鲜明的群体特点而言,个人生平及作品的研究仍亟待整理。
相对来说,朝鲜半岛学术界对“上海派”电影人的作品以及他们离开上海归国后对朝鲜半岛电影的影响做了较为细致的整理。其中朝鲜族学者姜成率、李再明、金秀南和林大根分别对“上海派”电影人及其作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提出了“离散”、“异邦”和“流亡”影人的概念,并对“上海派”电影人的作品给予了肯定。李英一、安泰根和朴赞久几位学者则对“上海派”电影人对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电影合作交流做了系统的整理,认为“上海派”电影人中李庆孙和全昌根这一生最耀眼的时期便是在上海自由创作的时期,虽然两个人由于性格和环境的因素导致两个人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不可否认的是,“上海派”电影人在回到朝鲜半岛之后对朝鲜半岛电影界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
鉴于中国与朝鲜半岛电影学界对“上海派”电影人当前研究的现状,笔者借鉴中国学者李道新“影人年谱”的治史方法,对朝鲜半岛电影光复期代表“全昌根”(原名钱昌根,1908—1972)的史料进行“搜集、解析、鉴定、考明和比对”等基础性工作,以朝鲜半岛电影资料馆提供的文献和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早期的报纸杂志等史料为中心,依照全昌根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两个地区的发展足迹、抗日运动、电影作品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进行详细的梳理,进一步挖掘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在建交前电影方面的合作交流,以期能对这段时期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有所增益。
一、全昌根与电影的邂逅
根据学者李英一提供的资料显示,全昌根1908年1月18日出生于咸镜北道的会宁市。会宁作为朝鲜族电影人罗云奎、尹奉春、朱仁奎和全昌根等诸多电影人的故乡,也被称为电影之乡。全昌根自幼沉默寡言,但思想上非常奔放自由,在参与各种活动或是在电影片场工作的时候特别健谈。据与全昌根在上海共同生活过的朝鲜族小说家金光洲回忆,他在高中时期就已经与戏剧有过一些接触,那时的他受到会宁著名电影人士罗云奎、尹奉春、金亦珍和朱仁奎的影响,经常在会宁观看话剧、戏剧团的巡回演出和摄影展览。这些兴趣和观看经验也为全昌根日后从事电影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25年,18岁的全昌根立志投身于电影行业,他加入“尹白南”的电影制作公司并和其他几位新人一起参加了同为“上海派”电影人李庆孙导演的新片《开拓者》的选角面试。其热情、活泼和对电影的执着态度打动了导演李庆孙。李庆孙认为,“全昌根对电影的热情不亚于他当时第一眼看中的罗云奎,认为全昌根很有可能会成为朝鲜半岛第二个罗云奎”。所以李庆孙全力提携全昌根,并给了他在电影界崭露头角的机会,让其参演了《开拓者》并在此片中担任副导演一职。片中和他共同出演的还有郑基铎、金泰镇和金正淑等朝鲜族演员。但遗憾的是,“由于全昌根母亲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将自己在《开拓者》中的戏份全部剪除,才平息了母子间的风波”。全昌根这次从影经历给李庆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庆孙在晚年的回忆中清晰地陈述了青年时全昌根的形象:“脸上长着青春痘,说着一口会宁方言,看起来聪明、大胆且对电影有着强烈、执着的热情。”
《开拓者》这部作品是他在朝鲜半岛电影初创期参演的唯一作品,却没有在荧幕上留下他的身影。但对于完全没有过电影经验的全昌根而言,他找到了自己毕生的努力方向,坚定了对学习和制作电影的不懈追求。同时与李庆孙的邂逅激发了他对电影的认知,引领全昌根走上了电影之路。
二、全昌根与朝鲜半岛“流亡”影人的重逢
1919年,朝鲜半岛在独立运动之后遭到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同时日本殖民政府也进一步加紧了对当地电影业的管控。全昌根所在的尹白南电影制作公司由于资金上的限制在影片《开拓者》制作完成之后不久便已无片可拍了,全昌根的电影之路也告一段落,但这为其上海之行埋下了伏笔。学者金秀南认为,全昌根之所以去上海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国际大都市上海在电影创作上相较被日本统治的朝鲜半岛而言会自由很多;其次,上海的电影公司资金充足、设备齐全、技术优于朝鲜半岛,电影制作起来会更加便利;最重要的是上海是朝鲜族革命斗士和独立运动家的栖身之地。可见全昌根在离开朝鲜半岛之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自己的电影梦想寄托在了中国这片土地上,希望能够在上海完成自己的电影梦。
据朝鲜半岛学者姜成率梳理的有关“上海派”电影人的生平记录的资料显示,全昌根在1925年底抵达上海,先是在上海中华学院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在友人的介绍下到武昌大学(现武汉大学)学习中文,毕业之后和同为侨胞的同窗在上海完婚,并一直生活在上海的岳母家中。在上海期间全昌根结识了朝鲜族小说家金光洲,通过金光洲的介绍得以在上海三一学院执教美术。同时又通过妻子家人的介绍结识了“韩国国父”金九先生。之后全昌根又在上海三一学院院长的引荐下进入大中华百合电影公司开始演一些配角,直到朝鲜族其他“流亡”影人的到来,全昌根才开始拍摄自己的电影。
1928年,底日本政府加大了对朝鲜半岛电影摄制法案的制裁力度,以李庆孙为代表的进步电影人士受到了日本宪兵队的监视。彼时,朝鲜族电影人拍摄的带有反抗殖民统治和揭露社会现实的影片很难在日本殖民政府支持的低俗爱情剧泛滥的时代生存,“无法自由创作”的朝鲜族影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电影事业,陆续“流亡”到具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上海。郑基铎、韩昌燮、李庆孙和李弼雨等“上海派”电影人便是因此而来的。此时,早已进入大中华百合电影公司的全昌根,虽然在拍摄经验上不如后来的几位影人,但是精通中文、熟悉环境的他无疑成为了这些“流亡”影人最初的“依靠”。全昌根也借着与友人重逢的机会,决定一起制作电影,“流亡”影人就此开启了在上海新的篇章。
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正处于“左翼文化运动”的广泛影响之下。1930年8月,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1932年后改名联华影业公司)成立,并在“复兴国片”的旗号下提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纲领。受到“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电影制作的进步人士开始关注社会、人生的价值取向以及弘扬本土艺术形式与精神。中国电影也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全昌根民族主义电影风格的形成与坚守
(一)民族主义电影风格的形成
1928年,全昌根凭借《爱国魂》这部作品在中国电影界崭露头角,这也是“上海派”电影人为数不多的作品中颇具价值的电影作品。据资料记载,郑基铎是影片导演,全昌根是影片编剧,周诗穆担任摄像,由中国演员汤天绣和朝鲜族演员郑一松共同担任主演。从主创阵容来看,这部电影是由当时在上海的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电影人共同努力合作的成果。
《爱国魂》原名《安重根》,影片原本讲述的是朝鲜族烈士安重根刺杀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的真实事件,但由于当时日本政府的干涉,最后不得不将其名字改为《爱国魂》,且内容遭到了大量的删减和改动。
根据《电影月刊》的详细记载可以看到,影片对真实事件的原型进行了艺术化处理,将推行侵略中国满蒙地区政策的侵略国设定为魏国,并将被侵略国家设定为黎国,中国与黎国的爱国志士联手刺杀魏国的侵略策划者,数次失败后终获成功并悉数慷慨就义。可见,这部带有朝鲜半岛民族意识和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融合了中国元素并以隐喻的方式宣扬反日的爱国思想,《爱国魂》精彩的剧情征服了当时的观众,堪称巨作。在当时的“武侠神怪片”时代,为了抒解残酷社会现实对观众造成的心灵创伤,“侠客”们把电影观众带入一个近乎无政府无国别的虚幻“江湖”,从而疏导观众对腐朽社会和统治阶级的沮丧和愤怒的情绪。作为一度被武侠神怪片霸占的“东方好莱坞”却被这部抗日爱国题材的现实主义电影所折服,其民族意识的“隐喻”式表达可谓是影片制胜的关键。同时也正是这种“乌托邦”式的、“隐喻”式的表达帮助《爱国魂》成功过审。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武侠神鬼片”中的“侠义精神”和朝鲜族电影中的“民族意识”都体现了一种对充满压迫的、落后的社会的“悲”与“恨”,只不过中国武侠神鬼片的复仇是在虚拟的“江湖”之中,而“上海派”电影人的作品则显得更真实,颇具现实意味。
全昌根正是通过将反抗压迫社会的现实主义风格和中国武侠神怪片的“侠义精神”加以融合,以一种虚幻的视角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彻底区分开来,将抗日英雄和中国的“侠客”形象相结合,在模糊了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三地的阵营的同时,既弘扬了抗日爱国精神,又满足了苛刻的审查制度。尤为重要的是,此次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的首次结合也唤醒了被“武侠神怪片”麻痹的中国观众。
《时报》和《罗宾汉》对《爱国魂》进行了高度评价:在观影效果上,“中央大剧院人影憧憧、半为日人、半为韩人,则于今日日人暴横之下、一泄其胸中气、故于每幕痛快处、掌声如雷”。在思想上,“足以促进文化,富有民族主义之革命性,极能使观众产生民族意识”。不仅如此,朝鲜族学者对《爱国魂》也进行了相应的评价并肯定了影片的历史价值,认为它是朝鲜半岛殖民地时期第一部也是唯一朝鲜族人制作的抗日题材电影,虽然没能在朝鲜半岛本土制作和上映,但对朝鲜半岛电影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可以说这部“军事爱国巨片”打破了中国观众醉心已久的“武侠世界”,激发了他们对充满压迫社会的愤怒和反抗意识,并对周遭世界的动荡现实持有不满的态度,而这种“悲”与“恨”的民族意识正是朝鲜族电影长期以来特有的民族“符号”。被统治、被压迫的民族命运和动荡的家国环境使得电影的制作人员和电影观众在悲恨愤懑的情绪上达到了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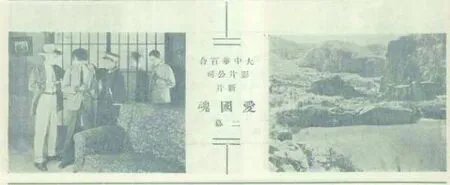
图1 《爱国魂》剧照(8)引自:《第八艺术》,1929年第1期,第43页。
继《爱国魂》之后,由全昌根和李庆孙等上海派影人共同发起并组建的“东方艺术协会”正式成立,这也是当时朝鲜族影人在上海唯一的一个民间组织,此协会吸纳了当时在上海的“上海派”电影人。1930年与孤星电影公司合作拍摄的电影《扬子江》便是其协会的第一部作品。
(二)民族主义电影风格的跨国传播
电影《扬子江》作为朝鲜半岛上映的第一部带有朝鲜语字幕的外国影片,以“悲”和“恨”的民族意识征服了当时的大多数观众,成为“上海派”电影人制作的电影中海外票房、评价最高的一部。影片依旧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讲述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无法忍受当时的地主阶级,最终加入革命军成功复仇的故事。影片于1931年1月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华大戏院举办了首映式,得到了上海观众的认可和称赞。同年5月,《扬子江》得以在朝鲜半岛上映,这在当时的殖民统治背景下堪称奇迹,也得到了朝鲜半岛观众的强烈好评。其中《每日申报》的记者金乙汗在观影后称赞道:“《扬子江》阵容如此之庞大是朝鲜半岛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主要的是这些流亡电影人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还能够完成如此优秀的作品是值得学习和尊敬的。”不仅如此,朝鲜半岛影评界的沈勋也对在上海的朝鲜族电影人做出了评价,认为这些“流亡”影人即便在异国他乡,也依旧能够看到他的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感和抗日决心,这一切都离不开他们对电影持之以恒的热情和不断的努力。
《扬子江》与《爱国魂》一样,通过唤起两地在殖民统治时期对阶级社会的愤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中国的“侠义精神”和朝鲜族的“民族意识”相结合,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异国他乡的情调化,既符合两地观众的口味,又能够将艺术化为“武器”教导大众。虽然朝鲜半岛的观众在地理上远离中国内陆,但是在共同的社会背景下,他们也能够对当时中国的老百姓心目中的“侠客”产生认同感。《扬子江》在朝鲜半岛创下了不可复制的奇迹,它将中国传统的“侠客”从一个“武侠世界”带到一个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共识的“现实世界”当中,通过对阶级社会的复仇,表达了当时“上海派”电影人心中强烈的抗日民族情感。
全昌根在《扬子江》之后又受到金九先生的邀请,一直与李庆孙跟随韩国临时政府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实际上,全昌根民族主义电影风格的确立深受“韩国国父”金九先生的影响。朝鲜族学者周润泽在回顾全昌根意识形态的变化时发现,“全昌根的民族意识正是在遇到金九后才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升华,并在回到朝鲜半岛后继续坚持民族主义作家的信念”。他积极参与金九所设的朝鲜族人学校的教学活动,策划了各种抗日演讲以及临时政府的演出,特别是他和李庆孙等“上海派”影人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起筹划的“三一节”纪念活动,无形中成为了“上海派”解散的“导火索”。
如果说带有强烈抗日情绪的《爱国魂》是对动荡的家国现实的不满和希冀、反抗不合理现实的个人内心情感投射,那么金九则作为全昌根的人生导师,通过上海的种种民族救亡活动激发并升华了他内心潜在的民族意识。同时,上海的“左翼电影”运动和中国特有的“武侠神怪片”的个人英雄主义形象的感染,奠定了其日后的电影风格,这从他受“火烧”系列电影的影响编写了电影《火窟钢刀》(1929)可见一斑。
据《上海时报》记载,1932年1月8日,由金九组建的“韩人爱国团”(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特务队)精心策划了谋刺日本天皇“东京樱田门事件”,同年4月29日又进行了谋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事件”,日军开始对常居法租界和英租界的朝鲜半岛独立运动人士进行报复。参与过抗日活动的“上海派”电影人全昌根也受到牵连,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及朝鲜半岛的抗日爱国斗士们无法在上海存身,最终在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帮助下纷纷撤离到了南京。而全昌根是其中“唯一选择继续留在上海并以中国人身份在上海 ‘艺华公司’从事电影工作的‘上海派’电影人”。厌倦了“武侠神鬼片”的观众正焦急地等待着具有民族意识的现实主义影片的洗礼。深受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现实主义”风格创作影响的全昌根很快融入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氛围,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全昌根隐藏了朝鲜族人的身份用中国人的假名在上海编写、指导了《大地的悲剧》(1931)、《初恶》(1937)、《正祖》(1937)、《春尸》(1937)等反映现实和民族精神的作品”,奠定了其作家电影风格的基础,直到1939年,全昌根才回到故土。
由此可见,金九则作为全昌根的人生导师,通过在上海的种种民族救亡活动激发了他内心潜在的民族意识,再加上中国进步的左派电影运动精神以及中国特有“武侠神怪片”的英雄主义形象的感染,奠定了其日后的电影风格。另外,随着日军的搜捕和中日战争的爆发“上海派”也随之解散。
全昌根在上海期间以电影人和“抗日斗士”的双重身份度过了他在上海的数载时光。这段期间他从一个生涩的配角成为了一名赫赫有名的主演和编剧,并将“现实主义”风格和“左翼电影”思想带回到朝鲜半岛,与朝鲜族电影人共同制作的电影《福地万里》(1941)和《自由万岁》(1946)等大量民族主义影片被研究至今,其在上海期间强烈的抗日民族意识与现实主义电影风格影响了整个朝鲜半岛电影界,成为朝鲜半岛电影史上的“奠基人”之一。
(三)民族主义电影风格的延续
根据《东亚日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介绍,1939年全昌根回到朝鲜半岛后进入高丽电影公司,影片在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取景拍摄,历经3年3个月的时间筹备《福地万里》的电影拍摄工作,是当时朝鲜半岛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大制作。当时朝鲜半岛尚在日本殖民时期,全昌根能有如此之大的动作拍摄电影实属罕见,并且刚刚返回朝鲜半岛就能得到这么大的投资也充分证明了朝鲜半岛电影界对全昌根在上海期间电影作品的认可。
但遗憾的是,因历史原因,影片并没有留存至今。学者安钟和的记载中留下了影片的相关文字:《福地万里》讲述了在日本殖民时期,一群被日寇剥夺土地、向往自由与和平的朝鲜半岛逃亡者移民到中国生活的故事。在中国生活期间,韩人村与中国当地的老百姓发生了冲突并酿成了灾祸,韩人村的一位名为“江”的青年在化解两个民族的冲突中意识到只有中国与朝鲜半岛两个民族共同携手才能守护所谓的“东方和平”。最终“江”以一人之力弥补了两民族酿成的灾祸并死在大火中,继而成为了两个民族敬仰的英雄。“江”的侠义行为为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人民带来了新的和平。影片为唤起大众的民族意识和对日寇的“恨”,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饱受苦难的朝鲜半岛人民对悲惨现状的哀叹,又以“江湖侠客”的英雄形象化解了两民族矛盾,最终团结一心携手共创未来。此片上映之后,可以说唤醒了朝鲜半岛民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灵魂,这一切都缘于全昌根对日本帝国统治下的抗日民族意识。然而,由于对社会的真实描述导致了日本政府的不满,此片在上映后不久全昌根便被日军抓捕,在狱中开始了自己的剧作生活。
直到朝鲜半岛解放后,全昌根才回到大众的视野中。这一时期全昌根致力于朝鲜半岛的话剧活动,在高丽电影公司出演了《青春繁盛》和《冰河花》等,还负责创作了《前夜》的策划。全昌根看到了朝鲜半岛电影前景越发好转,借机和其他影人创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并在《东亚日报》上呼吁朝鲜半岛的作家积极参与制作和改造电影,认为电影的技术是日后可以轻松掌握的,作家才是电影未来真正的核心力量;主张国家扶持作家进行电影创作,强调了剧本在电影中的重要性。受中国“左翼电影”影响的全昌根用实际行动更进一步影响了朝鲜半岛的电影格局,这些文字的记载可谓是中国早期“左翼电影”思想传播海外最有力的证据。

图2 《自由万岁》剧照图3
坚持以民族意识为信念的全昌根为了庆祝朝鲜半岛解放胜利编写并出演的光复期的第一部电影《自由万岁》,票房大获成功并深受观众喜爱。最重要的是全昌根带着这部《自由万岁》于1947年10月再次回到中国与广大观众见面,但这次正式的交流通过了国府、外交部和海关的便利检阅手续,并由外交部亲自运往南京和上海放映,同时也得到了《申报》和其他各大新闻报刊长达两个月的的宣传(见图3),全昌根以“东方著作家”的身份重新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成为当时影评界谈论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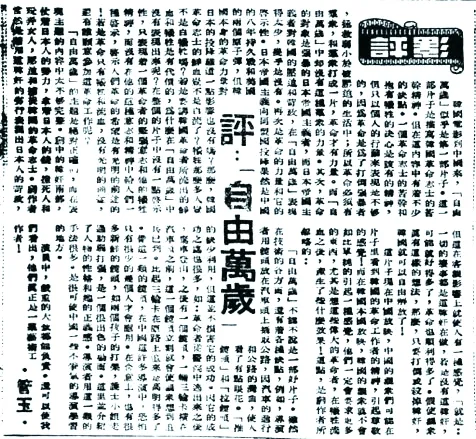
图4(21)引自:《时事新闻报晚刊》,1947年12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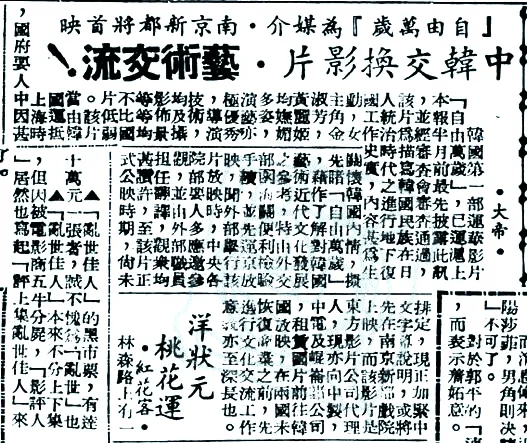
图5(22)引自:《小日报》,1947年12月16日。
根据《时事新报晚刊》和《新闻报》的记载,《自由万岁》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朝鲜族人电影,叙述了朝鲜半岛在日本投降前,朝鲜半岛革命志士策划响应盟军而遭日军迫害的感人故事。中国影评界对此片的评价较高,不少影评人认为:“在当时大量好莱坞情色片充斥的上海,‘大先生们’始终追求着超物质生活,而这部影片的到来给予观众新的温暖。”《自由万岁》从思想上解放了中国大众,“观众的情绪都从剧情中被提升到一种情操更崇高的境界,与其达成共鸣,真实地感受到朝鲜半岛民族在日寇的蹂躏下民族的血与泪”。当然也有认为其不足的地方(见图4),由于全昌根电影中的“侠客”元素尚未得到“进化”,其“英雄救美”等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的场面被个别影评人认为:“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革命的,革命的过程中必须和群众联合,影片过于刻画个人的英雄形象。”但这些个别的批评并没有影响影片在中国的票房和电影宣传。
《自由万岁》在南京和上海的电影文化交流上开了先河,因为《自由万岁》到中国来放映并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促进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的文化交流(见图5),确切地说是一种中国与朝鲜半岛交换影片的文化交流,在南京首映结束后,东方影片公司代表和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协会理事司徒德又相继到中电、中制及昆仑等公司租赁影片前往朝鲜半岛放映,欲在两地未恢复商业之前先进行文化交流工作。这也是继“上海派”电影人解散后,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文化交流,而全昌根可谓是两地早期文化交流传递的使者。
此后,全昌根又在一年内连续编写和制作了讲述朝鲜半岛烈士李准因为日寇而剖腹自杀的人物传记《不灭的密使》(1947),讲述朝鲜半岛国军创立初期士兵日常训练的纪录片《民族的城壁》(1947)以及讲述朝鲜半岛青年在解放后回到家乡为故乡工作奉献一生的故事片《被解放的故乡》(1947)三部民族解放电影。通过这几部电影可以清晰地看到,全昌根在自己国家的光复电影和启蒙电影阶段中注入了相同的民族意识和创作风格。或许这便是对旅居上海期间民族主义文化思想的一种传承和致敬,现在的韩国电影仍然是延续这个方向发展。
朝鲜半岛内战期间,避居釜山的全昌根制作了《洛东江》(1952),内战后回到首尔制作了《不死鸟的丘陵》(1955),之后又执导了《太宗哀史》(1956)、《马医太子》(1956)、《高宗皇帝和医生安重根》(1959)、《金九金不凡先生》(1960)等历史题材电影;执导了和中国香港合作的电影《异国情鸳》(1957)、夏威夷侨胞访问韩国的《水晶塔》(1958),还制作了以美国旧金山为舞台的《中国城》(1963)等跨国合作电影。
结 语
综上所述,全昌根是早期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电影界活动最频繁的一个,从首部进入朝鲜半岛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扬子江》再到中国上映的第一部朝鲜族影片《自由万岁》,全昌根可谓是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电影交流的“先驱者”,为电影上的合作交流奠定了基础。
尤为重要的是在上海的这段流亡时期全昌根深受中国电影影响,不仅将中国“左翼电影”思想融入现在的韩国电影,亦将中国“武侠神怪片”中的“侠客”英雄形象融入其日后历史大片的创作。这些影片以还原历史、刻画英雄人物为主,通过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英雄”形象来征服观众,唤醒了自己国家电影观众的民族意识,成为当地历史剧的启蒙电影。
全昌根一生中所经历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上海的生活经历、中国的“左翼电影”运动以及朝鲜半岛的独立运动对他的电影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全昌根的电影以他对动荡时代的社会现实认知为基础,围绕唤醒民众的民族情绪为中心,以艺术化作武器直面日本殖民朝鲜半岛的悲惨历史,顽强地向着民族独立和民族团结的方向全力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