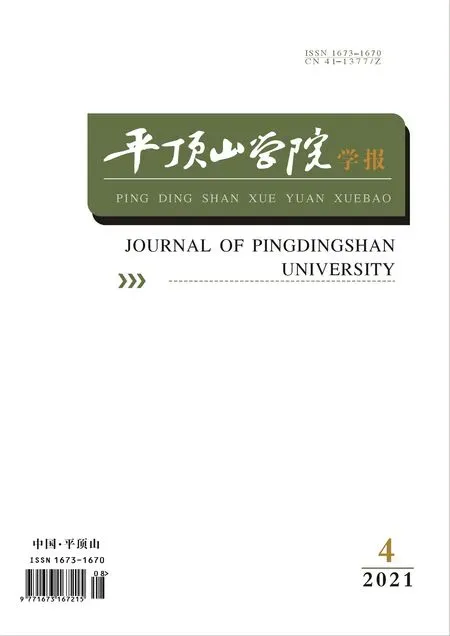《直隶汝州全志》中的清代义士形象
2021-08-27李智萍
李智萍
(平顶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36)
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义”不仅地位显著、含义宽泛,而且被广泛应用。以“义”为名的事物当然也很多,义士应该是人们最熟悉的,宋人洪迈将它归入“至行过人”类[1]。但义士的形象究竟如何?这样的解释显然过于笼统。且不说地域差异,义士形象在不同的时代就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不过,在学术研究中“义”并不是热门的课题,义士更是少人问津(1)刘师培、陈弱水从与古典的“义”观念比较的角度,对中古以下的义士及其义举作了宏观上的考察。详见刘师培:《义士释》,载刘师培:《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汪宇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71页;陈弱水:《说“义”三则》,载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196页。另外,由于义士与义夫曾经通用,那晓凌《从“义夫”的进化史看“义”的走向》(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15—119页)在考察义夫之“义”的过程中,对义士的情况也有涉及。微观研究上,田丽具体考察了明代山西义群体的阶层特点,并就其行为展开分析,详见田丽:《明代山西孝义群体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9—69页。,尤其缺少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本文拟以清代河南汝州直隶州(治今河南省汝州市)为对象,以当地地方志中义士材料最为丰富的一个版本——道光二十年(1840)出版的《直隶汝州全志》为基础(2)因义举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加之被该版汝州志采录的前代义士较少(汉代1位,明代7位),故本文仅就清代义士及其义举展开论述。,考察清代汝州义士的身份及其义举,探究清代地方社会中的义士形象,以期丰富义士问题的研究,并加深我们对当地历史文化的认识。
一、身份特点
在中国古代社会,职业性质决定人的身份[2]632,所以表1中关于义士群体身份的统计主要依据其职业性质。

表1 义士群体的身份统计
在汝州义士群体中,农民所占比重最大,达到51.03%。这里的农民,包括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和庶民地主[2]610。《直隶汝州全志》卷六《义士志》中明言农民身份的义士仅3位——马善学[3]710、丁成[3]726、傅全[3]736,这显然与实际情形不符,所以对于其余96位不知出身的义士,笔者主张将他们计入农民。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体,这些不知出身的义士既然不是缙绅、士人、吏员、医者、工商业者、佣工、职员等,那么除了农民,他们还可能拥有别的身份吗?第二,农民从生产关系上看很复杂,包含非特权等级的地主、自耕农、佃农等多个阶层[2]16,社会经济地位跨度较大。这些不知出身的义士就具备该特点,如在财力上,杨文选“家本素封”[3]741,李桂联“家不中资”[3]743,潘英“家贫好善”[3]731,不一而足。另有一些辅助统计方法,如根据其男性直系亲属的身份进行推断:马善学是农民[3]710,据此说其曾孙马景堂[3]731也是农民,应该问题不大。
士人的比重位居第二,占30.93%。这里的士人,指未入仕而有功名的读书人,包括举人、监生、贡生、生员[2]600。具体情况如下:监生30位、贡生4位、生员26位。他们数量可观,在当地享有礼遇,但入仕艰难、滞留民间。即使自身谋生不易,仍然努力在地方社会一展身手。已售官职者之所以被排除在外,是因为义举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而士人一旦获取官职,哪怕是教授、教谕、训导等地方教官,多任职于本省,也要回避本府。如王厚成,例贡[3]965,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前署荥阳县(今河南省荥阳市)训导,曾率其子侄捐助童试正场、册结等费,以助寒士,且具呈州守白批准,具详学宪立案,并禀请给匾奖励[3]747-748。此举显然是标准的义举,王厚成等人也无愧于义士之称,但却只能以“捐童试卷资”之名“附”于义士志之后。
职员在人数上虽然与农民、士人存在明显差距,但所占比例也比较高,达到第三。这里的职员,指捐纳职衔者。具体情况如下:千总职2位,布经职3位,州同职3位,县丞职2位,从九职2位,还有仅笼统地言其为职员者3位。他们多有一定的财力,郝宗扬“幼贫困,长习贾致富”[3]732,马云翼“丰于财”[3]744,行文中明言其富裕状况。而布经职李汴乃李大赠之子[3]723,“捐直隶州州同加二级”李泮乃李大赠之侄[3]738,竟是纸坊东街李氏家族中人,义士中职员的出身愈加显赫。像如此有经济实力者,在捐纳之风愈演愈烈的清代社会,他们却只捐虚衔而非实官,且做起义举多很卖力,应当主要是为了提高在当地的社会地位(3)早在1990年,陈春声先生已言及佛山(今广东佛山市)职员与当地乡正、监生、举人、生员、耆民等联袂,为社仓事务与官府交涉。详见陈春声:《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载《学术研究》,1990年第1期,第76—80页。。
工商业者居第四位,占5.15%。他们多从商:5人从事贸易活动、2人开设旅店、1人放贷、1人经营杂货,还有1人治庖为业。清代从事工商业的人大大增加,汝州“素号山涧荒凉之区”[3]674,“向鲜富户”[3]748,以经商发家者却也不乏其人,并为同业在义士榜上争得一席之地。他们不仅在自己赚到钱后回馈社会,而且在经营生意的过程中,特别是面临义利冲突时,彰显出义士之风,如李永禄[3]726和刘子绳[3]720烧毁债券,魏森[3]740、龚之珍[3]734和牛飞鹏[3]735还客遗金。虽然有些事例带有拾金不昧的性质,但他们对这些不劳而获之财尚无贪图之心,当更不至于欺诈经营,搞歪门邪道。
医者的比重为2.58%,位居第五。由于医疗“打上了浓浓的道德经济(moral-economy)的烙印”[4],医者与义举之间具有某种天然联系:“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5]该版汝州志标榜“有善而必录”[3]705,那么它为良医作《义士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兼具不矜名计利以立德、济人性命以立功之两善的处世良医大有人在。此外,黄绅“凡有公举,率捐资以为众倡”[3]730,翟天爵慷慨助人、修葺桥梁[3]710,如此无所为而为以立义者也不失为一善。医者一艺而三善具备,自然成为清代汝州义士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乡绅和吏员人数较少,占比一致,并列第六位。这里的乡绅,是指原任具有官僚身份的人(4)乡绅一般指现任或原任具有官僚身份的人(详见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4页),但在该版汝州志中,未获官职是遴选义士的一个硬性标准,所以此处将现任具有官僚身份的人排除在外。。典型例子如义士马金瀛。他“少习举业不售,援例捐礼部司务,行走三年,奏留本部,兼精膳司事”,“补缺后奉讳旋里,即优游林下,不乐仕进”[3]745。进士罗一玉的履历中虽然出现了不连贯的地方,但该例也可以作为参考。他位列乾隆十年乙丑科(1745)第三甲206名[6-7],曾任汝宁府(治今河南汝南县)教授[3]932,后仕途不详(5)关于罗一玉,《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未见此人,《清代传记丛刊》中无传可查,《清代职官年表》中也不录其何年任何官。。加上该版汝州志据其照顾家族、助葬施地等事迹,将罗一玉归为义士[3]715-716,料想他虽然入仕,但仕途短暂。吏员是中国传统社会各级政府机构中的低级办事人员,此处专指地方吏员。他们虽为衙门中人,但并非正式官员,且为本地人[8],所以其社会地位与当地普通百姓相差不多。基于对于乡土的主人翁意识,王嘉图[3]714、郭应选[3]710两位吏员也跻身义士之列。
佣工占比最小,仅有0.52%。佣工是平民身份的雇佣劳动者,明代后期以降他们的人数不断扩大[2]621。《义士志》中有1个佣工,即伍于宁,他因“家贫”而“为人佣工”[3]711。
总之,就义士的身份而言,该版汝州志中的义是地缘之义,即义士必须是本地人。一个人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只要做义举时没有官职,就有成为义士的可能。遗憾的是,与当时阶级结构的实际情形相比,上述统计结果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农民义士的比重偏低,刚过半数。这与明清时期的阶级结构严重不符。因为据冯尔康分析,当时大致上地主占人口的百分之十,自耕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四十,佃农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十[2]633。第二,商人的比重被压低。这里至少可以再补充一例,即郝宗扬,他“幼贫困,长习贾致富”[3]732。第三,个别职业甚至被省略。表1中不见教师身份的义士,实际上却有人教书谋生,即胡紫芝,他“舌耕养母”[3]714。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职业界限相当模糊。以农民为例。据冯尔康估计,明清时期大约有占人口十之二三的人“力学务农,兼事商贾”[2]604。加之该版汝州志在涉及义士的身份时,首重士人、次及其他职业,且对农民出身多加省略,所以凡是确有其他身份信息的义士,本文在统计过程中,即不将其计入农民。就名震汝州(治今河南省汝州市)的纸坊东街李家而言,其庶民地主的身份毋庸置疑,但李恭[3]727及其子李大赠[3]738为监生,计入士人;李大赠之子李汴捐布经职[3]723,侄李泮“亦援例捐直隶州州同加二级”[3]738,计入职员。如此一来,农民义士的比重自然大大降低。
最后,必须要指出的是,义士并非清一色的男性,该版汝州志中还收有1位女义士——杜吴氏[3]732。换言之,义士无性别之分,义举也无性别之分(6)并非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如明代山西义群体就有义士和义妇之分,两者的义举也不尽相同。详见田丽:《明代山西孝义群体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9—67页。。没有留下姓名的女义士更多。儿子“道拾遗金十三两”,胡起龙的妻子曰:“贫困吾家命也。当觅失主还之。”[3]734嘉庆十九年(1814)岁大饥,杨文选“输粟至城,协济赈务”,“承母志也”[3]741。鲁崇喜之妻毛氏“尤好施与”,“乃知喜生前义举多赖内助赞成云”[3]741-742。
二、行为特点
有时一位义士会兼有多种义举,所以我们在表2的统计中以事项为单位进行计算。

表2 义士群体的义举统计
(一)热心公益
热心公益致力于解决或改善地方社会问题,占比第一。包括参与诸工、义葬、发展文化事业、发展经济、为民请愿。
1.为各项地方公共工程倡首、捐钱、施地、出力一百一十五件
以轸恤行人为最大宗。有的修桥梁:李本先“念汝河冬月病涉,尝出资建木桥二十余座,行人称便”[3]723。有的通道路:“嘉庆九年六月间暴雨倾注,山水奔沸,直向东流,自官庄至唐(家)店东大路尽成石沟,行旅病之”,唐家店村村民辛有荣“年近六旬,每日携篮运石挑土补葺。凡水发后率以为常。道光九年寿终,计修路二十六年。人皆以善人目之”[3]740。有的建茶亭:连锡“尝于本村建一茶亭,捐资施济。康熙五十八年,生年八十,复捐己地二十余亩为烧茶资,以垂永久”[3]711。有的置渡船:陈贵彝“于汝水捐置渡船,以济行旅”[3]711。有的修沟渠:南关外“西邻洗耳河,每逢夏秋暴涨,往往流入街中,行旅病之”,刘仁“慨捐己产,开渠一道,俾退水有所归宿,永免冲决之虞”[3]731。
修建坛宇次之。有的创建坛宇:王复云捐资于半札街创建关帝庙[3]724。有的补修坛宇:“风穴寺凡有工程”,李如松“必捐资首倡”[3]726。有的施香火:任守玉“乾隆四十八年施入崇宁观宅院一处、香火地二十余亩”[3]730。
设学助学再次之。多为设义塾者:冯焯“立学延师,以训里中子弟之贫乏者”[3]722。还有捐学者:杨岸清先捐钱“增春风书院膏火”,“复以捐修十里义学获邀议叙”[3]746-747。也有力促改善办学条件者:吴士珩“为斋长时,尝倡捐于校士院重修桌橙(凳),完固倍昔,至今生童咸赖之”[3]711。还有迁校者:“嘉庆十六年移建学宫”,马卓群“躬襄其事”[3]742。

修建牌坊复居其下。以修建节孝坊者居多。马金瀛[3]745-746、黄汉章[3]746、樊锡龄[3]747皆为该工出资出力。另有李桂联,“道光六年任姓建烈女坊助银十八两,十六年修节妇祠并建总坊又捐钱三百余缗,尤其义举之彰彰者”[3]743。
修建祠堂居末。仅见两例:马善学“修理寇莱公祠”[3]710;曲自和的长孙合德昆季“捐资协成”“宝丰之忠义祠、本州之乡贤祠”[3]732。
2.义葬十七件
以捐地施棺的形态最常见。平时即有,如范成章“尝捐地以济贫无以塟者”[3]716。灾荒后这种情形更是难免,而且规模较大,如“乾隆初年岁饥,疫疠大行,路死者甚众”,陈太贞“尝施棺木二百余口”[3]723。也不乏亲自掩骼埋胔的:宋国顺“康熙时尝独行旷野,携筐拾白骨埋之,年久成冢”[3]713。还可见保墓护茔者:“有邻人耕犁无主孤坟”,张起元“即捐资买之,以安枯骨”[3]717。
3.发展地方文化三件
有的惜字纸:王廷干“收买字纸,盖终身不替云”[3]739;郭建林“携筐路拾已三十余年”[3]757。另有马金瀛,“现修州乘、刻汝帖,赖其力尤多焉”[3]746。
4.发展地方经济两件
有祷雨的:“乾隆三十七年六月旱甚”,李如松“祷雨于村北玉皇山,独行至庙,旋被甘霖”[3]726。有捕除蝗虫的:“道光十六年六月,蝗飞蔽天”,汪清一“尝与其弟监生汪瑗率人昼夜捕除,秋禾得以无损”[3]742。
5.为民请愿一件
彭鳌“尝呈恳前守达恩免本里支官农车”[3]743。虽仅见此一例,但该义士不仅切实关心地方利害,而且敢于直言,反而是多数义士所无法企及的。
(二)助人
助人义举致力于帮助陷于困境的个人,占比第二。包括帮助亲属、朋友、老师、乡人、顾客、病人,甚至是帮助陌生人。
1.帮助亲属四十二件
除了与帮助对象具体亲属关系不明者五件,以帮助宗族成员为最大宗,计二十五件。收养在家的有失养子女:“堂兄问诰丧妻,遗一子,甫五十日”,张问怀“怜其无依,付己妻鞠之,成人授室予田”[3]745;有孤苦老人:“胞伯乏嗣,贫老无归”,杨圣诏“迎养在家。立叔子圣贵为其后,给田产使奉祀焉”[3]718;有困苦妇女:“有族侄妇许氏孤苦无依”,叶永绪“收恤在家”[3]725;甚至有一家几十口人:堂侄“家俱赤贫,合计五十余口,难以存活”,李恭“皆收养在家,且为之完娶,各承宗祧”[3]727。有的馈钱粮,以资养赡:“族人仰给”罗一玉者“尤多”[3]716;以助婚丧:“同族希孟夫妇死无以塟”,翟天爵“为买二棺”[3]710;以助学业:张起元“为人醇质好义,族中子弟贫不能读者捐资助膏火”[3]717。或给田屋:“有族人食指浩繁”,李坦“遂割卢沟街山场并地百余亩以恤之”[3]722;或还田屋:张起元“尝契买族侄之地一区,怜其贫,给还原约,不责偿”[3]717。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提:进士张凤鸣甫赴任即病卒于官,经其族侄张兆启上下奔走六年,他才得以还柩故里归葬[3]707-708。
帮助出嫁姐妹者次之,但数量上与前者相差较多,计七件。三件给田屋:张生文“取己地一顷,召姊婿及甥至家,凭中立券,慨与之”[3]711-712;“妹氏归韩门,贫无立锥”,罗一玉“为营室给产,以资衣食”[3]715-716;李大赠与弟大定“柬召妹婿张苍璧暨甥凤翔至,凭中立券,授腴田百亩”[3]738。三件收养在家,如张勉[3]710、焦振德[3]720,更有细心者为之妥善安排以后的生活,如席汝璧的弥甥任天相“孤苦无依”,席“抚养成立,为之完娶,并给地二十亩、地基一处”[3]714。一件为外甥完婚:“外甥马元贵家贫”,常可禄“为之婚娶”[3]716。
帮助妾室者再次之,计三件。或遣嫁之:王廷璋“年逾四旬无子,以百金买妾,未婚,女泣道其苦情”,“璋遂禀于母,收为妹,字马姓,厚奁以嫁之”[3]731。或遣还之:连承先“年四十七无子,其妻刘氏以百金为之买妾”,“妾至,见承先,跪泣,道其夫殁家贫姑老子幼之状。承先恻然怜之,厚赠遣还,不问身价”[3]727。
帮助妻族、中表亲者各一件,并居末。前者如潘周鼎。其妻乔氏的祖母将自己的积蓄八十两银子“同氏埋穴中,人无知者”。两人结婚时祖母已经去世,乔氏将这笔银两如实相告,他坚决不取。事情还没有结束:“后乔氏弟及伯叔贫乏,谋欲鬻宅,鼎命妻至母家,出穴中金予之保留遗宅。”[3]709后者如董金生。乾隆五十年(1785),其中表亲——社正磨万箱“例应更替,欠有仓谷三百余石不能完缴”,他“慨然独任赔费四百七十余缗”[3]726。
2.帮助朋友三件
既有自己的朋友:靳元贞“尝代友人吕天顺偿债三十余金”[3]736;杨岱“倾橐赈贷”,“年余无间然”[3]746。也不乏家人的朋友:翟天爵之父有挚友“贫老无依”,翟“养事二十余年,丧葬如礼”[3]710。
3.帮助老师一件
“业师王家贫”,杨岸清“月给粟以养之,数十年无少间”[3]746。
4.帮助乡人五十五件
除了帮助内容不明者九件,无外乎两类。一类是救急,计二十一件。(1)以完聚为最大宗。完人婚姻者居大半,如郭振芬收养邻人高登爵夫妇,“不使仳离”[3]714;“里党有贫者被商索欠,将卖妻以偿”,李炳元“出资代完之”[3]717;阎琚“济朱姓以粟米夫妇得以生全”[3]721;“有同里杨姓者童养一媳,年荒欲卖之”,“居所代为收养,将笄,归于杨,成夫妇焉”[3]728。也有帮忙赎子者:“邻人鬻子于人”,孟继曾“即为出资赎之”[3]721。(2)代完积欠次之,不过仅少一件。多半为代输仓谷,郭思明[3]728和靳元贞[3]736乃社正。王森之行相类,“族邻凡有借贷并不责偿”[3]716。(3)帮人治病再次之。伍于瑢“亲制丸散,救人之病,里党称之”[3]720。阎琚“施药疗病”[3]721。赵纪的行为比较特殊:他曾因“母亡哭泣丧明,逾年始愈”,后“里民李世泰与纪同病目,家贫”,赵“贷以粟,为出三十金延医调治之,目亦复明”[3]712-713。(4)其他。如杜维慈收养本里一个“饥寒将死”的幼儿[3]724,马良贵出资令“阖家将饥死”之乡邻“行运谋生”[3]720,阎乘机“将己地熟麦三十亩,令人自刈,以济贫乏”[3]728。
另一类是帮助解决人生大事,计二十二件。除了王景义[3]719和董金生[3]726-727“培养子弟”,其他全是助婚丧,如陈识“助杨法之娶妻,帮温顺之殡殓”[3]717,席玉章“尝倾己囊助人婚丧之费”[3]722。
5.帮助顾客十一件
借贷活动中最常见。或不责偿,或焚其券,甚或再助之:李可权“尝以银假王姓,未还王殁,后家贫甚,其妻范氏励志守节”,李“怜其孤苦,不索前欠,又赠庄基一处,俾氏得以栖身,纺绩事翁抚子,尽孝完贞,皆权之助也”[3]712。买卖活动中也不鲜见,如李永禄“贸易粮食为业,每至不计偿直,概为付与”,“被人积欠钱五百余缗,自焚其券,悉置不问”[3]726。不动产买卖中更多见,诸如郭应选焚券还地[3]710,鲁崇喜给还原地契不责偿[3]741,叶朝给还宅院原券且时加周恤[3]737-738。
6.帮助病人五件
张典“施舍药饵,活人无算”[3]725,杨克举“到门即出药调理,疾愈不受谢”[3]731,马松林、马柏林兄弟“精诊视,有聘之者兄弟同造,互相质证,疗病恒十不失一”且“兄弟皆不言谢,人亦不之谢,知谢之勿受也”[3]745,黄绅“尤精痘疹,不计资,人请辄往”[3]730,翟天爵“精于痘疹,概不受谢”[3]710。这正如明人吕坤所言:“世上养生之法,积德之术,医为第一。”[9]
7.帮助外地人八件
多发生在本地。如散者聚之:洛阳王姓夫妇避荒,欲卖妻以偿店资,张健龄替其结清,并厚遣之[3]729;宜阳李姓夫妇寄住南关,欲卖妻以偿人钱,王廷选“慨然出资代还,俾夫妇得完聚焉”[3]730。受害者援助之:王国柱力挺襄阳寄居者保护家产,搭救从登封被拐至汝州的母子三人[3]712。幼者育之:“嘉庆十八年大饥,流亡载道”,陈鸿声“尝买一幼童,恩育之,及长,焚其券,纵之归”[3]737。饥者饱之:阎琚“恤太康之流民母子不至饥死”[3]721。殁者葬之:“凡外来孤客殁而无归者”,席汝璧“俱助棺埋葬之”[3]714-715。
个别的也发生在外地:道光十三年(1833)陈鸿声到南阳经商,“适岁饥,见鬻女者,怜之,出银百余两,买五口携归”,并以义女待之,“及长,皆择配而嫁之”[3]737。
(三)还遗金
还遗金即归还别人遗失的财物,占比第三。它貌似“小善”,“固足以厚人心、激流俗已”[3]705,从而被大书特书。具体表现有二:第一,它是重义轻财最直接的表现,从而最具代表性。在该版汝州志中,还遗金义举共计二十九件,却有二十三个人仅凭这一行为而荣膺义士称号。第二,它不受财力、职业、功名等条件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从而最具广泛性。比如“家最贫”的滕騕[3]734,家贫困而“一门好义”的胡起龙[3]734。另,该版汝州志中明言其农民身份的义士仅有三位——马善学[3]710、丁成[3]726、傅全[3]736,不过他们都有还遗金的行为。
(四)赈济
赈济在这里专指用钱或衣服、粮食等救济灾民,占比第四。包括民间自发和协济官赈两种形式。
民间自发十七件。多为赈饥。或捐粟,如嘉庆十八年(1813)大饥,马卓群“于本村每日给饿者面一瓯,赖以存活者数百人”[3]742;或施粥,如“康熙六十年岁大饥”,陈贵彝“力施粥,以救饿者,全活甚众”[3]711。这势必要消耗大量的粮食,为了筹粮,义士们结合自身情况,想出了不少办法。如王家安利用自己管理社仓之便:他于嘉庆十八年(1813)“充膺本里社正,领仓谷三百九十余石,年荒尽以赈饥”,“至二十年如数赔垫入仓”[3]739。如张培基采用平粜之法(8)灾荒时期,平粜比免费施粮或施粥更为理性且持久。详见宋玉珠:《明清时期商人的救荒思想研究——以徽商为例》,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期,第9—11页。:“嘉庆九年春旱,市镇绝粮”,他“乃捐资向滍阳贩米以归,减价平粜,耗资五百余金”[3]737。除了赈饥,也有个别施棉衣的:崔昌“尝于冬月施衣施粥,赈济贫民,历久不倦”[3]721。
协济官赈六件。四件捐粟,更有如贾嵩秀“首倡”之者[3]737。两件捐钱:如嘉庆十八年(1813)大饥,“州守熊设厂煮赈”,张应辰“捐银二百五十两助之”[3]739。
上述赈济义举多半发生在嘉庆十八年(1813)至十九年(1814),协济官赈全都集中于此时,1813年民间自发的赈济也多达七件。这与当时河南合省大旱的时代背景相符。
(五)孝顺
孝顺即奉养父母等尊长,占比第五。除了具体孝行不明者八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顺从尊长意志五件。四件与笃同气相关,如李增瑞让产与弟[3]717,张生文[3]711-712、李大赠[3]738给出嫁姐妹田屋,张勉收养出嫁姐妹及外甥[3]710。杨文选则是为了达成父母行善的心愿:“父乐善好施,惟命是听”,父殁后事母益恭[3]741。
第二,侍疾三件。吴尽忠久侍母疾[3]715,王伟侍奉父病备至[3]718,冯吉衣不解带者月余以侍亲病[3]733。
第三,独力奉养一件。“诸兄皆贫苦”,任绍祖“独任”其母之“生养死葬”[3]720。
第四,亲人去世后哀戚异常一件。赵纪因母亡“哭泣丧明,逾年始愈”[3]712。
第五,还产归宗一件。胡紫芝之父曾“出继马姓,受田百余亩、屋一区”,后来“马生子,胡本宗无嗣”。胡紫芝重孝义,不愿贪此“腴产”而使“本宗绝嗣”,“遂还产归宗,舌耕养母”[3]714。
(六)友悌
友悌,谓能与兄弟相友爱,占比第六。除了常见的互相供养,还有“我忍得田宅失手足耶”[3]709的骨肉深情。
抚弟事兄九件。以抚弟成立者居多。或供养之:李本修之母去世时,“其季弟生方五月,修有女亦在襁褓中”,他“令其妻将女寄养于人,而乳哺弟”[3]721;或教养之:李倓“为两弟延师课读,均得入庠”[3]715;或为之成家:伍于宁“为弟于容娶妻,继又为之续弦”,自己却鳏居数十年[3]711;或为之立业:杨圣诏“为兄弟完娶,已而析居,分给田庐,俾资存立”[3]718。反之,奉养兄长者也不鲜见,尤其是他们老病时:“兄于廷老迈”,伍于宁“自忍饥寒,供兄衣食无缺”[3]711;陈运泰“幼失怙恃,赖兄嫂抚养成立”,“后其兄病痿,运泰事奉不衰”[3]719-720。
供养亡兄(弟)家人六件。多为兄亡后抚教孤侄、养赡寡嫂:“兄谦早亡,遗寡嫂弱侄”,李恭“善抚之,嫂黄氏以旌表入祠,侄大云已列武庠”[3]727;还有为亡兄立嗣的:兄亡后,陈运泰“事嫂如母,以长子从仁承嗣,数十年绝无间言”[3]720。当然也有弟弟早逝的事例:“弟大定早亡,遗二子俱幼”,李大赠“抚如己出,延师课读”[3]738。
轻财物以笃同气三件。同胞之间已然难得:析居时姚嗣兴将“己所应得分给之”,后“兄弟暨诸侄有贫乏者,仍随时周恤之”[3]708-709;马良贵“尝出嗣二门”,“所得嗣产三项皆分给诸弟,毫无所私”[3]720。非亲生兄弟之间更是“人情所难”:虽然“家渐落”“子女众多”,武璧不忍其兄“归本生父”,遂“请凭亲族,愿与兄永造同居”[3]709。
(七)正俗
正俗致力于构建公序良俗,占比第七。其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是不离伦理道德、行事准则。
示范感化两件。马文明“为人刚方正直,学者比之王彦方云”[3]708;唐新业“天性淳笃,行重一乡”,其德甚至教化了耕牛[3]709。
信守约定两件。李云蛟之父“尝于崇祯年贷某银百两”,后双方俱殁,文约也已不存,他仍“勉力措还”[3]708;杨若时与同学马星燝曾“有婚姻之约,而礼未成也”,后马星燝病故,“杨守前诺,卒以女妻其子振垣”[3]708。
治家有方三件。马懿“教子与孙有方”[3]713;陈运泰“家法整肃,训子有方”[3]720;杨岸清“著有家训数十余条,刊以行世”[3]747。
解纷息争两件。唐瀛“居心平易,喜为人排难解纷”[3]715;张永健“解纷息讼”[3]733。
包容谦让两件。有欠自己地价不偿“翻作无礼状者”,唐瀛“置之不较”[3]715;阎光奇“性谦退,凡事让人”[3]716。
劝人为善三件。如“有魏氏女适黄姓,遇岁歉,夫家欲鬻以自给”,“女胞叔以金赎之”,却很快“以倍价强嫁许姓”。李天定知道后,“以义责许”,“许惧郎,令女母领回,仍归黄姓,夫妇得完聚焉”[3]728。杨岱则捐资刊印善书善文[3]746。
(八)同居
同居即不析产不分居,占比第八。它既强调同居时间长短,也强调家庭关系好坏,体现出中国传统大家庭的基本特征:其一,累世同居。王嘉图家“六世一堂”[3]714;王模家五世同居[3]722。其二,家庭关系和睦。张勉“与弟同居友爱,人无间言”[3]710。其三,经济一体。“诸兄皆贫苦”,任绍祖“独任”母亲之“生养死葬”,却“仍与诸兄合爨”[3]720。
(九)抗贼
抗贼是在发生动乱时保一方平安,占比居末。仅见两件,且集中于嘉庆(1796—1820)初年:“嘉庆二年楚匪猖獗,乡里震惊”,李大赠“出粟百余石修筑寨垣,一村恃以无恐”[3]738;“嘉庆六年,宝邑翟家集教匪猖獗”,州守令李振南“亲率乡众驱逐匪类”,事平[3]740。这在数量上显然过少,因为汝州地处伏牛山区,战略位置重要,战事频发,抗贼义举绝不罕见,所以上述只可谓比较突出者。
总之,就义举而言,该版汝州志中的义主要也是地缘之义,即它必须义笃乡里。无论是用财力,还是用能力、气力,只要行义的对象不是自己的配偶、子女,就是做义举。换句话说,义士的行义对象不仅包括乡邻、宗族、兄弟、出嫁姐妹,甚至包括父母。随着亲的范畴愈窄,义举对象的范畴愈广。这是中国自宋代以后,义进一步深入血缘关系的最终结果。
另外,上述义举有类别之殊,而无高低之分,所以一如该版汝州志所收诸事迹,义举不是只跟钱有关的事情。遗憾的是,细究之下,因义举“急人之难,济人之穷”[3]705的性质所限,义士普遍具备一定的财力,其义举大多需要消耗财物。以孝顺义举为例,与常见孝行相比,该版汝州志中的孝顺义举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轻财物,并突出表现在顺从尊长意志、独力奉养、还产归宗等方面。当然,这也可能是纂修者故意为之,以示这些孝义之士与《孝子志》中的孝子之区别。
结语
义士本来是灾荒、兵火等事有不虞的副产品[10],但在《直隶汝州全志》中,清代义士的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其风评既基于赈济、舍身等偶然事件,也基于日常美德。对此,该版汝州志在《义士志》序中即直言:义“岂必以杀身见奇哉”,“天下事凡有所为而为者利也,无所为而为者义也”[3]705。正因为如此,只要符合硬性条件,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义士。第二,义士的行义对象进入血缘关系团体。明清以前义士之义限于非血缘关系团体(9)血缘关系团体则归入义夫名下。详见那晓凌:《从“义夫”的进化史看“义”的走向》,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15—119页。,它的对象可能完全是陌生人。此时义士的行义对象也不必是本地人,义举也不必发生在本地,但义士之义不仅进入血缘关系团体,而且由远及近,直至以赡养父母至亲为义举,核心家庭本位已初见端倪。总之,在清代地方社会,义士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而在地方志中占据一席之地,且《义士志》在《人物志》中的篇幅是最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