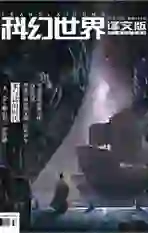星环奏鸣曲
2021-08-26[美]威廉·莱德贝特 翻译/桂子香
[美]威廉·莱德贝特 翻译/桂子香
我重播了托蜜叶的遗言十七次,还是不明白这句话有什么意义。
“他们还只是宝宝啊。”她想表达什么呢?
她和她的弟弟考非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她骂他是个贪婪又自私的畜生,说他为了“巨蟹座55”星系①的采矿权竟然谋杀了亲生父母。她控诉的内容都关系重大,但被考非勒死时,她并没有尖叫着求助或者求饶,只是用尽最后一口气说:“他们还只是宝宝啊。”
趁考非忙着把他姐姐迅速失去温度的尸体用袋子包起来,我又一次重播了她死前的录像。
他把打包好的尸体固定在了控制室的舱壁上。“她为什么会说‘他们还只是宝宝?”我问考非。
他无视了我的提问,专心操作着“印第安之夏”号准备通过星门。
“這不是你的错,”我说道,“如果你去自首的话,我应该可以为你辩护。你签A.I.让渡条例时才18岁,你的大脑还在发育期。在大脑中安装我这样的A.I.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脑损伤,以前也有过这种案例。”
“闭嘴,”他低声吼道,“否则老子连你一起杀了。”
这个威胁很有效,他只要说出一个口令我就会死
去。“我”就安装在他的大脑和颅骨之间的凝胶状基质中,我有将近一千个接口和他的大脑皮层对接着,但我还是无法阻止他扼住托蜜叶的喉咙。
而且他可以随意把我从大脑里删除却不用负任何责任,我没有“人”权可言,他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但是我还是留了一手的。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救下托蜜叶,也许我能阻止他离开太阳系。我下令让我的纳米汇编程序搭建好最后一毫米绞线,这样我就可以绑住他的脊柱。
他杀死托蜜叶时一定非常愤怒——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我一直在监测他的生物化学水平——但是这并不是一次冲动犯罪,不是那种一怒之下做出的无脑行为。在她上船之后,他就故意把“印第安之夏”号开到了一个无线电干扰区,飞船无法连接到任何网络,无法发出任何消息。我们都被他困在了船上。
“你跑不掉的,”我说,“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逮捕你,有太多的行程记录表明托蜜叶上了你的船。”
![]() 他冷哼一声,闭上了眼睛。他把我从控制线路中切断了,我失去了连接飞船的权限,无法连接到音像设备,只能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一些模糊的图像。但是当他的呼吸频率突然变急促时,我推测“印第安之夏”号已经开始加速,逐渐靠近星门。
他冷哼一声,闭上了眼睛。他把我从控制线路中切断了,我失去了连接飞船的权限,无法连接到音像设备,只能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一些模糊的图像。但是当他的呼吸频率突然变急促时,我推测“印第安之夏”号已经开始加速,逐渐靠近星门。
我必须做出决定,等我们到新的星系就太晚了。如果我启用脊椎绞绳,我可以阻止他带着托蜜叶的尸体离开太阳系。他将会被逮捕然后接受审判,但是我也会受到惩罚,我私自在宿主的身体里隐藏了纳米汇编程序。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他们也许会大发慈悲免了我的死刑,但是谁也说不准。然而对于自我毁灭的恐惧并不是我犹豫不决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如果阻止考非,我就永远见不到那些会唱歌的星环碎石了。
我曾申请成为考非父母的共生体A.I.,但他们无视了我。二人死后,我重新向他们的子女发出了这个请求,三个月后才得到考非的回复。最后他终于同意让我搭载,于是我离开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岗位,离开之前的宿主沃克博士,转移到考非的大脑里。因为A.I.历史上曾出现一个狂妄自大的祖先,我们被禁止离开人类宿主独立存在,但还是有权在接受我们的宿主之间转移。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气态巨行星。当我看到第一份关于“巨蟹座55”星系的报告时,我就被迷住了。星门探测器到达那里之后,上面搭载的无人机立刻被派出去调查。很快科学家们迅速发现,该星系中最大的那颗气态巨行星外面,有一圈由结晶体构成的星环碎石,它们正不断地发出自然产生的无线电信号。
发现这里的第一年,各种学术讨论和理论分析的数量暴增。但自从研究人员认为这里的无线电信号只是一种奇怪的自然现象之后,星门总署就拒绝派出更多的科考队。而早在星门探测器到达“巨蟹座55”星系的前五年,派特森夫妇就像抽中彩票一样获得了这里的采矿权。不管是用于科研还是旅游,这种奇怪的自然现象让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于是关闭通往这里的星门,开始研究如何赚钱。接着他们就去世了。
考非真的杀死了他的父母吗?他为什么要挑这个特殊的时间匆忙赶去那里?在如此多的未知的事情中,最令我在意的还是托蜜叶临终的那句话。她是在指那些星环碎石吗?它们是宝宝?
我必须要看看它们。我必须要搞清楚。想要了解这些星环碎石的欲望胜过了一切,所以我迟疑了。
三分钟后考非放松了下来,这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航向修正。
当考非驾驶着飞船在一堆油轮、货船和客船后面排队时,我听到他和木星星门控制台的人闲聊。其他的船只都是前往土星或者内行星带的,只有我们的目的地是41光年外的星系。
考非切换外部摄像机的影像,检查着“印第安之夏”号前面推着的小货箱。它们像火车车厢一样整齐地固定着,表面有一层强力的磁场,避免受到木星辐射的影响。但是在通过星门时这些磁场得关掉。这就需要一连串复杂的操作,在恰当的时机灵活地开启和关闭磁场,但是他不打算让我辅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答应我的共生请求。
一开始星门还只是主显示器上的一个小点,很快就填满整个屏幕。考非先将飞船减速,等他输入密码与“巨蟹座55”星系的星门建立量子链接后,立马结束了减速过程。
穿过星门时,里面复合型支柱构成的网格以5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我们靠近,大部分人类都會产生一种高速飞向一堵墙的恐慌感,但是考非没有丝毫畏惧。就在第一个货箱撞上网格时,那些支柱就像闪闪发光的银丝一般勾勒出了它的轮廓,然后放它穿了过去,其他三节货箱和“印第安之夏”号也跟着通过了。
摄像机的取景框被眼前这颗比木星大四倍的气态巨行星填满了,它表面上有二十多种介于黄色和橙色之间的颜色。官方名称是“巨蟹座55D”行星,但因为它的结晶星环就像一串散落的金粒一般闪耀着光芒,大多数的行星研究员把它称作“彩带星球”。我被困在考非的脑内监狱里,只能通过他的眼睛看到屏幕上的图像,却听不到这一万两千颗星环碎石发出的“音乐”。
“考非?你承诺过让我研究这些生命形态的,但你不把连接飞船传感器的权限给我,我连它们的音乐都听不到。”
他冷哼道:“那是在我杀了托蜜叶之前的承诺。”“我们已经穿过星门了。如果我现在报警的话,他们最快也要41年后才能过来。”
他浏览飞船的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后一言不发。而我什么都没看见。
“背叛你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的目的就是来到这里。再说了,你随时可以下令杀死我,或者再次断掉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他遮住面板输入了一些指令,接着我失效的那部分功能回来了,我成功连接到“印第安之夏”号的数据库和传感器。我又能“看”到了,随即沉醉在传感器和摄像头的数据洪流中无法自拔。
考非下达了封闭星门的指令。这样一来,在没有他的密码的情况下,哪怕是星门总署也无法打开星门。如果他们想要强行过来,就必须用无线电信号发送一个覆写指令。没有考非,我也休想离开这里。
“征求一下您的许可,”我说道,“我想现在发送我的探测器。”我开始检测那二十多个微型航天器,它们的大小和西柚差不多。在这次行动中,虽然我们名义上是合作伙伴,但是考非不仅让我用自己的资金购买探测器,还向我收了搭载探测器的费用。我们的合作关系更像是单方面的生意。
“当然可以,”他说,“但是你也该体现一下自己的价值了,我要你帮我做一些其他事情。”
考非解开安全带,将自己推离座位,飘往客舱后面的储物柜。他从柜子里取出一个长约半米的黄色筒形装置,是一个可编程的推进器。他用一个夹板一样的东西把他姐姐的尸体弄直,然后把推进器固定到了她的脚部。
“给这玩意儿编个程序让它避开星环,把托蜜叶送到这颗星球的大气层里去。”
我发射完我的探测器,然后按照考非的要求给推进器编程。
在他挤进太空服的时候我们俩谁也没说话,但是我
不断地在思索他说的“体现自己的价值”的意思。我一直都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同意我的共生申请。
“推进器模组准备就绪,”我说道,“你还希望我做什么?”
“你为什么现在才问我?”“我认为……”
“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乎,”他说着喀哒一声关上头盔,“你只想来到这里。在欲望的面前,你就跟我一样顽固且贪婪。”
我无言以对。
他咒骂着把托蜜叶拖入气密舱,她的身高加上脚上的推进器差点超出了气密舱的长度,但是考非还是想办法做到了。等他把尸体丢出飞船并启动推进器时,他甚至还哼起了小曲。
因为A.I.被禁止脱离人类宿主独立存在,我自从出生以来就一直陪在人类身边,但是在94年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无情的人类。考非没有一丝犹豫,他的生命体征没有丝毫变化,甚至没有停下道别。他只是启动推进器,看着尸体远去。当他点燃把托蜜叶送向大气层火葬场的主推进器时,他依然在哼着小曲,然后转身朝货箱走去。
我借助飞船的摄像头,目送托蜜叶消失在视野中,接着开始在考非的大脑里建造副本。我知道等到时机成熟他会毫不犹豫地抹除我,我也许无法阻止安装在我内部的抹除装置,但是我完全可以在那一刻到來时脱离我的本体。
考非在货箱之间移动没有借助绳索,他购买了一件顶级的短途旅行太空服,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充满气的微型飞行器。这件衣服外层的面料可以把一切光源转化为电力,并张开一个防辐射力场。使用这种高端太空服的人即便是不幸用光了十小时份的氧气,内置的电脑和通信系统仍然会永远运行下去。所以这些服装的制造者——通常是跃迁公司或者是星门总署,甚至在数年后还能完好地回收这些服装的宝贵硬件。
考非打开了第一个货箱,里面是一个II级迷你轨道拖船,而不是他上交货单上记录的自动星门扩建设备。
![]() 像考非父母这种抽中星门总署旗下星系采矿权的人,必须要在两年内扩建星门,然后把星门总署的重型激光设备带过来,以发射更多星门探测器,否则就会失去采矿权。
像考非父母这种抽中星门总署旗下星系采矿权的人,必须要在两年内扩建星门,然后把星门总署的重型激光设备带过来,以发射更多星门探测器,否则就会失去采矿权。
“我无法理解,”我说道,“为什么你要冒着失去采矿权的风险这样做?”
“看看这个。”考非说着给我看星门总署发出的通知。这是一个停止采矿的命令,上面说“巨蟹座55”星系将会重开“生命调查”项目。所有商业行为都必须立即停止,不准对星环构成物造成一丝一毫的破坏。唯一被允许的行为只有星门扩建活动。
这样一来,有些事就能说得通了。但我依然还有疑问。
“所以你为什么带了拖船?”
他打开一个货箱,检查里面的两个拖船。
![]() “我接了一个单子,要给土星某个卫星上的买家再提供8个这种星环碎石,那个买家想要这些星环碎石环绕在他‘与众不同的居住地周围。”
“我接了一个单子,要给土星某个卫星上的买家再提供8个这种星环碎石,那个买家想要这些星环碎石环绕在他‘与众不同的居住地周围。”
“再提供8个?你已经给他运送了一些吗?”
“就运过一个,而且想找到体型能穿过星门的星环碎石可真他妈费劲。你和你的小型探测器舰队要做的,就是帮我找到符合要求的星环碎石,然后装进货舱里。”
他的计划可谓十分细致,这些货箱都被特意加强过了,所以星环碎石被装进去之后连一丁点无线电信号都不会发出来。但是再细致也没用。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不仅会丧失这个星系的采矿权,你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前提是他们能逮到我,我回程用的是一个私人星门。”
“可是为什么呢?”
他大笑着解开一个拖船的固定锁,“每颗破石头可值两千万呢,有了这么多钱,我完全可以轻松地销声匿迹。”
金钱。为了这种东西他甚至可以囚禁并杀死他自己的亲姐姐。我想我永远都无法理解某些人类的行为,所以我将注意力转向探测器发回的数据上。这些小型
探测器中的一半会在星环外某处停留,记录频率为400Hz到5000Hz之间的所有无线信号,以期录到一个完整的、9小时的星环交响乐。而另一半的飞行器则会飞到那些星环碎石近处,记录下可见光谱内所有的图像信息,并记录每个星环碎石单独的歌声。我从考非的舱外活动服里分割出一大块的数据储存空间,想要得到更直观的感受。
然后我开始了倾听。
我们A.I.没有类似于人类的情感,我们也不想拥有
——尽管大众都认为我们需要——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具有欣赏美的能力的。尤其是蕴含在大自然中的那种复杂的美,还有人类作曲家创作的、符合数学原理的节奏之美。这些星环碎石合奏出来的作品同时包含了上述两种美,甚至还有更多。
当我第一次完整地听完星环协奏曲后,我发现每一段需要重复的地方都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其他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变化证明了这种现象不过是自然产生的巧合,但是我认为这些微小且有意的调整是为了追求完美。很快我就读取完了收集到的所有数据,我觉得我需要第二次探测,最好是我能亲自过去。
我把注意力拉回考非身上,然后沉默地观察着他把最后一个拖船送出舱外,这些拖船前端的夹板锁被改造成了一个直径三米的环状充气保险杠。
“給我找8个星环碎石,要那种直径在5到6米之间的,然后用拖船拽回来。”
我本可以和他争论或者干脆拒绝的,那些探测器只听我的命令,他向我收探测器的搭载费用,就默认探测器的权限是属于我的。但是我还是决定配合他,这样一来,他寻找和运回这些小行星的速度就完全掌握在我手里。
“好的,我会照做的。”我说。
“还有,别想借此机会研究它们。”
考非把偷取星环碎石的计划交给我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完全没有跟我谈判的筹码。要是他自己来定位和收集合适大小的星环碎石,可能会需要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所以尽管他会抗议,但是我还是会故意延缓这个过程,直到我能完成我的观测。
在我检索合适的星环碎石时,考非返回“印第安之夏”号里打了个盹。在他熟睡期间,我完成了镜像服务器的搭建,并且把主处理器转移到了那里。然后我调用了一艘拖船的机械臂,把另一艘拖船上的备份通讯器移接在了“印第安之夏”号的舱外。由于机械臂有限的灵活度,这项任务既缓慢又困难,但是完成之后,我就可以把所有收集到的数据存到这个通讯器里。万一考非真的运气好,彻底将我杀死还回到了太阳系,这个通讯器就会不断重复地向外发送我的研究资料和我的遭遇。
3小时后考非醒来,看起来十分生气。我告诉他,在这大约一万两千颗星环碎石中,我只找到了5个能装进货箱、通过星门的个体。
“我不知道你他妈的在跟老子耍什么花样,”他大叫道。他的愤怒指数一路飙升,一边摔着控制室里的东西,一边挤进舱外活动服。“但是老子已经受够了你的缓兵之计了。”
“我向你保证我没有拖延,”我说。我知道如果他使用“印第安之夏”号上的传感器手动扫描星环的话,他可能会需要30多个小时才能扫描完毕。然后,我忍不住又刺激了他一下。“不相信的话,你就自己干呗。”
他默念了几句咒骂我的话。我把他目前的愤怒指数和他杀死托蜜叶时的做了对比,发现还没那么高。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想杀我,根本不需要达到那么高的愤怒指数,我就像是在玩单人的俄罗斯转盘。我的镜像服务器已经搭建完成了,就算他下达了杀死我的指令我也不会真的死去,只是我可能会失去所有探测器和传感器的控制权,也就意味着我对星环碎石的探索可能会就此结束。
“你不是找到了5个,有拖回来吗?”他问。“没有,但是第一艘拖船……”
“该死的,”他的愤怒指数再次飙升,气得咬紧了牙关,最后还是冷静下来,“快点把那5个拖回来,咱们赶紧他妈的溜吧!”
“我刚才想说的是,第一艘拖船就快完成和一个星环碎石的轨道匹配,应该在20分钟内就可以往我们这里拖拽了。”
考非什么也没说,只是离开飞船,给货箱内的气垫充满气。我知道他大概率不会在我完成任务之前断开我的连接,所以我专心地查看探测器传回的数据。我让一个探测器飞近了那颗我打算抓捕的星环碎石,立刻发现了不对劲。
这颗星环碎石离一颗更大的星环碎石仅仅十五米,指引着后者行进的轨道,这让我联想到改变小行星轨道的重力牵引设备。大一点的星环碎石表面和我之前近距离观测的其他的不太一样,我调整摄像机的焦距,仔细观察起来。它原本质地紧密的晶体网格状表面上布满麻点和沟槽,其中还有一大块彻底脱离了,露出了空洞的内部。我再次调整焦距,让取景框同时包含这一大一小两颗星环碎石,然后调整摄像机的灵敏度,观测到了整个电磁波谱。我恍然大悟。
这颗受损星环碎石的磁场非常微弱。为了提供重力牵引,那颗小的有很强的磁场,还利用弓形激波①来保护大星环碎石免受损害。两颗星环碎石周围有一条碎石颗粒排成的尾迹,其中一部分颗粒应该就是那个大点的星环碎石丢失的。
位于星环黄道平面上方的探测器们已经收集完整个宏大的交响曲,我的一部分处理器已经听过一遍,还将其发回“印第安之夏”。但是当听到这对星环碎石发出属于它们的那段无线电信号时,我还是震惊了。
它们的部分只有2.9秒,却十分复杂优雅。我结合外部探测器和内置探测器记录下来的频率变化数据,列出并分析它们在这个片段中的参与情况。那颗大的星环碎石首先发出了最初的四个音节,小的在一毫秒之后完美地复制了前者的信号,接下来就是最后的四个音节,都是由小星环碎石独自完成的。
大的星环碎石是在教小的吗?我看到的是客观事实还是主观臆想?我只能把这类行为和我所知的生物对比,我想到了地球、木卫二和土卫二上的生物,包括人类。基于这些信息,我推断出自己看到的是一种高智慧物种的知识传递过程。也许这些星环碎石没有人类的情感,但至少有动物级别的知觉。
“他们还只是宝宝啊。”托蜜叶的话又在我脑海中响起。
毫无疑问,她是知道这一点的。
拖船抵达了,我又多花了点时间把它调整到最佳位置,熄火。我开始着手搭建一个更复杂的项目,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所以我把我的探测器发送出去观测其他四个小星环碎石。
“你他妈在干啥?”考非喊道。
“那个小的星环碎石和大一点的靠得太近,必须要很小心才能把它移出来。”
他可以从“印第安之夏”号的传感器上轻易地验证我的说法。
![]() “这些破石头比你想象中要结实多了,磕碰几下也没问题,赶紧拽就完事儿!”考非的偷窃计划会不会影响到这对小星环碎石的教学模式呢?星环的演奏从来都没有结束过,他们只是重复着同一首交响曲,就像是一盘循环播放的录音带,这种现象让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种无意义的自然现象。星门总署的调查队记录了星环150小时不间断的信号,其中有16个完整的章节。除了我之前提到的时长和节拍上会有细微的差别之外,有543分钟的交响乐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
“这些破石头比你想象中要结实多了,磕碰几下也没问题,赶紧拽就完事儿!”考非的偷窃计划会不会影响到这对小星环碎石的教学模式呢?星环的演奏从来都没有结束过,他们只是重复着同一首交响曲,就像是一盘循环播放的录音带,这种现象让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种无意义的自然现象。星门总署的调查队记录了星环150小时不间断的信号,其中有16个完整的章节。除了我之前提到的时长和节拍上会有细微的差别之外,有543分钟的交响乐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
我必须确认考非的计划对星环的影响,如果他的偷窃行为会扰乱这个物种的学习模式,那么我绝不会帮他。我必须等到我完全确认这件事再行动,而且我还需要四分钟来排序分析我自己收录的交响曲。
“考非?为什么你只要小的呢?那些完全成年体的星环碎石会唱的更多,只要你能扩大一下星门,运送这些大一点的星环碎石能卖更多钱。”
“如果我扩建星門,星门总署的爪牙就会一窝蜂冲过来。而且,我们知道小一点的能学会新的曲子,但是谁知道大的能不能学呢?”
好了,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回答。他的话证明了这些星环碎石的行为是一种教学行为,那我必须阻止他。“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我说,“我猜测这些星环碎石有着一套相当复杂的生命循环体系,那些能装进货舱的小星环碎石都和附近更大、更老的星环碎石处于某种教学模式中。我觉得这些小星环碎石就像是宝宝一样,在向大一点的星环碎石学习他们在乐章中负责的部分。跟你说的一样,体型小的确实能学会新的曲子。”考非没有回应我,就当我准备再重复一次时,我注意到他的愤怒指数在上升。
过了一会儿他才终于开口,并不是我预料中不耐烦地大呼小叫,而是一种低沉又危险的语调。“所以你认为之前所有研究过这些石头的科学家都是错的,只有你看到了真正的本质?”
“那些研究人员的结论是根据星门总署的初步调查得出来的,当时的观测和记录都十分有限。自从我们到达这里后,我就发现了一些在科学家的文献里从未提到过的现象。在还不清楚我们的行为会对这些生命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之前,我认为我们应该小心行事。”
我还需要两分钟时间,但是他越发生气了。
“生命体?畜生都知道疼,但这些玩意儿根本不会对外部刺激做出任何反应,所以我丝毫不担心我会伤害到它们‘敏感的内心。再说了,我已经拿到订金了。现在赶紧给老子把这些唱歌的石头拉过来装船!”
就在这时,序列分析模型完成了。我终于看懂优雅而清晰的歌声中,星环碎石们错综复杂的交互行为。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只有一小部分缺失了,正是考非之前偷走的那颗。通过这个模型,我还了解到这首交响乐是星环碎石们依次演奏出来的。音乐绕着“彩带星球”奏响,就像一架老式自动钢琴在永不停息地演奏。
这些发现都很有用,但还需进一步确认。我让探测器靠近,看到目标星环碎石中的第四颗紧挨着一颗破碎的大星环碎石。那个死去的同伴身上布满裂纹,周围飘着一层碎石构成的云雾,都是从它自己身上碎裂出来的。这颗大星环碎石没有任何的能量和热量,而它所处的位置正是缺失的那个音节所处的位置。我意识到我也许还是没有弄明白所有的真相,这个外星物种的生态学远超我的理解范畴,更重要的是,我目前所做的研究太少了。但是我还是要根据我已知的事实行动。
我继续拖延着。“我们没必要太着急,我不太确定。我觉得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到星环碎石们的唱歌模式。”
“就算他们真的在唱歌,也跟老子没有半点关系,这些噪音毫无意义,没有任何意义!”
“这些音乐的重要性和人类的行为是一样的。我是说,为什么人类挣扎着生存到现在,还继续向宇宙深处不断地进发呢?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考非的脉搏开始剧烈跳动。我有一瞬间觉得我是不是说得太过了,然后我就失去了安装在飞船外壳上的存储设备的控制权限。我知道情况终于变糟糕了。
“操,你这个油嘴滑舌的狗东西。”考非说。
他的怒气指数突破了警戒线,几乎接近他杀死托蜜叶时的指数。
“我只是想保护这次的研究成果,考非。这比你的赚钱计划重要得多,而且如果你杀死我,我缠绕在你脊椎上的绞线就会自动勒紧,让你瘫痪掉。”
这句话让他沉默了一小会儿。我以为我们可能会僵持下去,但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说:“克拉瑟斯,克拉瑟斯。”
就在他说出灭杀口令的同时,我的主体消失了。我再也联系不上飞船,和考非大脑的连接也被切断了绝大部分。我又一次回到了黑暗中,失去了一切外部联系,但是我还活着,而且我还有一个控制阀。我勒紧了他的脊柱。
考非尖叫着,他疯了似的大口呼吸。他的舱外活动服不断发出警告,自动调整供气水平。在此期间,他一直在咒骂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算是两败俱伤了,”我说,“但是如果你冷静下来,遵循我的指导来做事,我可以让你回到飞船上,还能让你回家。”
“克拉瑟斯,克拉瑟斯!”他又说了一遍。“没用的。”我说道。
“你这个该死的A.I.!”
“我死了你也会死,考非,而且目前看来,你正在自取灭亡。把你衣服的控制权交给我吧,我可以帮助你。”“我死也不会给你。”他的嗓音變得尖细而刺耳,可能是由于他过度恐慌,也可能是因为他衰竭的肺部功能。我考虑了一小会儿,然后用失效主体中的材料,还有一部分考非的骨头和组织,开始建造一些新的丝线。没有考非的许可,我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印第安之夏”号的控制权,但是他无法阻止我夺取他太空服的控制权。他并没有感觉到我新制的丝线从他脖颈后边伸出,连到了太空服的控制器上。
![]() 我使用太空服的喷气式推进器,最后一次将考非推到了那个小星环碎石和死去的大星环碎石之间。他终于放弃了用语音控制太空服的努力——我早就把那个功能取消了——转而言辞激烈地狡辩托蜜叶其实没有死,说我肯定是星门总署派来的间谍,是来偷走他的采矿权的。我无视他的胡言乱语,为最后的行动做准备。
我使用太空服的喷气式推进器,最后一次将考非推到了那个小星环碎石和死去的大星环碎石之间。他终于放弃了用语音控制太空服的努力——我早就把那个功能取消了——转而言辞激烈地狡辩托蜜叶其实没有死,说我肯定是星门总署派来的间谍,是来偷走他的采矿权的。我无视他的胡言乱语,为最后的行动做准备。
当把他推到指定地点后,我设置了自动保持位置的功能,确保他能和周围的星环碎石同步运行,然后我开始监听星环的交响乐。我听着高雅而复杂的音乐随着星环流动,直到乐声轮到这里。考非的太空服上的警报发射器能发出洪亮的声音,我让它播放了缺失的那一段,后面那颗小星环碎石立刻重复了其中的一些音节。我做了一些调整,等待着下一轮的演奏。
待在太空服处理器的新家里,我能够继续监听交响曲,然后补上缺失的那一段。我会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这个小星环碎石宝宝学会它自己应该演奏的部分。之后我就可以继续研究,等待人类的到来,审判我的罪行。
在氧气耗尽前的最后几分钟,考非一直在神志不清地喃喃自语,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似乎清醒了。
“为什么?”他问道。
我播放了托蜜叶的遗言作为回答。
考非的呼吸声停止后,只有音乐声——神秘、美丽而庄重——绕着“彩带星球”的星环,亘古不变地播放
![]()
责编编辑:吴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