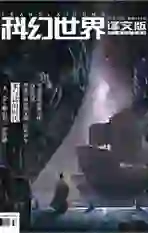亡者的脚步
2021-08-26[澳大利亚]杰瑞米·萨尔翻译/Renne
[澳大利亚]杰瑞米·萨尔 翻译/Renne
待在外骨骼里不好受,但比起暴露在充满冰刀的风暴中,皮肉像浸水的纸一样被一片一片撕掉,骨头像粉笔一样被一截一截切开,有外骨骼穿还是很不错的。熬过头一两个月就不觉得太痛苦了,但绝对也不可能舒服。
我抓紧机枪,金属表面冰冷刺骨。面板开始自动扫描敌对目标,并显示出天气状况。今天的沙尔星是一片冰冻的地狱,昨天也是这样,前天也是。天地一片灰白,连续的风暴和冰刀把地形凿得无比崎岖,也让我的机枪小队举步维艰。锋利的冰片打在机甲上,每一击都能削下一小块合金。随处滚动的碎石在我厚厚的靴子下咯吱作响,其中一些沾了水,亮晶晶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爱吃的果仁。想到食物,我的嘴里立刻开始分泌唾液。穿外骨骼的人无法吃喝,也不需要。所需营养通过一些管子直接送入你的身体,另一些管子则把你不需要的排出体外。导尿管是插上之后最疼的。
排气扇全功率运转,把严寒挡在外面。但问题是这东西效果实在太好了。汗水沿着我的背往下流,积聚在腋下。我活动了一下发烫的肩膀,往身后看了一眼。队员们艰难攀登,像抱婴儿一样把机枪抱在胸前。风暴这么大,出来巡逻根本没意义。如果不是基尔利长官亲自下令,没人想出门。
没人能对基尔利长官说不。
外骨骼抵御了大部分冲击,但因为爬山,双腿依然又累又痛。这里的重力和氧气浓度都跟地球不同,需要几代人来适应。早期移民者在这方面有明显优势
——他们已经与这颗行星的原生环境相处了几个世纪,自给自足地生活在这银河系的边缘。
我朝悬崖下望了望,崖底住着一群移民,沙尔星上有很多这样的移民聚落,被一圈防御型隔栏围住。聚落完全看不到人类活动的痕迹,这也正常,毕竟风暴太猛烈了。
有人走了过来,耳麦里传来瓮声瓮气的呼吸声。“雷麦斯,你没事吧?”是乔,她伸手搭在我肩上,沉甸甸的。“有点担心你,毕竟……对吧。”
我嘟哝着回了一句。那是漫长的一天,诸事不顺。我们遭遇了一群偷运武器回村的叛民。说不清是谁开的第一枪,我只记得胸口的金属在燃烧,我被猛烈的冲击力推下悬崖,在坚硬的岩石上翻滾。
外骨骼用生物泡沫修补了一些小伤,给我注入抗生素和镇痛的吗啡,但一些有着复杂名字的重要部位遭到了损伤。我被火速送回基地进行手术。骨科医生修好了我的骨头,治疗非常完美。但一等到我痊愈,他们就立即命令我穿上外骨骼回到野外,一刻也不愿意等。
在我看来,这是基尔利对我手术期间无所事事的惩罚。我想提醒他我当时还在昏迷,但想想还是算了。多年来被人一脚踢在屁股上、摔个狗啃泥的经历教会了我在适当的时候闭嘴。
风暴小了一些,风中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冰刀。我用意识命令外骨骼在聚落上聚焦,面板放大图像,仿佛我就站在几米开外。我拖动画面,完整查看了整个建筑群,发现屋顶的支柱都经过特殊设计,用来抵御严酷的环境。人们从屋里探出头,想看看外出是否安全。孩子们裹着厚厚的衣物在集市广场玩耍。男人们用拖拉机清理蜿蜒道路上亮晶晶的片状碎石,让每家每户能顺利走到外面的天然温泉。
我经常不懂,为什么有人愿意在这个离其他殖民星球数光年、鸟不拉屎的地方安家。眼前这样的场景就是答案。他们享受独处,远离喧嚣的人群,远离不断扩张的城市、繁忙的生活节奏、严苛的移民和工作政策,以及高昂的子女教育费用。
但为了这些就和联盟作对?太不值得了。
我示意所有队员跟上。他们大部分时候人都不错。诺瑟姆是个话痨,小代不太说话。
“你从来没吃过培根?”诺瑟姆对小代说,“不会吧?”
小代在肩甲上刻了数字13,这是某种闹着玩的迷信。他耸耸肩,数字在淡淡的光线下闪烁。“我长大的地方吃不起那么贵的肉。”
我也是。我长大的那所孤儿院对我们的饮食不太上心,连合成食物都很少提供。那东西吃起来像塑料,但作为唯一的食物来源,我们依然像狗一样激烈争抢。争抢时造成的伤口依然留着疤,藏在外骨骼下面。
“以后一定要吃上一次,”诺瑟姆说,外骨骼随着他的动作发出摩擦声,“那种浓郁多汁,带着一层厚厚脂肪的大培根。”
“别忘了,”乔伸展手臂附和道,“还有土豆煎饼。”“是的,是的,土豆煎饼也要。”
我笑了。聊吃的让人感觉很好,但大家都知道在这鬼地方,这么奢侈的享受是不可能的。我一直盯着聚落,诺瑟姆走了过来。“我们要过去吗?别啊,雷①,我的腿要疼死了。”
乔笑道,“联盟士兵永生不死,你忘了吗?”
这是一句老话。以前我们没有外骨骼,死亡率比现在高得多。当然,为保护士气,这事不能让身处后方的联盟成员知道。所以,即使一名联盟士兵的脑浆像烂番茄一样飞溅,联盟也不会为他宣布死亡。不过我感觉基尔利下属的部队从来没有死过人。人们称赞他的指挥能力,但其实真正保护我们性命、让我们至今还能喘气的是这些外骨骼。
我开始往下爬,寻找能作为落脚点的突出石块。不用回头就知道,小队成员全跟在后面。
我们沿着崖壁突出的一段往前走,崖底溪流中白色的浪花拍打着长满青苔的岩石,头上传来隆隆声,许多圆石顺着崖壁滑落,一个笨重的身影从我的面板屏幕前跑过,一手拿着单筒镜,脚底打着滑冲向聚落。
![]()
![]()
![]()
诺瑟姆咯咯笑道:“看来要暴露了。”
“是个孩子。”小代把机枪收在背后,含糊地说。
“我们本来就不打算藏。”我提醒道。这个地方叫蒙迪,是少有的不用子弹招呼联盟士兵的聚落之一。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痛恨想要占领他们家园的联盟,只不过他们知道贸然开枪是不明智的。
像往常一样,众人注视着我们,目光中有对高科技装备的畏惧,也有难以掩饰的仇恨。小孩在大人的小声叮嘱下,纷纷跑回屋内,有几个回头偷瞄我们一眼,好奇地交头接耳。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走过来,身上穿着缀满补丁的外套,“你们要干什么?”
他手指微动,朝别枪的地方挪近了一点,我立刻注意到了。“别的聚落有什么消息吗?”我问。我试着站在他的角度看问题:一个辛苦养家的男人,面对手持武器、全副武装的闯入者。“任何消息都算。”
“消息?”他问。
无须我提醒,他很清楚他们和联盟之间的交易:他们提供各种风声传言,用信息换平安。“潜在的麻烦事。”
他摇头,“没有,我们不想和那种人接触。”我想相信他,真心的。但这不是我的工作。
一个女人走上前来,“我听到一些消息。”她死盯着我,目光穿透了镜面一样的面罩,“是伊里乌姆,他们在商量制造炸药,很多很多炸药,打算做出来埋在你们的基地。”
一絲寒气钻进我的身体,渗入我的血液。好吧,我以为这次任务会很轻松。
“伊里乌姆是什么地方?”我问。沙尔星上每天都会冒出新的聚落,有的露天修建,有的藏在迷宫般的地下洞穴里。
我注意到男人和女人交换了一下眼神,男人的手指又动了动。他们悄声交谈几句,不时看我们两眼。大概是在计算我们的命和他们孩子的命哪个更值钱?我全身紧绷,贴在外骨骼内侧。空气都紧张得都要凝固了。他们应该不会愚蠢到开枪吧……应该吧?
女人又回头望了望众人,接着将伊里乌姆的坐标发给了我。面板显示器上,一个蓝色的方块出现在地图上。
我含糊地道了谢,把坐标分享给其余队员,便踩着碎石往回爬。我能感到他们的目光落在我背上,几乎要把后背灼出洞来。不怪他们,我小时候在新瓦勒让生活时也不喜欢联盟。我那时充满愤怒,四处惹祸,为了寻求刺激而偷鸡摸狗,任性地挑战法律。
后来我听说,联盟要扩张领地,那些从他们那儿独立出去的殖民地也打算重新吞并。薪水还行,免费吃住,是个养活自己的好出路。当了大半辈子穷鬼,突然有了下属,感受着握在手中的权力,对人发号施令,看着他们服从,感觉很好。我很擅长当领导,一路晋升。但我发现,我最爱的还是队员们随意地冲我打招呼,并不因为见到我而紧张。他们全力支持着我,每次我下令开火时,都真心相信我的判断。
我呼叫了基尔利长官,他的脸出现在面板屏幕上,灰色的瞳仁让人想起机枪,在眼眶里游走。“你有什么事?”他冷冰冰的脸充满算计,但声音却像慈父般温柔,仿佛在和他最宠爱的儿子说话。
“长官,蒙迪这邊有人提供消息,伊里乌姆可能在私制炸弹,”我停了一下,让他好好消化这个消息,“可能打算装在联盟基地。”
基尔利的灰眼睛眯了起来,他只用了一秒钟就做了决定。“立刻去伊里乌姆,必要时允许使用致命性武力。我们自己的人一个都损失不起。”幽幽的灰色眼睛像两根钢钉一样死死盯着我,“雷麦斯,记住,联盟士兵永生不死。”
通话结束,他从不说多余的话。
面板显示所有队员都已经接到指令。我断开通信连接,“都准备好了吗?”
“早等不及了。”小代擦拭着他的机枪,似乎沉浸在
![]() 某种刺激而血腥的幻想中。谁知道他面板下的脸长什么样?我认识这些人几个月了,他们对我来说与家人无异。但一直以来我都没见到他们的脸,也不是很想见。有些面具还是不要揭开为好。
某种刺激而血腥的幻想中。谁知道他面板下的脸长什么样?我认识这些人几个月了,他们对我来说与家人无异。但一直以来我都没见到他们的脸,也不是很想见。有些面具还是不要揭开为好。
乔活动了一下宽阔的肩膀,“带路吧,雷。”
于是我领着小队,沿着一块巨大的基岩行进,河水在我们脚下流淌,拍打着岩石,溅到空中。我真想试试水花溅在脸上的感觉。
路上,诺瑟姆和乔又拌起了嘴,好像在争论如果发现了外星人,它们会长什么样。猛烈的风将他们的话断断续续传到我耳边。我们爬上峭壁,穿过广阔的微微发光的黑色沙地。我不止一次想道,如果地势没这么陡峭难行就好了。这样,一辆陆行车就能把我们连带外骨骼一起运到目的地。
小代在我旁边喘着气,没有加入争论。我停下来松了松筋骨。身上的肌肉似乎被灌了铅,手臂、腿和肩膀都在酸痛。紧贴皮肤的外骨骼之内,我的身体又被一层黏糊糊的汗水包裹着,空间更加逼仄。我用沉甸甸的手摸了摸后颈,穿着外骨骼,这就算是挠痒了。你会渐渐习惯在外骨骼中活动,但过程绝不容易,也绝对不可能舒服。
诺瑟姆和乔聊起了外星人征服人类的可能性,就在这时,一块尖尖的黑色石头突然变成碎片,岩石在我们周围爆炸。我扑倒在地,震耳欲聋的轰隆声的在悬崖间回荡。面板显示,大家的心率急速上升。“狙击手!”乔压低嗓子说道。
我感到关节僵硬,无法动弹。我一面数着秒,一面回头望了望,机枪小队没人受伤。乔趴在岩石上匍匐前进,挪过的地方刮开了一层砂砾。我终于能动了,也慢慢地向前挪。远处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我放大画面,聚焦在峭壁对面,这才看到了攻击者。一个人影穿着厚厚的皮毛,挥舞着一把带瞄准镜的狙击枪。我的外骨骼自动瞄准了他,用表示目标的方框框柱他的脸,下面显示:目标锁定。我不敢相信地眨了眨眼,一般外骨骼只在我们举起枪、准备射击的时候才会自动瞄准。我想退出,但瞄准画面并没有消失。
那人知道我们在看,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点——他竖起一根手指朝我们打招呼。这手势全宇宙通用。我差点被他幼稚的行为逗笑。躲回岩石后面后,锁定目标的方框消失了。大概外骨骼出了什么小故障吧。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子弹会钻进岩石,将它们炸成弹片一样的碎块。应该是用了爆炸性很强的弹药。
“你看,”乔朝着被子弹击中的地方点了点头,“离我们远得很。他有足够的时间瞄准,一枪一个把我们干掉。但这家伙显然只想吓吓我们。”
“有这样吓人的吗?”我抱怨道。但她说的没错,如果狙击手想杀掉我们,我们已经是死人了。这几枪只是警告,表明再往前就是他们的领地了。
![]() 风暴可怕的隆隆声从远处传来。我想狙击手应该自顾不暇了,但有准备总是好的。贸然前进本来也不明智,毕竟,关于炸弹的传言还不知真假呢。“我们绕路,”我对机枪小队说着,在面板上规划出新的路线,“把这片地方好好探一遍,免得对方有埋伏。”
风暴可怕的隆隆声从远处传来。我想狙击手应该自顾不暇了,但有准备总是好的。贸然前进本来也不明智,毕竟,关于炸弹的传言还不知真假呢。“我们绕路,”我对机枪小队说着,在面板上规划出新的路线,“把这片地方好好探一遍,免得对方有埋伏。”
众人戴着头盔点了点头,默契地排好队形,确保爬上对面峭壁之前,队伍的每个方向都有掩护。机枪小队紧紧挨在一起,熟悉的站位让我感到安心了些。我又能专心观察地形了。
我们就这样在这片没什么起伏的旷野中行进,呼啸的风裹挟着碎石和冰刀,摩擦着微微呈弧面的岩石,就像有人扔出了千万颗骰子。和平时的行军比起来,这简直是一种享受,不知道能持续多久。
几小时之后,外骨骼发出了提示音,表示我们接近目的地了。这段路很长,此时,被磨损的皮肤刚刚开始愈合,又伤上加伤。穿着这身装备,绷带裹几层都不嫌多。
“得走近一點,看清楚一些。”我对着话筒说。不排除蒙迪的人是闭着眼睛瞎说的,让我们白跑一趟。但还是得小心应对,不能拿人命去赌。
最后,乔跟我一起往前走。小代和诺瑟姆负责探索,他们带了设备,一边走,一边进行地形3D成像。
我趴在岩石边沿往下看,伊里乌姆比蒙迪大得多,人口也密集得多。光是我看到的就有好几百人。他们来来往往,有的在交谈,有的在玩某种全息影像游戏。笨重的深红色无人机在他们上空穿梭。一个螺旋形钻头正在一块岩石表面开钻。
接着,我看到了狙击手。
他的狙击枪靠在一根金属柱子上,他本人则举着一个保温瓶喝热水。皮毛披风的兜帽被取了下来,露出一张和这个星球一样冷酷的脸。除此之外我还能看出疲惫。这个人显然干了一整天活,急切盼望着回家。不过他朝联盟士兵开了枪,他是什么样的人都不重要了。
![]()
下方传来一声喊叫。对面岩壁上的哨兵发现了我们。
“该行动了。”我翻过岩石边沿,向下攀登,队员们随即跟上。下方响起警笛声,人群闻身而动。有的将小孩塞回屋子,关上房门;有的带着手枪朝我们冲过来。我给出命令:下到岩壁底部立即立定,机枪拨出来做好准备。
我们和对方的人面对面,小心翼翼地靠近,手指紧张地扣住扳机。一个看起来像头领的人朝前走了几步,他身材瘦弱,我总觉得一阵风就能把他刮飞。“你们要干什么?”他异常愤怒,“穿着铁皮衣服,拿着枪,这是威胁吗?”
“冷静点。”我一边打量他身后的武装人员,一边说。回答我的是更多人的怒吼,他们的脚步落在黑色的沙土上,窸窸窣窣。
“见鬼的混蛋,在我们的领地上乱插旗,你以为你们什么都能占完吗?”他吐了一口唾沫,身后几个人为他喝彩,“我们不跟联盟往来。”
我没法给这十几个拿枪对着我的人讲解跨星系政策法规,这种事还是适合基尔利。“你们是不是在做炸弹?”
他薄得像刀刃一般的嘴唇扭曲了。“什么?”“你们是不是——”
“雷麦斯!”诺瑟姆猛地调转枪头,瞄准一小块凸出岩壁的岩石。狙击手正藏在那儿,已经锁定目标,上了膛。更多人开始叫喊,给枪上膛的声音此起彼伏。
“马上离开。”他朝我吼道。
我指着狙击手,十几个枪口紧跟着我的动作。“来这儿的路上他朝我们开枪了。”我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外骨骼好像突然提高了功率,某个机构贴着我的肌肉疯狂转动。
“伯克,你个白痴。”头领大骂。
“你们有私藏炸药吗?”这句话我费了很大的力气,仿佛每说一个字,都有一个鱼钩伸进我喉咙里不断拉扯。
“你没资格问这些问题!”“把炸弹交出来!”
“滚回你们自己的星球!”
“你敢说这话?”乔上前一步。她那把机枪找人改装过,威力和散弹枪有得一比。
“我们当然有炸弹。”头领恶狠狠地说。我们全呆住了。
“真的有?”紧张的气氛迅速扩散弥漫在空气中。我感到胸闷气短,恨不得撕烂这身装备。汗水流进眼睛,我使劲眨了眨眼睛,又吞了一大口唾沫。“为什么啊?”
“当然是为了建设家园啊。炸开岩洞,把住处转移到地下,才能躲开冰刀风暴。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胡说八道,”诺瑟姆低声说,机枪握得更紧了,“他们在骗人!”
外骨骼突然像痉挛一样抽搐起来,我也跟着摇晃,两腿努力保持着平衡。我仿佛被卷进了一阵由静电形成的漩涡,我快速小口地吸着气,心脏猛烈敲打着肋骨。通过嗡嗡作响的外骨骼,我看到伊里乌姆的居民整齐一致地抬起枪口对着我,扯开嗓子大声叫喊,机枪小队同样大喊着回应,警告他们后退。我头痛欲裂,想伸手按住头盔,但不知怎么回事,双手抬不起来。我只能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双方用颤抖的手握住武器,来来回回说着威胁的话。
我想叫双方后退,好好讲道理。但我无法动弹,仿佛被扔进太空,冻成了冰块,无法与世界产生任何形式的互动。不管我怎么挣扎,依然被外骨骼牢牢困住。
接着,有了第一声枪响。
一个孩子从屋里跑了出来。他没有理会追上来的母亲,径直向我们冲来,大声哭泣着叫爸爸。出于本能,整个机枪小队转向声音的源头,枪口也跟着转过去。小孩的尖叫声在峭壁间回荡。
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什么也做不了。
孩子的父亲再也无法忍耐,朝小队一通扫射,其中一枪打中了诺瑟姆的护腿。
我没说话,甚至嘴巴都没有张开。但外骨骼用我的声音合成了两个字——只是短短两个字,但两个字就足够了:“开枪。”
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小队服从命令,子弹像雨点一样喷射而出,周围升腾起的浓烟连风都来不及吹散。大块的岩石被打碎,堆满石块的小车被炸成碎片。人们拼命逃跑,又一个个被密集的弹雨击倒。血液喷射而出,大片大片地溅在石头上。尖叫声此起彼伏,空弹夹叮叮当当落在地上。我感到血液凝固了,心脏猛烈撞击着肋骨。
但我被外骨骼困住,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着。几秒后,一切都结束了。
外骨骼放开了我,我瘫倒在地,激起一片尘土。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还有零星的哭泣声,是活着的人一边哀哭,一边用颤抖滴血的手指为死者按住伤口、
碎裂的骨头和从肚子里流出来的内脏。这次交火至少有十几个人倒下,全出自一条由我的外骨骼下达的命令。
一只手放在我背上,我想挣脱,却感到一阵无力。“雷麦斯,你还好吗?”乔问道,她的声音微微颤抖,似乎刚刚费力压制住了内心的黑暗面。
我喉咙被什么东西哽住了,最终只吐出一个“不”字。
不然我该怎么解释?
我再次抬头,看向那些正在死去和已死的人。他们在这儿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结果我们来了,把他们踩在泥里。
我挺直后背,皮肤上沾着滑腻腻的冷汗。“找到炸弹。”我嘶哑地说,“然后撤退。”
![]() 回到基地,我立刻收到基尔利要见我的指示。挺好,我也有些问题想问他。
回到基地,我立刻收到基尔利要见我的指示。挺好,我也有些问题想问他。
我快步穿过走廊,来到基尔利的房间。一群文职人员和技术员慌忙让道,免得被我笨重的外骨骼撞飞。“你好啊,小鬼。”基尔利坐在他的位置上,看我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同情,但我只觉得他卑鄙无耻。
我眨了眨眼,“为什么——”
“我都看见了。”他站了起来。不过,他依然比我矮一个头。“你缺乏胆色,于是我替你做了决定。”
“外骨骼,”我的手捏成了拳头,“是你控制了我的外骨骼?”
“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小鬼。联盟高于一切,从过去到未来永远如此。”
“但那些人,”我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们并不是威胁。”
“要确认了才知道,”他那双冷酷的灰眼睛盯着我,“不得不承认,你让我失望了,小鬼。”
“很高兴让您失望,长官。”最后两个字我说得咬牙切齿,我指了指外骨骼,“你休想控制我。让我做你的奴隸,我宁愿去死。我受够了,这玩意儿我再也不穿了。”
“你还是不懂。”基尔利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冷漠中带着一丝怪异,“你已经死了,小鬼。”
“什么?”我试着向前一步,但发现自己动不了,仿佛被定住了。外骨骼颤抖了一下,开始侵入我的皮肤和脊椎,铬合金挤压着我抽搐的肌肉。
“你在上次意外中受伤太重,还伤到了脊髓,”基尔利围着我转了一圈,就像买家在打量一件商品,“不救治的话,你就没命了,或者变成植物人。我们采取了必要措施。”
“什么措施?”
基尔利远程发出了一个指令,一大块镜面从屋顶慢慢滑到我左边。外骨骼发出震耳欲聋的嗡嗡声,将我的身体向左转,然后打开胸甲,露出下面裸露的、沾满汗水的皮肤。
只不过,我看到的不是皮肤。我的身上镶满了亮晶晶的金属。电线盘绕在我的胸口,有的钻进肉里。皮肤被细细的钢条分成小块,仿佛这具身体被拆开过,又像拼图一样重新拼在一起。两根宽宽的肩带将我固定,外骨骼内部充满略带粉色和紫色的触须,连接着我的身体。双臂的护甲也打开了,露出被灰色钢筋加固过的骨头,微微跳动的血管里不知流着什么,看起来远比普通血液更加鲜艳夺目。
接着,面罩打开,本该是我头盖骨的地方,我看见了千万根细细的电线、闪烁的小灯泡和各种微型零件,将我的大脑和外骨骼的动力机构连接起来。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永远拿不下来。
“这是唯一保住你性命的办法,小鬼。”基尔利用指节轻轻敲击我一起一伏的胸口,“只有外骨骼能救你,为你提供维系生命所需的各种物质。”胸甲重新合拢,紧紧贴住我的皮肤,就像关上了一扇牢门。
“为什么?”我抬起双手,“为什么?”
“你太珍贵了,我们损失不起。从街头混混到联盟士兵,你的成功之路堪称完美。机枪小队追随你,可以为了你而死战。联盟士兵永生不死,雷麦斯,至少我手下的士兵不能死,特别是你。”
“你这个混蛋!”话到了我的嘴边,却说不出来,没有声音。我仿佛被捂住了嘴,无法说话,就像被困在琥珀中的蚂蚁。
“我们需要一个领导者,雷麦斯,一个有名声,能服从命令、不惜代价、做一切必须做的事的人。”他向我指了指,仿佛我是他最得意的牲口,“你是完美人选。”
我突然能说话了。“拔掉管子吧,”我沙哑地说,“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再次伸出手臂——两只并不属于我的手臂,“我是个怪物。”
基尔利摇了摇头。“抱歉,小鬼,你必须继续为联盟效力,直到我们不需要你了为止。你已经死了,死人没有话语权。”
我没力气告诉他这么做是错的,不管怎样,他都已经做了。我将永远被关在这副由血肉、金属、护甲和神经组成的监狱里,无法感受浪花打在我脸上,无法真正成为机枪小队的一员,更永远无法和他们一起品尝培根。
“我们刚刚收到探子报告,有个聚落准备接收一大车武器。你去处理吧,下一个任务紧接着也会来。”外骨骼抽搐着挤压我的肉体,使我蜷缩起来,然后把我扔出了房间。我无力反抗,基尔利走到门口。“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等着吧。”
接着他便消失了。
![]() 我被護甲包裹着,走在走廊上,突然想到:是我在走路还是外骨骼在走?我咳嗽着发出一阵苦笑——还是抽泣?不重要了。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已经死了。
我被護甲包裹着,走在走廊上,突然想到:是我在走路还是外骨骼在走?我咳嗽着发出一阵苦笑——还是抽泣?不重要了。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已经死了。
一具行走的尸体。
责任编辑:钟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