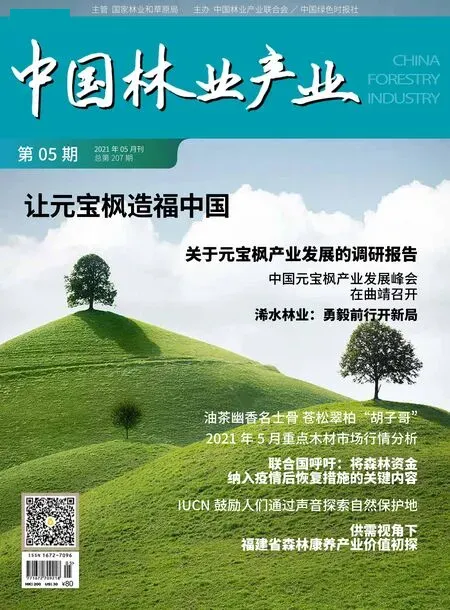榴花开处照宫闱
2021-08-24文那海
文 那 海
一
是五月了。熙和门外的石榴花开了。
犹如那些不经意的少年时光,无意去吸引什么,却让人直抵明澈而热烈之境。
榴花开的时候,走在紫禁城,有种莫名的欢愉。
这是在白天和黑暗之间感受到的毫无倦意的欢愉,也是宋人咏榴花诗句“枝枝叶叶绿暗,层层密密红滋”的沉静与暗涌。
生有热烈,藏与俗常。
在黄瓦红墙间,在繁密的绿意中,榴花星星点点,绚烂而不声张。
我猜想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称“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他当时或许正对着一树盛开的榴花。
在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见到了石榴的那抹红。
这是一个穿着绿衫红裙,坐着吹笛的女子。
她出现在这幅连环长卷的场景之中。长卷的迷人之处便是它常以极强的叙事性,在纵横绵延的时间与空间中,寻找最恰当的情感厚度。
韩熙载为避南唐后主李煜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所,在家中开宴行乐。李煜闻其荒纵,欲知情状,“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本欲借图画来规劝他,岂料熙载视之安然。”
画中的这个女子,身着的红裙,色调鲜妍明媚,如同开了一朵榴花,无法不让人将视线落于其中。
想必这就是让多少人拜倒的“石榴裙”。
原本屏气敛息的模样,一切缤纷奢华有着浮夸与无奈之味,或许尽皆消失,或许将陷入一团混乱。
这一抹石榴红,让人遁入若有所思的妩媚中。
一幅画在视觉上与我们日常的思虑极其妥帖,在这幅色彩的盛宴中,人物以石青、朱砂、绯红、石绿等色为主,室内陈设大抵以深棕、黑灰等凝重之色,浓丽沉着,色墨相映。
当我们可以在一幅画里承载更多的情绪,无疑也是一个孤独的人可以在这里度过等候多时的时光。
夜宴难尽欢。
唐寅的《临韩熙载夜宴图》,笔墨浓重,亦为传世之作。
唐寅还有一幅《韩熙载夜宴图》轴,则是将“观舞”中舞姬王屋山舞“绿腰”的一个情节加以补充,场景设在夏日的庭院,成为再创造的故事人物画。
葱茏的园苑,石榴花开得正盛。莲花池,桌上的一瓶榴花,点缀着新绿密叶。
如唐寅致友人信札所云:“丈夫潦倒江山花竹之间,亦自有风韵。”
倘若将场景放在秋日,多了几分萧瑟。夏日刚刚好。
纵然“北方谁唱延年曲,犹有倾城独立人”,亦是红尘俗世的忆旧。
在夏日,总有一份和煦的东西,如这榴花,使得这份悠然沁入的明丽而又极度深味的色泽,唤起人们对静穆的观照与飞跃的生命的觉知,还能怎样呢?
于是,人们酌满斑驳中夹杂着青翠的时光的酒杯。
二
那日匆忙路过,看到细雨中宫墙边的那两三枝石榴,正如火如荼地开花。
这样的时节,月季花也开得正盛,断虹桥、左翼门、慈宁宫,总有花儿艳非寻常。
御花园的山梅花,色白如雪,初夏的风拂过,满是淡雅的花香。
山梅花又称“太平花”,承蒙宋仁宗赐名“太平瑞圣花”,花开千百苞,却有分寸,并萃一簇,舒展又节制,据说是慈禧太后的钟爱之花。
紫禁城中的石榴,大都是经历一定年代的。你看它热烈,你看它静寂,没有看穿世事,哪来这般云淡风轻冷冷清清地娇艳如火。
这番的心性鲜活,风风火火,榴花开欲燃,突然,它就柔情起来。
说起来,让花朵都有意义是件无趣的事,就如每样事物都有其局限,包括柔情蜜意。
但榴花开的时候,心性怎能凝滞。这么热烈的生命,一种以最丰富的激情做出的证言,是某种灵性与深度的东西。一切艺术皆可当作某种证据。
恽南田痴迷于宋人石榴图,曾见宋人所画石榴,渲染数十遍,至无笔可寻,无色可拟,几乎神韵俱妙,心识之已久,始终不得法。
一日在白云精舍,刚好友人携一颗成熟的石榴,硕大丰丽,霜皮剥裂,正书家所谓壁折路。由此大悟,“因以宋人设色法图之”。
在文本上看到恽南田作的《安石榴图》题跋与末跋,“余凡写榴十数本,唯此为得势。揽之磊然,流珠欲滴;缃肤赤犀,晶彩陆离”。犹是进入诗与人生合一的浪漫的美学命题,将人置入醉境。
恽南田自小遭遇家国之变,后与父亲削发为僧,于灵隐寺苦度光阴。
他的《古木寒鸦图》萧瑟与哀婉,瑟瑟西风,寒鸦寻找归处,透着凄惶而又无可住的茫然。这是在南田绘画中很少见到的情绪。
或许是那一刻,黄昏古木,寒鸦无处栖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凄凉悱恻。
当世界从丰盛回到简单,不可把握的命运追逐着每一个人。
无疑,这当中,纠缠、矛盾、激切、疏远,一切的情绪,都只是在万化之中。
世人身上总是无可避免地遭受一些为人所无法摆脱的生命的内容,命运、衰老、死亡,让人迷惘的同时,艺术总是在寻找一种永远必定要回来的情绪。
我对经历最冷、最硬的情绪的人,依然去表达个体生命摆脱一切苦难的重负,他的心绪以及作品与大自然共频,有着莫名颤动的统一感的人,总是充满敬意!
就如此时,看到南田的石榴图,瞬间忘记他一生的颠沛流离,只有这份清净宽和的心绪,无边际地蔓延。
三
曾在云南澜沧江边的小村落,看到满枝白花的树,待到走近,才发现是白色重瓣石榴,与红色石榴完全不同,简直难以置信。也曾被杉洋古镇的粉石榴花惊艳到。
生命中有些事,沉重、委婉都不可说。
古物中的石榴,却让人有话想说。
石榴作为一种典型的陶瓷装饰纹样,曾以石榴纹抽象图案的形式出现在唐三彩陶器上。
作为喜庆吉祥图案,明代的石榴逐渐采取折枝花卉的形式与其他花果一起出现在瓷器的纹饰中。
到了清代,在青花、粉彩瓷瓶上,常常可以看见石榴纹饰。
相较于明代器物色釉的浓厚深穆,瓷器上的石榴纹饰用笔粗疏而古气横溢,康熙朝的石榴纹大抵行其缜密,于工致之中而寓其高古,雍正时期则是逸丽而秀倩,乾隆时期于繁密富丽之极而时露清气,“百花不落地”便是其中一种。
我们感受器物,牡丹绚烂,榴花火红,玉兰芬芳,见其光辉里有欢喜,便觉盛世升平,万花呈瑞,世道与人事皆是宽心与明朗,便有一种从心而发的宽慰了。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个“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款的剔红石榴花圆盘。盘面满雕石榴花,茂密的枝叶,花朵或开放,或含苞。
这是黄金时代的作品,是被光抚摸过的时刻锻造的漆器。结构、材质已经无与伦比,浑然天成。
器物制作到了明代,已经进入游刃有余的时期。
一切都已更加开阔,可堂皇,可奢华,可简纯,又有朴素的念力,将一切控制得合理,极致。
与宋代定窑的白釉盘面上呈浮雕形的印花石榴纹不同的是,明代的剔红石榴花圆盘,以温和的、谦逊的特性,让我们进入难以想象的真实之中。
乾隆朝有粉彩百花不落地石榴尊,仿石榴形,侈口分五瓣为蒂,通体榴花、牡丹、玉兰、茶花、月季等繁密细致,各尽其妍,却又粉润清新,覆盖全器。
这是粉彩器之珍贵隽品,专供宫中赏花,历为藏家所珍。
榴花种种,澄明,浓烈,让人“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酣畅而通透。这样的器物,总是佳偶天成的。
各色花朵将整个画面填满,又不露出瓷底,烧制工序之繁缛,也绝非数人之力可成,故称彩瓷翘首。
此时瓷器上的线条、层次、颜色,都是一场奇异的相逢,又是预谋已久的布局。
如果说永劫、矛盾、苦恼、极乐,都是万物之源,那么生命力一定是充满激情的实在,它的存在势必使感性个体深挚、坚强。充实、宏大的生命力,早已幻化在器物之中。
有一日见清道光天蓝釉石榴尊,形如石榴,通体莹润,合“雨过天青”之意。瓷上刻折枝栀子花两株,清新怡人,生趣盎然。
这番的雅致与圆润吉祥,让人剔除凡俗种种,而这美意的表达,总能把自身中蛰伏的生命和缓起来。
四
不知宋人是如何数十遍渲染石榴的颜色。
我一直以为“石榴红”是用石榴染成。
直至后来看到一个科普文,说古代染红色的染色剂,主要是赭石、茜草、红蓝花、苏木、紫铆虫胶等。
周代开始用茜草染红色,它的根含有茜素,人们以明矾为媒染剂可染出红色。
但茜草不是正红而是暗土红色,后世逐渐发明了红花染色技术,才得到了鲜艳的正红色。
石榴皮的主要染料成分是鞣花酸类物质,可直接染色,也可以加媒染剂做媒介染色。
用石榴皮,还可染成一种素雅的浅黄色,称为“缃色”。宋诗“缃裙罗袜桃花岸,薄衫轻扇杏花楼”,着缃色裙子的女子,该是多么美妙。
《雪宦绣谱》将“缃”分老缃、墨缃、银缃,此色有深浅之分。《清稗类钞·服饰》中记载“香色,国初为皇太子朝衣服饰,皆用香色,例禁庶人服用。”此处的“香色”应为“缃色”。
单纯用石榴皮,还可染成“秋香色”。
《清史舆服志》中,皇帝“礼服用黄色秋香色”。
秋色加上香气,便是这秋香色吧。
而这香气,是怎样丝丝缕缕沁入心中,又是怎样不可言喻的微妙之香,只能想象了。
这些纯粹的、温和的色调,有着石榴的色泽与温度,尤其在阳光下,透着无穷色。
清宫旧藏有一款《月白缎织彩百花飞蝶袷袍》,领口系黄条,上墨书:“月白缎百花妆袷衬衣一件,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收”,是乾隆时期后妃的闲暇所穿服饰。
月白色妆花缎面,有折枝花卉及虫蝶纹样,以红、绿、黄、绛、蓝、会、黑、白等十余种色线织制,花卉有石榴花、牡丹、水仙、牡丹等,虫蝶有螳螂、蝈蝈、蜻蜓和蝴蝶。犹如把整个春天都穿在身上。
不知乾隆时哪个后妃曾经穿过。
或许,与那些皓腕上戴着珈蓝香镯子,双鬓浅戴金海棠珠花步摇、镶宝石蝶戏双花鎏金银簪的妃子相比,穿过这件衣裳的后妃,纵然没有佩玉鸣銮,却旖旎曼妙,温文流美。
在《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正册中,贾元春的判词为:“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从女史到凤藻宫尚书,直至贤德妃,元春在宫中生活了二十多年,她似榴花荣耀一时,却又历尽多少孤寂与荣辱。
不知为何,总让我想到加缪笔下的那些花儿:
“我还住在阿尔及尔的时候,冬天里总是引颈期盼,因为我知道在一夕之间,在二月某个寒冽而纯净的夜里,路上的杏树将全部覆盖白色的花朵。接着我会满心惊奇地看着这片脆弱的白雪在雨水和海风中抵抗。然后,年复一年,这些花儿从不放弃,恰如其分,为了结出果实。”
关于她们,废名说:
“不管天下几大的雨,装不满一朵花。”
春深闭户可染衣。用草木染出的这些织物,又是绕过多少时序轮回、风霜雨露,才能穿到你的身上。
五
石榴,称为丹若、金罂,又一种味最甜者,名天浆。
说起来,石榴就是普通的植物,却被世人所喜。当它从遥远的西域安石国被张骞带回,它便有了另一个名称,为“安石榴”。
似乎这个“安”字,亦是让人心更为安妥。
晋人潘岳在《安石榴赋》中写道:“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缤纷磊落,垂光耀质,滋味浸液,馨香流溢。”这也是石榴的魅惑之处了。
在清代陈淏子《花镜》卷四花果类考中见到石榴:“唯山种者实大而甘,千房同膜,千子如一。花有数色,千叶大红,千叶白,或黄或粉红,又有并蒂花者。南中一种四季花者,春开夏实之后,深秋忽又大放。花与子并生枝头,硕果罅裂,而其傍红英灿烂,并花折插瓶中,岂非清供乎?”
能把石榴的科普文写成文采飞扬的文字,如同一篇华美的赋,让人读了后实在忍不住,也想种上一棵石榴树。
看张恨水写过五月的北京小院,石榴花开着火星样的红点,夹竹桃开着粉红的桃花瓣、在上下皆绿的环境中,这就是五月的小院,几点红色,娇艳绝伦。
人们总愿赋予植物一些情感内涵与意象。千房同膜,多子多福。
宋人用石榴果裂开内部的种子数量来占卜预知科考上榜的人数,“榴石登科”便是寓意金榜题名。
石榴也因其好寓意与好兆头,使得我们常在古画上遇见它。
清代宫廷有逢节必画的传统,宫中档案说《午瑞图》“端阳节备用”。端午有“端五”之称。清顾禄记《清嘉录》: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妇女簪艾叶、榴花,号为“端五景”。
在清代郎世宁的《午瑞图》中,见到榴花。它与菖蒲叶子、艾草、蜀葵花一起插在一个青灰色的瓷瓶里,托盘里盛有李果,边上还散着几个角黍。
据清廷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记载:“四月二十九日,西洋人郎世宁画得《午瑞图》绢画一张……端阳节备用。”
郎世宁此幅看上去有点像西方静物画的作品,作于雍正十年(1732年)。
郎世宁并不是一个绘画上让人觉得功德圆满的画家,《午瑞图》却满是祥瑞雅致。似乎一个刻板的人,突然有了人情,让人心契。
榴花在明隆庆陆治的笔下,则有另一份“妍丽”。
《画榴花小景图》轴,点以朱砂的榴花,水墨和花青染成的菖蒲,以墨写百合,只觉画面清新古雅,时序分明,画上自题“隆庆庚午(1570年)天中节,包山陆治写”。天中节即是端午节了。
端午临近,翻开古画读之,总觉置身那个香气馥郁的五月,被榴花所包围,大雨倾袭而至。
还是徐渭的《榴实图》,萦绕不绝。一枝倒挂的石榴,画中题:“山深熟石榴,向日笑开口,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走。”却并不苍凉。
就如某一日醒来,满眼晨光,饱满而又清透,以为人生还可以很长,最爱的人就在身边,万物和从前一样,人生才刚刚开始。
六月的一天,从大暴雨的杭州出发,开车近300公里,到了那个开满榴花的小院,只为喝到一杯“荒野古树茶”。
如今记起就是那个茶气醇厚的夜晚,与老古树茶的几分沉穆,以及世事回味时,总有的那份甘甜。
榴花也就是如此吧。
生有热烈,藏与俗常。
这是我钟爱它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