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李勇访谈
2021-08-23孟尧李勇
孟尧 李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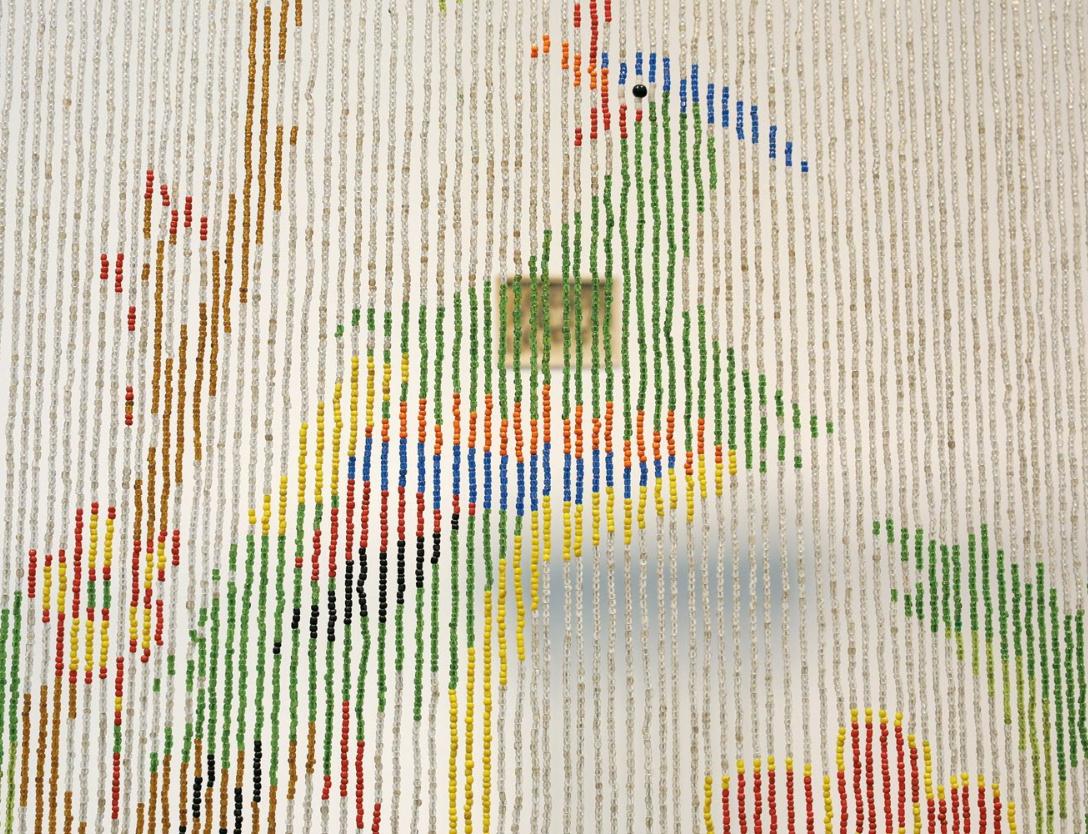
孟尧:为什么会用驻地空间的艺术“残存物”来回应“《画刊》封面计划”的“归零”主题?
李勇:最初我只是从“归零”这个词语字面的意思去思考,把它理解为一种时间概念;但随后我觉得它不仅和时间认知相关,其实更多的是指向了一种工作态度,或者说工作方法。与《画刊》这次合作期间,恰巧我又在成都做一个驻地项目,于是就在展厅、工作室里,搜寻之前艺术家遗留和废弃的展览物来重新创作。这些材料在展览展示系统里,可能随着展览的结束就已经归零了;但是在我这里,它可能又会被重新激发起一种可能性,以此获得一种登场和再定义。
孟尧:具体谈谈封面的内容吧,圆圈、石头、蓝色水管、好像是缝了草皮的绿布,为何将它们搭在一起?
李勇:其实它之前不是这个样子,它是铝合金窗上废弃掉的钢条,我把它拧成了圆圈。套在圆圈上的蓝色水管是我从柜子里面找出来的;压住圆圈和破布的石头块,也是我在屋子里翻出来的,之所以压在布上,是因为刚好可以支撑起这个结构。并不是要刻意去对应这个圆形有归零的相似性,或者说是不是会有了一种时间的恒常状态。当然你可以理解为一种“圆相”,这种圆的造型会被认为在生命历程中是圆满与绝对。但我感兴趣的却是处在这种临时组合和不稳定之间的模糊性,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在那种模糊的时态——正好处于一种中间的不好界定的环节,这种模糊性,刚好是艺术家的一种工作区域,至少我是这样来做的。
孟尧:在作品中利用拾得的日常物品或者各種材质的现成品,以不同方式在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建立“模糊”关联,也是你经常使用的工作方法。在你艺术创作的不同时期,从《剩余价值的低级景观》《迷局》《总是不怀好意》《十日谈》等具体的作品,到 “允诺作为想象之物”“郊区文学”“寂静时刻的两端:沣水研究计划”等展览项目,都能看到这种工作方法的成果或者影响。
李勇:没错,这种工作方法确实是我反复使用过的。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十日谈》,我在其中用了很多碎布料,那些布料是我前女友和我分手之后剩下的,她以前是学服装设计的,我把这些碎布料从工作室里清理出来,重新做了一个很个人化的展览,讲述一种情感的流逝。我的作品中的很多人造物,有些是我偶然拾得的,有些是我专门去买的,它们要么是日常的,要么是被废弃的东西。我以自己的逻辑捕捉和理解其中蕴含的信息,对它们进行处理、加工、再创作。事实上,今天的艺术家都在使用不同的媒介处理作品。不管在平面上,还是以新的科技手段;不管是在现场空间,还是在社会街道:大部分艺术家的工作方法都是如此。但你得明晰自己在作品里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上下文逻辑和生成系统,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往下走。
孟尧:整体来看,你的创作既有针对社会现实语境的诙谐调侃,也有依托个人经验的情感抒发;但无论何种类型和主题的作品,都稳定地凸显了你对形式语汇的“迷恋”,它尤其体现在你对色彩关系、视觉结构以及媒介关联的推敲和锤炼上。比如说,对黄色、蓝色、绿色的高频使用,对平面与空间中抽象秩序的理性把控,以及处理文字、图像关系的细腻手法。我认为这些视觉形式的表征,是你作品里特别外显又关键的审美信息,也是探讨你艺术演进的前提。
李勇:我把自己的作品大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我自己的日常,相对私人化一点的情感生活、过往的经历,可能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现实遭遇过后的感受力;另外一方面是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相关的。但即便是私人化的东西,它还是要转化到一种公共伦理或者公共体系里面去讨论,它不太可能是完全局部的一种私人化,那是无法进入的。关于你提到的形式语言的问题,我觉得你的观察还是准确的。对我来说,那其实是一种视觉系统语言的建构过程。2009年,我从德国回来以后,我觉得我的作品和我之前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2012年做《十日谈》的时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那个时候起我好像明白了一些。后来的创作,我实际上越来越注意建构一种类小说的结构,在作品和展览中把各种素材进行叠加或者穿插,暗藏了很多线索。后来做“郊区的文学”“寂静时刻的两端”的时候,我的创作变得更加场域化。我试图通过弥散、渗透或者侵入的方式,在某种场域中建立观念与材料的语法联结,它是语义丰富和信息杂陈的。在这两个项目的现场,很多熟悉我的朋友一眼就看出那是我的作品,包括你提到的色彩倾向、现场有文字和各种材料,比如说一个菠萝、一片树叶、一张照片,还有像甘蔗、香蕉、兔子等动植物。这些物料别人很少会这样使用,很奇怪却总会出现在我的作品里。这个后面还要慢慢去找出一条线索来才行。还有一些不经意的各种细节,一枚硬币、几个鲜亮色块或者某种带有心理暗示的视觉物的引导。
孟尧:这里可能需要特别提到你作品里对文字的使用。它不是简单地去表达一个观念。我觉得这些文字常常是要和视觉产生一种“通感”的关系。这其实是你建构小说结构的极为重要的一环。
李勇:最近两次的展览,我都使用了文字,包括我的画里面也有文字。它源自我过去对文学的爱好,一种文艺青年不好的爱好,但文字书写思考又让我多了一些维度和滋养。在概念艺术里,比如科苏斯(Joseph Kosuth)的作品里,文字是作为观念直接使用的,可能是概念上的思辨考量,这种方式我也不排斥。但我不太习惯这种作品直接效仿哲学的方式。
文字这个东西确实不太好用。过于明确,它可能会大过你的作品;写得弱了,它可能就变成一种鸡肋。但在一个大的场域里,一般我还是会加那么一两句。有些语句的含义会比较模糊,只和相关作品的言说概念成为一个平行、并置的关系;有些语句则会作为元素放在作品里,刚好贴近这个现场和作品的结构;有些语句则是不做具体指涉的描述性的语言。像“郊区文学”和“沣水计划”里金属板上的文字,它们和整个作品的关系其实更像是一个平行的时空;而“沣水计划”里蜂蜜水杯上面的那一行文字就更加抽象,起到比较肯定和严肃的概括性作用。但无论如何使用,我作品中的文字都是隶属于作品和现场的整体“场域”的。
孟尧:在麓山美术馆驻留后,你做了展览“在到达之前停下来”(2018);考察了沣河和秦岭后,又做了“沣水研究计划:寂静时刻的两端”(2020)。面对这两处差异极大的地理与历史空间,你是如何思考和选择切入现场的角度的?在具体的表达中,你最看重和关注的分别是什么?
李勇:成都麓山美术馆周边(天府基金小镇)就是一个被规划出来的金融小镇和别墅区,它跟一般意义的城市片区的空间没有任何差异。西安沣河及上游沣峪口秦岭一带看着是一个地理空间,山与河流都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麓山那次可能就是夏季在小镇午后的日常写作,而沣河则需要打开一个全方位的信息进行筛选加工,但必须在历史和当代之间划出一个片刻,让那些被遮蔽的现实被提示、被显现,这个可能是我比较看重和关注的吧。

孟堯:“应物和感觉结构”是否是你对自己创作方法的某种总结?应物、感觉结构又该如何理解?
李勇:“应物”我觉得还是艺术家主体对物质和对象的一种对应处理关系,大意就是人与物、词与物、词与材料,你用什么逻辑去建立这种关系和诉求,这是一个语言系统。一杯蜂蜜水,一段《诗经》里的诗歌,一个历史残存的陶俑,一则当代的社会新闻,这些都是你的材料信息,你需要怎么去面对它,做到你自己的语言体系里来。比如说我到沣河上游的秦岭,看到山上有养蜂人家,又通过网络看到养蜂人因为疫情隔离无法去追赶花期而导致没有蜜糖因而抑郁自杀,这些信息和可能的材料都是你作品构成的一个信息来源。我理解的“应物”,不只是对应,它还需要突破自身的概念和范围,成为一个新的环节。它提示了一种当代或者当下的遭遇,如何在你塑造的感知和理解的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一种结构和叙事。所以这个物,它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普遍的。这个可能就是我理解的感觉结构,它在复杂易变的结构中形成一个文化空间。
孟尧:你曾说你的创作就是一种“编辑和裁剪工作,把思考和行动以及哲学理论,还有鲜活的社会现场,通过艺术剪辑成一种文本”。那么,在这个文本中,时常出现的意识流的、非逻辑的无法言说的东西,是如何参与到你作品的视觉结构的总体叙事之中的?
李勇:“无法言说”可能只是一种知觉体验,它从感知再到一种概念理解形成知识认知,再形成意识形态的话语,是一个循序的过程。但知觉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并不直接导致审美的建立。艺术可能会是对现实的一种解码再回到一个编码制造的致幻过程,艺术家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对现实世界重新编码的过程,他在自己的这套言说系统里面形成了一套系统关联逻辑。另外你之前说的“弥散”可能是一种个人气质和现场氛围吧。有些人的作品就像一部电影一样,它充盈着这种迷人的镜头语言和视听穿插在叙事的结构里,它无法描述但是又可见可感。我希望它是节制的作品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