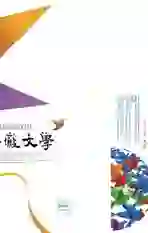河流、大学与学院派作家的书写
2021-08-20向吟
向吟
一
“早上朋友们约我上丽娃栗妲摇船去;他们说那边儿有柳树,有花,有快乐的人们,在苏州河里边摇船是江南人的专利权。”这是1933年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小说《公墓》里的一段文字。穆文提到的“丽娃栗妲”,就是华东师大人念兹在兹的丽娃河,毕业于华东师大的学者张闳认为这是关于丽娃河的最早的文学书写。其实不然,茅盾在《子夜》第18章中至少就有五处提及丽娃丽妲。在茅盾的笔下,丽娃丽妲河畔有许多被五四的青春召唤的妙龄女子,她们跳着探戈舞,唱着丽娃丽妲歌,尽情地享受着自由与欢乐。吴荪甫的小姨子林佩珊即是丽娃丽妲的常客,她是个自由至上主义者,生活对她而言就是及时行乐。在她看来,若为自由故,贞操和婚姻皆可抛。张素素也正是在丽娃丽妲村看穿了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的本质,这一群耽于行动的红男绿女令她不禁感喟:“全都堕落了——然而也不足为奇!”
再往前溯,丽娃丽妲还有一段浪漫而悲伤的爱情故事。1920年代初,有一个西班牙侨民在苏州河北岸买了一块地,并建造了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座郊外度假村,度假村里有一条未命名的苏州河的支流,西班牙人用西班牙语取名为“Villa Rio Rita”,西班牙语中“rita”即“河流”之意。于是这里就被中国人叫作了“丽娃丽妲”“丽娃丽妲村”“丽娃丽妲河”等(薛理勇《华师大“丽娃丽丹”的传说》,2019年)。西班牙人回国后,“丽娃丽妲”转到一位白俄贵族名下。白俄贵族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她爱上了一位中国小伙子,却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對,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夏夜,她跳进了这条河里以死抗争。白俄女子对爱情的忠贞与执着令人感叹,其纵身一跃为爱而死的壮举则增添了丽娃丽妲河的传奇色彩。1929年美国歌舞电影《丽娃栗妲》在上海的上映,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丽娃丽妲”这个名词的传播。多年之后,这河上的一小片绿洲被命名为夏雨岛,很难说与这个故事无关。考据派总喜欢去考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对于这条河流和这座校园而言,故事的功能在于赋予她更多的浪漫与传说,而真与假没那么重要。
据1931年3月4日《申报》刊登的《荣宗敬捐赠大夏西河》称:“中山路大夏大学新校址之西,有河流一条,自该校北首,流经运动场及丽娃丽妲村,直达苏州河,面积六十余亩,水深岸阔,清澈见底,直视无碍,游鳞细藻,倒影成趣,风景极佳,为海上所仅有。该河原为无锡面粉巨商荣宗敬氏产业,现有荣氏捐资大夏。该校自得此河后,即加以疏浚,作为课余游钓泛舟、游泳之用。”可以想象,在茅盾创作《子夜》、穆时英创作《公墓》的年代,丽娃丽妲村不仅可以划船、游泳、打网球,还可以在音乐亭里吟风弄月,歌唱盛世繁华,是当时的上流阶层和时髦青年争相前往的度假胜地。由此看来,早几年已到上海定居或工作的陆小曼、丁玲,在这一时期应该也常去丽娃丽妲划船或漫步的。那个年代,青年男女最想要的是自由,爱恋自由也好,婚恋自由也罢,都希望能自己做主。所以当胡也频冒失地向丁玲表白时,丁玲才会直截了当地回绝:“我要是想恋爱,不如找瞿秋白恋爱好了。”陆小曼也同样如此,她远比林徽因活得真实而率性。林徽因是理智的,她不会为爱自毁清誉。而陆小曼则被徐志摩一声声的“眉”感动,纵使千夫所指,她亦是无怨无悔地选择了“摩”,因为这才是她最想要的爱情。
多年来,丽娃河深情款款,夏雨岛垂柳依依,吸引着无数深陷孽海情天的青年男女流连忘返。在毛尖的记忆里,丽娃河“夏天一到,水葫芦长得跟草坪一样高一样平,一个晚上误入一对恋人那是起码的,两只青蛙两张嘴,扑通扑通跳下水,湿漉漉的上来,继续热吻。同时,校园文明纠风大队也出发了,他们打着手电,看到恋人们快吻上了,就及时吆喝,‘住嘴!”(毛尖《丽娃忆旧三题》,2008年)。在丽娃河畔求学和工作过的格非多年后回忆说:1930年代的“这片郊野之地已成为沪上游人踏青远足的绝佳处所。……我也曾从旧报刊上见过几帧小照:身穿旗袍的摩登女郎浓妆艳抹,泛舟河上,明眸皓齿,顾盼流波,其笑容在岁月的流转中与相片一并漫漶而灰暗”(格非《师大忆旧》,2019年)。岁月流转,丽娃河慢慢地成了华东师大的爱情圣河。回过头来看,丽娃河及其所在的大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既得益于丽娃河水旖旎的温柔与诗意,又得益于大学在那个年代里作为自由书写和传播空间的存在。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华东师大学子诗意栖居的时代,诗人宋琳定居巴黎数年之后,念念不忘就读过的母校,他在劝阻学生不要盲目到国外求学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这世上真有所谓天堂的话,那就是师大丽娃河边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对于华东师大来说,丽娃河意味丰饶而深长:“她给校园带来一种舒缓、温润和柔情的品质。某种程度上说,这条河已经成了华师大人记忆的载体。成了华师大特殊精神的滋生地。”(张闳《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2006年)
二
与张闳、宋琳等人的诗意书写不同,李劼笔下的丽娃河里藏污纳垢,鱼龙混杂。大学校园也不再是令人尊崇的象牙塔,而成了贪婪人性的流俗地。
在诸多关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华东师大的记述中,李劼是华东师大公认的青年才俊,也是那个时代蜚声文坛的著名批评家。其长篇小说《丽娃河》(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写尽了几代知识分子的丑态:校领导贾利民阳痿不举,却长期霸占着苏里的妻子;中文系主任吴天云恋物成癖,借用手中权力,将女研究生江瑛哄上床;“接班人”辅导员毛善平流氓成性,不仅奸污女学生,还收取学生钱财;著名博导袁逸儒为保全自己,“文革”中将私藏于己处的学生日记交给了“组织”。在李劼笔下,特殊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掌握着权力,为所欲为,他们“不学无术,唯一的专长就是搞运动,汇报这个,揭发那个,相互勾心斗角又共同沆瀣一气”。他们蝇营狗苟,趋炎附势,沉溺于权力和酒色财气,早已背离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优良传统。对他们来说,知识只是工具,只是整人的缘由与借口。诚如鲁迅所言:“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狂人日记》)似乎只有在面对“同类”时,“他们”才会无所不用其极,通过作恶来寻找快感或优越感。
1990年代,中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重重跌落,大学校园也越来越世俗化,在新一代学术领军人物博导张超眼里知识就是赚钱的工具,“全仗着体制给他们的好处,免费吃喝嫖赌”。现实中丽娃河的真实存在以及作者成长经历的相似,使得《丽娃河》一问世就体现出了黑幕小说的意味,而诸多读者也随之成了索隐派或考据派,看官们按图索骥,探究的重点大多是那个肥头大耳的博士是谁,那个喜欢与女学生坐而论道的博导又是谁。然而这些无损于李劼的批判锋芒,身为大学教师的他在揭露同侪的犬儒心态时丝毫不留情面,他对当代知识分子丑陋嘴脸的批评尖锐而犀利。
温儒敏认为《废都》“包含有对传统文化断裂的隐忧,有失去人文精神倚持的荒凉感……《废都》也许可以称为东方式的《荒原》”(《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惑》,2001年)。与《废都》相似,李劼笔下没有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早已置身于精神荒原,《丽娃河》的深刻之处即在于预言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死亡。陈平原在论及“大学叙事”时说:“近年出版的《丽娃河》《桃李》等,则显然更愿意追摹钱锺书的讽刺笔墨。”(《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2006年)可谓一语中的。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对儒林众生相的生动描写与辛辣讽刺,钱锺书乃揭橥之人。就像《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压倒全唐一样,一部《围城》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苟且心态做了生动演绎,遂成“新《儒林外史》”,尽得中国讽刺文学之风流。《丽娃河》的讽刺与批评力道虽不输钱锺书,但其行文的智慧程度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意识则远逊于钱。
比较而言,张者将小说命名为《桃李》(2002年)自有其用意,所谓“桃李满天下”既是他人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称许,也是大多教师的自我期待。然而必须明白的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首先强调的是德行,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小说的主人公邵景文是研究生心中的偶像,不仅是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法学家,还是一个精通诉讼程序的大律师,成功地开着一个律师事务所,学生在所里面打工,他给弟子发工资,所以他成了学生口中的“老板”。在学生的眼里他不仅是学术导师,还是一位具有超强能力的经济主宰者。学法学的邵景文在打官司时是严谨而理性的,但一遇到金钱与美女就会溃不成军。当金钱与美色成为新的欲望能指时,原本被视为净土的大学校园愈加市侩化与世俗化。在物欲横流中迷失自我的邵景文最终死于非命,被情人梦欣捅了108刀,而且每一个刀口上都被情人种了一颗珍珠,而这些贵重的珍珠本是他送给梦欣的。张爱玲的《色·戒》里的王佳芝被“鸽子蛋”打动,不惜出卖战友也要放走老易,她原以为遇到了爱情,却不知在易先生那里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邵景文的运气简直坏透了,108颗珍珠虽不能说是情根深种,却也没少情感投入,毁容后的梦欣已经没有了自信,在得不到婚姻的承诺后便残忍地将情人杀死,与王佳芝相比,到底还是自私了些。
其实,张者笔下的邵景文并不坏,他学问很好,对学生很好,甚至對情人也很尽心,虽然他放纵自我,但并不愿意放弃对家庭的责任,他也不愿意学其他老板堂而皇之地包养小三,他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孤傲,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他认为婚姻和爱,爱和逢场作戏不能混为一谈。张者的写作中渗透着悲悯情怀,他甚至同情邵景文在这个时代的遭遇,认为知识分子的选择太难了。当金钱成为这个时代衡量知识分子的一个价值取向时,知识分子拿知识来换取金钱,这到底是知识分子变了还是社会的评价标准变了?与《丽娃河》一样,《桃李》关注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诚如王干所言:“《桃李》并不是揭露法律界的黑洞,也不是揭示高校里的学术腐败,《桃李》重点反映的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呼唤健康的理性的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品格。”(《人文的呼喊与悲鸣》)
虽然未像《丽娃河》那样命名为《未名湖》,但《桃李》同样是一部很容易让人对号入座的作品。作者的中文本科背景和北大法学硕士出身令读者考据的兴趣大增,小说中的故事与法学院的现实事件大同小异,很难让人不怀疑其对北大的影射意义,据说北大中文系和法学院的诸多学者都因此被比对过。张者在访谈中说写的是不是北大并不重要,但能让很多人觉得像,这可视为是小说创作的成功。但他同时也提醒读者:小说不是新闻,不是真实事件的记录和报道,现实中的大学校园并未污浊不堪,而是依旧美好灿烂(刘育英《〈桃李〉:校园小说,影射北大》)。小说本是虚构,所以,《丽娃河》的污浊不堪,《桃李》的败絮其中,都不会有损大学的名声,敢以自身之短揭示1990年代市场经济以来高校知识分子中存在之种种怪状,恰是出身高等学府的作家的责任。
三
与《丽娃河》《桃李》相比,差不多同一时期问世的葛红兵的《我的N种生活》(2001年)多了许多学院派作家的反思与自省。
从海门师范学校到扬州大学再到南京大学,工作、读研、读博,“红兵”的命名和成长带有明显的1968年生人的时代特征和精神烙印。“回家吧,葛红兵。”这一声呼唤,不是乡恋,更无乡愁,而是顽固世俗的重重羁绊。原单位领导的强力挽留,对相信“人在以前是能够飞的”渴望自由的葛红兵来说,简直就是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无可逃避,挣脱不得,以至于他频频产生玉石俱焚、鱼死网破的念头。数年后,在回忆起这些往事时,他仍然难抑心中愤怒,直陈其人其事。当然,作为作家,他也深知文字的力量,因而在作品的开篇他即请求原谅:“如果有谁因此而遭受伤害,请原谅我。实际上,我要请求所有人的原谅,原谅我诅咒你们,攻击你们,诬蔑你们。”一个典型的《伤逝》式的开头为全篇奠定下忏悔的基调,但同时也在无所顾忌地向所有的“你们”宣战。“你们”是异己存在的他者,是在早晨六点洗衣服让“我”无法安然入睡的“妻子”,和不让“我”流动的“领导”,以及一切阻碍“我”自由飞翔的力量(比如户口和权力)。
据说,鸵鸟在遇到危险时喜欢将头埋在沙堆里,以为自己看不见就安全了。别里科夫也以为将自己装进套子里就不会出什么乱子了,然而仍免不了早逝。当他被装进棺材这个真正的套子再也不用担惊受怕时,同事们脸上虽然一副忧伤的神情,内心却感到异常快活。原来,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契诃夫想说的道理大家都明白。然而,碍于现实规范和道德约束,大多时候人是戴着“面具”生活的。荣格认为:“人格面具是个人适应抑或他认为所采用的方式对付世界体系。”(《原始意向和集体无意识》)就此而言,“我”的N种生活,其实是“我”的N个人格面具。白日里正襟危坐的“他”,夜间也会“化装出行,来到公园里,和欢乐幽会,他渴望欢乐,日夜追逐欢乐,可是又为欢乐感到可耻,为自己不能拒绝欢乐的诱惑感到无脸见人,所以一个欢乐的他总是和办公室里一本正经的他毫不搭界,每当他完成了欢乐的夜行回到办公室,他立即变化了自己的嘴脸”(《我的N种生活》)。人性是有弱点的,“我”因此而苦苦挣扎在爱与欲、学与术、邪与恶中。为了获得“飞翔”的机会,“我”宁愿放弃尊严去给领导送礼,在被领导拒绝后,“我”甚至想通过吃屎而获得领导的恩赐。这并非是对权力的服膺,而是对所谓规则的彻底无奈,否则,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又怎会卑贱到尘埃里?
与其说《我的N种生活》是一部非情节性的自传体小说,毋宁说这是一部学院派作家的思想自传。在“知识分子”成为“妥协、委琐、虚无、颓废的代名词”的时代,葛红兵大胆直面自己虚无、衰颓、炽狂、偏执、软弱的精神气质,率真揭露自己恐惧、忌恨、邪恶、轻蔑的阴暗心理,其恳切的叙述、犀利的自剖,为已经被污名化的“知识分子”找回了重生良机。事实上,自我解剖并非葛红兵的唯一诉求,他的真正诉求是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与责任担当。在众人皆醉的年代,他希望知识分子保持清醒:“普通人可以保持沉默,但知识分子不能,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喉舌,在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说话的角色。”(《我的N种生活》)
2003年出版的《沙床》延续了《我的N种生活》的自叙传色彩和忏悔意识。小说主要讲述了青年哲学教授诸葛和他的学生以及多名恋人之间复杂的情欲故事。其实,诸葛并非纵欲滥情之人,也无意将女性视为玩物。在与裴紫发生“一夜情”之前,诸葛已经许久没有欲望和激情了。不同的女性对他而言是不同的爱的体验。在诸葛眼里,罗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大姐姐,给了他成熟之爱;张晓闽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妹妹,给了他纯洁之爱;日本女孩Onitsuka 是一个浪漫的情人,给了他激情之爱;而裴紫是一个生活的守护者,给了他日常之爱。本真的生活才是常态,所以他才会与裴紫结为夫妻。
该书封底有一段作者独白:“这是在爱欲中死亡的故事,这也是在信仰中复活的故事;这是在生命中沉迷的故事,这也是在祷告和忏悔中寻求永生的故事。”意在提醒读者不要被师生恋、群恋、派对恋的表象迷惑,应该关注其背后的关于生命与死亡、信仰与救赎的故事。小说中诸葛对实践、虚践、价值、时间、意义、灵魂、寂寞、悔恨、病苦、贫穷、永恒等问题的思考,既是一个哲学教授的精神思辨,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所以,诸葛夜读《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个体哲学》《小逻辑》《圣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著,均非闲笔,实乃有意为之。
在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商品经济时代,精神失范的知识分子该如何自救与他救?在与喜欢的多名女子发生关系后,诸葛意识到性爱无法安顿自己漂浮的灵魂:“甚至做爱并不能解决问题!那一刻也是好的,过后,茫然还是茫然,孤独还是孤独,伤感还是伤感!”(《沙床》)因为家族疾病而一直被死亡阴影笼罩着的诸葛最终由于裴紫的自我牺牲與无私奉献而获得拯救,然而拯救的只是诸葛的肉身,精神的残疾仍然需要精神来医,获得新生的诸葛最终的感悟是:“为什么人能得救?那是因为信仰,信仰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理由。”事实上,诸葛断断续续撰写哲学随笔《个体及其在世结构》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找信仰的过程。虽然作者提供的皈依宗教并非最好答案,但知识分子因为缺乏信仰而导致的精神危机已经被学院派作家敏锐捕获。
中国现代作家泰半以大学教师为职业,不仅可以传道授业解惑,还可以著书立说,传布新知。近20年来,作家进校园做驻校作家已不鲜见,而诸多成名学者也开始从事写作,跻身文坛。暌违已久的创作与批评的良性互动终于进入佳境。大学是最包容也最开放的知识分子聚集地,也是思想与精神生产的策源地。对在大学安身立命的作家而言,如能充分利用大学的自由空间和学者的精神资源,秉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和批评精神,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身作则,然后诉诸他人与集体,对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显然将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