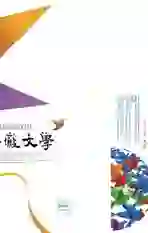红蜻蜓
2021-08-20郭本龙
郭本龙

昨天晚上,老董被老高拽去喝酒了。
老董老高不仅是安徽老乡,还是当年补习班的难友,如今又先后来到深圳这一方热土,不约而同进了一家电子厂,如今还是邻居,这缘分,恐怕要一万年才能修得来吧。所以老高一喊,老董没讲二话,爬起来揉揉眼就拐过去了。
昨天是十月六号,还在“黄金周”里,中国人民正乐呵着。
原来是老高把他和黄丫的照片取回来了。
老董进门的时候,老高正站在凳子上,举着相框左右比划:快来帮我看一看!这样行不行?啊,歪了没有?
这老高一意孤行,一定要把它挂起来示众了?老董眉头皱了皱,敷衍地瞟了瞟,说:嗯,蛮好的。就这样子吧。
老高挂好了照片,跳下来。
这两个人,一个西装一个婚纱,还浓妆艳抹的,弄得笑容黏糊糊的像两块奶油蛋糕。
老董脱口而出:你们人五人六的,跟真的一样……
老高拍拍手: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可是在正儿八经的影楼照的,五百块哩!他们还说对“来深建设者”打八折。打了折还这么贵,扯淡!
黄丫笑着岔开了话头:老董,晚上在这边吃饭,把春草也喊来。
老董一怔:啊?你俩还打算举行个仪式啊?
老高说:没……没那么夸张,就我们四个。
春草来了。
春草一进屋眼珠子就停在照片上了:我的乖乖!你俩赶上大明星了!
黄丫说:眼馋了吧?哪一天,你们也去拍一张。
春草把收回来的目光投向老董:我们……也可以?
老董正在研究厨房那边飘过来的味道,置若罔闻。
黄丫还真弄了不少菜,有炖猪蹄、炒鱿鱼、糖拌西红柿,还有拍黄瓜和冬瓜汤,小桌子都摆满了。老高一连撬开四瓶“老金威”,又帮每人倒了一杯。啤酒白沫像瀑布一样挂下来。
老高端起杯:来吧,先走一个!
黄丫附和道:感情深一口闷啊!
春草干了,擦了擦嘴:我以往喝不惯啤酒,跟马尿一样。今天觉得还可以哦,你说怪不怪?是不是因为喝的是喜酒啊?
黄丫笑眯了眼:草儿,你真会讲话。
老董也干了,但没说话。他不晓得该讲什么。一时间他有点恍惚,仿佛真是在参加某个婚宴。他想:这老高糊里糊涂的,把事情搞大了,就要失控了。
老高见状,就问:哎,你怎么回事啊?
老董说:啊……没什么。来,喝酒。
原来啤酒也很有后劲,说不定还是假酒,总之这一夜老董头疼死了,且去了七八趟厕所。
老董醒了,摸出手机,三点零五分。
他翻了个身,借了屋外的灯光,打量着睡在身旁的人。
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头发略有点黄,长得不丑,一般般。她虽然睡着了,喜悦却从嘴角荡漾开来。她在做黄粱美梦哩。她在梦里照相了?正在摆pose、说“茄子”?
眼前的一切很虚幻,老董不禁往床边挪了挪,重新调整了焦距。
我……我怎么跟她睡到一块了?她是谁啊……肯定不是我老婆。想起来了,她叫春草,是服装厂的。我老婆叫夏苗。夏苗在老家哩,在安徽董山村哩。这里是深圳西乡。这里和那里相隔千山万水……
思绪如同搭乘了时光机器,跨越了时空……
老董和老高是补习班同学,而他和夏苗却是初中同桌。那时老董是小董。小董成绩好,总考前几名,夏苗的成绩却是中等。所以她很崇拜他。到中考,他考上了县一中,她没达到分数线。光阴似箭,转眼过去了好多年。有一天,他和夏苗在爱华超市门口碰到了。久别重逢,两人都很开心。人太多了,熙来攘往的,他俩边讲话边往后退,最后干脆躲到旁边一个小巷子里去了。她问他:六年了,没你的音讯。你现在在哪块?他很难为情:我在补习。今年考了515,比大专线低了两分,只能上那些交钱的民办学校,没意思,学费又贵,就没去了。说到这里,他苦笑道:我要是北京户口就好了。这个分数,放到那边,能上重点。她感同身受,泪花闪烁:同分不同命啊。他说:我爸生病了,脑血栓。我再不能复读了,就进了钢管厂。她安慰他:也蛮好的。我在装订厂,离你那块很近哦。他说:有空我去找你,行吗?她说:行啊。又过了三年,也许是四年,他父亲病逝了,钢管厂也倒闭了。那一年,夏苗嫁给了他。后来夏苗生了一儿一女。过了几年夏苗也生病了,经常莫名其妙腿疼,还有腰疼,不能吃重了。去年腊月二十三,那天“送灶”,老董在车站意外地碰到了回来过年的老高。架不住他一番鼓动,今年正月初八,老董也来到了深圳。
四点半了。
老董悄悄下床,套裤子、穿拖鞋。皮带头响了一声,春草醒了。
她打了个哈欠:你……起来啦?这么早啊?
老董正低着头扯拉链:嗯,你睡你的。
拉链搞好了,老董系好皮带,开了门。
门口有个水池,一排水龙头虚位以待。老董拧开一个,嘴巴凑上去,“哗啦啦”,腮帮子鼓了,遂塞进去一根牙刷来回捣着,又吐出一滩水。他又伸出双手,接了一捧水捂在脸上,上下搓了两遍,脸就洗好了。又咳了几声。
是老董啊?怎么这么早?
老董扭头,定睛细看,是赵庆。腿还是一瘸一拐的。
老董说:你也很早啊。
赵庆说:我光棍一个,睡不着很正常。你就不同了,啊?你应该……他打着哈哈进了厕所。厕所里立即传来“嗤嗤”声。老董转身进了屋。
春草靠在床上,脸像向日葵迎着太阳迎着老董:我起来,做早饭给你吃。
老董从暗处摸出钱包,揣进裤兜,又走到镜子前,五指划拉了几下头发:不了,胃不舒服。
春草说:不吃东西,不更难受吗?
老董说:没事。我出去走走。
春草说:你早点回来。
老董答应了。他临出门时顺手撕下一张日历,10月7日。
老董心里“咯噔”一下。
天还没亮,四周一片昏暗,唯有东方泛出一片白光。
这里是一个城中村。村里的房子高矮不一,亲密无间。村西有一条小河,河边有两排平房。很久以前这里是一所小学,后来小学搬走了,谁将它砌成一个个单间,每个单间十三四个平方,又被隔成卧室和厨房。没有卫生间。老董老高都是租客,分别住201和202。
老董过了桥,上了一条大路。
路灯亮了一夜,困了,无精打采。路两旁的花花草草看上去都是深色,茂盛而凝重。他才走几步,裤脚就被露水打湿了,黑了一截,沉甸甸的。他的脑海里忽然跳出两句古诗——有一年“江南十校联考”考过的,因为做错了反而印象深刻——“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近来,老董嗅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那气息似有若无、细若游丝,他说不清来自哪里。但这几天这气息似乎越发浓烈了,有点刺鼻了,就像儿时闻过的氨水。他需要清静,所以他一大早就把自己放了出来。他想把这一天在外面耗掉,所以他走走停停、晃晃悠悠。
他踏上了一条老路。这条路通往宝安国际机场。
听起来是奇闻,讲起来是笑谈——老董虽然才来九个月,竟已去过十三次机场。有如当下很多“干爹”不是爹、不少“小姐”非小姐,去机场而不是乘客的大有人在。比如老董。他去那里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看飞机,当然也少不了仰望祖国的蓝天。
老董在电子厂,老高也是,春草和黄丫则在服装厂。这一带全是厂,每每上下班时段,人头攒动,如蚂蚁搬家。平时,他们白天很忙,晚上也常常加班,碰到客户催货,星期天就要搭进去。生活总是两点一线,难得碰到个休息日,自然很珍惜,就希望这一天过得很慢且色彩斑斓。
实际上老董他们一直没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逛街?没钱;唱卡拉OK?除了没钱还没嗓子;泡吧?缺得更多,尤其缺乏情调;打高尔夫?我的天,你怎么想得出来的?还不如打自己一顿靠谱哩……想来想去,唯有这件事最划算。如果你不想坐大巴,还可以徒步(又省了两块钱)。八公里,两个小时总差不多了吧,反正你也没什么事,还顺带健了身。久而久之,“看飞机”,正如春晚的大合唱《难忘今宵》,成了这一天的保留节目。
远眺航站楼,它酷似一条巨大的飞鱼(网上说,那鱼叫“蝠鲼”——见到它的人真有福分啊)。相比之下,那些来往穿梭的小轿车简直就是小鱼小虾了。偌大一块空地上,停满了五颜六色尖头大肚子的家伙,一帮人忙前忙后,让人联想到养鸡场。看客真不少,一个个脸上写满了好奇。其实人是可以貌相的,光看外表就能猜出他们大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人行道上,他们像麻雀一样一字排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当某一架飞机哼哼唧唧地滑行着、磨蹭着,随后一咬牙一跺脚冲上云霄,他们都看傻了,一个个伸着脖子看,好比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老董是个善于观察和总结的人。他去了两次就发现,在停机坪的东北角,经常栖息着一种头大、身子长、尾巴细且后半截被漆成了红色的飞机,远远看去,就像一只只红蜻蜓。这些飞机飞起来更像。老董每次去都以“凝视”它们为主,以寄托思乡之情和表达对美好童年的怀念。小时候,夏天的某个傍晚,天很闷热,东北角乌云翻滚,山雨欲来,稻场上,成百上千只红蜻蜓泰国红衫军似的上下翻飞、载歌载舞……
老董一个人在路上“叮叮咚咚”地走着。
太阳很高了。阳光射到不远处的几栋高楼上,经过玻璃幕墙的反射变得明晃晃的。这几栋楼的外形很像昨晚的啤酒瓶。
老高这人,向来口无遮拦。有一次(也是在机场),他无缘无故,大发感慨:唉!没劲。我们这日子,无聊不无聊啊?
老董没表态,等他的下文。
老高眼巴巴看着一架飞机就要潜入云层,无奈地摇头。他说,上班,就一个字:累;下班呢,还是一个字:烦。长夜难明赤县天啊,身边没个体贴的人,连个搭话的人都没有。
老高的话基本属实,老董没有异议。
老高只好又说:你今年多大了?
老董说:你废话,你又不是不晓得,你属龙,我属马。
老高说:你比我还小两岁哩,装得跟七老八十一样。
老董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老高阴险地笑了笑:你就装吧。
老董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若有所思,还是没吱声。
老高忍不住挑明了:你实话实说,你……你就没……那方面的需求?
老董脸红了:你嫑哪壶不开提哪壶……
老高說:没有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可怎么办呢?
老董说:怎么办?凉拌。哪个叫你不把老婆带来的?
老高冷笑道:哟,哟!听你的口气,好像你天天洞房花烛夜似的。
老董嘀咕道:你废话。家里哪块走得开?老人、小孩,田地、牲口。我老婆身体又差,动不动就腿疼、腰疼……
老高疾首蹙额,一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样子:还是的!我们虽然被人喊作“老高老董”,可我们还只是四十!如狼似虎啊!这样守活寡,非憋出毛病来不可!这难道不是个事情吗?全中国,这样的情况有多少啊?这么大的事情,也没个领导来管一管。
老董说:这你就为难领导了。你叫人家怎么管?哦,给你安个工作再配个老婆?你啊,半夜里要吃屁——想得倒美。
老高说:你来得晚,搞不清,周围都起了雾了。那帮家伙,有的就去找小姐,就在公园的草地上……
老董瞠目结舌:那多危险!又不卫生。
老高说:逼急了呗。狗急跳墙,人急跳床。
老董说:恐怕也不便宜。
老高不以为然:挣的这点钱都搭掉了。话又说回来,不这样还能怎样啊?要不,就像我们这样子——白天看飞机,夜里打飞机。
白天看飞机,夜里……打飞机?老董复述了一遍,面红耳赤:你能不能小声一点、文雅一点啊?
老高说:你太虚伪了。你敢对天发誓你不是这样子?
老董望着天,天上空空荡荡,连一只鸟都没有,连一片云都没有。
老高自言自语道: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力更生了……
老董信马由缰,且行且珍惜,近四个小时才到机场。
他心无旁骛、目不斜视,径直跑到东边人行道的尽头。
此刻,恰有两只“红蜻蜓”停在那里。它们尾巴上都画了一只金色的狮子,机翼上有编号:B6201和B6202。
老董心里再次“咯噔”一下。
自从那次发了牢骚,老高就神出鬼没了。一个月之后他就搬走了。
那天下了班,老高回来风风火火地收拾。他跟老董说他要搬到小学那边去了。这边一间住六个人,每人每月交两百。人家那边是单间哩,两个人平摊,每人也不过三百五。虽然贵了一点,但多宽敞、多自由啊!
老董问:两个人平摊?你跟哪个住?
老高支吾道:你……等一下子来参观吧。
老董随后就去了。
老高指着一个忙碌的身影说:她叫黄丫。黄冈的,王小丫的“丫”。
黄丫听见了转过身,腼腆地笑了笑。牙齿确实有点黄。
老董环顾四周,请老高借一步说话。
两人来到了小河边。水上飘满了塑料袋和泡沫饭盒,还有杂草。
老董真急了:你们就这样……并家了?搭伙过日子了?啊,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漏啊?我讲话你嫑动气哦,我看她,就是个一般人。
老高哑然失笑:她当然是个一般人。她要像范冰冰,还有我这个猴子喝的水啊?唉,马马虎虎讲得过去就行了……
老董不解: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老高说:这还要我讲啊?你明知故问……她那个丈夫,在老家哩,不是个东西,好吃懒做不说,还老打她。我们接触了几次,感觉不错……
老董问:你真准备离了婚娶她啊?
老高笑起来: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简直老外了。我们都讲好了,目前就是个互助组,干什么都二一添作五,AA制。如果有一天,哪一方没兴趣了,不想干了,就自动解散,没什么瓜皮啃的。
老高又说:你放心,我又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前辈们有的是经验。你还不晓得吧?多少人早就这样了。赵庆,你认得吧?他那女的,你也见过的。你说他们是原配?呸,还天仙配哦!还有那个电工老张,他那相好就跟黄丫一个厂。那个厂没别的长处,就是女工多。你发呆了吧?嫑急,改天也给你物色一个。
老董说:你嫑胡扯了。
老高说:你看你,还不好意思了。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我都先走一步了,能不拉扯你吗?
老董说:我不要。我跟我老婆,好得很……
老高说:这跟夫妻感情没半毛钱关系。你担心没法交代是吧?山高皇帝远的,交代个屁啊!你有点动心了吧?那好,我叫黄丫留意。
有道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老高说了三四遍,老董就被洗了脑、拖下了水。后来,黄丫隆重推出了她老乡春草。
春草除了长相比较普通,其他都很好,比如她很朴实、勤快。更主要的,她似乎很满意老董。她总是悄悄对他说:你比我家里那位……强多了。老董被夸得飘飘然,想让她说具体一点:你指的哪方面啊?春草娇羞道:哪方面都强。
说曹操曹操到,手机响了,是春草。
春草很急切,也很关切:你在哪里?啊?又跑去机场啦?那你中午还回来不?不回来了?也是,太晒了。那你下午可要早点回来哦。不要再甩腿走了,坐大巴,350路,一直坐到工业园大门口嘛!哦,你坐过啊?你估计四点能到家不?尽量早一点。我菜都买好了,你回来吃现成的……你中午怎么办?你不要舍不得。你听我讲啊,你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农民工,就像一个坐得起飞机的人。那你就大模大样地闯进去,保证没人拦你。你先买一点吃的垫一垫。哎呀能有多贵啊?这一顿算我的行不行呢?回来我给你报销。你下午一定要早点回来,有意外惊喜哦……
九点五十了。春草提醒了老董,真是饿了,饥肠响如鼓了。
春草激发了老董的表演欲和冒险欲。他想:我今天就当一回侦察兵,我倒要看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老董先走到僻静处,上下拍打一番,又牵了牵衣领,扯了扯衣袖,然后,啊哼!他咳得掷地有声。他器宇轩昂阔步向前。
他走向三号门。离大门还有大约两米,他就感受到了冷气的吸引。他瞄了瞄左右,没人注意他。于是他自信了,步伐趋于稳健。里面果然别有洞天,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人很多,却不跳广场舞。这些人待会儿都要上天吗?天哪……迎面一块超大电视广告屏,一个女明星近在咫尺搔首弄姿。想不到她的汗毛孔这么粗,快赶上吸管了。
老董上了二楼。这里仿佛是餐饮一条街。他挨家挨户地访问。
第一家是“加州牛肉面”。明码标价,一碗面条48元!他舔了一下嘴唇。这个价格让人无法接受。
第二家,“东北饺子馆”。10个蒸饺60元!什么蒸饺?心如刀绞。
第三家第四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老董连连告退,更下一层楼。
不用再看了。机场餐厅八字开,我和它们八字不合。都是我的错,我根本就不该来这种地方冒充大头鬼。自责一番过后,老董心一横:不吃了,喝水吧。喝凉水不光能塞牙,也一样抵饱。刚才看到了好几个饮水机,水是免费的。
两杯水下肚,心中波澜起伏。
老董今天算是懂了,原来那帮有钱人吃的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他们只是穷讲究罢了,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他们真傻。
春草又來电了:你吃了没?
老董说:吃了。牛肉面,还有咖啡,花了八十八。
春草叫起来:这么贵啊!你碰到打劫的啦?我……付一半,行吗?
不用了。我吃的,干嘛要你付账呢?
呵呵,主要是……今天我买了好多菜,没钱了。
啊,你干嘛要买好多菜?
我想晚上请老高黄丫吃饭,回他们的情。
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还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哩。
春草嗫嚅道:这事……我想一个人承包,让你轻松一点。你玩你的,还早哩。你只要按时到家就行了。
她多像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主人啊,几乎就是红袖添香了!不知道为什么,她越这样,老董越烦躁,还有恐慌。
老董离开大厅,走了出去。
又到凭栏处。老董进一步弄清了自己的定位:这里才是他的地盘。
那架标号为B6202的飞机正在跑道上缓缓前行,像一个红衣女子在练习花样滑冰。
它的速度越来越快,如百米运动员进入了冲刺。接着,它抬头挺胸,似乎只是一个激灵,就腾空而起。周围的人大呼小叫。
老董觉得它真的像红蜻蜓。他想起很多年前看过的一个电视剧,名字忘了,里面的歌很好听——
低低地飞,低低地飞,你这红蜻蜓,你丢失了什么,飞得这样低……
同样是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有的在蓝天上飞,有的在黄土上跑,还有的在泥泞里拱。作为一个“走兽”,老董难以想象“飞禽”的感受。他老是杞人忧天:他们坐在机舱里,会不会发晕?老董想:不管别人怎样,我肯定不会。这一点他有把握。小时候,他能站在原地一口气转二十几个圈。这种基础,训练一下都能上宇宙飞船了。说来遗憾,时至今日,老董还没见过空姐,一次也没有,连远远地看一眼她们背影的荣幸都不曾有!老董想不通:难道她们一年到头都待在飞机上不下来吗?她们只是仰望星空却不愿脚踏实地啊?谁能告诉我她们到底漂不漂亮啊?是不是此女只应天上有……有一次聊起这事,老高即惆怅又愤怒:有钱的人太讨嫌了,好看的女人,一半被他们收藏进了红楼,一半被他们托运到了蓝天,看都不让看!下辈子,我要是进了福布斯,就先到天上找个老婆,再像卫星一样带回地面,放到车里……
老高啊老高,嫑好高骛远了,先想想怎么解决眼前的麻烦吧!
就在上个月,黄丫回了一趟老家,大家都没在意。哪晓得她是回去办离婚了。她动真格的了。结果非但没办成,还被她丈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人说:老子晓得你在外面有人了!你给那个混蛋带个话,他最好先做一做广播体操第八节整理运动,等老子去深圳,亲手骟了他。老高听了故作镇定地哈哈大笑:让他来吧。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黄丫从老高的笑声中得到了莫大的鼓舞,轻伤不下火线,屁颠颠地拉着老高去照相,高调秀恩爱……
老高很乐观,老董却忧心忡忡:你不是讲前辈们有经验吗?依我看都是教训。那个赵庆,前阵子,那女的老公来了,逮了个现行。那女的当场反水,硬说是赵庆强奸了她。结果,赵庆被骂得狗血淋头,被打得人血淋头,腿断了不说,还被带到了派出所。你看他现在,安分了吧。出过很多事了,你比我知道的多。你要当机立断。你不像我。我们目前还挺和谐。我讲话你嫑动气哦,春草就是比黄丫聪明,她和她老公好得很,三天两头煲电话粥。她可会麻痹他了。你看看你,后院都起火了……
老高脸黄了,嘴还不软:你嫑听风就是雨,没什么大不了。敌进我退,实在不行我就撤呗……
话音刚落,相框子却上了墙。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上有份调查显示,63%的夫妻平均一天通三次话。
这一天春草一共给老董打了两个半电话。
春草打来第三个电话的时候,老董还滞留在航站楼東侧的人行道上。
起风了,大片大片的乌云像听到了集结号一路向西,很快给太阳盖上了厚厚的棉被。现在,明显凉快了,很多观众活跃起来,流连忘返——这些人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了?
手机又响了。
春草问:你在路上吗?大概还有多久到?
老董说:啊,还没……要不,你们先吃吧。
春草说:给你过生日哩,主角没到,我们怎么能先吃呢?
老董一惊:啊,给谁……过生日?
春草说:给你啊!今天不是十月七号吗?
老董很诧异:今天……我生日……你怎么晓得的?
春草有点得意了:哈哈,保密。好了,不逗你了。有一回,我无意当中看了你的身份证,就记下了。
老董不知道应该感动还是需要警惕:你……你可真有心啊。
春草本想继续表功,说着说着却伤感了:我前几天就订好了蛋糕,早上拿回来了。我买了不少菜,都做好了。我请老高黄丫,也是为了给你庆生……本来想给你个惊喜……你快回来吧,我没别的意思……是不是昨天黄丫鼓动我去照相,让你有压力了?
老董一时语塞:这个……是……不是……我不习惯过生日,我从来也没过过生日……
春草说:我不会逼你的。你不想照不照就是了。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文化深,眼眶子高,心重……你是不是,一直就没看上我?
老董语无伦次了:没……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不好!前面要出事了!不讲了!
前方五十米处,一辆小车正迎面驶来。它像一个醉汉在扭秧歌……说时迟那时快,这辆车突然加速,直接冲上了人行道!人群中一片尖叫!老董本能地闭上了眼睛。
两秒钟后,老董睁开眼:车子在撞断几根护栏之后停住了,一个轮子悬在空中。
千钧一发!如果再往前五十厘米,这辆车就有可能……这可是几十米高的立交桥!人们常说的“后果不堪设想”其实不难设想:车毁人亡。
众人一齐涌过来,蚊香一样围成几个圈。
有人嚷嚷:报警!赶紧打110!
开车的小伙子面如死灰,副驾驶位子上的女孩瑟瑟发抖。
你怎么开的车?啊?怎么回事?
女孩不说话,“嘤嘤”地哭。
小伙子吞吞吐吐:刚才……我俩在吵架。
你不好好开车,吵什么呢?
我俩……今天回老家,六点十分的航班。我们有一个女同学,明天结婚,我想去……参加婚礼……
这不挺喜庆的吗,有什么可吵的?
女孩抽抽搭搭地说:那女的……是他前女友,我不想让他去……
小伙子辩解道:我才跟她商量,她就发飙了,上来就抢方向盘。
所有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少顷,又七嘴八舌说开了。
就为这事啊?你这个人真是的,都跟人家断了,还黏黏糊糊的。人家结婚,关你屁事啊?你瞎掺和什么呀?
你这姑娘也是,他开着车哩!你忍一忍,待会儿再吵不行吗?
待会儿只要空姐同意,你罚他在飞机上跪着也行啊!
你们就作吧!亏得没出更大的事,不然的话,哼,我看你俩啊,去参加刑场上的婚礼吧。
咱别在这儿磨牙了,让警察来处理吧!他俩不受点惩罚,就不长记性,下次还会作死!
这两个人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
站在外围的老董眼前一阵阵发黑,手心全是冷汗。
手机再一次响起,屏幕跳出来一个字:家。
啊,是家里的座机!是夏苗!
夏苗的声音轻而柔:圣文,你在忙吗?
老董大名叫董圣文。
他脸上火辣辣的:不忙。我昨天不是才给你打电话了吗?
夏苗说:那是你打的。我就不能打个电话给你啊?
老董说:能,当然能。
夏苗说:刚才我看日历,才发现今朝是寒露。日子过得真快,你走的那天,是惊蛰。
老董说:哦,是吗?
夏苗说:吃了寒露饭,少见单衣汉。天凉了,特别是一早一晚,你要多注意,小心感冒。
老董笑了:深圳还热得很哩,动不动还三十度。
夏苗也笑了:这样啊?我真是想当然了。哦,今天是你的生日,要是在家,我会为你打蛋下面。你为自家买个蛋糕吧!
老董说:我们又不是城里人,不习惯过生日。谢谢你啊!
夏苗说:老夫老妻的,还谢什么?都有点生分了。
老董挠挠头,憨憨地笑了。
夏苗说:好了,没旁的事了。家里一切都好,你就把自家照顾好吧。
老董说:好。
不知何时,那架B6201也飞走了。
挥之不去的,是那缠绵悱恻的旋律——
低低地飞,低低地飞,你这红蜻蜓,你丢失了什么,飞得这样低……
老董下意识地打开手机,点了那个字——家。
通了,他却无言以对。
夏苗不停地问:圣文,是你吗?说话呀!你怎么了?
大約过了三分钟,老董说:我……我想回来了。
随后的两小时,老董让自己失联了。
他并没有走远,他又进了机场大厅。
他在离洗手间最近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空椅子。
他走过去坐下了。
他陷入了思考。
中间有几次来电,他看了一眼就掐了。后来他索性关了机。
不知过了多久,他开机,找到一个“未接来电”回拨了过去。
那边是春草。
这是史上最艰难的一次通话。老董说着说着,汗流浃背,额头上也沁出了一层晶莹的汗珠。他虽然磕磕绊绊,甚至一度眼圈红了,却没有停留,他不能让自己有哪怕一分钟的犹豫和喘息。他的结束语言简意赅:今天晚上……也不回来睡了。
终于画了一个句号。老董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
夕阳西下,老董将今天的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老高。
责任编辑 陈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