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通义》:“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
2021-08-16钟岳文
钟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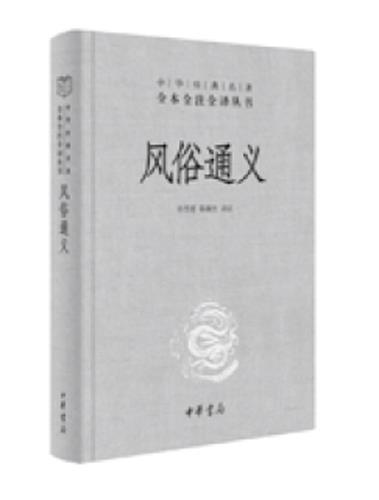
《风俗通义》是东汉学者应劭所著的一部极有特色的作品。《隋书·经籍志》将其列入子部,清代学人开始将其归为小说家,现代学者张舜徽在其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中又将它列入“杂史类”,可见这部书涉及文、史、哲诸多领域,内容极其广博,以致难以归类。
最早对《风俗通义》进行评说的是南朝宋的历史学家范晔,他在《后汉书·应劭列传》中说:“(應劭)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不典,是说这部书的文字不够典雅;洽闻,则是肯定这部书内容丰富,涉猎广泛。《晋书·王隐传》记载:“应仲远(应劭的字)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其中“不朽”二字,足以说明《风俗通义》具有极高价值,也是对此书很大的赞赏。
一、生不逢时的应劭
应劭字仲远(一作仲瑗),东汉汝南郡南顿县(今河南项城)人。关于他的生卒年,《后汉书》本传没有交代,从其行事的记载中,可知他主要活动在灵帝和献帝时期。
应劭出生于官宦世家,四世祖应顺在和帝时为河南尹、将作大匠;祖父应郴官至太守,成语“杯弓蛇影”讲的就是关于他的一则逸事;父亲应奉历官武陵太守、从事中郎、司隶校尉,此人也是史学家,“著《汉书后序》,多所述载”。《后汉书》李贤注引《袁山松书》还有这样的记载:“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这是综合《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书而成的“简本两汉史”,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可以说,家学的影响,为应劭涂抹上一层深厚的学术底色。
应劭少年时即专心向学,有博学多闻之誉。读书之外,他还像其他学子一样遍访名人,游学京师,颇有声誉。成年后,应劭被举孝廉,而后做了车骑将军何苗的掾属。灵帝中平二年(185),汉阳边章、韩遂与羌人侵扰三辅地区(即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朝廷派皇甫嵩出兵讨伐。因兵力不足,有人建议让鲜卑前来帮助,应劭驳之以为不可。经反复辩论,“于是诏百官大会朝堂”,最后“皆从劭议”。可见应劭在当时是很有发言权的,而且见解得当,受到了认可。中平六年,应劭被提拔为泰山(太山)太守。汉献帝初平二年(191),黄巾军进入泰山境内,应劭带兵应战,大败黄巾军。兴平元年(194),曹操之父曹嵩和曹操的弟弟曹德由琅邪郡到泰山郡,曹操令应劭派军队接应他们到兖州,但是应劭的军队尚未到达,徐州刺史陶谦便秘密派出数千骑兵截杀了曹氏父子。应劭害怕曹操责罚自己,无奈之下弃官投奔了冀州牧袁绍。建安二年(197),朝廷下诏任命应劭为袁绍的军谋校尉。校尉是仅次于将军的中级军官,军谋即在军中负责参议谋划。据史书记载,“时始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存。劭慨然叹息,乃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此后,他再未离开过冀州,最后在邺(今河北临漳)病逝。
东汉以经学取士,世代通显的官宦之家,同时也是经学世家,应劭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一生恪守经义,加之他天资聪颖又胸怀大志,本应大有作为,只可惜生不逢时,身处东汉末年这个时代。桓、灵时期,皇帝荒淫无度,朝纲不振,内忧外患,江河日下。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东汉后期的黑暗腐朽主要体现在,一是外戚、宦官交相掌权,他们谋害忠良,排斥异己,导致民众与朝廷离心离德,东汉王朝岌岌可危。二是臭名昭著的“西园”更是创史上政治腐败之最,明码标价卖官鬻爵,官职成为统治者换取私财的物品,“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整个朝廷陷入极端无序的混乱状态。其三是“饰虚矜伪,诳世耀名”的虚伪风气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士人沽名钓誉,矫揉造作。各种夸大其词、虚妄无据的言论,各种不实的互相吹捧和溢美之词充斥坊间,假仁、假义、假孝、假悌现象层出不穷。然而,尽管“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但应劭仍然坚持儒家知识分子的操守,勤于政事,尽忠报国;而“乱靡有定,生民无几”的社会现实,更刺激了他内心深处的责任意识。
应劭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太多建树,但在学术文化上却很有贡献。他想用著作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从而起到求实尚真、改变风俗、收揽民心、恢复社会秩序的目的。《风俗通义》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二、《风俗通义》的写作宗旨
《风俗通义》是一本特殊性质的著作。这部书以记述历代风俗礼仪为中心,上至考察古代历史,下至评论时人流品,旁及音乐、地理、怪异传闻等。意图通过“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起到齐风俗、明义理、正人心的作用。
对于此书的写作宗旨和关注风俗的必要性,应劭在书前的序中作了详细阐述。他认为,汉朝建立后,的确开启了一个学术的新天地,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学术界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文辞繁杂,儒生们孜孜不倦、皓首穷经,却与儒学要旨渐行渐远;二是只看重儒学在学术圈的传播与效用,而忽视了理论联系实际,与日常生活的隔阂越来越深,积非成是,产生错误的价值观念。
那么,该如何扭转和改变这样的学风、文风从而拯救世风呢?应劭开出的药方是从风俗入手。他认为社会风俗、风气的好坏,直接影响社会安定与否以及国家的治乱兴衰。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应劭的远见卓识以及对今天的借鉴意义。
同时,应劭还强调知识学术要关注日常生活,要发挥它在为人行事方面的重要指导作用。与其他史著更多关注治乱兴衰的思路有所不同,应劭从对治乱安危转向对为人行事的指导,把教化工作做到生活日用层面上,强调要从人的思想改造入手,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古人虽然常有整肃风俗之论,但对其重要性强调得如此明白,且用专门著作实践其说的,应劭应有首创之功。《风俗通义》的特殊价值正在于此。可以说,这部书在与其他史著相同的出发点下,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这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后来郑樵、颜元、李塨等人强调实学,与应劭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应劭的《风俗通义》以儒学精神为核心,以匡正时弊及救国为目标,考释物类名号,从而实现正人心、厚风俗、存典章、复礼仪。他认为“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通过纠正错谬的流俗,可以使“事该之于义理”,即恢复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
应该说,应劭的“风俗”既包括“相沿积久而成的风气、习俗”这一基本义项,同时也涵盖学术、政治、典章、礼仪等文化内容,深刻反映了东汉及东汉以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正因如此,《风俗通义》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我国第一部民俗学专著。
三、《风俗通义》的主要内容
《风俗通义》原书三十一卷,包括《录》一卷。到了北宋仁宗时期,此书仅剩十卷。宋神宗时,苏颂以官私本校定此书,当时所见的就是十卷本。宋代的官私书目,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都著录为十卷。现在通行本的卷数与篇名次第与苏颂所校本相同。而且现存的十卷中,内容也有部分缺失和讹误。
苏颂之后,清人对《风俗通义》整理得较多,其中卢文弨和孙诒让为恢复此书本真做了较大贡献。现代学者吴树平先生整理的《风俗通义校释》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通行本《风俗通义》共十卷十篇,每卷一篇,具体篇目为:《皇霸》,上述三皇、下记六国,是简明的先秦历史常识;《正失》,纠正民间传言的失谬,内容多为汉事误传;《愆礼》,例举行事苟妄过头,不顾礼俗限度,是对东汉世风的分析批判;《过誉》,对因行为乖张、违背情理而招致众誉进行察辨,从“愆礼”的反面抨击世风;《十反》,列举十件行为相反的事,予以褒贬评判,阐述进退取舍的处世道理;《声音》,述说音乐起源、五音、各种乐器及其故事,是音樂知识的专篇;《穷通》,辑录古今人物先否后喜、穷而复通的事例,以明人情世故与做人原则;《祀典》,记叙神物,解释了一些重点神灵和祭祀常识;《怪神》,分析民间流行的各种怪力乱神,认为大多属于淫祀,故而持否定态度;《山泽》,介绍五岳四渎、林麓陵丘、湖泽陂薮、河渠沟洫,以及京、墟、阜、培等地理名物,是关于地物的常识。
在编写体例上,应劭斟酌得法,书中的结构大致是这样:各卷皆有总题,题下各有散目。总题后略陈大意,而散目先详其事,以谨案云云辨证得失。也就是说,每篇前有总序,讲立篇之由,时时关照整齐风俗的主题。其后是散目,比如《皇霸》篇下有《三皇》《五帝》《三王》《五伯》《六国》等目。在每条散目之后,应劭又用案语(即“谨案”)加以点评,使其因事明理的作用更为显豁明朗。
从《风俗通义》的篇目上看,应劭的考虑是十分周全的,涉及面非常广,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此书的有益世用,于此可见一斑。而且书中所载内容多有正视听、解疑惑的效果。
纵观全书,我们能够总结出应劭的主要思想:
一是正风易俗。正如应劭所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他认为“风”是自然其然的自然界,“俗”是自然其然的人世间。正如天气有寒暖一样,人也有善恶。如何让人避恶趋善,应劭认为要效仿圣人:“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历来儒家学者都有一种圣人情结,应劭也是以圣人自勉,他要像圣人那样挽风俗于迷惘之中,他要给世人树立行为准则和规范,而正风易俗的终极目的就是扭转东汉的乱世。
二是崇儒尚礼。应劭希望通过整顿风俗净化民众的思想,使他们的行为统一到符合儒家伦理的标准上来,从而恢复礼的秩序。东汉末年,与孔子所处的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有相似之处,因此应劭反复申说孔子“复礼”的主张,不厌其烦地征引《尚书》《论语》《仪礼》《周礼》《礼记》等经典,为“辩风正俗”和品评人事提供理论依据。比如,《风俗通义》中的第一卷《皇霸》,辨析“三皇”“五帝”“三王”“五伯”等名号,强调礼制所规定的宗法等级、尊卑秩序,同时阐释“圣贤”被儒家膜拜的缘由,从而规范世人的价值取向,树立儒家的礼义制度。
四、《风俗通义》的现代价值
《风俗通义》内容广泛,涉及风俗、文学、历史、地理、思想等多个领域,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它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劭在对社会风俗进行考察的同时,又对东汉末年的陋俗和虚伪之风进行了批判,显示出很强的求实精神。比如,汝南人袁夏甫,年轻时被举为孝廉,担任司徒掾,人世间的事,他都不关心。后来,他关闭大门,堵塞窗户,不接见宾客。孩子也不能见他,只能遥拜。其母去世后,他也不为母亲服丧设牌位。应劭对此批评道:“《孝经》说:‘双亲活着,就用爱敬之心来侍奉他们;双亲去世,则用哀戚之情来对待他们。本为一家人,却犹如分居不同地方,起床后不当面问候母亲,离爱敬之心太远了。母亲去世后,又不能送葬,离哀戚之情也太远了。”
《怪神》一卷对汉代敬鬼神和淫祀的情况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西汉时,人们为城阳景王刘章立祠,并“烹杀讴歌,纷籍连日,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历载弥久,莫之匡纠”。应劭认为“安有鬼神能为病者哉!”此种祭祀浪费了大量的财力民力。因此,他主张从今往后每年可以祭祀两次,准备祭品就够了,不许杀牛,不许远远地迎接唱戏的人,不许到家族村落去收赋税,不许使用繁华奢侈的装饰。这件事既体现了应劭的唯物主义思想,又反映了他务实、爱民的作风。
应该说,《怪神》表面上是写神怪,实际是为了说明这些事情不足为怪。应劭在“世间多有见怪惊怖以自伤者”条中,以齐桓公见泽神委蛇以及自己祖父应郴为汲令时“杯弓蛇影”的经历,说明很多所谓的怪事都是自己吓唬自己的。在“鲍君神”的故事中,人们竟然把一条鲍鱼当作神灵加以膜拜,直到鲍鱼的主人把它取走才作罢,应劭揭露说这不过是众人的自欺欺人罢了。
综合来看,《风俗通义》既有风俗和文化知识的求实性研究,也有带政治思想倾向的批判性揭露,作者寓教化于褒贬评论之中,社会领域是其关注的主要对象。如对虚伪之风的批判多是从礼出发,批判人们在处理家庭关系以及君臣、师生关系中的表现;而对人性真实情态的揭示,主要从朋友关系及更广泛的人际交往等方面来阐述。至于求实的方式,主要有文献考证、走访亲历、据实分析、训诂、合理推理等。
其次,《风俗通义》有着较高的史学价值。应劭在考辨名物、订正俗讹的基础上,关注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习俗,同时对士人官吏的道德行为风尚进行了记述评论。这是《风俗通义》的主要史学特色,为我们了解汉代以前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
若从历史评论的角度看,《风俗通义》的议论部分承接《左传》《汉书》论赞的遗绪,又少了通常史书中的篇幅限制,因而能够广征博引,很有特点。应劭“一据典礼,不杂申、商之说,平允纯正”,同王符、崔寔、仲长统持名法之论、综核名实的思路有明显不同。应该说,品评人物的风气促进了历史思想的发展,丰富了人们认识历史人物的理论。如果我们把刘劭《人物志》看作魏晉南北朝人物评论的开端,那么《风俗通义》似乎可以看作汉代人物评论的总结性著作之一。
《风俗通义》的史学特色还突出体现在继承“考信求实”的传统,考辨史事传说上。比如《正失》篇的总题先以孔孟言行说明考辨史事传说的重要性,所举的例子以及开篇几个子目都直接引自《吕氏春秋·察传》。有学者指出,《察传》篇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到审察历史资料的重要性,提到有关的事例和依据。由此可以看出应劭对“考信求实”这一传统的把握。而这个传统,也是今天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最后,《风俗通义》还有着文学价值。先秦两汉时期正是我国小说的孕育萌生阶段,尽管当时的“小说”概念与我们今天的小说并不一样,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小说已经开始逐渐摆脱依附子史的地位而向独立方向发展。此书不仅吸收、继承了史传中的诸多小说因素,一些篇章具备了小说的特征,而且对后世志怪、志人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是这种承上启下的地位,才使它在中国文学史、小说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众所周知,史传文学与诸子散文是中国小说的两大源头,一个偏于叙事,一个长于论说。而历史散文不但孕育了小说文体,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发展,而且其中非史官文化因素的发展,还派生出介于历史散文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体—— 杂史别传。这些杂史别传,从史学角度讲是“朱紫不别,秽莫大焉”,但从小说角度讲,却在历史散文与小说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风俗通义》就是其中的代表。
而且,在艺术形式上,《风俗通义》也为后世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应劭根据写作需要,多将民间传说、奇言怪事与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相结合,真假相掺,虚实相伴,因果分明,从而为中国小说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