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爱情与现实矛盾
2021-08-11刘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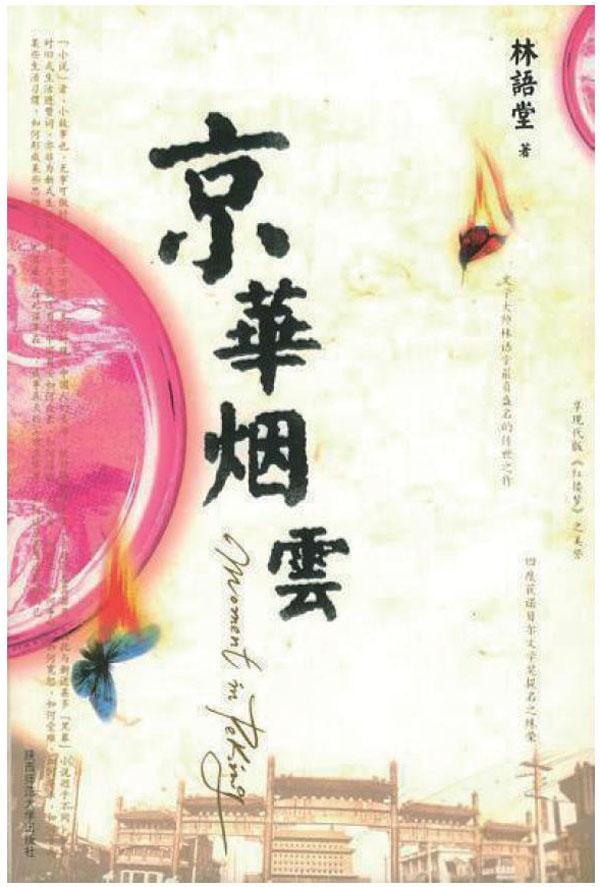
摘 要: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以板块化的家庭活动为主要框架,而这些家庭里面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活动则充当着连接三大家庭的线索。在京华的世界里,这群青年男女由于社会际遇、家庭背景、个人性格、所受教育的差异从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为我们演绎了一段段充满浪漫性、悲剧性、现实性的爱情故事,给读者带来了更加多样化的艺术审美体验。
关键词:京华烟云;理想爱情;现实矛盾
《京华烟云》作为我国著名作家林语堂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有着“现代红楼”的美誉。这部小说既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与道的独特诠释,也传递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悲剧意识,而且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之下更是创造了一群真实鲜明、可爱可悲的青年男女人物形象。正如林语堂在《京华烟云》的“序”中所说:“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1]序言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京华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因阶级地位不同导致的爱情之悲,如体仁与银屏;因家庭相交推动的既定婚姻,如平亚与曼娘、经亚与素云,木兰与荪亚;因命运使然成就的贤女奇士,如莫愁与立夫;还有因猜疑误解破碎的青梅之恋,如阿非与红玉。这些青年男女表面上有着追逐自己理想爱情的自由,但又在个人性格、家庭阶层、社会动乱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下被迫走上了理想爱情相反的道路。而透过这些青年男女命运交织的网,我们可以窥见《京华烟云》的人物世界里闪烁着爱情晶体的多面光辉。
一、浪漫性:内心精神的驱使
林语堂一生追求的是“一种浪漫的骑士风度和闲适的士大夫情趣”[2],他将自己的浪漫与情趣完全赋予了自己心中的完美女子—-木兰。林语堂为木兰安排的虽然是一场不算完美的婚姻,但却为她创造了一份足够浪漫的精神之恋。
从木兰、立夫二人在白云观打中铜钱时开始,命运的齿轮就已悄然转动。在秘魔崖相见,一起共游西山的时候,木兰投石头、吹口哨、唱京戏这些事,使立夫大感意外,而立夫认为残基废址最美的见解,同样也让木兰心中暗暗赞赏。两人的初次相遇就已经让木兰心中逐渐生出了对立夫的好奇与欣喜。在立夫寄宿于姚府的那段时间里,与木兰共同探讨甲骨和古墨的经历让两人心中爱情的嫩芽逐渐萌发。书中这样写道:“立夫从来没有想过男女之爱,甚至对于女人的美也是无动于衷的。可是他喜爱木兰,只因为木兰懂得这些东西,并且智慧高,精神好。”[1]179种种迹象表明木兰与立夫的心灵是相知相通的,精神上能够产生共鸣,可以说立夫是男性化的木兰,是木兰的另一个自我。
虽然和荪亚订婚了,但木兰在情感上无法割舍立夫,阴雨多云的天气,她会犯罪似的想起立夫。在立夫的面前,木兰能够摆脱礼俗传统的约束,变得活泼愉快,谈笑风生,内心有无法言喻的快乐。跟立夫在一个屋檐下时,木兰能感觉到精神上的自由,感受到甜蜜的、陶醉的、幸福的味道,这是爱情的力量。木兰是幸运的,她在最好的年华,遇到了让自己春心萌动的人。在莫愁和立夫订婚前,木兰是最有可能成为立夫灵魂伴侣的人选,但灵魂伴侣侧重于灵魂上的共振、交流与共鸣,而“妙想家”木兰和“激进派”立夫是同一种力量的叠加,二人恐怕无法实现生活上的完美契合。回归到现实生活之中,正如傅先生算命时所言,莫愁是土命,沉稳、安静、圆通,而立夫是木命,凡事喜欢向前冲,他需要以柔克刚,而莫愁正是那个能滋长他、使他繁荣向上的人。
作为道家女儿,木兰相信个人的婚姻大事,是命里注定的,她对嫁给荪亚一事,一向也没有怀疑过,她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是她对立夫的情感并未随着自己嫁给荪亚而消失,而是悄悄地掩埋于心中,偶露峥嵘。两人年少期间在什刹海看水时,曾有过一个去看圆明园遗址的约定,多年之后登泰山之时,木兰还记得这个约定,立夫亦然。其实京城内外的名胜古迹木兰全部游览过,唯独圆明园遗址是她有意留下的。甚至于她和荪亚路过圆明园之时,木兰并没有和荪亚一起去,而是提出日后等立夫和莫愁一同前去。这是木兰和立夫二人之间的小约定,无论过多少年,她都愿意为立夫保留位置。又或许木兰并没有真正掩藏住自己的情感,登泰山之旅,木兰曾故意让立夫拉她起来,立夫也不胜大姨子的撒娇与魔力,将木兰拉了起来,以至于轿夫还误认为他俩是夫妻。这次登泰山之旅,木蘭深深体会到只要接近立夫就会快乐满足,甚至于日后她因丧女消沉绝望之时,还会想起和立夫登泰山的情景。直到立夫因罪入狱,木兰孤身夜闯驻军司令部为立夫求得赦免令,那一刻木兰对立夫的爱是一种伦理秩序再也压制不住的释放。她无法承受失去立夫的痛苦,立夫是其精神支柱,木兰在遭受到重大挫折时,不仅会想到父亲,还会想到立夫,伤心失意的时候,只要想起他,心里便会觉得熨帖,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爱心的驱使,让木兰在立夫被捕之后义无反顾地四处营救,显露出了其对立夫的爱,但在立夫脱离险境之后,木兰开始变得理性,将这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秘密重新放入了心中。
所以,木兰对立夫的暗恋不仅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还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诠释,更是林语堂“浪漫的骑士风度和闲适的士大夫情趣”在二人情感上的寄托。
二、悲剧性:个体生命的消亡
曼娘是林语堂笔下中国传统女性的理想人物,是古典美的化身,同时她又是全书最值得同情的女子之一。曼娘作为曾家的表亲,从小便与平亚相识,两人心中暗生情愫,心意相通,但曼娘是由孔门儒者的父亲教养长大的,思想守旧的她内心藏着的是一份压抑的爱、逃避的爱、想触碰却又突然缩手的爱,以至于每当平亚向曼娘表示亲近,想要去接近她时,她是闪躲的、慌乱的。封建礼教的思想在她心里作祟,使她觉得必须在未婚夫面前保持高雅、端正,更何况他们俩的好日子还有一辈子呢。可是命运的钟摆从未为人停留,留下的只有叹息。一直以为的来日方长,等来的却是平亚身染重疾。当她终于能名正言顺地嫁给平亚,而不再是暗中静悄悄地自言自语地说“平哥,我是你的人了”的时候,却是以冲喜的形式去挽救她最心爱的人。但哪怕是以冲喜的名头,她也是毫不犹豫的,甘愿以处女之身向爱情的神坛郑重地献祭。她认定自己只会是平哥的人,活着是曾家的人,死了是曾家的鬼。但婚姻生活仅仅持续了十天,爱情的痛苦却伴随了曼娘的一生,或许曼娘的一辈子仅仅只有那十天真正活过。旧式的礼教成就了曼娘的节妇形象,赋予了她从一而终的思想,这也让她的命运有了悲剧的底色。
同样是青梅竹马,同样是表亲,阿非与红玉的感情之路同样让人痛心。自傲、任性、敏感的性格使红玉最终难逃雹碎春红、霜凋夏绿的命运。红玉读的虽然是教会学校,但她骨子里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她缺乏主动追求爱情的意识,总是等候自己的爱人来俯就她,这一点从阿非与红玉小时候装洋鬼子、扮作一对夫妻时就可见一斑。阿非想要去牵红玉的手,思想守旧、性格敏感的红玉立马把手缩了回去。但当阿非转向和立夫的妹妹环儿玩闹时,红玉气得只能在旁呜咽哭泣。红玉和阿非一块长大,她早熟,但阿非却不是,所以阿非一直不能读懂红玉的内心所想。阿非不明白为什么他和丽莲一起聊“洋”东西会惹红玉生气,也不明白他和宝芬走得太近会惹红玉生气。红玉当然知道阿非爱她,但她希望阿非能读懂一个怀春少女的心,她只愿阿非为她一人所有,时时环绕在她的周围。巴尔扎克说:“无论处境怎样,女人的痛苦总比男人多,而且程度也更深。 女人是静止的,面对悲伤无法分心,她直往悲伤替她开的窟窿下钻,一直钻到底,测量窟窿的深度,用她的愿望与眼泪来填满这一窟窿。”[3]红玉之悲在于爱得太深,她太怕失去阿非,以至于想牢牢地把他攥在手中。但爱是永远不能封口的创伤,攥得太紧反倒会弄疼自己。与此同时,她也想得太多,自古红颜不见得薄命,聪明多才才薄命,无知是一切快乐的源泉。她躲在假山后偷听到的阿非与美国小姐的那一段对话,让她以为阿非是由于怜香惜玉才愿意跟她在一起,愿意伺候她一辈子。这份误解让羞愧、自责、爱恋、惋惜、自尊、牺牲等一系列字眼像一块块坚硬的石头砸向了她自身,彻底瓦解了她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她认为她的自尊遭受到了伤害,她的爱情遭到了亵渎,于是月下老人祠的签文成为了牵引红玉走向月夜寒塘的绳索,一块美玉最终陷于污淖。
三、现实性:理想生活的落差
在《京华烟云》中,有两个人物对理想的生活有着执着的追求,一个是银屏,一个是木兰。不过,银屏是試图以下犯上,成为姚家的女主人;而木兰是想自上而下,去过质朴闲适的生活。
银屏跟《红楼梦》里的晴雯颇为相似,都是心比天高、身份下贱的丫鬟角色。银屏从小就开始伺候体仁,长期的侍奉让她与体仁之间产生了爱情,正是这份爱情让银屏冲昏了头脑,试图凭借体仁来改变自己的身份,用体仁的爱来换取地位,过上光鲜亮丽的生活。但她没有认识到她和体仁之间存在着一条阶级的鸿沟,而身为封建家长典型人物的姚太太是决不会允许自己的儿子同丫鬟结合的。虽然体仁在决定去英国留学时郑重其事地在母亲面前为银屏许下承诺,让银屏等他回来,但事实上在体仁离开家的那一刻,爱情的保护伞已经在银屏头上撤去。留在姚府做太太的理想生活对她来说终究是一个很快会消逝的梦,而她在华太太那里的蛰伏只是美梦幻灭前的最后挣扎。
在体仁回家之后,银屏用尽狐媚之术将体仁留在自己身边,而且留得越晚越好,并将其视为对姚太太的报复。此时的银屏心中向善的一面逐渐被恶所吞噬,她为了留住体仁,甚至愿意和华太太共同合作占据住体仁的整个身心,只为控制住体仁。银屏在为姚府生下一个孙子之后,本以为在这场挣扎中获得了全胜,这个孩子是银屏实现自己理想生活的救命稻草,但同时也是这根稻草刺破了她的美梦。在姚太太的权威下,这个孩子只能归姚府所有,当仆人抱走孩子的那一刻,银屏的美梦也就彻底消逝了。尽管体仁跟她站在统一战线上,但阶级的鸿沟永远容不得一个充满野心的丫鬟来跨过。或许是认清了现实,银屏最终也只能选择自缢而死来表达抗议。正如书中所问:“银屏算不算一个好女人呢?”倘若她不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份,正视阶级的落差,也许她会成为一个能干的主妇、热爱子女的母亲、儿女心中的完人吧。
木兰的婚姻是受到家族支持、众人祝福的,那么她的婚姻是理想的生活吗?恐怕不尽然。木兰婚后和荪亚虽然过上了快乐充实的生活,但身为“妙想夫人”,木兰对生活有着自己独特的追求。她想要放弃富家豪宅的生活方式,到乡间过一种草木小民的淳朴生活,她愿意做饭,自己洗衣裳,做个平民百姓,不问政治,不求闻达,只要荪亚在她身边,一起过平安日子。但荪亚对人生的向往不说跟木兰完全不同,至少是有着分歧的。因为他是富里生富里长的,他喜爱物质生活的舒适和应酬宴饮的欢乐。木兰觉得拿个锅铲去铲掉饭锅底上的黑烟子、同孩子们一起捡柴、自己亲手折断树枝子这些事情新鲜有趣,充满诗意,而在荪亚眼里木兰的这种生活理想是滑稽可笑的。与之相反的是当莫愁和立夫去杭州探望木兰时,立夫对木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大为赞赏,这就是灵魂伴侣和生活伴侣的落差。事实证明,木兰追求理想确实太过火了,以至于她没有注意到荪亚内心的真实想法。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让荪亚觉得单调乏味,所以他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去寻找年轻、漂亮、时髦的艺专学生曹丽华。幸而姚老先生和木兰的巧妙处理才让这出丑剧有了一个幸福的收场,让自己的婚姻生活重回正轨。但这次事件证明,荪亚只会是木兰淳朴、自然的理想生活中无奈的参与者,而不是完美的同行者。
四、结语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为其笔下的众多青年男女创造的一个多情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展示了爱情的多面性,为着内心去爱、为着崇拜去爱、为着地位去爱、为着认可去爱、却又因着一份婚约、一道鸿沟、一场疾病、一个误解,被迫与自己所爱的人分道扬镳。在无能为力的现实面前,他们是勇敢的,哪怕在经历过命运无情的拨弄过后仍然没有放弃爱的希望。这群青年男女的爱情是在京华中绽放的烟火,绽放时霞光万道、光彩夺目,但在烟消光散之后,空气中却氤氲着数不尽的遗憾和泪水,夹杂着无数的叹息。
参考文献:
[1]林语堂.京华烟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陆明.试论林语堂的幽默与闲适[J].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2):36-38.
[3]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M].傅雷,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刘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刘贵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