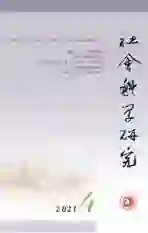重访英美“新批评”:起源、承继与超越
2021-08-09赵元
〔摘要〕 流行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虽被其后出现的更新的批评理论所取代,但是面目各不相同的批评理论仍带有“新批评”的诸多痕迹。当前,西方批评理论走到了一个关口,重访“新批评”的起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不仅是对“新批评”的遗产做出一次重估,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更好地看清西方批评理论的整体走向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本文的最后着重讨论了卡勒的近著《抒情诗理论》如何再次聚焦“新批评”最能发挥优势的诗歌领域,并指向了一种超越当代批判理论而又不同于“新批评”的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 新批评; 文学本体论; 内部批评; 乔纳森·卡勒;《抒情诗理论》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4-0191-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威·休·奥登戏剧创作研究”(18YJC752053);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资助(2019THZWJC53)
〔作者简介〕赵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084。
严格来说,“新批评”并不成其为一种批评流派,一般被划归为这一流派的批评家们实际上并没有组成一个有着统一观念的团体。新批评家们个体之间的差异远大于他们的共性。如果想探讨新批评家们具体的、全面的文学主张、批评理念和批评实践,需要对他们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还原他们那被“新批评”的面具所遮蔽的本来面目。正如“新批评”的理论总结者、批评史家韦勒克在其巨著《现代批评史》所说的那样:“在批评中至关重要的是个人的创见,而不是集体的思潮。绝不应该把批评家仅仅看作是(思潮)的实例”。①不过,如果要从批评史的角度探讨新批评与后来的批评理论之间的关系,倒不妨把这些批评家放在一起,只关注后世的批评家、理论家眼中所见到的新批评家的群体素描,而不是个体肖像。本文要做的主要是后者,但对前者略有提及。
一、“新批评”的起源
首先,有必要对“新批评”的发端做一番简要回顾。1941年,美国学者约翰·克罗·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出版了一部题名为《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的批评专著,书里讨论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瑞恰兹(I. A. Richards)、燕卜荪(William Empson)、艾略特(T. S. Eliot)和伊沃·温特斯(Yvor Winters)为代表的几位“新批评家”(new critics)的批评理论。兰色姆认为这些批评家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意识到了诗歌与散文之不同,但他们的不足在于未能明确说明二者的差异是什么。在兰色姆看来,心理学批评家(瑞恰兹)、历史批评家(艾略特)和逻辑学批评家(温特斯)都不能令人满意,他心目中理想的诗歌批评家是“本体论批评家”(ontological critic),但當时并无合适人选。兰色姆在三年前出版的论文集《世界的形体》(The Worlds Body, 1938)一书中反复阐发一种他所谓的“本体论”的批评主张,并首次提出诗歌批评应着眼于诗的“本体”。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兰色姆正是他在《新批评》一书中虚位以待的那位本体论批评家,而“本体论”的观点后来往往被视为“新批评”的理论核心。无论如何,自从《新批评》一书问世后,英美学界便以“新批评”这个名称来概括书中涉及的那几位批评家(包括兰色姆本人在内)所代表的那种批评倾向。据后来学界的看法,瑞恰兹和艾略特被视为“新批评派”的先驱,兰色姆以及几位辈分比他低、但同样毕业于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诗人和批评家——艾伦·泰特(Allen Tate)、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人——构成“新批评派”的第一代核心成员,而第二代“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则包括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威姆塞特(William K. Wimsatt)和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等人,他们都曾在耶鲁大学任教。
瑞恰兹是新批评的开创者。兰塞姆在《新批评》一书开篇中指出,“对新批评的讨论必须从瑞恰兹先生开始。新批评几乎就是从他开始的。”②瑞恰兹漫长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20世纪10年代末至30年代末,瑞恰兹在剑桥大学从事美学、语义学和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研究。从3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他在哈佛大学从事教育、“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和普及读写能力的工作。对“新批评”产生影响的是瑞恰兹的前期作品,例如“张力”“平衡”“情感性”(emotive)和“指称性”(referential)语言、“反讽”以及“伪陈述”(pseudo-statement)等耳熟能详的“新批评”术语都出自其《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4)一书。瑞恰兹从语义学角度出发,认为文学语言不同于指事称物、传达真实信息的语言,前者以“伪陈述”表现不同于客观事实的艺术真实。对诗歌语言与科学、哲学语言加以区分也是“新批评派”的追求之一。瑞恰兹着眼于文学作品在读者心理上产生的效果,认为“所有最有价值的艺术体验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由对立面之间的极度张力所造成的那种微妙的平衡,“凭借涵纳的力量而非排斥的力量达致的平稳状态”。③后来,布鲁克斯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瑞恰兹的这种诗歌阅读理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抛弃了瑞恰兹的心理学视角,转而采取语言学和修辞学的概念。瑞恰兹在《实用批评》一书中描述的诗歌教学方法也被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潘·沃伦等美国“新批评家”所采纳、吸收,他们以瑞恰兹的著作为蓝本,十年后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诗歌赏析教材《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 1938)。
艾略特是新人文主义创始人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学生,但是他本人却可以算得上“二十世纪英美形式主义批评的鼻祖”。④艾略特早期批评作品中的某些观点便为后来的“新批评派”所继承。例如他提出了迥异于浪漫主义表现论的非个人化的诗歌理论,认为“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⑤在艾略特看来,诗人不应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掺入诗歌,而是应该像催化剂那样在促使诗的材料变成诗的过程中保持中性;诗歌里要表现的不是诗人个人的情感,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艾略特的新古典主义诗论,尤其是把关注点从诗人移向诗歌本身的基本观点,为新批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当然,艾略特的这些论点远非他文学观的全貌。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艾略特的文学批评论述中增加了历史、社会和伦理的层面。在他的学术生涯临近尾声时,艾略特甚至声称,“切断文学批评与其他领域的批评是不可能的;无法彻底将道德、宗教和社会判断排除在外”。⑥事实上,瑞恰兹和艾略特各自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都十分丰富,给他们扣上“新批评”的帽子并不合适。后来的新批评家们只是强调了这两位先驱人物观点中与“新批评”观点相应的部分,而忽略了他们与“新批评”相左的其他观点。
以下概述“新批评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核心观点。兰塞姆持文学本体论,即把作品视为独立存在的实体,“本体即诗的存在的现实”。⑦他认为文学批评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定义和欣赏文学的审美价值或典型价值”。⑧兰塞姆提出,“一首诗是一种具有局部肌质的逻辑结构”。“逻辑结构”即表层的概念内容,“局部肌质”则指诗的具体形式。诗的逻辑结构可以用散文语言加以转述或概况,诗的具体形式却无法尽述。根据兰塞姆的观点,诗的“局部肌质”犹如圣诞布丁上的“果料”和“甜馅”,他将诗的具体形式对诗的概念内容的增色称为X,认为这个X才是“我们所需要寻求的”本体。⑨
布鲁克斯是专业批评家,他将艾略特、瑞恰兹、燕卜荪、兰塞姆、泰特等人的观点综合在一起,把“新批评”的原则具体化,形成容易付诸实践的要点。他在《释义的邪说》(“The Heresy of Paraphrase”)一文中主张,诗如同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生生的有机体,“构成一首诗的本质的那个真正的意义核心”是无法用散文加以释义的。⑩在《反讽作为一种结构原则》(“Irony as a Principle of Structure”)一文中,布鲁克斯认为“反讽”普遍存在于一切诗歌之中。在一首诗中,诸多意象相互关联,形成一种语境(context),每一个意象的含义都受语境的牵制和影响,产生明显的扭曲和变形,于是形成“反讽”。“反讽”是就诗的结构来说;在诗的语言层面,“反讽”则表现为“含混”(ambiguity)或“悖论”(paradox)。说起诗歌语言的“含混”,我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燕卜荪的名著《含混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在燕卜荪那里,“含混”指的是语言意义的多面性,即歧义,而布鲁克斯所强调的“含混”多指诗歌语言的多种意义之间形成的张力,互相对立的意义在同一个诗歌语境中妥协、互容和共存。布鲁克斯认为诗歌语言的本质就是悖论式的语言,关于这一点,他在1942年发表的《悖论语言》(“The Language of Paradox”)一文中有详细阐述。布鲁克斯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诗歌具有戏剧化的结构,一首诗就如同一出戏,“戏的全部效果来自戏的所有的构成部分,一首好诗,就像一出好戏一样,它没有一个无效的动作,没有任何多余的成分……诗歌从来没有抽象的陈述。这就是说,诗中的任何一个‘陈述都受到上下文的压力,它的意义都要被上下文调整。换句话说,诗中的陈述——包括那些看上去象哲学性的总结似的陈述……都应该当做剧中的对话那样去读。”B1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批评”在美国进入了全盛时期,第二代“新批评家”对他们这一派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归纳。维姆塞特和比尔兹利在他们合写的两篇著名论文《意图谬误》(“The Intentional Fallacy”,1946)和《感受谬误》(“The Affective Fallacy”,1949)中指出,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不能以作者的意图为圭臬,同时,一部作品的优劣也不能以读者的反应为准绳。韦勒克和奥斯丁·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1949)是对“新批评”观点的理论总结。他们在书里重申了兰塞姆的观点,认为一部作品是“具有特殊本体状态的独特的认识客体”。B12他们把文学批评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两类,显然,他们本人是站在“内部批评”这一侧,虽然他们并没有绝对否定“外部批评”存在的理由。
然而,要想对任何一种批评流派形成一种较为全面的认识,就必须留意它与其发生发展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当然也适用于号称只关注文学作品内部形式特征的“新批评”。
二、“新批评”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从一开始,“新批评”就反对从传记、历史、社会、心理或哲学等“外在”方面出发研究文学。流行于20世纪初美国的批评流派——印象主义式的批评、新人文主义的道德主义批评、门肯(H. L. Menchen)和范怀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所代表的反现代主义文化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等——皆在“新批评”反对之列。此外,“新批评”还对学院派的批评——语文学、文本目录学、历史考证和文学史——表示不满。与这些批评流派和方法不同,“新批评”着眼于音韵、格律、文体、意象等形式因素,通过细读,对文学作品做详尽的分析和诠释。“他不仅注意每个词的意义,而且善于发现词句之间的微妙联系,并在这种相互关联中确定单个词的含义。词语的选择和搭配、句型、语气以及比喻、意象的组织等等,都被他巧妙地联系起来,最终见出作品整体的形式。一部作品经过这样细致严格的剖析,如果显出各部分构成一个复杂而又统一的有机整体,那就证明是有价值的艺术品”。B13
由此可見,“新批评”式的细读并非一种纯粹的批评技巧或批评手段,它实际上暗含着批评者预设的价值判断。“新批评家”在分析一部作品时,已经预先假定这是一个由互为关联的词语构成的复杂统一体。一首诗犹如一只精致的瓮或者一台有效力的机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与个人和历史无关的人工制品来构造的。对“新批评家”而言,虽然诗歌提供意义(一种高度复杂的意义),但一首诗是独立存在的客体这一事实比它具有意义这一点更加重要。存在先于意义。因此,在“新批评派”眼里,最好的诗就是那些充满微妙语义关系的复杂而独立自存的诗歌。于是,“新批评”的细读活动实际上是对文学史上的诗歌经典作品进行重新评价。在他们眼里,英国17世纪的玄学派诗歌和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无疑要优于注重情感表达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形式简单、语言朴素的民间歌谣。
在讨论“新批评派”的文学观点时,不能忽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从“新批评派”的先驱艾略特和瑞恰兹开始,即流露出保守主义的倾向。艾略特早在1920年出版的《圣林》(The Sacred Wood)中,就描绘了西方文化逐渐衰颓的发展趋势。艾略特认为,传统的有机社会在怀疑论和科学中分崩离析,导致了“情感的脱节”和人类的异化,但是他相信这种由世俗主义和工业主义带来的西方社会的持续衰退是可以得到遏制的;通过抵制堕落的现代文明,通过返回神话、宗教和同质文化,是可以将理智与情感重新统一在一起的。与艾略特的情况类似,另一位“新批评派”先驱瑞恰兹在他的著作里也对现代社会的堕落加以批评,历数其种种问题,呼吁更高的道德标准。
19世纪20年代初,美国第一代“新批评家”兰塞姆、泰特和潘·沃伦等人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共同创办了《逃亡者》杂志(The Fugitives),并在该刊物上发表诗作。B14到了20年代末,这三位“新批评家”与另一批南方知识分子提倡重农主义,于1930年出版文集《表明立场》(Ill Take My Stand),高举美国南方旧的价值观,呼吁返回乡村文明,抗议北方的工业化道路。大多数美国“新批评家”都厌恶科学,对他们而言,科学是“历史的恶棍,它摧毁了人类共同体,打破了古老的有机生活方式,为工业主义铺平了道路,让人类在本世纪成为了异化了的、无所寄托和不信神的造物”。B15
由此可见,“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批评不可避免地与保守的价值观和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虽然他们竭力让文学批评脱离社会、道德、宗教和政治等外部因素,但是他们的批评实践和批评理论却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批评”与19世纪浪漫主义诗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新批评”反对浪漫主义的表现论;另一方面,“新批评”理论观点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尤其是诗人、批评家柯尔律治。首先,“新批评派”重视文学作品在丰富人的经验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理解诗歌》里提到他们希望引导学生去直接体验诗歌,而不是用被人用滥的批评术语去言说诗歌,他们鼓励学生通过读诗扩大想象力,从而延伸个人经验,发现自身的潜力。B16其次,从兰塞姆有关诗的“肌质”和“结构”的论述,以及从布鲁克斯诗如同活的生物的论述可以看出,“新批评”观点与浪漫主义的有机形式论一脉相承,它们都贬低受古典主义推崇的逻辑、结构和理性。事实上,20世纪早期在英美两国占据主流的诗歌创作风格(现代主义)和诗歌批评流派(“新批评”),表面上是在反对浪漫主义的诗歌和理论,但其实质却明白无误地是浪漫主义的后裔。
三、新批评遗产的价值重估
英美“新批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在四五十年代进入全盛时期,到50年代后期,受到欧陆(尤其是法国)传来的各种新的批评理论的冲击,“新批评”逐渐衰落。但是,说“新批评”已死为时尚早。“新批评”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为后来的批评理论所普遍接受,化为了所有后来的批评理论的基本要素,以至于后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那些观点和方法是“新批评”的遗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批评”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永生。另一方面,“新批评”虽已风光不再,但来自其阵营的批评家开始注重与其他批评理论展开对话,吸收后者的合理成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正统“新批评”观点的偏颇。
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批评潮流打破“新批评”对作品本体的片面强调,开始关注作品间的关系,体裁类型的研究,作品阅读和接受过程,或者文学作品与历史、社会、政治等其他话语形式的关系。
维姆塞特与布鲁克斯合著的《文学批评简史》(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出版的同一年(1957年),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问世,并立即受到英美文论界的广泛关注。弗莱吸收了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成果,他将来自荣格心理学的“原型”(archetype)概念明确定义为“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意象”,它“把一首诗与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B17强调一部作品的意义与同类作品的依存关系,意味着弱化作者对作品意义之产生所起到的作用。这一点是可以在荣格的心理学里找到依据的。荣格认为作品的内容根源于非个人——或者说,超个人——的集体无意识,因此作品的创造过程并不全受作者自觉意识的控制。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在英美文学批评界领了几年风骚之后,便被更新潮的结构主义的光芒所掩盖。从对作品意义根源的理解来看,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理论如出一辙。
结构主义文论家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模式应用于文学,把具体的作品视为文学的“言语”,同类型作品的传统程式则是文学的“语言”。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借由文学的“言语”探索和发现文学总体的规律,或者说“语法”。被视为“新批评”先驱之一的艾略特,其文学传统观侧重文学作品的共时性,而非历时性,把国别文学、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视为有机整体和有序体系,事实上已经具备了结构主义文论的核心特征。此外,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论及的诗歌“非个人化”主张在结构主义那里得到了呼应。卡勒(Jonathan Culler)在其名著《结构主义诗学》(Structuralist Poetics)里讨论了诗的三种程式,第一种就是诗的非个人性(impersonality),其次是诗的整体性(totality)。非个人性使诗摆脱了作者的个人身世和历史环境;诗的整体性仅存在于作品文本之中。结构主义固然否定了单部作品的封闭性,将关注点放在作品之间的关系和体裁类型的研究,因而超越了新批评,但是结构主义把文学整体视为一个封闭系统,切断了其与作者以及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其实质“似乎是放大了的新批评形式主义”。B18
继结构主义而起的解构主义突破——或者说,消解了——“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思维定式,否定单部作品或文学整体的封闭性,否认作品的意义由結构——无论是“张力”“反讽”“原型”还是“语法”——决定。在解构主义者看来,作品文本就像洋葱头一样,没有中心或内核,作品的意义是游移的。把限定性结构强加给游移的意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因而遭到解构主义的批判。尽管如此,从解构主义者所做的“作者已死”的断言可以看出,解构主义在完全切断作品与作者及其社会历史语境之间联系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笔的是“新批评”后期(70年代)的主要捍卫者默里·克里格(Murray Krieger)。1976年,克里格在他当时所任教的加利福尼亚大学Irvine分校发起创立了后来在全美产生重要影响力的“批评与理论学院”(School of Criticism and Theory),并邀请当时最流行的几种批评流派的代表人物共襄盛举。克里格对“新批评”的主要功绩是,通过主动吸收竞争对手的批评术语来为“新批评”辩护,延续了它的生命力。克里格的整体文学观建立在一系列悖论之上,例如,他认为诗歌既是隐喻也是幻象,既独立又开放,既是特殊语言也是普通语言,既是审美对象也是读者体验。由此可见,克里格的理论融合了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但是其中解构主义的成分是为其形式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基本主张服务的。身处批评和理论文本渐趋凌驾于文学文本之上、甚至取而代之的后现代时期,克里格坚持认为,文学作品始终是批评活动的起源和中心。虽然作品本体论这一“新批评”的核心观点遭到读者反应批评、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的挑战,但克里格仍坚守形式主义的基本信念。所不同的是,他不再把文学和真理画上等号,而是把文学视为一种必要的虚构,通过阅读、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读者或批评家获得一种内在的目的性和完整性,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得以彰显。
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语批评界逐渐开始反思源自欧陆的纯理论,更加关注批评理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历史、文化、社会、政治、阶级、性别、族裔等关键词进入文学研究的话语。关注文学的社会历史语境,强调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形式与特定历史语境中各种社会话语形式的博弈,确实打破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语言牢笼,扭转了自“新批评”以来文学研究过于文本化的倾向。不过,这些批评理论并不反对新批评派提出的“意图谬误”,作品的意义是由作者之外的非个人因素(如:意识形态、阶级、性别、族裔、身份和文化)决定的。从这一点来看,这些语境化的批评理论仍可视为“新批评”的后裔。
西方批評理论从原型批评直到文化研究的发展,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单纯的文学“内部研究”不复存在,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历史、艺术、思想史、文化,甚至法学都可以为文学研究所用。换言之,只要“把包括‘文学话语在内的各种社会话语的博弈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就是在从事文学研究。B19这就意味着,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在“新批评”那里得到突显的审美批评不再重要。这些批评理论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审美价值的标准,经典作品与通俗艺术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文学作品不存在好坏高低之分,甚至莎士比亚戏剧与肥皂剧的价值也并无二致。
当代批评理论中的这种泛文化趋势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出版于1994年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重申审美批评之重要,精神与“新批评”相通。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化或道德化的文学批评,将它们称为“怨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布鲁姆坚持要“把一首诗当成诗歌来读”,而不是首先把它视为社会文件或文化产品,他坚信“个人和自我是理解美学价值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B20在布鲁姆看来,阅读西方正典并“不会使人日趋完善,成为更有用处的公民,也不会使人穷凶极恶,变成为害一方的恶人”,它的真正作用是“扩增我们不断增长的自我”。B21由此可见,布鲁姆的主张与当年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理解诗歌》里提出文学作品能丰富人的经验的论述本质相同,他们针对不同的现实问题开出了相同的药方:“新批评派”面对的是工业化社会对人心的伤害;布鲁姆面对的是“怨恨学派”对学人的误导。西方当代批评理论不仅受到传统人文学者的诟病,甚至在“怨恨学派”内部也有人发出批评的声音。例如,后殖民文化理论的鼻祖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90年代末撰文,痛感当今人文之堕落,疾呼回归旧日的细读传统,培养基本功扎实的文学家。B22
面对西方当代批评理论的缺陷,布鲁姆和萨义德试图走的是一条恋旧之路。这意味着全面取消批评理论的洞见,重新投入“新批评”传统的怀抱。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抑或仅仅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觉,目前尚未可知。至少,布鲁姆不重视经典作品的历史社会语境,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弱点。
四、结语:“新批评”的未来
如果说还有一条路可走的话,那就是超越之路——吸收批评理论之长处而弥补其不足。卡勒于2015年出版的《抒情诗理论》(Theory of the Lyric)一书可以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抒情诗理论》从探究抒情诗语言中最能引起读者兴趣,同时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方面入手,详细探讨了抒情诗的诸种形式特征以及诗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新批评”及其后的批评理论做出了回应。
首先,卡勒重申他于40年前在《结构主义诗学》一书中提出的对“新批评派”的批评。“新批评派”对诗歌的阐释学假定——即认为诗歌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被解读——遭到卡勒的摒弃。在他看来,研究诗歌的目的不是为了产生更新、更复杂的释读,而是为了“关注它们提供什么样的乐趣,强调它们言语行为的奇特之处,辨识它们独特的修辞策略,并试图解释它们所提供的历史可能性的限度”(Theory of the Lyric,viii)。由此可见,卡勒所致力的是高于阐释学的诗学。
其次,卡勒发现,从“新批评”开始,英美学术界往往将抒情诗视为一种虚构形式,是由一个人格面貌(persona)言说的、对该虚构发言者的行动的再现。根据这种观念,抒情诗便成了“对真实世界的言语行为的虚构模仿或再现”。B23卡勒指出,这种抒情诗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会导致读者忽视抒情诗里那些在普通的言语行为里无处可寻的显著特征,例如节奏。卡勒援引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名诗《老虎》(“The Tyger”),试图证明这首诗之所以出名,并非因为它是“一段关于创造的力量,或者法国大革命的威胁,或者别的什么的散文沉思”,而是因为它那强劲的四重音节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句法节奏和音韵特质。各路批评家把《老虎》一诗置于各种主题、神话或历史语境中加以阐释,产生了不可胜数的解读。在卡勒看来,这与批评家们感受到了诗中强烈节奏感的冲击从而试图寻找合理解释有着很大的关系。B24
在卡勒看来,抒情诗是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向读者提供思想,供后者反复吟诵。诗歌呈现的是诗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但是诗歌呈现思想的方式与散文中的逻辑论证不同。卡勒认为,在诗歌里,思想是以“自助餐”(smorgasbord)的形式呈现的,读者各取所需,只选择自己愿意接受的内容。卡勒以20世纪大诗人奥登(W. H. Auden)的名作《1939年9月1日》(“September 1, 1939”)在美国发生“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再次走红的事例说明,抒情诗对读者所发生的效用是难以预料的。卡勒指出,读者发现诗中描述的时间、地点、情景和情感与现实惊人地相似。他们对于诗中“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否则就得死亡”这类警句感同身受,但是对于同样出现在诗中的简单真理往往视如不见:“我和公众都知道/学童们熟记的那个道理,/那些为邪恶所害的人/必会以恶相报”。B25在此意义上,评论者无法仅凭历史、文化、社会、政治、阶级、性别、族裔等非个人元素就判定一首诗的意义及其社会政治效用。
卡勒的抒情诗理论综合考量诗歌的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和社会效用。他认为诗歌的意义至少是由文本、世界和读者共同决定的。虽然卡勒在书中并未明确表述诗人对诗歌意义之产生起到何种作用,但是从卡勒的论述中不难看出,瑞典式自助餐是不会自动摆到桌上供食客自取的;如果不是诗人首先创作出形式令人难忘的作品,提供思想的盛宴,便不可能发生读者与文本的相遇,意义也就无从生发了。
正如伦特里基亚(Frank Lentricchia)在《“新批评”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一书的前言里所说的,如果说“新批评”已死的话,它是“以一位威严而让人有压迫感的父亲形象死去的”。B26“新批评”之后出现的批评理论虽然面目各不相同,但仍然带有“新批评”的诸多印迹或者——用伦特里基亚的话来说——“疤痕”。B27关于“新批评”的历史功过,早在40多年前便已有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做了较为公正的论断。当前,西方批评理论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是继续沿着泛文化研究的路子走下去,还是重新踏上“新批评”的老路,抑或开辟一条不同于前两者的新路?显然,第三条路最不容易走,但值得付出努力。默里·克里格和卡勒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具有开拓性意义。前者在20世纪70年代所采取的兼收并蓄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新批评”的转化和对“新批评”的超越。卡勒的《抒情诗理论》再次聚焦“新批评”最能发挥优势的诗歌领域,但该书所指向的是一种超越当代批判理论而又不同于“新批评”的新的可能性。一方面,《抒情诗理论》扭转了当代批评理论只关注文学中的非个人因素而缺失审美维度的偏颇,论证了诗歌的独特形式有助于诗歌意义的传达。另一方面,该书把遭到“新批评”悬置的作者和读者重新纳入文学批评活动的图景之中,二者都参与了作品意义的产生。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镜与灯》中论述的批评四要素“宇宙”“作品”“艺术家”和“受众”B28在经历了自“新批评”以来的形形色色、各有侧重的西方批评理论之后,得到了较为均衡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联也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释。
“新批评”重视文学批评和读诗这类审美活动对个人经验的拓展,考虑当时战后文化有待复兴的社会现实,具有极为积极的意义。乔伊斯、艾略特等人的现代主义美学理论与“新批评”主张暗合。但是乔伊斯要求读者终其一生阅读、研究他的小说,将这种拓展个人审美地平线的活动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这就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扩大审美经验之后,个体应该积极投身到社会文化的建设中去。这情形颇类似佛教中小乘和大乘的区别。小乘重视个人的修养和成就,认为个人若自身难保,便无法拯救众生。大乘重视愿力,奋不顾身,以解救苦难大众为己任。更为可取的态度似应是先以小乘路径打基础,待自身力量强大之后,再入世走大乘路线。此外,这也暗合儒家修齐治平理念的次第以及孟子关于独善和兼善的判析。
① ④ ⑨ B11 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6、72、77-78、82页。
② John Crowe Ransom,The New Criticism, Norfolk, CT: New Directions, 1941, p.3.
③ I. A.Richard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24, p.248.
⑤ T. S. Eliot,The Sacred Woo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1, pp.52-53.
⑥ T. S. Eliot, To Criticize the Critic,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65, p.25.
⑦ ⑧ John Crowe Ransom, The Worlds Body,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8, pp.111, 332.
⑩ Cleanth Brooks,“The Heresy of Paraphrase,”in The Well-Wrought Urn: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ry, London: Dobson, 1949, p.180.
B12 Rene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9, p.157.
B13 B18 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44、127页。
B14 美国女诗人劳拉·赖丁(Laura Riding)曾在《逃亡者》上发表过诗作,并熟知《逃亡者》编者的诗歌批评套路。她1926年移居英国,与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合著《现代主义诗歌概览》(A Survey of Modernist Poetry, 1927)。燕卜荪在写作《含混的七种类型》时承认他受到了格雷夫斯与赖丁那种细致入微的解诗方法的极大启发。详见Grant Webster,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History of Postwar American Literary Opin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95-97, 310, n.7.
B15 Rene Wellek, “The New Criticism: Pro and Contra,”Critical Inquiry, vol.4, no.4 (Summer 1978),pp.611-24.
B16 杨周翰:《新批评派的启示》,《国外文学》1981年第1期。
B17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ed. Robert D. Denha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 pp.91-92.
B19 程巍:《编后记》,《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B20 B21 张龙海:《哈罗德·布鲁姆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
B22 朱刚:《从“批评理论学院”看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现状》,《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1年第2期。
B23 B24 Jonathan Culler,Theory of the Lyric, Cambridge: Harvard UP, 2015, pp.2, 142.
B25 奥登:《奥登诗选:1927—1947》,马鸣谦、蔡海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302页。
B26 B27 Frank Lentricchia,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xiii, xiii.
B28 M. H. Abrams,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6.
(責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