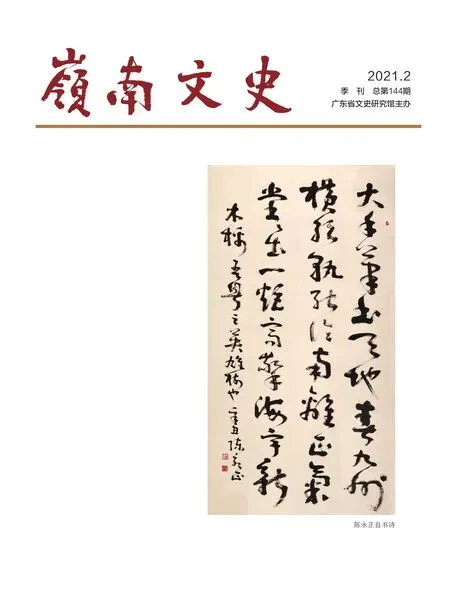从传统学宫到红色地标
——广州番禺学宫建筑沿革及功能考
2021-07-31杨琳
杨 琳
学宫又称学庙,有孔庙、文庙、圣庙、官学等多种说法,是历史上祭庙与官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以祭孔为主兼有高等学校功能的场所。番禺学宫是明清时期岭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庙建筑。当时,番禺学宫与广府学宫、南海学宫并称为广州三大学宫,番禺学宫是广州现存的唯一学宫。番禺学宫在当时既是祭孔圣地,又兼具育才的功能,抗清英雄陈子壮、清代状元庄有恭、著名学者陈澧等皆出于此。

农讲所旧址纪念馆
1926年5—9月,毛泽东在番禺学宫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学宫成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1953年,在旧址基础上建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并由周恩来亲自题名。广州农讲所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中华传统文化与革命精神在番禺学宫这座古老建筑完美融合,红色文化在这里薪火相传。
一、建筑沿革:从“前庙后学”到“左庙右学”
中国文庙按性质可分为家庙、国庙和学庙三大类。家庙即孔氏宗庙;国庙则为封建帝王祭祀孔子的专用场所;学庙则是以兴学为宗旨,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的庙宇相结合的场所,传播儒家思想,培养学子。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文庙都属于第三种性质。以孔子为主要创始人的儒家学派能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长期发挥着“以文治拱卫天下”的作用,与遍布全国各地的孔庙密不可分。“庙学合一”是学庙的主要特征。通常“庙”指祭祀孔子的建筑大成殿及附属建筑如泮池、大成门、崇圣祠等,着重于祭祀、仪式上的功能;“学”即讲学的场所,侧重于培育人才,一般指明伦堂以及有藏书功能的尊经阁、魁星阁等。
公元前479年,孔子卒于鲁,享年73岁。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居的三间立为庙,是最早祭拜孔子的庙宇。两汉以后,孔子的地位与日俱增。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亲临曲阜,以“太牢”祭祀孔子,开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公元72年,汉明帝东巡回朝时,“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 命皇太子、诸王说经。”此举首开孔庙讲学之先河。自此,孔庙又增学校的职能。公元153年,汉桓帝下诏修建孔庙,设守庙官,立碑刻记,这是国家设立孔庙的开端。公元630年,唐太宗下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以尊崇孔子,促进教化。“庙学合一”成为定制,世代沿袭。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为了适应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儒家思想作为教化民众和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明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朱元璋谕中书省:“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1]
明洪武三年(1370),新上任的番禺知县吴忠、训导李昕在广州东城外建造学宫。洪武十三年,驻守广州的永嘉侯朱亮祖下令扩建广州城,把宋代中城、东城、西城三城合一,辟东北越秀山麓扩建城墙800余丈,番禺学宫被囊括入广州城内。从同治《番禺县志》卷十六《建置略三》记载“(洪武)二十五年,知县高鸾、教谕张敬增修之,辟‘射圃’[2]于学右,建‘先贤祠’于戟门左”推测,初建的番禺学宫建筑格局应该是有庙有学。
由于学宫本身是木构建筑,易受风雨和蛀虫摧蚀,同时出于完善规制的需要,番禺学宫在明代进行过大小修整十多次,特别是万历年间曾五次增修。至明朝末年,番禺学宫的规模“自文庙棂星门、戟门、启圣祠、明伦堂及两庑而止,而犹阁有尊经祠、有文昌、有先贤楼、有聚英亭、有敬一、有射圃、有会膳、有号舍数十间。”[3]已经建设得十分壮观宏伟。
明末清初,广州连年兵乱,番禺学宫遭毁坏。清朝统治者在接受了儒家文化后,清顺治十四年(1657)开始重修。清朝前期基本是在明代所修文庙的结构基础上进行修葺,或修、或补、或添,没有大变。
乾隆十二年至二十二年(1747—1757),番禺学宫进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整修,耗资万金,历时十年,经数任知县。此次重修拆去明代大成殿,重新营建,将原本在东北隅的崇圣祠改建在大成殿与名伦堂之间;将名宦祠和乡贤祠分布其左右,使建筑更加规整;殿宇堂庑及内外围墙都改用砖石;在明伦堂后面创建尊经阁。此时,代表学宫建筑“学”的组成部分明伦堂,位处“庙”的组成部分大成殿之后,说明直到此时,番禺学宫的庙学建制仍然是“前庙后学”。
清道光十五年(1835),番禺知县张锡蕃主持重修学宫。此次重修对孔庙的布局进行重大改动,在大成殿的东侧创建明伦堂,明伦堂后面建光霁堂。至此,番禺学宫布局改为明清地方庙学的正规布局——左庙右学。经过重修后的番禺学宫格局分为左中右三路建筑。中路建筑包括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东庑、西庑、崇圣祠、尊经阁等,右路建筑包括明伦堂、光霁堂、名宦祠等,左路建筑包括节孝祠、忠义孝弟祠、乡贤祠等。同治三年(1864)左路建筑增建射圃。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因废科举、兴学校的需要,在番禺学宫北部及西北部设立了第一间番禺中学堂——八桂中学。为配合学校的建设,拆除尊经阁、乡贤祠和名宦祠,改建课室和办公室,又将射圃改建学生宿舍和操场,左路建筑大部分和右路建筑的名宦祠以及中路建筑的尊经阁遭到破坏。此后,再也未能重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番禺著名士绅丁仁长的倡议下,番禺学宫进行史籍记载的清代最后一次重修,主要针对文庙区,“若戟门,若碑亭,若更衣之室,倾败之形皆具。事无偏废,而施工有叙……经始于光绪丁末二月,落成于其年十月。”[4]同时由于当时孔庙与皇宫等级相同,在重修时“覆屋之瓦,悉数以黄而威神”,[5]即把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等瓦顶全部改成黄琉璃瓦。
二、庙学合一:兼具崇孔圣地与育才之所功能
车腾芳在《重修番禺学宫碑记》中明确指出:学宫的价值核心是“以崇先圣、以育人材、以昭化治”。[6]在庙学时代,其校园是由列为祀典活动的祭孔庙宇(大成殿)与官学教化之所(明伦堂)合二为一,目的是利用儒学来强调亲亲之仁及君臣父子间等级差别以建立起社会秩序,并通过“释奠礼”这种常行于学校中的“礼”来规范人们们的行为。因而孔庙是学宫的信仰中心,学宫是孔庙的存在依据。
1.番禺学宫的祭祀程序
文庙的祭祀功能包括祭祀孔子的建筑大成殿及附属建筑如泮池、棂星门、大成门、崇圣祠、东西两庑等。整座建筑群遵循突出中心,设一中轴线,两旁协调相配的原则。大成殿是整个主轴线上最重要的建筑,也是文庙建筑的中心。殿内供孔子、四配、十二哲塑像或木主,孔子端坐正中,四配、十二哲两两相对。番禺学宫亦遵从孔庙建筑的主体格调,同时运用砖雕、石雕、陶塑、灰塑等建筑艺术突出岭南地方特色。
文庙最重要的作用是祭祀孔子,每年2月和8月的上丁日是祭孔日。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典礼,称为“释奠礼”。文庙的祭祀有严格的程序,整个过程由迎神、奠帛、初献、亚献、终献、赐福胙、撤馔和送神共八部分组成。参祭人员的称呼由承祭官、陪祀官、分献官、赞引官、读祝生、乐舞生等组成。
根据清同治《番禺县志》记载,番禺学宫的祭祀程序大致有16道。[7]
祭奠先师孔子、四配时,是由承祭官担任献礼;而十二哲、两庑则是由分献官献礼。祭祀程序、等级也有严格的制度。如官员释奠先师,只能从大成殿的东台阶上,由左门进入大殿祭拜。但如果在国庙由皇帝亲自释奠先师,则是从大成门中门,沿中轴路直行,由中门进入大成殿祭拜。
2.番禺学宫的科举情况
文庙建筑的另一组成部分“学”,即讲学明伦的场所,侧重培育人才的作用,一般指明伦堂,以及有藏书功能的尊经阁、魁星阁等。明伦堂有面阔三间、五间、七间不等,主要依据古代行政级别高低来划分。县学的明伦堂为三间,如番禺学宫明伦堂。
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作为广州官方教育重要场所的番禺学宫,是学子入仕的晋升之阶。清代岭南一些名儒如陈衍虞、[8]莫元伯[9]等都在番禺学宫担任过学官,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番禺学宫的入学条件有严格的门槛:只有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三道考试取得生员资格才可入读学宫。番禺学宫的生员属县学生员。各县学程序一样,分大、中、小学三种规模取进生员。番禺学宫为大学,取生员40名。新生入学须绕泮池一圈,即“游泮”,之后到大成殿祭孔,行三跪九叩礼,最后到明伦堂向老师行一跪四叩礼。
学宫生员有文武之分,文武生员课业不同。西路建筑的射圃是武生员习武之所。除骑射外,教以五经七书、百将传及孝经、四书等。文生员课程有《御纂经解》《性理》《诗经》《古文诗》《十三经》《二十四史》《三通》等。生员有月考和季考,除考四书文外,兼试策论。每月还集诸生于明伦堂,诵政府颁布的卧碑文及训饬士子文,[10]谓之月课。生员除丁忧、患病、游学等事故外,不上课三次的给予警告,终年无故不上的即开除秀才资格。
番禺学宫生员走上仕途有两种途经:一种是参加乡、会试中举人、进士,这是主要出路;另一种是通过贡举成贡生入读国子监,肄业再酌情授官。
据统计,[11]番禺学宫生员中举人的有1400多人,被授予县官、学宫教官等职(含进士入仕者)的有900多人,出仕率60%左右。如果举人参加会试几次不中,则可通过拣选、大挑、截取等途径入仕,人数有600多人,入仕率40%左右。
乡试第二年,各地举人到京师应进士之试,称会试、殿试。会试是集中会考之意,中式者为贡士。取得贡士资格后,方能参加殿试。明清科举殿试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起初,三甲头名亦称传胪,后仅限于二甲头名),中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明代番禺学宫约有94人中进士,清代番禺学宫约有115人中进士。
清代番禺学宫中进士人数多于明代,而且清进士中二甲居多,明进士则主要集中在三甲,说明清番禺学宫的规模、教学质量都要高于明。此外,番禺学宫的进士人数主要集中在清道光、光绪年间,说明此段时间是番禺学宫的全盛时期。
明清两代,番禺学宫出过一名状元,[12]一名榜眼,[13]二名探花,[14]而当时整个广东只有6名状元,6名榜眼,7名探花,可见当时番禺学宫在广东影响力很大。
清代后期,以礼乐等为核心的教学内容缺少实用价值,逐渐消亡。“读书做官”的道路日益凝固化,官本位主义也日益严重化。尤其八股取士,造成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学宫的教学只剩考课,实际上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下令“停科举经广学校”,番禺学宫的教育职能,也随之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学堂——八桂中学。为此,番禺学宫拆除了尊经阁、乡贤祠和名宦祠,改建成教室和办公室,又将射圃改建为学生宿舍和操场。但春秋祭孔活动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
辛亥革命以后,广东军阀政权更迭,战火纷飞,学宫遭到破坏。至20世纪初,滇桂联军盘踞广州期间,巍巍殿宇沦为驻兵场所。只要营房需要,即可拆祠毁殿,甚至劈神牌为柴火,无所顾忌。
三、薪火相传:续庚红色基因 传承革命精神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番禺学宫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所长。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在此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学宫也被烙下光辉的红色印记。粤桂混战期间,番禺学宫又沦为伤兵的后方医院。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下令恢复对孔子的祭祀。随着陈济棠的下台,祭孔活动也随之冷却。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番禺学宫遗址被开辟为纪念馆,学宫成为纪念毛泽东在此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红色教育基地。进入新时代,历经岁月打磨的番禺学宫以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厚重的人文历史吸引八方来宾,其独具特色的红瓦黄檐,高脊巍峨的宫墙建筑更是成为年轻人的拍照打卡点。光阴流转,岁月变迁,虽然功能随着百年学宫到红色地标而有所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革命精神在此弘扬,红色血脉在这里延续。
1.革命摇篮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为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15]使之成为“农民运动之推动机”,[16]在彭湃等共产党员积极倡议和推动下,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39次会议,决定正式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历时两年两个月中,先后在广州共举办过六届农讲所。
1926年5—9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址番禺学宫,聘请毛泽东担任所长,并大幅扩大招生规模,在全国20个省区招收327名学员。毛泽东同志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在这里首次讲授。为总结和推广农民运动经验,毛泽东把当时搜集到的国内外有关农运的重要文献,农讲所教员对农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以及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的调查材料等,汇集起来加以认真审订和修改,最后编成《农民问题丛刊》。这套丛刊的出版,不仅改变了以前研究农民问题资料匮乏的状况,为农讲所学员以及全国各地的农运干部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学习材料,而且在宣传革命思想、提供政策指导、介绍农运经验和传播知识信息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历届农讲所中,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规模最大,招生范围最广,学习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学员在此学习革命理论,接受军事训练,参加社会实践,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播撒革命火种,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办、主持农讲所期间的理论思考和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探索,创立了丰富的革命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取得了一个个重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实践的结果,在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2.红色地标
1953年,为纪念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革命圣地,政府对番禺学宫进行大规模整修,将学宫开辟为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以下简称农讲所纪念馆)。整修之后,番禺学宫目前右路建筑尚存头门、明伦堂、光霁堂和石板路,左路仅剩头门,而中路建筑尚有棂星门、泮池拱桥、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和东西庑廊等。在陈列方面,根据学员回忆,按当年农讲所的布置原样复原。馆内辅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历史陈列”展览,向广大观众展示第一至六届农讲所的历史。1961年,国务院颁布广州农讲所纪念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该馆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把红色场馆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为向广大群众培养爱国情感、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农讲所纪念馆承载着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使命。几年来,农讲所纪念馆深挖自身文化价值和特色,根据学宫文化、革命传统、红色信仰等关键词,举办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红色展览,推出一批品牌红色教育活动,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它丰富的红色资源和文化内涵,吸引着八方来客。
进入新时代,这座历经风雨的传统建筑,经过革命精神的洗礼,赋于崭新的历史任务,焕发着蓬勃向上的新生机,续写新的辉煌。
注释:
[1] 《明史·选举一》。
[2] 明代学宫多设射圃,供生员联系弓矢之用。
[3] [清]李福泰修,史澄、何若瑶纂:同治《番禺县志》,卷三十一《金石略四》。清同治十年(1871)广州光霁堂刻本。
[4][5] [清]梁鼎芬修,丁仁长、吴道镕等纂:《番禺县续志》,卷十《学校志一》,民国20年(1931)年重印本。
[6] [清]车腾芳:《重修番禺学宫碑记》。梁鼎芬修,丁仁长、吴道镕等纂:《番禺县续志》卷三十六《金石志四》。
[7] 根据清同治《番禺县志》,卷十六《建置畧三》整理。
[8] 陈衍虞(1603—1688),字伯宗,号园公,广东海阳(今潮安)人。1655年出任番禺学宫教谕(即“正式教师”,宋代开始设置,负责教育生员)。在任学官八年期间,向他求学的士子众多,并著有《禺山草》。该诗文集不仅记录他在学官任上的心情意志、学问交游,还保留了清初广州风情风貌的宝贵资料。
[9] 莫元伯(1753—1815),字台可,号善斋,广东高要人。清嘉庆年间,担任番禺学宫学官八年,热心教学,推行各项教化措施。慕名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官舍根本容纳不下,于是很多学生就在学宫旁租赁房屋,比邻而居。1815年,病逝于家乡,谥号“孝文先生”。
[10] 清顺治九年(1652),礼部奉旨规定八条规则,刻立于学宫,令全国士子诵习奉行,谓之“卧碑”。康熙三十九年(1700)又颁布“圣谕”十六条,四十一年颁“训饬士子文”。雍正年间,更把康熙时十六条“圣谕”大为发展,演化为“圣谕广训”,并且颁布了“御制朋党论”。乾隆五年(1740),又有《钦颁训饬士子文》。这些,都是生员所必须尊奉,也是经常进行考课的内容。
[11] 参见梁惠彤:《试论番禺学宫的历史沿革及其作用》,《广州农讲所纪念馆论丛》第一辑。
[12] 即清乾隆四年(1739)己未科状元庄有恭(1713—1767),字容可,号滋圃,广东番禺人。以番禺学宫拔贡生的身份考授宗人府教习。清乾隆四年成为己未科状元。累官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江南河道总督、湖北巡抚、浙江巡抚、刑部尚书、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等职。他任封疆大吏十多年,以救灾抚恤和兴修水利著称于世。乾隆十八年曾撰写《重修番禺县学碑记》。
[13] 清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一甲榜眼许其光(1827—?),字懋昭,号涑文,广东番禺人。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北乡试副考官、福建道监察御史,顺天乡试同考官。因编纂咸丰皇帝《圣训实录》有功,加四品。编纂《皇清奏议》,加三品顶戴。后任广西思恩府知府、直隶候补道,深得李鸿章器重。因病请假回乡医治,适士绅筹设“册金局”为新进邑学各生印卷之资,许其光为其奔走出力,举为学海堂学长。假满旋津,病卒。
[14]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探花涂瑞和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己未科探花陈子壮。涂瑞(1447—1493),字邦祥,广东番禺人。官至翰林院编修。涂瑞为文汪洋宏放,性格豪宕不羁,顷刻数千言;书法遒丽,为一时之冠。陈子壮(1595—1647),字集生,号秋诗,广东南海人。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等职。永历元年(1647),广州被清军攻陷,陈子壮临危不惧,坚持抗击清军,殉国于广州东郊。后被追奉太师上国柱,特进光绿大夫,中极殿大学士和吏、兵二部尚书忠烈侯。有《礼部存稿》存世。后人立有宗祠纪念。
[15] 《农民讲习所之简章》,《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24日。
[16] 罗绮园:《本部一年来之报告概要》,《中国农民》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