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都市生活的文学书写
——读邓一光的两篇新作
2021-07-28唐小林
文/唐小林

深圳是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作为文学意义上的深圳,多年来,在许多读者的记忆中,或许满脑子都是“打工文学”,其呈现出的文学形态,总是停留在初期的深圳,或者说是许多生活在深圳边沿地带,乃至打工人眼里的深圳。而那些白领阶层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居住在繁华大都市里,那些形形色色的深圳人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反而被许多深圳作家所忽略掉了。在当代文坛,邓一光以其大量书写深圳都市生活的小说赢得文坛的赞誉,从而让读者不但看到了一个经济发达的深圳,更让人看到了深圳这个别具魅力,经济发达的城市的日新月异和世态人心。仅仅从他许多的小说名字,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其显著的“深圳特色”。比如《深圳蓝》《深圳河里没有鱼》《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深圳在北纬22°27′~22°52′》《如何走进欢乐谷》《香蜜湖漏了》等等。
深圳是一个典型的新移民城市,和众多的深圳市民一样,邓一光也是从外地来到深圳,并且爱上深圳的作家。邓一光说:“迁居生活都一样,生活环境变了,会有全新的体验。最初几年生存压力比较大,得把家人安顿好,花了很长时间,这两年慢慢从容了。我对我的移居地一直有着强烈的好奇,可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经验和情结的人,谈不上对一个地方有血缘和谱系上的情感,也许现实生活会逐渐加深我与这座城市的岁月联系,但我更依赖写作帮助我建立某种个人化的地域情感。”来深多年,我们欣喜地看到,邓一光对深圳的书写总是持续不断,佳作迭出。诚如邓一光所说:“它们持续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陪伴我度过了十年,让我觉得生活始终在变化着,有无穷无尽的迷,有意义。”或许,这正是激发邓一光深圳书写的巨大动力。十多年与深圳的朝夕相处,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邓一光的写作轨迹和雄心勃勃的写作理想,这就是:书写个人的“城市”,建立“我的城市史”。
邓一光的深圳书写,受到了国内文坛的高度关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邓一光侃侃而谈,袒露出了他一系列深圳小说的创作动因:“基本来自个人生活。比如《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是我刚到深圳租房时的感受,想租而没租成的房子,变成了故事里的场景。《深圳河里没有鱼》,写我一个没完成的计划。《深圳在北纬22°27′~22°52′》,写我一个梦。有一段时间,我睡眠严重不好,老是凌晨出门看星星,看着看着就写了《要橘子还是梅林》。有一次,我和儿子在梅林教堂过马路,马路中间躺着一条被车辗过的流浪狗,我儿子特别受打击,过不去,有点崩溃,那一年我做了两件事,为被辗过和没辗过的流浪狗们写了《如何走进欢乐谷》,做了一个流浪猫狗收容中心的提案。我去一所学校,见到一群合唱团孩子,以后写了《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坐着坐着天就黑了》是写给我的工作室的,我在B 栋3A 借住了两年,离开时,突然挺感谢它,想给它写篇东西,就写了。《香蜜湖漏了》是和一些作家在香蜜湖吃饭,他们的移民经历比我早,饭局上交流时全是曾经的历史,我心里一动,说要写这顿饭局,第二天就写了。不过,这些小说的内容,和真实发生的事情基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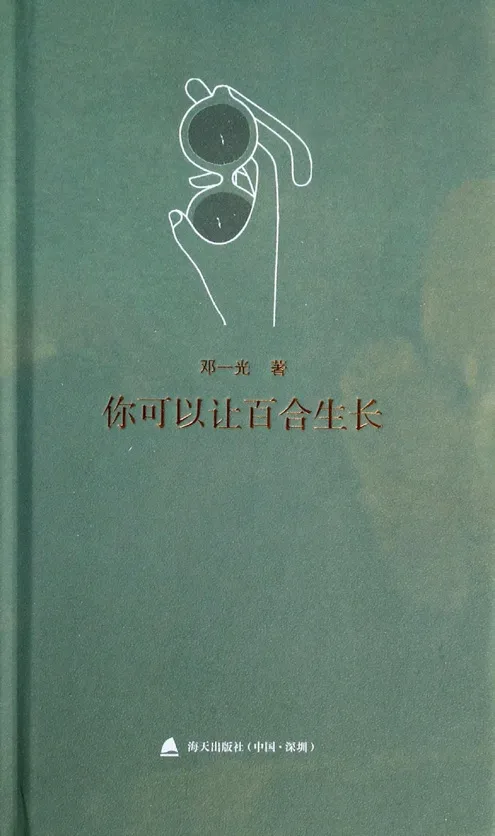
知人论世,了解邓一光与他相处的这个繁华大都市的关系,及其创作的心路历程,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新作《入侵物种》和《带你们去看灯光秀》,尤其具有锁钥般的意义。只有真正掌握作家的创作目的,才能深刻地理解其作品中所隐含的文学意义。对于一个深知小说创作三昧的作家来说,所谓故事,仅仅只是一个载体,因为作家写作的目的,并非仅仅只是要为我们讲述一个故事,让我们知道一点未曾了解的新鲜事,增加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为了通过小说,并以文学的方式深刻揭示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懂得人与人之间,以及与我们这个世界如何和谐相处。不然,在当今这样一个娱乐至死,有那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劳神费力,花时间来读小说呢?就像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所说:“好小说流传着,并放射出独特的光芒,它唤醒我们对理想境界的渴望。”

2020 年12 月23 日,邓一光参加第七届“深圳十大佳著”(虚构与诗歌类)颁奖盛典。中短篇小说集《坐着坐着天就黑了》获评第七届深圳十大佳著。
《入侵物种》,可说是邓一光对当下深圳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索。小说主人公易谷丁“是一名二级资质人力资源管理师,早先供职于IBM 大中华区,五年前转到深圳一家彩色柔性显示技术公司,公司主要由研发人员构成,占据了公司员工百分之六十七,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多数毕业于斯坦福、康奈尔和港科,因此,和制造业员工招聘、绩效考核、薪酬福利管理以及劳动关系协调稍有不同,易谷丁的服务对象不是高级镗工、自卸货车司机、模具工程师和玉石检验员。”根据小说开篇这样一段描写,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有别于我们习以为常的庸常的深圳故事,而是一个有关业界精英的深圳,乃至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易谷丁工作在深圳,其妻子回到武汉,却不幸遭遇疫情,意外死亡,一个原本完美的家庭,突然变得支离破碎。接下来的心理干预和一系列的生活和工作问题,却是易谷丁每天不得不时刻面对的严峻问题。“易谷丁对自己的心理医生产生了某种微妙的移情,决定接受他的建议。长假最后一周,易谷丁选择了去‘大地母亲协会’做义工。那是一个与流浪猫援助有关的民间公益组织。和SPCA 性质的失援宠物之友、预防虐待动物协会之类的组织不同,它的宗旨是追求对流浪猫的最终解决方案,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野外救助。”
在作家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水到渠成地提出了流浪猫解决方案这样的社会问题。作家从深圳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人们的生存,及其心理问题,进而扩展到对于动物的关爱,乃至怎样才能妥善解决好这样极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以及其他动物与我们人类的关系问题。小说写道:“比起幽灵猫,他更愿意听陶大夫讲那只信天翁的故事,主人公无端地射杀了一只信天翁,以至水手们一个个死在他面前,每个死者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盯着主人公。心理学大夫都是潜在的作家,陶大夫肯定读过柯尔律治的《老水手行》,他应该和那位深陷忏悔的老水手一样,把那个可怕的故事讲出来。‘我不认为猫的问题有多难。’陶大夫说,‘如果这都应付不过去,还有比它们更聪明的动物,要是遇到章鱼、大象、猩猩、海豚和鹦鹉,我们怎么办?’”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并非是简单和孤立的,小说的深刻之处,或者说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作家看似在讲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深圳故事,但作品的容量却是非常巨大的,涉及到的问题却是多方面的。
作家在讲述爱心,关爱动物的同时,绵里藏针地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进行了无情的针砭。作家告诫我们,有的人在以爱心的名义,沽名钓誉,他们所奉献出的爱心,完全是与社会公益南辕北辙:
有位获得了“爱心大使”荣誉称号的年轻明星——真正的明星,拍化妆品广告或者演小品那种——那天带着一支摄影队,身后跟着一众仰着迷蒙脸蛋的粉丝来到公园施善。年轻的“爱心大使”穿着朴素的衬衣,施了淡妆,健康、友好、模样儿干净,完全符合他拥有的荣誉。易谷丁一眼认出了他,同时认出他的助手从福特E350 行政房车里搬下的两箱宠物火腿肠。易谷丁在资料清单中见到过,是昂贵的纯种冠毛犬或者热带草原猫的奖励级零食,据说有补钙和增智作用,让宠物长出金钢的身子骨和最强大脑成员的智力。
助手们布置好反光板,将流浪猫中的雏子,那些被人遗弃不久,还不完全懂得户外世道艰难的家猫引诱出藏身地,摄影师开始拍摄。在粉丝们景仰的目光下,“爱心大使”正准备在镜头前为小可怜们赠送爱心能量棒,公园安保赶来阻止了他。“爱心大使”的助手坚持这是一场爱心推广行动,拍摄……投食必须按计划进行。公园安保不由分说,收缴了宠物香肠。这引发了一场骚乱,场面一度失控。受到打击的是粉丝,那些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的孩子和孩子他妈激动得浑身发抖,眼泪泼洒在高高举起的直播手机上。“爱心大使”什么都没有说,他假装微笑,脸上带着一丝想要拯救蓝色星球却遭到愚昧者围攻的深深委屈。
就此而言,《入侵物种》可说是一篇具有醒世意义和前瞻性的小说。在许多社会学家还没有来得及,或者说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时候,邓一光已经对深圳的流浪猫等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和表达出来。它就像是为深圳的城市管理者和社会学家提供的一份文学性的深圳都市管理问题报告。在小说的结尾,作家写道:“易谷丁在S 公园待到很晚。他在公园里一直走到月亮升起来。一群晚归的白头鹎吵闹着从他头上飞过,去了南山方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它们当中有谁会某处滩涂觅食,或者在某处丛林栖息时死于非命。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无所作为的入侵者,不知道入侵了谁的领地,又被谁入侵了,对任何系统都没有建树和破坏。他决定给陶大夫打电话。”就像小说中的心理医生陶大夫对易谷丁所说:“作为朋友而不是医生,我希望你知道,原来的世界不在了,你得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既是心理的,又是现实的。
《带你们去看灯光秀》,同样是有关深圳题材的现实力作。小说的描写,同样涉及到新冠疫情:“当人们被疫情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文小青和杭思嘉却像身处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在视频中持续讨论一件事情,在深圳买房。文小青和许森的女儿大宝在新加坡读书,疫情中,一家三口不断纠结大宝回国避难还是留在星岛抗疫,夫妇俩想离孩子近一点,近到只要孩子动了闯关的念头,登上万元票价的新加坡航空或者捷星航空,一过口岸,他们第一时间就能见到她,陪她14+7,陪她哭闹,‘黑死病’和‘上帝之手’都不能阻止这件事情。如此,文小青决定卖掉洛阳的房子,在深圳买房,建立一座接应女儿的桥头堡。作为文小青最好的闺蜜,在深圳生活了二十年的杭思嘉理所当然成了文小青的置业顾问。”小说由此徐徐拉开了序幕。而小说的故事,却在洛阳与深圳之间不断发生勾连和转换:

杭思嘉和倪秋鸿讨论了两年,在漫长的两年时间里,这几乎成了他们事业之外唯一的家庭议事内容。他们讨论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讨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他们精疲力竭了,最终决定“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回到洛阳去,找一份适合的工作,带老人逛逛国花园,去关林庙抽个签,下班后顺便去菜场买条活伊鲂,为老人做一道既营养丰富又易于消化的清蒸鲂鱼,岁月如年,送他们一个个归山。罗湖的一居室留给语焉,他们打拼了半辈子,她还要在这座城市里继续打拼,不能让她从零开始——如果她不嫁给某个科企二代或者公务二代,根本不可能在这座城市里安放下自己的床。
来到深圳——回到洛阳——今后或许还会回到深圳。在离别深圳的时候,再好好看一看深圳,而最好的去处,就是去看一场灯光秀:“那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灯光秀,用了150 多万套灯源、功率最大的民用激光、阵容最大的无人机队、最强大的设计师团队,它表现了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永不停歇的脚步。他带杭思嘉去看过一次。杭思嘉不想去,她睡眠不够,想睡觉。倪秋鸿平时一直依妻子,那次没有依。他们被灯光秀表达出的和谐之境和创新之意感动得热泪盈眶,完全说不出话来。他们一直深深地热爱着这座接纳和消化掉自己青春的山海之城,舍不得离开它,他们会永远怀念它。”
在我看来,《带你们去看灯光秀》,仿佛就像一篇寓言小说,深圳的灯光秀是那么的美轮美奂,却又是那样虚幻飘渺,即便是不能拥有它,但却可以将它长留在自己的心中。深圳是一座魅力无穷的国际大都市,它的神奇,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深圳。有的人在这里从此扎下根来,成为新深圳人,有的人却像天空中飞翔的鸟儿,短暂地在深圳工作和生活之后,最终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尽管他们没有在天空中留下鸟儿飞过的痕迹,但在许多人的生命中,他们确实来过深圳,与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发生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