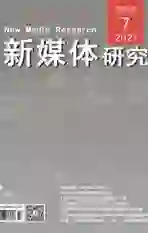风格·抵抗·收编——伯明翰视角下“饭圈”文化时代性解读
2021-07-27裴敏
裴敏
关键词 伯明翰学派;“饭圈”文化;主流话语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7-0078-03
作为网络青年亚文化代表之一,“饭圈”文化具有重要的传播价值,一方面吸引着主流话语的嵌入,另一方面其充满反叛性的“风格”也引起了社会关注。为了对“饭圈”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发挥其在话语传播层面的价值,学界近年来不乏针对其的研究。本文沿用对亚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伯明翰学派中关于亚文化“风格”“抵抗-收编”的逻辑,对当下的网络“饭圈”文化进行时代性解读,挖掘经典理论视角下,“饭圈”这一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时代特色。
1 “风格”建构:“饭圈”特征解读
伯明翰学派作为对亚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一派,其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包括“风格”“抵抗”和“收编”。该学派认为“风格”是青年亚文化的图腾和第二皮肤,也是其最醒目的标识[1]。“饭圈”受众借助独特的文化景观、狂欢仪式等方式形成自己的“风格”,搭建专属的“文化空间”,在此基础上塑造自我并强化自我认同,形成一套完整的“饭圈”价值体系。
1.1 异化的文化景观
在互联网上,“饭圈”文化总以一种充满异化的反叛特征呈现出来,受众借助“唯粉”“团粉”等符号体系,建造起严密的准入机制,与其他亚文化圈子区隔开[2],成员们通过符号互动强化群体联系,搭建起一个拥有不断巩固的群体认同和群体情感的“饭圈”。“饭圈”由此形成自身的文本和话语系统,各种“饭圈”用语、“控评”等“饭圈”行为成为这一圈子的标签,构架出一个与大众化主流话语相背离的文化体系[3]。另外,“饭圈”对于自身内部阶层的严密划分也使其呈现出与其他亚文化相异的特色。不同于其他圈子尽管对主流话语充满反叛性,对内却有相当高的凝聚力和同一性;“饭圈”文化内部存在严格的阶层划分。人气高的“爱豆”被称为“顶流”,反之则被叫做“糊豆”;对于“爱豆”的粉丝,也有着“团粉”“唯粉”“CP粉”的划分,且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鄙视的关系。即使同处于“饭圈”文化之中,不同“爱豆”的粉丝圈及同一“爱豆”的不同粉丝之间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使“饭圈”文化“风格”以一种特殊的、异化于其他文化体系、充满尖锐性的文化景观呈现出来[4]。
1.2 “他者”镜像的塑造
在“饭圈”内部,通过符号表达、话语互动等方式构建了专属“我群”的文化景观;在外部,其他亚文化及权威媒体对这一圈子的认知和反映也构成了一面“他者”的镜像。库利“镜中我”理论认为,“镜中我”也是“社会我”,感知社会“他者”对自身的形象认知,也是在进行自我塑造的过程。“饭圈”文化正是在这种“镜像”的对照下,其主体不断地经历解构与再造,不断“再标签化”。
在主流媒体话语中,“饭圈”媒介镜像下的“他者”群像往往呈现“狂热、非理性”特征,这与大众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存在议题选择偏向密不可分[5]。主流媒体对“饭圈”的报道多带有批判态度,具有二元对抗性色彩,因此在“饭圈”以外的人群眼中,“饭圈”往往和低龄化、非理性等贬义标签相连[6]。在这种外部“他者”凝视下,“饭圈”文化又无法与现实逻辑、主流话语完全分立,于是他们试图主动与大众文化展开互动,在强调主流文化权威地位的同时,以偶像之名展开公益等良性活动,试图改变主流媒体“镜像”下自身的负面形象[7]。这既是他们对抗社会对其污名化的一种措施,也在不断形成新的圈层仪式,创造出充满矛盾性的文化“风格”。
1.3 狂欢的媒介仪式
亚文化由“趣缘”连接,这种“趣缘”关系,在互联网时代有了得以聚集的虚拟媒介空间,支撑受众有条件进行狂欢式的仪式活动[8]。在仪式活动中,通过“趣缘”相联系的“饭圈”成员在虚拟的共同空间中以同一行为相连接,在大规模、狂欢式的互动活动中,不断强化群体关系,产生情感共鸣,树立起牢固的群体认同[9]。这些仪式性活动也如地标性建筑,扮演着“饭圈”的“风格”缩影。
首先,媒介狂欢仪式在亚文化形成之初,就对其起着重要的“风格”构成作用。“饭圈”文化作为由追星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发展而来的亚文化,其成员在网络空间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控评”“打投”等具有仪式性的活动,为其奠定了“狂热性”“组织性”等最初“风格”[10]。
其次,随着文化的发展交融,其“风格”也在不断地流变,狂欢媒介仪式更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当下的“饭圈”文化是高度的消费文化,成员们通过“集资”、重复购买专辑等消费行为,进行了狂欢式的情感宣泄,这种消费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权利贩卖,消费者获得的是情感上的满足、与“爱豆”虚拟的联系以及这种行为使其在圈子内获得的认同感和圈层地位。这种“消费”仪式,既使群体认同感被大大激发,也使消费社会的逻辑逐渐嵌入“饭圈”文化,成为其显著的“风格”标签。
2 “抵抗性”弱化:“饭圈”娱乐符号解码
在伯明翰学派观念中,亚文化对主文化和霸权的抵抗是一个核心论点,抵抗性与阶级冲突相联系,展现了亚文化“风格”背后的现实矛盾。但随着时代演变,逐渐出现后亚文化等反对此观点的理论,后亚文化认为亚文化的形成更多来自受众的娱乐,而弱化了階层问题和抵抗关系。不可否认,在互联网去中心化加持下,具有反叛“风格”的青年亚文化天生带有消解权威的抵抗性,但在娱乐至死的时代,亚文化从伯明翰学派笔下的“强抵抗性”逐渐走向一种“弱抵抗性”。
“饭圈”文化正是一种“弱抵抗性”的亚文化。尽管其“风格”上呈现出异化特征,但实际上这是“饭圈”成员通过情绪表达和符号互动进行自我塑造,而非直接对主流话语发起“正面冲突”。反抗性是这一亚文化的侧面;在高速发展的社会和“赛博空间”的挤压下产生消极抵抗情绪的年轻人借助追星进行情感寄托和焦虑宣泄,通过狂欢娱乐活动进行自我价值塑造和认同才是“饭圈”文化的真正内涵[11]。这种避免“正面冲突”的泛娱乐性活动,虽然展现了成员们拒绝被主流定义,蔑视权威的解构心态,但实际上也促使受众沉溺于娱乐化的情感消费,而非伯明翰学派所说的对阶级矛盾等社会问题发起正面抵抗。“饭圈”成员在无形中走向自我妥协,甚至陷入“犬儒主义”,“饭圈”文化本身的抵抗性在这一连串符号消费中被逐渐弱化、消解。
3 互动中“收编”:“饭圈”与主流话语互嵌
在伯明翰学派看来,亚文化的发展逃不了被权威“收编”的命运,亚文化对“收编”是排斥的,但随着研究深入,伯明翰学派发现亚文化与主流“收编”的关系是暧昧复杂的,亚文化对被“收编”表现出一种抵抗又妥协的态度。将这一观点落实到互联网时代的“饭圈”文化,尽管“饭圈”以一种异化的文化“风格”表现出来,但其逐渐弱化的抵抗性也证实了其在面对“收编”时开始主动与主流话语互动,在互动中实现主亚文化的相互转化和嵌入。
3.1 依靠符号的借鉴打破固有圈层
由于充满反叛性的“风格”在大众媒体的报道下导致了负面形象,对“饭圈”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名化[12],为了突破这种困境,“饭圈”成员积极通过对主流及其他亚文化符号的借鉴与重塑,打破原本封闭的圈层界限,与大众文化进行互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话语的相互嵌入[13],推使“饭圈”文化在内容上不断扩容的同时走向大众视野,日益“大众化”。
不同于二次元等其他亚文化秉持“圈地自萌”的原则,依靠“次元壁”等符号强硬地与大众文化划清界限;“饭圈”文化在各类青年亚文化中显得相当跳跃,其跳跃性主要来自于对其他圈层话语的不断借鉴。譬如“饭圈”成员在为自己的“爱豆”进行“控评”等仪式性活动时往往会自发迎合主流话语,带上诸如“正能量偶像” 等嵌入了主流价值观的标签,从而与权威话语展开一种互动,并通过这种方式,对“饭圈”文化在大众化媒介中的消极“镜像”进行一种重塑。同时,这种互动本身也使“饭圈”文化主动靠近主流文化,其抵抗性被无形消解,逐渐走向被收编的结局。
3.2 主动搭建主流话语亚文化资本
除了通过符号借鉴拉近与主流话语的距离,在面对权威嵌入时,“饭圈”也较其他亚文化表现得更积极。不同于主流话语在二次元等亚文化领域进行意识形态传播时频频受阻,不得不放低语态;在进入“饭圈”文化时,主流文化的权威地位却难以撼动,甚至其成员们主动为主流话语构建了强大的“亚文化资本”[14],使其在“饭圈”内享有相当高的权利与地位。
“亚文化资本”是萨拉·桑顿在《俱乐部文化:音乐、媒介和亚文化资本》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由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发展而来,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饭圈”文化内,成员们将央视新闻等官媒尊称为“央视爸爸”;以自己的“爱豆”能登上央视舞台为荣;对被官媒“点名批评”的明星也报着批判态度。“饭圈”受众对主流话语的迎合,使其不需要像在其他亚文化内被迫转变语态以积累影响力,成员自发为其提供了足够的“亚文化资本”,赋予其高度的权威地位和话语权,主流话语因此总是在“饭圈”中呈现出一种高姿态。这使得“饭圈”文化虽然有着“狂热性”“非理性”等反叛性标签,却是一种被权威所导向的文化,尽管其在“风格”上趋于异化,实则无形中主动迎合了主流对其的“收编”。尤其在各大官媒点名整改“饭圈”的当下,其文化表面确实充斥着各种扭曲的价值观倾向,但也在通过不断弱化自身的“抵抗性”,以顺应主流,突破合法性困境。
3.3 “饭圈”文本嵌入宏大叙事
“饭圈”文化与主流话语的互动还体现在其善于将自身文本嵌入宏大叙事中,把原本边缘小众化的亚文化属性与家国政治等事件相联系,从而改变外界对其的消极刻板印象[15]。主流媒体也开始积极地利用“饭圈”文本进行宏观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传播,二者在这种互动中,实现了对“饭圈”这一亚文化的收编。
为了突破自身合法性困境,“饭圈”成员们披上了“饭圈女孩”的标签,并试图借此身份在国际问题上与主流话语保持统一战线。从“帝吧出征”到香港暴乱事件,“饭圈女孩”们在外网上积极表达爱国主义情怀,他们将国家作为“爱豆”一样守护,形成了“粉丝民族主义”[16]。这种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形象,在参与宏观叙事的过程中逐渐被内嵌到“饭圈女孩”的符号意义中,对其进行了意义重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本“狂热”“非理性”等负面标签。主流话语在此过程中也关注到“饭圈”文化对权威价值观传播的作用,进而主动借“饭圈”文本,将国家比作“阿中哥哥”;推出了“江山娇”“红旗漫”等虚拟偶像来进行宏大话语的表达[17]。尽管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不可否定的是,“饭圈”文化已经开始与主流话语相互嵌入,而这种嵌入并非权威方的强势“收编”,而是双方在不断的互动中达成一种和谐[18]。
作为对亚文化研究影响最为深刻的学派,伯明翰学派的理论为“饭圈”文化的解读提供了参照模板。但在依照伯明翰逻辑对“饭圈”文化进行探讨时必须注意的是,“饭圈”尽管在弱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性”,但也以一种更加娱乐化的形态呈现出来,网络低龄化也使得这一问题被不断放大,而主流媒体在互动收编时不可被过度影响,导致政治娱乐化[19]。 应该以正面的态度肯定其价值,并对负面的层面进行适当整治,进行有选择有分类的吸纳与引导[20]。
参考文献
[1]胡疆锋,陆道夫.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2006(4):87-92.
[2]朱白薇.符号与变现:网络空间亚文化涌现的生成逻辑[J].学习与实践,2020(5):122-127.
[3]吕志文.构建与解构:“男性向”网络小说改编剧分析[J].艺海,2020(7):82-83.
[4]尤旖芸,何雨欣.冲突消解:新媒体语境下粉丝暴力行为的变迁[J].东南传播,2019(6):76-79.
[5]胡玉宁,徐川.青年圈群脉动的媒介感知与文化诠释:基于“饭圈”现象的叙事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0(11):70-79,93.
[6]秦阳,万丽唯,潘瑜.使用与满足视角下的网络语言低龄化现象探究[J].新闻知识,2019(23):9-24.
[7]徐娉婷,冯菊香.大学生时尚杂志电子刊消费的心理动因与行为特征[J].东南传播,2020(9):89-92.
[8]赵呈晨.共享式传播:青年同辈群体中网络语言流动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2-80.
[9]杨鑫,冯广圣.基于趣缘的隐形连接下文化的狂欢:基于“惊雷”“淡黄长裙”现象的考察[J].东南传播,2020(11):83-85.
[10]赵呈晨.共享式传播:青年同辈群体中网络语言流动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2-80.
[11]位云玲,冯广圣.算法新闻推荐的社会责任反思[J].新闻知识,2020(9):23-26.
[12]尤旖芸.新媒体语境下粉丝形象的污名化探析[J].東南传播,2019(12):116-119.
[13]赵呈晨.嵌入式传播:网络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与再生产[J].新闻大学,2020(8):16-30,126-127
[14]赵呈晨.文化协商:代际沟通视角下的网络语言传播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11):16-19,90-97.
[15]陈相雨,丁柏铨.自媒体时代网民诉求方式新变化研究[J].传媒观察,2018(9):5-12,2.
[16]殷文,张杰.水平集体主义与参与式文化:网络化时代青年个人价值观新变化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20-129.
[17]李越,吴斯,冯广圣.UGC视角下的网络社区内容分层管理个案研究:以站酷社区为例[J].东南传播,2019(7):121-123.
[18]孙梦婷,何晴,黄蓉.故宫文创的跨媒介传播策略[J].东南传播,2020(9):83-85.
[19]孟威.“饭圈”文化的成长与省思[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9):52-59,97.
[20]陈相雨,丁柏铨.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情感逻辑及其治理[J].中州学刊,2018(2):166-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