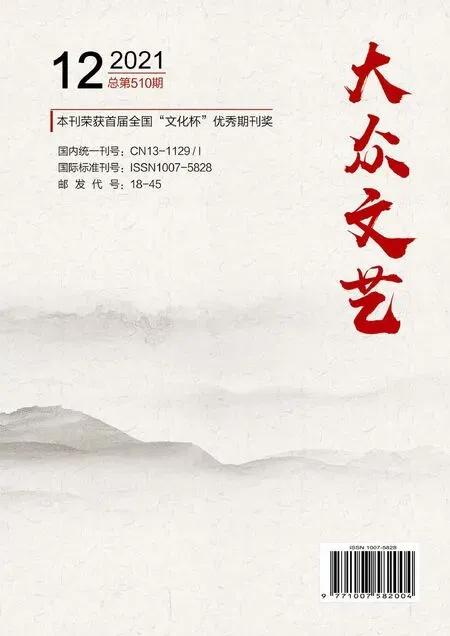贾樟柯“故乡三部曲”中的民俗文化生活呈现
2021-07-23伦欣
伦 欣
(山西省艺术研究院,山西太原 030001)
贾樟柯早期作品“故乡三部曲”,从导演所熟悉的故土取材,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内陆欠发达城镇的真实风貌。影像中的县城为角色塑造、情节开展提供活动平台,更通过整体的空间展示和人物行为记录了时代和思想的变化。本文从民俗学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路径出发,选取影片中具有代表性的民俗符号分析,思考变迁中的人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在民俗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构建个人生活,应对社会转型,进而让民众看到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流行音乐、影视作品:流行文化进入
贾樟柯电影中最明显的一个影像符号是利用流行音乐营造时代气氛,把广泛传唱于民间的音乐作为背景,串联成一幅时代图景,为电影的叙事做了很好的时间背景铺垫。《站台》中,崔明亮他们在电影院观看印度电影《流浪者》,影片中的片段即是电影的插曲《流浪者之歌》。“文革”后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电影来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印度紧随其后,这首电影插曲曾经在当时的年轻人中流传甚广。温州发廊里播放的背景音乐《美酒加咖啡》,张军从深圳带回来的收音机里播放出的《张帝问答》,还有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演唱的《成吉思汗》等,都是起先年轻人私下收听、改革开放后急速扩散流传的港台歌曲。再到《小武》,20世纪90年代中的内地流行歌曲《心雨》《爱江山更爱美人》《霸王别姬》,这些标签都成为时代变革的记忆,是对时代的侧面记录。
除了标记时代,有些歌曲还起到突出主题的作用。最直接的就是《站台》和《任逍遥》两部电影直接以歌名为影片命名,与人物的心情相配合,传达与歌曲中相似的时代情绪。《站台》的歌词反映了年轻人对青春的叛逆、茫然,以及无可奈何的状态,那些被大局势逼迫的流浪者在青春的流逝中失去了爱情、破灭了理想,最终又回到了最开始出发的起点。贾樟柯在选择歌曲时不但考虑到时代因素,还注意配合片中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情绪的抒发,将角色的命运巧妙地融入社会的大背景之中。
除了流行音乐,影视作品也是流行文化另一个重要元素。《站台》中,年轻人在电影院门口哄挤购买电影票,《小武》中则是录像厅,到了《任逍遥》,很多家庭以购买影碟机为时尚,反映了不同的年代的观影模式。除此之外,电影的内容和题材也有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电影艺术还未得到全面复苏,上映的电影以苏联等国家的译制片为主。《流浪者》作为最早一批引入中国的印度电影,反映了在印度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人们仍保有生活的热情。这部电影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轰动,引起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中国民众的共鸣,《站台》中就反映了当时的这一场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香港武侠、黑帮、喜剧类型电影的黄金期,《小武》录像厅外的公告牌可以看到的《赌神》《流星蝴蝶剑》都属于此类作品,小济的着装和行为也明显受《古惑仔》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期,好莱坞商业大片进入中国市场,占领年轻一代观众群,斌斌和小济就是受到《低俗小说》的影响,模仿其中的情节抢劫银行。《站台》中崔明亮漂泊归家后,与母亲边聊天边看电视剧《渴望》。电视剧是比电影更具有群众基础的休闲娱乐方式,《渴望》作为造成20世纪90年代万人空巷轰动效果的电视作品,播出的年代正是商品经济大潮来袭、社会秩序动荡变化的时期。《渴望》在这种茫然的时代背景下被创作,契合了观众对传统道德观念沦丧的失落和怀旧之感,所以具有淳朴善良、勤劳贤惠等传统美德的女主角刘慧芳,成为当时观众推崇的完美女性形象和道德楷模。
二、高音喇叭到电视新闻的发展:传递背景的媒介
在贾樟柯的电影中,高音喇叭和电视新闻不是一种普通的传播媒介,而是代表历史和政治的声音。导演借高音喇叭电视机传递出来的内容,反映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走向。
高音喇叭里时刻传递着国家意志。《小武》开场,街道上的人群都在布告前围观,画外音的广播也在制造压抑的氛围,法治宣传铺天盖地,而小武挤入人群看完布告还在顶风作案,违反秩序的小偷和广播中的政策法规形成了戏剧冲突。穿插在《站台》整部电影中的刘少奇平反、1984年国庆阅兵等高音喇叭的声音,反映了当时所处的时代,四位主人公的个体的流浪与回归,都与这些宏大声音背景相互交织展开。这些声音无处不在,每天都在人们的耳边响起,看似与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其实普通民众一直被这些声音包围,每一次喇叭的响起就是一次变革的产生。
在“故乡三部曲”中,电视机中播放的节目和新闻也是交代影片故事发生时代背景的一种途径。在《小武》里,多次出现有关严打法令法规和犯罪分子伏法的新闻;在《任逍遥》里,播放着特大杀人犯张军现场审讯、京同高速公路通车的时政新闻。除交代时代背景的功能,电视也成了维护强者的工具。在《小武》里,作为乡镇企业家的靳小勇曾跟小武一样是小偷,后来因为做“正经生意”发了财,开始有意疏远小武这个幼时伙伴。汾阳县电视台将小勇塑造成民营企业家的光辉形象,并专门报道了他的婚礼。一条在同一时间观看的新闻把处于两个不同空间的人物巧妙地串联。另外一处,电视上正在播出小武被捕的新闻,被采访的路人包括曾与小武都是小偷的三兔,三兔在影片开头一个同样也是面对电视台采访的场景中曾不知所措,到电影结尾处却义愤填膺地反目指认小武是“害群之马”。电视媒介不仅有传播作用,更是取代传统的价值标准做出了价值判断。
三、歌舞厅与KTV:情感的宣泄地
歌舞厅与KTV包房,是20世纪90年代非常火爆的娱乐场所。在社会转型的年代,民众的价值取向和生活观念都在转型中变化、动荡,新的群体秩序还在不断调整,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冲击成了先富起来的那批人的唯一追求。歌舞厅和KTV便在这种现实需求下产生,在现实中遭遇的激情、茫然、彷徨与无奈都在此得到发泄和安慰。《小武》的一个夜景画面中,街道两侧的二楼建筑几乎全是歌厅,有近乎统一的门面,取了像“大上海”“维也娜”“红河谷”这样以国际都市或旅游名胜为谐音的名字。
在贾樟柯构建的民间影像世界里,安排如此多的歌舞厅和KTV与他本人的个人记忆有关。他曾经回忆,在家乡的卡拉OK厅唱歌时看到一个孤独的男人反复唱同样的歌,他在这样的场景中感受到对于挣扎在生存困境中的普通人来说,以歌舞厅和KTV为代表的流行文化为其提供了一个舒缓压力、发泄情绪的途径和方式。小武就像他讲述的这个孤独的男人一样,偶然走进歌舞厅认识了胡梅梅。在不善表达的小武眼里,歌舞厅成了打开心中壁垒的场所。《任逍遥》中,封闭狭小且有些破旧的KTV包房成了斌斌和女朋友圆圆谈恋爱的固定场所,代表了普通人被挤压的精神空间,成了一种压制和禁锢情感的象征。
四、方言:身份的标志
除相貌外,语言是在与他人的交流过程中体现的第一特征。县城里的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交流很少会使用普通话,但长期以来,银幕上都是没有口音、统一说着普通话的人物,听不出家乡、无法辨别文化身份。导演有意识地使用方言对白,能增强影片场景的真实性,再现人物的生存状态,增强影片的纪实性。贾樟柯片中的演员基本上都是山西本地的非职业演员,他认为演员在使用自己母语表演时会更流畅自然,这种自然的现实感是他在建构自己电影形式美学时特别重视的一点。贾樟柯认为他电影中的人物是非权力的拥有者,他们是权贵之外的人群,他们无法掌握跟控制这个社会的资源,他们被动地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而这些人物的话语长久以来在主流影视作品中一般是不被重视的。从这个层面来讲,贾樟柯电影的一个目的是传达底层的声音。
《小武》《站台》中的多位主角都是从小生活在汾阳的人,自然说的是汾阳方言。《站台》中的钟萍,虽然也是自小在汾阳长大,但她却始终坚持说普通话,这样能看出钟萍潜意识里的骄傲和不安于现状,也符合县城里紧跟潮流的女性形象。《任逍遥》的拍摄地在大同,相比汾阳这个县城而言,大同是稍显繁华的地级市,九十年代开始跟随政策推广普通话。斌斌和小济正是成长在这一时期,他们是生活在后改革开放时代、没有社会集体主义记忆的一代人,他们不会说大同方言,这暗示着他们否认自己的本土身份。方言的使用不仅是揭示人物地域背景的工具,也是凸显人物性格、反映社会问题的途径。
五、结语
与第五代导演以浓墨重彩的形式和风格重构民俗的态度不同,如《红高粱》中呈现的祭酒神仪式,《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以挂红灯笼为影射的同房仪式,还有《霸王别姬》中的京剧国粹艺术,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大多是对现代城市或小城镇中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像呈现。在他们的电影作品中,民俗不再是被虚构或夸张的符号,而是民众真真切切每天经历的日常生活,是生命经验和生活现实。这类作品不再强调视觉冲击力的民俗符号,而将平淡真实、处处渗透着民俗文化的日常生活以影像方式呈现出来。
贾樟柯并不刻意回避自身农业背景和县城生活的个人经验,并且抛弃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从俯视众生的启蒙者位置走下来走向民间,回到自己所从属的社会系统中,将镜头平视个体的生命体验,融入他们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透过角色与所处环境的脱节来呈现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的个人境遇。小武虽然是小偷,但他身上仍然有许多传统道德观念遗留下来的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他对共患过难的朋友讲义气,对歌女梅梅体贴,对父母孝顺,然而在人人崇尚物质、追求利益的现实中,这些并没有换来他所希冀的兄弟友爱、父慈子孝、家庭美满的美好结局,反而是友情、爱情与亲情相继离他而去,最后落得个被铐街头任人随意唾弃的下场。《站台》中崔明亮张军们早先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美好的幻想、对改革后的未来充满希望,但经过走穴演出的一次次冷场之后也回归平静的生活。《任逍遥》中的两个与家乡脱节的少年无法找到人生的出路。在这几部影片中,贾樟柯都是以非常写实的拍摄手法记录着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理解,以及在被卷在时代旋涡中无力挣扎的个体的生存状态。在这急剧变化的时代环境中,作为个体的人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这种不确定的命运正是个人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焦虑。贾樟柯电影中的主人公都处在这种焦虑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就是在社会转型期的一个个青年,也还原了我们自身的真实状态。
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呈现了一种稳定的表现主题和电影理念,表现了对“民”的认同和关怀。不管是作为主角的迷失在商品大潮中的扒手,解体改制生活境遇遭变的文工团演员,找不到人生出路的失学少年;还是匆匆略过的赶上政策发家的个体户,辛勤劳作的家庭妇女,工厂破产的下岗工人,这些人物都是一个个充满七情六欲、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不再时刻保持衣着光鲜的形象,他用电影替这些微弱的个体发出声音,表现在被卷在时代旋涡中无力地挣扎的个体的生存状态。另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对还原日常生活状态的痴迷,对纪实性的追求,使得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得到重现。吃饭、抽烟、闲逛、看电视、打麻将、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每部影片都由这些零碎的原生态生活状态组成,都是电影表达和记录的内容。每个人物行为都在这些琐碎的场景中展开,同时又巧妙地将个体境遇放置在动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此外,贾樟柯还非常善于通过具有明显时代印记的符号来构建影像中的民间社会。服饰色彩、流行音乐、新闻广播、娱乐场所、特色方言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日常生活符号,都体现了社会转型进程中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这些时间和空间的诸多要素共同凝结成社会转型期山西县城特有的民俗文化世界。他的电影可以作为影像博物馆将民间文化符号进行记录和留存,将我们原本并不重视的日常生活看作重要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