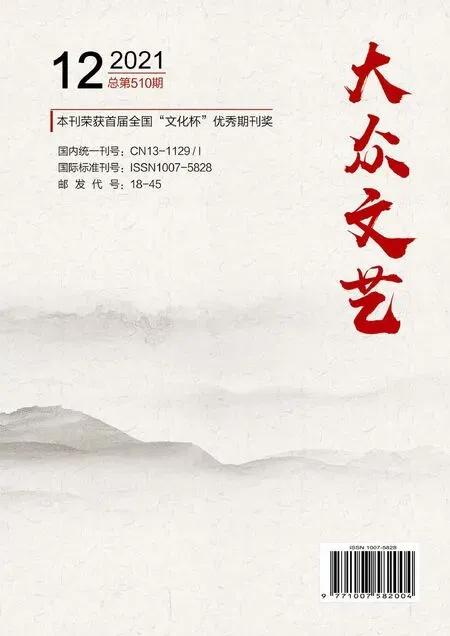绘画与摄影图像
——基于身体的模糊关联
2021-07-23吴晨凯
吴晨凯
(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浙江金华 321000)
一、摄影历史早期的摄影与艺术的关系:基于真实性的审美逻辑,以及一种与身体有关的能力诞生背景下的关系
早期摄影与艺术的关系可能显示出一种整体上更为不融洽的关系,对于摄影的批评也是争论不断。摄影早期的争论离不开以“真实性”为基础的审美体系,以及趋向于绘画“审美性”的价值评断。摄影的技术发展对于摄影与绘画艺术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但是由于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窥视到技术媒介对这些关系所起到的作用。
摄影出现之前,塔尔伯特希望可以让图像自动,自我的复刻在纸本上面。那么,摄影的出现,可以说是作为一种能力的延伸。摄影术作为一种功能媒介的价值是在于可以让一个“不是画家的人”拥有保存图像的能力。人们借助摄影可以获得一种由摄影这个媒介加以注释的“真实”,从而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视觉体验。而绘画中这样的“真实”在十九世纪大众的艺术意识中是极其重要的和关键的。“小鸟以为宙克西斯画的葡萄是真实的,飞下来准备享用它”。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词语与图像》 “既作为一种对世间物体完美复制的那种乌托邦梦想”。因此我们似乎也可以成立这样的逻辑,绘画的实用主义功能上,以及对复制场景的能力的刺激反应推动了摄影的诞生和发展。这既是对完美复制物像的向往,也是对人类保存文明和记忆的向往。
但是我们发现绘画所承载的“真实”本身不仅仅是摄影图像所还原的真实,绘画所含有的是一种诗学的真实。而摄影图像所注释的“真实”也许是包含了更多对现实还原的尊重。而这样的现实还原在摄影诞生的时代有类似于“巫术”的崇拜。“相片隔了数代以后再观看,却让我们面临了一种新奇而特别的情况”而对于绘画,人们则会更多地转向对于技法的好奇,对探知画面的好奇心就变淡了。正如本雅明在其《摄影小史》中所强调的“灵光”,“祭仪”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建立的语境就是,与其说这是一场与绘画本身有关的关系场,不如说是一场关于身体某种能力的关系场。而这个关系场所关系的又包含了画家在摄影诞生之前所拥有的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所带来的革新使摄影的触角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本雅明所强调的摄影的“本质”(即是一种与我们身体能力有关的乌托邦的幻境)产生了一种“遮蔽”的历程。在这里,由于“真实性”所引发的关系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又为其添加了一轮又一轮新的变化。
因此,无论是所谓摄影给绘画造成了冲击,还是摄影一直在通过以“真实性”在向绘画靠拢来获得艺术的话语权,这些视觉上关系的产生都会涉及整体社会基于“真实”的审美性的判断,以及一种与身体有关的能力诞生背景下的关系。
二、摄影作为一种官能的幻觉,一种基于身体在场的现实
“摄影是现代的驱妖术。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我们认为通过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世界。然而,其实是世界这一边通过技术向我们强调它的存在。这个主客关系的反转发挥着惊人的、不可轻视的作用。”让·鲍德里亚在其《消失的技法》中论述的摄影术作为一种其他物体消失而遗留下来的痕迹,否定了摄影作为固定,技法的主体视角的存在。客体,世界作为需要显示的主体存在于摄影图像之中。肉身,和身体的在场是对一切意志化的视角的消失,摄影的本质再次在其被“遮蔽”的历史中以另一种方式显现出来。摄影巨细无遗的展现,作为一种感官的遗留,是物体的痕迹以及身体在场的遗留。同样,我们可以在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对于尤里.阿特金的摄影的推崇中可以体会到。
本雅明表现出对于“快照”产生以后的“家庭相册”式的摄影的厌恶并称其为摄影的“没落时期”。场景设置的虚假,人物动态和神气的造作使摄影的“真实性”被极大的否定了,从而失去了摄影的永恒存在的,一种类似于“灵光”“祭仪”的消失。摄影完全成为一种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聚焦点,正如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提及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关系涉及社会的深层;它们不是固定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也不是固定在阶级的分野处,它们不仅在个人,肉体,行为举止的层面复制出一半法律和政府的形式”。“一方面,照片的产生最初被当作是自然界的自我复制,因而在细节上是‘真实’的;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不断变革以及照片被应用的语境不断变化,这一‘真实性’又基本被否认,而是表现为意识形态的隐性出场。”
三、媒介作为人的延伸
我们在谈论一种基于“身体”的图像观念时,我们并不能忽略摄影技术所带来的本质上的对于人类视觉观看方式的改变。摄影作为一种媒介,我们便需要面对媒介所产生的根本影响。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理解媒介》中所强调的新的媒介的形成并不是单单象征着一种新型的技术,而一种社会尺度的产生”,这种创造意味着新的社会内容。
“媒介作为人的延伸,媒介对信息、内容和知识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力,媒介不仅不是消极、静态的,反而有着积极、能动的成分,它们对信息有重大影响,决定着信息的简明度及组成方式。”因此,媒介是在图像的意义和意义呈现上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意味着如何将一种“消失的”的,“遮蔽”存在的事物有效的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是基于媒介对于人本身功能和知觉的强调,是一种类似于“再现”的真实,这样的语言体现着一种真实。因此,我们便可以成立这样的一种逻辑。
四、媒介是人“身体”的延伸,媒介作为图像的依赖所起到决定的作用。媒介承担了图像的全部语意呈现,同时也决定了图像的全部语意
同样,摄影与图像可能也有与绘画相似的创作结构,因为我们可能会很直接地意识到绘画和图像的创作者同样是“人”的同一性。但是,当我们不是以一种创作主客体的态度去区分摄影图像的产生时,我们会意识到媒介作为图像的依赖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同样,承载媒介和传播媒介承担了图像的全部语意呈现。
在这里,我们也并没有忽略创作主体行为的重要性,因为作为“原驱力”极大地把与创作者“身体”有关的图像从一种原始图形中衍化出来。而具体的衍化,依赖的不仅仅是创造者本身,更多的是与图像有关的整体媒介在其图像呈现中的作用。整体的媒介和语境决定了图像的有效性,既图像是依赖媒介而现实存在的。摄影图像对于媒介的依赖又决定了图像本身的开放性。因此,图像和媒介是相关联的,没有完全独立存在的图像。不同的媒介会决定同一图像的不同生发。
当作为绘画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在我们的身体中强调创作的主体行为,而作为图像时,我们在大多数的时候都会更多地去关注媒介本身。例如,当我们在观看视频录像的过程中,引起我们强烈和直观反应的总是这个观看环境下媒介所呈现的。媒介是人类功能的延伸,如果这时我们失去这样的媒介或是媒介的功能丧失时,图像所产生的意义便会发生消解或是消失。
五、绘画作为一种基于身体行为的意义存在时的绘画:决定绘画是否成立的是一种基于“身体”的绘画的过程,决定绘画是否有效的是绘画最终所形成的语意有效性
从“身体”这一基本的关系点,我们建立一种对于绘画的理解,以及决定绘画的特征是什么?那么这样的可能是否可以建立:绘画或作为一种循环反复,有关于“身体”的行为而存在,且是一种“有机的”行为过程,是作为绘画“自我意义产生”的过程。并且画面的意义不断伴随着绘画的推进而演变。
在绘画开始前,创作主体的“原驱力”就承担了作品进行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或引导绘画的发生途径,或是承载绘画意义的指向,或是作为不可见,不可预知的部分。在绘画的行为开始后,绘画便涉及了绘画的创造者行为,承载材料与“原驱力”在整个绘画的语境中所形成的画面自我的语意。这是因为创作者本身也是存在于语境当中。这是绘画进行中所强调的循环反复的过程,这一过程与身体有关,与物质有关,与整体的绘画语境有关。
在绘画的过程中不断地形成画面的语意,这样的形成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累计叠加的,而是模糊的,“雕塑般”的关系。最终,通过停止绘画的进行,我们获得了一个只与画面本身有关的语意,这个语意无法在绘画前预测,也无法预料在整体绘画语境中其所产生的效果。当然,这样的语意的形成只与作品本身有关,而形成的最后效果,亦决定了作品的语意是否有效。
绘画是否和摄影一样都是成为人类获得图像的手段而产生联系?当然,如果单一地把绘画作为一种获取图像的媒介,绘画便会丧失自身存在的意义。绘画为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绘画自身所产生所有的语意。因此在层面上,绘画的过程是决定性的,是不会为媒介所替代的或是媒介可以覆盖的。
六、结论
现当代艺术家愈加的显示出对于绘画行为过程暴露的强烈热爱。这里的过程并非指代绘画中画面上反复的过程,而是一种热衷于绘画推进过程中身体,环境,行为演变的探索。今天我们还可以听见很多关于“绘画已死”论述,或者说“绘画已经无法满足现当代艺术的表达”这样的论述。这样结论简单强暴地把片面功用的因素强加,覆盖在这一复杂多变的关系上,而且也否定了绘画的自我存在。本文基于一个“身体”在场的基本点来形成一种对于绘画与摄影图像之间的关系逻辑场。这种联系并不是一种可以十分具体化确立的关系,而是一种有关于身体的模糊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