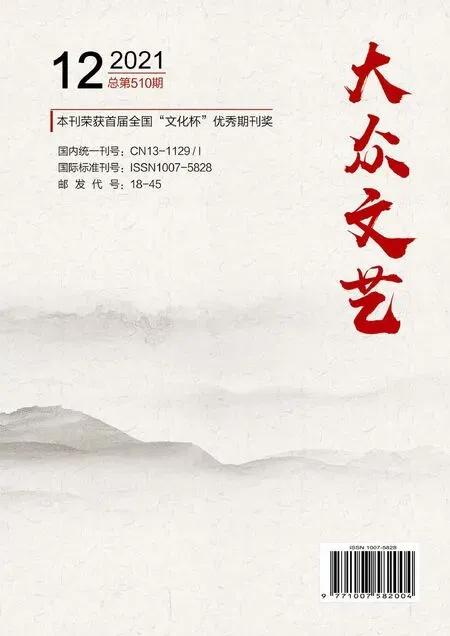从后殖民视角看库切小说中白人女性的历史困境*
2021-07-23陈雪
陈 雪
(泰山学院,山东泰安 271000)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是南非著名的小说家。其作品不仅呈现了殖民地有色人种的悲惨生活,也注意到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白人的生存境况。而白人女性这一群体及其特殊性也受到他的关注。在后殖民语境下,相对于第三世界的女性,白人女性的困境反而容易被忽视。在殖民体系中,相对于白人男性,白人女性始终处于一种他者地位;同时,白人女性拥有的种族特权将她们置于被殖民者的仇恨中。在后殖民语境中,女性的身体成为种族冲突的战场。相对于白人男性,白人女性更容易沦为种族报复的对象,成为历史的替罪羊。库切的小说《内陆深处》和《耻》虽聚焦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南非,但两部小说中的白人女性玛格达和露西都遭到黑人男性出于种族仇恨的侵犯。本文通过分析对比两人生存境况的异同,揭示南非白人女性的生存困境及这一困境的历史性。
一、南非父权制社会中的他者
殖民时代的白人女性享有种族特权而凌驾于与被殖民者之上。而这一特权实际是白人男性维护殖民统治,建构“白色神话”的手段。殖民地的白人女性面临着所有女性共同的困境:她们的主体性被抹杀,被看成是男性的附属品和工具。
在专横阴鸷的父亲面前,玛格达始终是被遮蔽的存在,被噤声的他者。如她所言,在殖民地全是像她一样的老处女,囿于家务琐事,慑于父亲专制,最终被湮没。库切是荷裔南非人,这也是其大部分小说创作的民族文化背景。荷裔南非人的家庭等级非常严格,女性处于绝对低等和从属地位,被视为传宗接代,照顾家庭的工具。长期受困于此的女性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玛格达的母亲弥留之际仍为未能给丈夫生育继承人而满怀愧疚。玛格达则因自己不符合社会建构的女性形象而轻视自己。
相比之下,露西更能认同自我。她违背父亲意愿到乡下当农夫,穿没有性别特征的衣服,从不掩饰自己的女同性恋身份,这都是她对父权制文化的反抗,与男性世界决裂的宣言。但露西与父亲卢里的关系表明她始终受到南非这个崇拜男性上帝的父权社会的束缚。小说采用第三人称视角,露西的形象是通过卢里的男性视角审视并呈现的。在卢里的凝视中,露西对男性世界的对抗——她对身材的放任,她的女同性恋身份——都被描述成一种遗憾。他爱露西,但视她为自己的附属品。在他看来,女人也是男性财产的一部分。他把女儿的受辱看成自己的损失,和他被抢的汽车、皮鞋一样。因此,在崇拜男性上帝的南非,玛格达和露西都处于他者的边缘化位置。
二、种族压迫的同谋者
殖民地严格的等级制度及被殖民关系合理化的种族歧视观念使白人女性即使不愿参与种族压迫,也无法与被殖民者建立平等的关系。更多时候,她们成为白人男性殖民统治的同谋。玛格达说自己从未被平等的目光打量过,但也承认自己从未用平等的目光看待仆人们。在种族等级制度下,她和父亲必须与仆人们保持距离。仆人亨德里克的新婚妻子安娜的出现打破了一切。父亲觊觎安娜的美貌并强占了她,玛格达为此感到忧虑和愤怒。她担心这是仆人的阴谋,害怕自己的地位被取代。同时她为父亲触犯种族关系的禁忌而愤怒。“我是一个保卫者而不是破坏者,也许我对父亲的愤怒只是对违反旧语言的愤怒……”这里“违反旧语言”其实是指父亲对语言所代表和维护的殖民制度的僭越。玛格达憎恨父亲所代表的等级制度,它否定了她对爱和人性的渴望;但作为制度的一部分,她无法摆脱其束缚。她不能,也不被允许同仆人发展出僭越等级的关系。当地位受到威胁时,她反而成了制度的捍卫者。
卢里认为历史在女儿生活方式的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段历史是荷裔南非人田园生活的黄金时代,也是殖民地人民的血泪史。露西的农场在东开普省边境,自18世纪以来,该地区一直陷于种族冲突。原住民在战争中失去了大部分土地,沦为白人的仆人。因此农场的位置暗示了“过去不可避免地存在”。露西拒绝卷入历史,她愿意接受新南非对土地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她尊重当地人并尝试与他们建立友好的关系,但她无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她的爱只限于她的花园、狗和水坝边的鸭子,即那些最不可能对爱做出回应的东西,库切将此称为“失败的爱”。种族隔离废除后南非有色人种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提高了,但大多数人的依然贫困,土地归属问题成为种族矛盾的焦点。作为殖民者后裔,露西无法消除历史的烙印,在当地人眼中,她是土地和财富不平等分配的受益者,本质上无异于其白人先辈。在南非权力更迭的动荡时期,拥有土地和财产的白人女性露西成为黑人男性眼中的猎物。
三、历史的替罪羊
白人女性享有的种族特权及其同谋者身份使她们受到有色人种的仇视。一旦失去庇护,她们就沦为种族冲突中的弱者。此外,白人女性的纯洁性在白人男性构建的合理化种族压迫的“白色神话”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使她们更容易成为种族复仇的对象,身体则沦为种族冲突的战场。
玛格达渴望摧毁殖民体系,与仆人建立超越种族的平等关系。但二元对立的种族关系已根植于殖民者及被殖民者意识中,扭曲的社会结构及长期遭受的剥削使亨德里克只能以压迫者/被压迫者的模式来看待种族关系。玛格达主动弑父弃权后,顺从谦卑的亨德里克变得粗鲁愤怒。他满怀愤恨地羞辱玛格达,占有她的身体,成为农场新主人,颠覆了殖民者/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但亨德里克对玛格达的仇恨并非针对她个人的,而是在漫长的殖民压迫中累积起来的。在后殖民时代的南非,这种仇恨激起了更强烈的报复欲望。
露西在侵犯自己的陌生的黑人男子身上也感受到让她震惊的仇恨。她认为他们是有预谋的。“我认为他们首先是强奸犯。偷东西只是偶然事件……我认为他们是干强奸的”。在父权制社会中,强奸最初被视为与盗窃、抢劫一样,是造成男性财产损失的犯罪行为。在后殖民语境中,强奸成为一场男性之间的种族战争。白人男性通过占有黑人女性摧毁并殖民黑人男性的尊严。黑人男性通过侵犯白人女性挑战白人男性的权威,解构“白色神话。”在殖民叙事中,女性身体象征性地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如果占有黑人女性是白人男性对殖民地霸权的宣示,那侵犯白人女性就象征着黑人男性夺回土地、主权和尊严的决心。女性则沦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四、寻求困境出路
在殖民体制下要消除对立的种族关系,实现平等交流是困难的。只有当自我成为他者时,才有可能完全理解他者,这意味着殖民者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力,解构自我。
玛格达邀请仆人住进象征等级秩序的房子,试图与他们建立跨越种族的关系,却发现在这种关系中他们既失去了原有的身份,又无法建构新的身份。“我们三个在这所房子里找不到自己真正的路。我不能说亨德里克和安娜是客人、入侵者还是囚犯”。最终亨德里克和妻子因害怕惩罚而逃离农场。玛格达试图找到一种跨越种族的存在方式,但小说中的南非社会早已千疮百孔,个人的努力不足以改变种族关系。但如库切所说,“她的民族对南非的爱是黑暗的、失败的,与之相比,玛格达至少对当地人有一种真诚的爱”。玛格达失败了,但这种真诚的爱对改变南非的种族关系必不可少。
露西坚持对自己被强奸一事保持沉默,因为她明白在殖民主义话语中,强奸是对所有黑人男性的公开审判。一旦白人女性指控被黑人男子侵犯就会得到广泛关注,因为这迎合了白人的种族偏见及其合理化黑人劣根性的政治需求。露西拒绝卷入种族仇恨的恶性循环,她认为自己的遭遇是在农场生活的代价,称那三个黑人是债务催收人。这说明作为殖民者后裔,露西无法摆脱因历史而产生的愧疚感。最终她选择留下来面对未知的一切。为了留下来,她把土地转让给佩特鲁斯并成为他名义上的妾,从满怀信心的新边境农民变成了黑人的佃户。她以一种相当屈辱的方式开始了新的生活,但这也是充满希望的开始,她以一无所有的“他者”身份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一种更坚实的存在。她的经历暗示了白人有可能放弃特权和优越感,以一种新的身份弥补过错,与当地人达成和解。露西腹中的孩子虽然在仇恨中孕育,但可以在爱中成长。作为两个种族的结合,它似乎象征着消除露西和当地人隔阂的希望。
五、结语
《内陆深处》和《耻》中两位白人女性相似的境遇揭示了长久以来南非白人女性由于性别和种族因素所面临的困境。她们既无法与白人男性对话,也不能同有色人种交流。而且白人女性更容易成为种族报复的受害者,历史的替罪羊。玛格达和露西都为摆脱困境而探寻出路,但在历史、政治及个体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不同结果。玛格达孤独终老,露西则与当地人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这一关系预示了在后殖民时代的南非实现种族和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