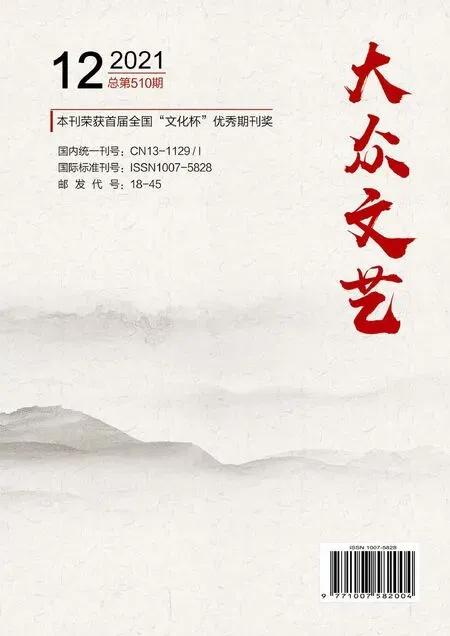隐秘·混杂·边界:安德鲁·马维尔《阿普尔顿府邸》的阈限解读*
2021-07-23孟璐西洋
孟璐西洋
(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 650000)
一、引言
人类学家维克多· 特纳(Victor Tuner)认为一个人或一种文化中最重要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时期,既不属于前一个阶段也不属于下一个阶段,是一个中间的、非此即彼的交界处。特纳把这个交界处定义为“阈限”(liminality),衍生自拉丁语limen意为“门槛”或“边界”。在观察研究了赞比亚西北的恩敦布青春期女孩成年仪式后,特纳总结出因为前一阶段不再适合事物的特征,而主导下一阶段事物的新特征也并不适用,因此,阈限具备创造性和自由性的特征,是一个正在变化的阶段。因此,阈限阶段能够激发神话、象征符号、仪式、哲学系统以及文化的产生。阈限是一种文化的虚拟语气,是某种社会差别被摧毁的瞬间,是前一种文化架构受到质疑和颠覆的时刻,而此时会为新文化提供萌芽的土壤。经历阈限这个交界处的人则处于新旧身份的转化,是暂时不确定的个体,具有模棱两可性,连接生与死、男性与女性、秩序与混乱以及神圣和世俗。
对于英国17世纪著名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英国著名的文学研究者伊丽莎白·斯多瑞(Elizabeth Story)在其关于马维尔的论述中曾描述他为“难以归类的”。以约翰·波特·雷什曼(John Butt Leishman)为代表的20世纪的文学批评家更认为马维尔的作品和他之后的18世纪奥古斯都风格极为相似。雷什曼认为,尽管他不能就某个诗歌特点而言与其他诗人旗鼓相当,但在诗歌主题的多样化和内容的广度上,马维尔可以和任何一位英国著名诗人相媲美。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马维尔作为英国17世纪著名诗人,是语言文学中最神秘、最难以界定派别、最独立的重要诗人。马维尔的一生都是难以理清的,正如约翰·多恩质疑的,马维尔到底是古典诗人还是浪漫主义诗人?作品是玄学派风格还是奥古斯都风格?是清教徒还是保皇派?这些问题都是不确定的。马维尔就像是处于一个连接两个边界的模糊不清的空间之内,是一位“过渡型诗人”。1905年,著名的传记作家奥古斯丁·比勒尔(Augustine Birrell)在完成了马维尔的第一部以书信合集为形式的《马维尔传记》的时候曾说比这(马维尔)更难以捉摸的人物很难再找到了。传记作家约翰·亨特(John Hunt)评价马维尔时认为至今为止,马维尔仍然是神秘幽默地拒绝后世人们任何想要深入了解他的意图。
《阿普尔顿府邸,致费尔法克斯勋爵》(Upon Appleton House:To My Lord Fairfax)是马维尔对于乡村别墅诗的主要贡献,同时也是马维尔写作中具备模糊边界特征的代表诗歌。本身表达的是马维尔对他的雇主,曾担任英国内战中的议会军统帅,直到1650年对克伦威尔长期不满愤而辞职的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Tomas Fairfax)的赞誉。这首诗的解读可以是多维的,既可以是史诗,也可以是田园诗,甚至还可以解读为宗教启示诗。在该研究中,《阿普尔顿府邸》中充满了变形、合成的,边界之上的意象。诗人创造了一个自己既是画家又是画面主题的空间,自己不仅担任费尔法克斯的描绘者,还赋予自己诠释者和谏言者的身份。
二、隐秘的主仆与府邸
马维尔于1650年至1652年末在位于约克郡的阿普尔顿府邸与费尔法克斯家族共同生活并担任勋爵女儿玛丽的语言教师。在此之前,马维尔有四年神秘的到荷兰、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旅行时间。而这几年恰好是费尔法克斯的一段不确定时期。1645年,他率领议会军打败保王党取得重大胜利,随后被任命为新模范军总司令。然而费尔法克斯拒绝担任委员会委员判处查理死刑。1650年,他抗议入侵苏格兰愤而离职,解甲归田回到修女阿普尔顿府邸。就如同马维尔一样,费尔法克斯勋爵的性格很难琢磨,宗教信仰甚至是模棱两可的。而在传记作家眼里,马维尔暂时的被强迫的罗马天主教信仰是一段众所周知的轶事。尽管费尔法克斯认为自己是一名无宗派的清教徒,并声称物欲是恶魔的圈套,但实际上他正好是约克郡最大的中世纪古董收藏者。在议会军攻占牛津的时候,他保存下了牛津大学图书馆。马维尔受雇于这位神秘的雇主后身份既是费尔法克斯志趣相投的同伴又是仆人。正如特纳把阈限定义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是一种试图对现实,对个人与社会、自然和文化的重新分类。马维尔利用其模糊的身份在费尔法克斯府邸创作出了《阿普尔顿府邸》,一个过去是现在的参考,未来是确定的但是当下有着多种可能性的世界。
诗的开头称赞府邸的谦虚与得体,符合乡村别墅诗表达房子特征与主人品格相似性的写作特点。而接下来马维尔身份的模糊性马上使诗的语气变得幽默起来,他描绘出一幅画质疑这位前统帅的过度谦虚和欠成熟的离职事件。马维尔承认有的人可能会嘲笑(line 39)这栋矮小的(dwarfish),受损的(distressed)房子(line 53)不得不膨胀(swell)起来容纳它的主人。尽管诗人承认“谦卑的人比起不寻常的伟人更能承受荣耀”(line 57-58),①但实际上在暗示费尔法克斯这样的伟人有责任护国家周全。紧接着,为了迎合主人对于古物的爱好,马维尔讲述了这座房子在1148年作为女修道院的历史来中断关于房子本身的描述。圣女思韦茨受到诱惑被监禁在阴郁的(gloomy cloister’s gate)修道院门内。其他修女承诺思韦茨在欢愉 (delight)和罪恶(vice)间护她周全(line 170),这样就能即享受欢愉又能保持虔诚(pleasure piety doth meet)。这些狡猾的修女此番最有劝导性的说辞迷惑地陈述了她们一种临时的,阈限的生存状态。因为只是尝试一下,上帝的审判既不会使人付出代价也不会成为负担(Try but a little while,if you wise:/The trial neither costs,nor ties)。诗人接下来描述了费尔法克斯的先人威廉·费尔法克斯在行动与隐退之间犹豫不决的状态:他将会敬重宗教,但忽视的话并非错误(225-26)。在讲述阿普尔顿府邸以及先人模糊不清的历史的同时,马维尔详细呈现了府邸中花园的美景,借此强调自己和主人对于自然风景共同的兴趣和审美能力,并隐含地表达对主人愤而离职的批判。看似诗人建立了一个自然自由统治的庄园(Nature here hath been so free/ As if she said,Leave this to me),实际上是精心构建用来折射大统帅过往功绩。因为费尔法克斯不能抽离自己的军事角色(284),他试图停留在行动与沉思之间,任他的花园“充当堡垒的角色游戏玩耍”(gardens out in spot/ In the just figure of a fort)。马维尔继而构造了一幅所有植物在宁静自然与硝烟战争中共存的阈限空间。比如每个早晨黎明升起一天的旗帜(290),蜜蜂嗡嗡叫就像吹着起床号(291-92),花儿们炫耀自己的丝绸徽章(294)并重新以新的声誉给步枪装满子弹(296)。
以拟人的手法描述了府邸花园的植物来陈赞主人后,诗人继而哀叹主人的离职对英国产生的巨大损失。就如同这个花园一般,英国会因为有费尔法克斯这样的骁勇统帅而安定繁荣,会因为他的缺席而走向阿普尔顿如同“深渊”(369)一般的杂草之地。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处,马维尔作为府邸的画家采用多种可能性的视角来构图。他描述了深不可测的草地(370),比人高大的蝗虫(371-74)。
三、混杂的他者与他物
阈限的不确定性让马维尔随意地混合人与物。深不可测的草地从干涸变为湿地沼泽,而人们成了会潜水的水手去测量草地的深度(377-84)。以色列人分开了这片草地(390),残酷的士兵“残杀”这些杂草。这几句充满暴力的诗句穿插在美丽的府邸花园描述中也并非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诗中出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色,马维尔称为“血腥赛提利斯”。“她为割草人铲起被屠杀的杂草和围栏,并称我们为以色列人”(406)。赛提利斯在这片杂草中成为诗人塑造的对于读者来说身份不确定的神秘人物,但诗人和费尔法克斯或许熟知她,因为她更像是一个熟知背景的讲述者。喜剧研究学者赛弗认为赛提利斯是一位在画面中占据显著位置的人物,她身体的一半朝外面向欣赏者,但又慢慢向内旋转,眼睛瞟向欣赏者,马维尔的意图在于拉近诗歌和读者的距离。赛提利斯先把读者带到了一个血腥的战争场面(417-24),接下来是一个乡村舞会(425-32),海面上的一座干草堆起来的小岛(433-36),然后是沙漠里的干草金字塔(427-40),紧接着又把读者置于绘画开始前的空白画布前(446)。马维尔把阈限空间的无限可能性(409-46)当作空白画布创作任何他想要的风景,可以是一个斗牛场(447-448),一个家畜圈(451-54),甚至是一群跳蚤(461-62)。正因为阈限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渡地带,因此可以激发随意的想象和无限的可能性。赛提利斯这个神秘的讲述者讲述了一段天马行空的故事,或真实或想象。
介于之前的血腥描述可以视为一种毁灭,接下来丹顿河被淹的确切地说是一个新开始的仪式。丹顿河被自己淹没(471)——一个可以产生想象力的开始。鳗鱼和牛一起低嚎(473-74),群马挂在水蛭上(475-76),船只在桥上航行(477),鱼入侵了马厩。看似不可理喻,而实际上也暗示费尔法克斯的沙场生涯。1643年9月14,费尔法克斯和他的父亲费迪南德切断了堤坝,打开了亨伯河的水闸,淹没了小镇方圆两英里的地方,阻碍了保王党军队的追击。马维尔再次呈现了事实与虚构掺半的画面,借此重新赋予自己阿普尔顿府邸这幅画的艺术创作者的身份。
紧接着,马维尔把自己重新插入阿普尔顿府邸的描述中(“myself embark”[483]),重新担任起之前赛提利斯所担任的叙述者的角色,把自己视为阿普尔顿这幅画的一部分,似乎是要为主人费尔法克斯解释自己的描绘。叙述者马维尔返回到树林中,树林在文学中向来和未知的危险和黑暗等意义相关联,在此处更象征着一个起点和“门槛”,也就回到阈限地带的核心——可以激发纯粹可能性和无差异性的模糊边界,以此理解自然的通用语言,使自己成为一名果园的教士(“great prelate of the grove”[592]),构架起人、艺术与自然的联系。在阈限的树林里,马维尔可以自由地体验和延续纯粹可能性以及各种可能性相组合的状态。
作为叙述者的马维尔也提醒费尔法克斯,这片树林的意义所在。“古老树干组成的森林”(489)字面上象征着费尔法克斯的家族。费尔法克斯巧妙地把自己的花园用作“防御”的港口(349),守卫树林里的“居民”——花草植物。但在花园里,一棵高大的橡树可以被轻而易举砍伐,因为树被叛徒蠕虫侵食(554),这似乎在暗喻查理一世的处决。鉴于马维尔的这幅名为阿普尔顿府邸的画既是创作又像是一面镜子,客观地呈现房子和主人的历史,因此“橡树的倒塌,目睹了叛徒受惩罚的下场”(559-60)也可以理解为费尔法克斯对于整个国会和查理一世之间种种的顿悟。然而,马维尔还把自己称为“果园的教士”(592),他也积极地暗示辞退的费尔法克斯保持现状的巨大危险性:叙述者马维尔被树林强行带走,橡树飘落的叶子渲染着恐惧的气氛(587),被常春藤紧紧地绕住(589-90),被冬忍树丛困住(609),被树莓锁住(615),被荆棘钉住(616)。更糟糕的是,这些囚禁并非仅仅是身体上的,同时也限制了思维(602)和心灵(603),无法回应爱和行动起来服务国家的召唤。
四、边界—玛丽的婚姻与府邸的消亡
诗人号召叙述者马维尔“行动起来”,不要再无所事事地用柳条在天地间垂钓,不要再过隐退的生活,应该再回到战场上。这样的号召对费尔法克斯来说关乎着他的未来,在诗歌剩余的部分具体体现在其独女玛丽的描写上。她在诗歌里的出现就像是把阿普尔顿这幅画的所有部分从模糊、模棱两可的状态拉拢在一个静态的聚焦点:大自然回想自己(658),太阳展示出对自然应有的尊重和谦虚(661-64),即使是翡翠鸟也不及玛丽的光芒,玛丽在府邸的存在凝固了空气和水蒸气,困住了愚蠢的鱼类(677),就好比水晶球里的苍蝇(678),自然万物完全凝固住了(688)。
从玛丽登场开始,诗人马维尔的语气也从之前的幽默甚至是天马行空失真的叙述以呈现费尔法克斯的阈限人生变为了专心细致地描述。她赋予阿普尔顿府邸的花园不可思议的美(68-90);把自己的芳香洒满草地(692);她使河流变得如水晶般的清澈(693);把之前充满危险和黑暗的树林变得笔直清晰(691)。正因为玛丽给予花园、草地、树林和河流自身的美好,大自然也以艺术的形式回赠了她草绿色的地毯(699)、花儿编织的皇冠(700)、小溪做成的眼镜(701)以及树木构成的天然屏障(704)。就如同大自然一样,玛丽也懂得美的通用语言——天国的方言(712)。但不同于树林中恐惧的叙述者马维尔和自己愤而离职的父亲,玛丽不会长期处于一种具有多种可能性的状态,她会嫁人然后把费尔法克斯的血脉传承下去。马维尔把玛丽比作“长在费尔法克斯橡树上的槲寄生的子孙”(739-40),以此来给主人提供自己的建议。根据埃里克森的解释,阿普尔顿府邸由费尔法克斯的独女玛丽继承,而玛丽与白金汉公爵二世乔治·维利尔斯有着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因此试图卖掉阿普尔顿府邸来为去世的丈夫还账。特纳把社会文化中的女儿角色视为阈限性的“门槛”即边界,她们的存在是为了堵住住宗族这个围墙的缺口。她们的存在的意义在于失去。
槲寄生从植物属性来看也是一种阈限性植物。严格地说,这种植物是半寄生的,它们通常会进行有限的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但又必须吸取寄生植物上的水分和无机物。槲寄生的种子通常在树皮和树木里层之间生根发芽,本身就是一个阈限——一个帮助寄生植物的水分和营养输向槲寄生的载体。有趣的是,这种植物虽然多寄生在橡树上,但更喜欢老苹果树,在诗里叙述者马维尔都有描述。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槲寄生作为半寄生植物能够穿过所寄生植物的树皮来更好地生存,因此槲寄生对树木有害,会慢慢导致树木的枯萎死亡。诗中把玛丽比作槲寄生是讽刺地预言阿普尔顿府邸的消亡,并把她置于吉利与不祥的中间位置。
紧接着诗人马维尔讲述了真正不祥的事件,即玛丽的婚礼。费尔法克斯不得不使他们的命运成为他们的选择(744)。他可能会继续留在他的府邸,一座折射他模棱两可一生的房子,但他也应该记住房子外面现实的世界的存在。阿普尔顿府邸仅仅是费尔法克斯家族第三代人托马斯·费尔法克斯还在继续的传奇一生的某个阶段,这个传奇将由玛丽继续延续。
画家马维尔以和主人的亲密接触以及能够体现阈限性的乱七八糟的意象结束了他的这幅阿普尔顿府邸绘画。鲑鱼渔夫穿着他们的独木舟,就像是把鞋子套在头上一样(771-73)。他还把这些像乌龟一样的渔夫比作两栖动物(774)。这些混乱颠倒的描述目的在于再次表现主人、房子以及未来的阈限性。然而变形的独木舟并不是渔夫永恒的庇护,它只是一个阈限的载体,是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临时意义。就如同费尔法克斯府邸,马维尔似乎在建议,不应该是卸下国家责任的持久隐退之地,而应该是一个让主人休息一会儿的场所,但不应该长期如此(71-72)。
五、结语
通过把自己当作创作者画家、叙述者和谏言者来呈现怪诞与无限可能性混杂的世界阿普尔顿府邸,并以此来折射费尔法克斯大统帅的阈限状态:既不在敢于行动的现实世界中也不在远离罪恶的天堂中,马维尔成功地建立并加深了自己和主人的关系,以此赋予自己谏言者的身份。在带领费尔法克斯在充满无限可能性的阈限世界里进行了一次有趣的人生之旅后,马维尔自信地邀请主人走出他过渡性的现状,和他一起越过“门槛”,走入费尔法克斯的未来人生,一段也有诗人参与的人生,正如他所说的“一起进来吧”(775)。
注释:
①本文所有《阿普尔顿府邸,致费尔法克斯勋爵》诗句均引用自Andrew Marvell :“The Complete Poem”,Penguin Classics.2005.
②1518年,威廉·费尔法克斯勋爵确实与继承了大量房产的孤儿伊莎贝尔·思韦茨结婚.(参见www.tudorplace.com.ar/Bios/WilliamFairfaxofSteeton.htm.)马维尔这部分的描述是事实与虚构的混合.
③此部分为费尔法克斯自己所著的Short Memorials of Thomas中的回忆。引自Fairfax,Thomas.Short Memorials of Thomas.London:Printed for Ri.Chitwell.1699: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