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摄影家王苗:“我们在那个时代没有缺席”
2021-07-21

王苗70寿辰时与摄影家朋友们合影。
我们只是记录了,而且应该说感谢那个时代,让我们在那个时代成长。我想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想再拍那个时代的纪实影像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它已经过去了
访谈/杨浪 编辑/黎立
《财经》杂志联合“巨浪视线”,推出系列影像专题视频节目—— 光刻。文艺评论家杨浪将陆续对话数十位中国摄影家。通过访谈回顾摄影家们的创作与经历,再现他们镜头下的高光时刻。本期嘉宾为著名摄影家、世界华人摄影联盟主席王苗女士。
杨浪:苗姐,咱们很熟了。
王苗:当然,几十年的朋友了。
杨浪:我想还是从这本书开始谈起,作为一个信息,摄影界许多朋友大概还没有接触过这本书,而且这本书马上就要面世。我想请你大概其说一下这本书的形成,乃至于你作为撰者、撰主,关于这本书的意义及你的判断。
王苗:你是主编,这本书是你的主意,对不对?
杨浪:其實是大家的主意,那咱一块儿说吧,毕竟你是这本书的主人翁。
王苗:对,我是主人,因为是王苗写的这本书。但是重要的是她的朋友们。前年在澳门的时候,是你起意,但后来因为疫情拖了一段时间,直到去年8月,才真正开始跟大家征稿。
杨浪:其实也就是哥们儿在一起闲聊,临时起意的。
王苗:是。
杨浪:因为那天说到年纪,我之于苗姐是不避讳说年轻的。
王苗:那当然。
杨浪:我说到你70岁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哎呦,苗姐都70了”。
王苗:我在摄影界这一辈人里面,是1951年的人。
杨浪:然后就跟“政委”(指王苗的丈夫何迪)说起来苗姐都70了,摄影家特别有代表性的苗姐应该出一本摄影集,是从这个角度说起的。大家议论着议论着就把它当真了。
在摄影界为什么叫你苗姐,比如说我叫苗姐,文澜也管你叫苗姐,除了几个年龄比你大的一般不叫苗姐,其他人都叫,我在想是为什么?
你在摄影界几十年来的经历,从“四五运动”到四月影会,再到纪实摄影、当代摄影的路,你不但作为摄影家,更是作为摄影组织者。当时突然冒出一个东西,就是王苗的这辈子其实就是中国当代摄影的这辈子。因此我就支持了这个讨论。但是后面这个组稿,我可组织不过来,因为稿子咱会编,但是关于稿件的组织是怎么回事,得请你来说说。
王苗:那还不是你一纸号令,发了一个征稿启示,大家就积极响应呗。但我没想到的是现在收了81篇稿,有81个朋友都写来了稿子。我的任务,其实是把所有跟这81个人在这些年里,他们的照片以及跟他们的合影,或者是我们一起照的有意思的照片,都找出来配到他们的文章中。
所以这本书有意思在哪儿呢?不光是他们写的这篇跟我来往的故事,实际上还有很多老照片,我自己都没想到能够翻出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些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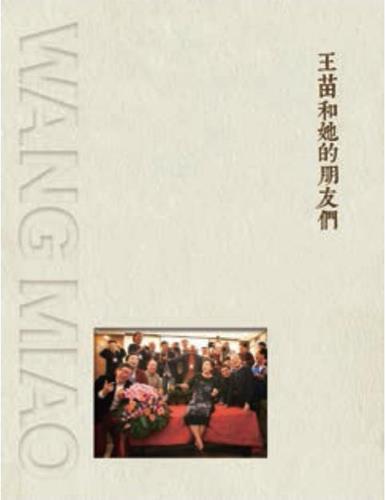
王苗新书封面。

顾城给王苗摄影作品抄写的诗。

北岛给王苗摄影作品抄写的诗。
野外拾回的小诗
杨浪:比如说四月影会的时候,北岛、顾城他们。
王苗:是啊,那就更难得了,这里面我还用到了北岛给我写的诗,你看,这是我在国际音乐节上要做个展览,叫《野外拾回的小诗》,北岛特意给我抄的。
杨浪:英文也是他写的?
王苗:对,他后来在国外,会英语。再后来,他到香港中文大学开始教诗歌翻译,所以他自己的诗歌都有翻成英文。
杨浪:北岛还能教诗歌翻译呢?!
王苗:我在书上也用了当年顾城给我写的小诗,是1981年到1982年左右。
杨浪:《野外拾回的小诗》。
王苗:《野外拾回的小诗》,正是朦胧诗最兴盛的时候,这是顾城的原迹,我手里有40多首,而且当时他都是用小纸片写的。
杨浪:这里的50是序号吧?
王苗:一共可能写了50首诗,他当时是照着我给他那个小幻灯片写的,那时摄影界有一个叫韩子善的。
杨浪:有韩子善。
王苗:你知道这是个老人了。80年代初期,他老拿着幻灯片去讲课,结果顾城就在一次看片会上看到了我放的小风景。
杨浪:韩子善老师拿你的照片去讲课。
王苗:对,去讲课。顾城就问韩子善,说我看了这些小照片特别想写诗,能不能借给我?
韩子善就问我了,我说“那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就给了顾城几个版,过了一个星期,顾城给了我四五十首诗,就是这个小纸片,我现在全部都存在这里。

《冷与热》,摄于1973年。

《约会》,摄于1974年。

王苗的第一张摄影作品拍的是下乡插队时的房东大爷、大娘。摄于1969年。
杨浪:“我在看你們,明天有风,另一个世界,更广大无垠”。这是顾城的。
王苗:都是照着我那个小风景照片,他有想法的时候就写。所以给了我这么多小诗,后来就认识了顾城。
你知道顾城最好玩儿的一件事是什么吗?他刚刚认识谢烨,在火车上,两个人坐在对面。认识了以后他就拿了谢烨的一张一寸的小照片跑到我家,找我给他翻拍。
杨浪:那就是成人之美的事。
王苗:那当然,我赶快就给他放大了,这还有这么段故事。
杨浪:80年代初期,那个著名的悲剧还远没有发生的时候。
王苗:那当然了。那个时候我就把我的那些小诗做成一个幻灯片,配了顾城的诗,感觉到还不够,就跑去找北岛,然后北岛就在那个小纸片上,他说我给你现写来不及,我给你抄一点我的诗,一个一个小纸片,给我抄了很多。
杨浪:反正他的作品也比较空灵的,没有具体的标题的。
王苗:对,就抄了一些,然后我就自己给他配起来,配到诗朗诵,当时在北京、在全国好多大学里面放。
杨浪:《野外拾回的小诗》的那组诗画,当时影响是轰动性的。
王苗:是。
杨浪:其实对于摄影界也是开创性的,此前个别的有过,但是这么一本高质量,这样的诗人和这样的作品,在当时直接影响到我。
王苗:我后来,你看这是邵柏林老师写的序,《野外拾回的小诗》,做了这么一本。
杨浪:邵柏林当年也是跨摄影美术界的。
王苗:是,邮票设计大家。
杨浪:大家、大师级的。
王苗:前言是他写的。
杨浪:这是哪个社出的?
王苗:这个版本是我在香港印的,内地版叫中国摄影家系列作品。
杨浪:这本画册我没见过,但真漂亮。
王苗:那送你一本。
杨浪:别,你现在都是文物级的,你是摄影界骨灰级的人物,得把这个都给你留好了。
王苗:没有没有。
摄影之路的起点
杨浪:邵柏林写的《野外拾回的小诗》的序。
王苗:是,其实因为我学摄影比大家都早,我跟大家一样,因为50年代出生的人赶上文革,正好是初中毕业前后。没得说的,“黑帮”子女一定下乡插队,兵团去不了的。所以我就到了山西,在临汾插了几年队。那时候就借了一个相机在那儿开始拍照,所以我手上第一台相机是借来的,是苏联一个老式相机。

1976年的四月影会。
杨浪:皮腔式的?
王苗:对,可能是,我都不记得了,是从一个叔叔那儿借来的。
杨浪:135,还是120的?
王苗:4乘5这样的大底片。
我现在存着一张最珍贵的底片,是1969年在农村拍的我的房东大爷大娘。他们拿着一本《毛选》,在那儿学《毛选》,背后还有毛主席像。
杨浪:是1969年?
王苗:1969年我插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17岁。所以那张是我拍摄的第一张照片。当然故事还有好多,在农村因为照相还被解放军给扣起来了,说我去刺探军情,这就是我最开初的摄影。
杨浪:那也就是说你的摄影起步比较早。
王苗:对,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搞摄影。
杨浪:到“四五运动”的时候,摄影已经成为一个民间不约而同的个人行为,就是说你从那时开始崭露头角。
王苗:其实,我后来从山西病退,回了北京,有一个机缘巧合,就进了故宫,在武英殿,真的是跟了老师傅,师从吴寅伯、罗哲文这些大家,拿着大座机去拍文物,所以在“四五运动”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小学徒了。
杨浪:已经在搞摄影了。
王苗:已经真正搞摄影了。
杨浪:而且就在故宫里。
王苗:就在故宫里头,离天安门特别近,那个时候弄了一个小的135相机,我还记得是老式的佳能,前面有一圈珠子,可以自动测光的。
那个时候经常溜到天安门去拍照,赶上“四五运动”,所以我现在还留有很多“四五运动”的老照片。
杨浪:就是说无论是摄影界还是我对苗姐的印象,都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四月影会和那场永久的纪念。
王苗:永远的四月。
杨浪:从此出现了一个叫做王苗的女的摄影家。当时女摄影家并不多,所以一开始就留下很深的印象。
今天大家都公认四月影会是中国当代摄影、当代文化艺术一个重要转折性的标志事件。今天看在这个标志性事件当中的那些重要骨干,也成为后来中国摄影史上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人物。
但对于苗姐来说,几十年来还干着这个,是比较罕见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又不断地变法,比如你刚才说到的小诗,因为小诗完全融入了一种审美的、情感化的,有别于四月影会高度纪实的那种奔放情绪。我觉得在你的创作经历中,不同风格间隔的时间并不长。

王苗在云冈石窟进行文物拍摄工作。

《笼里笼外》,摄于1974年。
王苗:是的。
杨浪:就是从四月影会很快就出现了小诗,小诗以后又很快跑去了香港,进入了非常深厚的人文地理摄影。
王苗:是。
杨浪:是可以这样评判你吧?你一个纤弱的女性摄影师,老搞得这么雄浑,这么实干,这么深厚,这是怎么回事?请谈谈这个过程。
王苗:其实挺简单的一个事,因为我是无意中进了故宫,但那时候拍文物,摄影对象它是死的。在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单位让我去拍石窟,所以呢,我是跑遍了中国所有的石窟,从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然后到敦煌。
我在敦煌蹲过三个月,拍敦煌的壁画并出了大画册——《敦煌飞天》。两次进敦煌,在那儿不光是用色彩反转片,当时叫E4,中间还要经过一个翻转的过程的那种胶片,我自己在洞窟里冲洗,看曝光准不准,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个曝光表,不像数码马上能看见。
我经历过严格的静物拍摄的基本功训练。再后来,在1979年四月影会后,我进了中国新闻社,因为当时不安于只拍摄静物。
杨浪:这里给我一个感觉,也就是说,其实你进入摄影最初的几步面对的是静态的、固定的、文物级的。
王苗:对。
杨浪:是与你后期的那些纪实的、人文的完全不同的摄影对象。同时你刚才也还说到了,你为了曝光准确,还得自己去暗房。
王苗:對,自己冲胶卷。
杨浪:那么我理解就是在你最初进入摄影圈的时候,对于摄影技巧,包括最基本的暗房胶片的感光的敏锐度和拍摄静物那种技术上的精确度,你是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个训练。
王苗:严格的训练。而且我给你说好玩儿的事,我在文物出版社干了七年暗房。从故宫武英殿,后来开始招工,这些叔叔阿姨们觉得小姑娘不错,就把我正式招到文物出版社,一个月26块钱工资,从1974年干到1979年。
杨浪:这里面我倒想对镜头外面的观众说一句,这样职业的摄影师,这样出色优秀的摄影家,有过七年暗房经历的,在我的印象当中是极少的。
王苗:我给你讲讲那时候我在暗房里洗什么东西。一个字一个字拼写宋版毛主席诗词,把它洗出来,然后编辑把它贴出一个版照相,相当于毛主席诗词的那个线装本宋版体那本书,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洗出来的。
杨浪:这就可以理解你作品本身的那个精致程度,和对影像的敏锐感觉,都得益于你当年刻苦的训练。
王苗:是的。拍敦煌对我影响也特别大,尤其是对色彩的关系的把握。敦煌壁画里面有一些抽象的,比如那些黑飞天,我非常喜欢,因为它非常简洁,颜色随时间变化以后,有的就是一个完全的黑脸、白眉毛,实际上是一个很抽象的图案。
杨浪:那么你是经过了这样的摄影训练,然后进入了中新社。
王苗:对。
杨浪:因此出手不凡,这倒是可以理解了。
王苗:进中新社之前,我在文物出版社期间,就拍了这张《笼里笼外》。
杨浪:《笼里笼外》,这可是摄影界的大经典。
王苗:对,为什么呢?就是不安于拍静物,我也想创作。所以呢,跟着一个老师傅,《人民中国》的一个归侨老摄影家,叫黄翔坤,我永远记着他。他带着我在北京动物园,钻到猴笼里头去了。

《康巴草原》,摄于1985年。
杨浪:今天当代人看这张片子,认为是在那个时候被压抑、束缚情况下的情绪宣泄。其实就是你从文物出版社的静物摄影到尝试纪实摄影中间的一个转换。
王苗:对。四月影会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文物出版社暗房期间,自己拍喜欢的,比如古松、风景,拍了很多。
杨浪:经过了纪实摄影这种自然的锤炼,然后从中新社开始介入新闻摄影。
王苗:介入新闻摄影。1979年11月,我去采访了四届文代会,拍了很多那个时候的老文艺家们。去采访过沈从文,拍过萧乾,拍过杨绛。
杨浪:杨绛也是四届文代会的代表?
王苗:她可能不是,钱钟书是,我是后来到她家去拍他们,拍她和钱钟书。我们中国新闻社是给海外供稿的,所以就开始拍新闻片。
那么在拍新闻片中间,因为受了多年拍摄文物的训练,我就发觉用长镜头去拍小风景,效果完全不一样。当然,在这个中间,是受了日本的东山魁夷的画展的影响,使我发现风景可以这么拍。
这些小风景用长镜头压缩后特别简洁、单纯的画面可以如此动人,所以在无意识间拍了一大批这样的小风景。
杨浪:也就是说这种画面的构图是受了东山魁夷的影响。
王苗:对。
杨浪:在技术上你发现用长镜头来拍小画面,能达到这种东山魁夷式的……
王苗:简洁的、单纯的,又宁静的。
杨浪:你这倒又说了一个小窍门。
王苗:因为它是压缩的嘛,当时是大好河山派,风景都是大的,大山大河、长城什么的,而我就去拍这些小花小草,拍一些流水……
杨浪:于是《野外拾回的小诗》是这么拾回的。
王苗:这么出来的。
杨浪:是长焦拍小风景。
王苗:对。
杨浪:画面上大家感觉出现了另外一种语言,不是大山大河,这倒有点像女性摄影,又因为有了顾城们的诗,更使它的画面意义完全不一样了。
王苗:加上诗和画的配音,当时是中新社一个音乐家帮着我配的外国音乐,然后加上朗诵的声音把这个诗念出来。
杨浪:那你是最早融媒体和多媒体的实践者。
王苗:对,最早的。
杨浪:这是1981年还是1982年?
王苗:1981年。
杨浪:那就对了,1983年《中国青年报》创办新闻周刊,我是一版编辑,我被强烈影响,我给大报一版风景照片配诗,如今说来都是快40年前的事情了。
在这个过程中,你进入中新社开始新闻摄影。
王苗:对。
杨浪:纯粹的纪实摄影。
王苗:对。
人文地理的探索者
杨浪:因为中新社把你派到香港去做那本《中国旅游》杂志,于是你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人文地理摄影。
王苗:我是因为喜欢拍小风景,然后到1985年的时候进了西藏。
杨浪:第一次进藏。
王苗:第一次,1985年我们开了一辆车,開了一个月才到拉萨,走川藏线,然后又在西藏境内走了两个月,所以呢,西藏使我彻底改变,原来不怎么拍人,因为新闻就是记录,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识拍好的人物,是西藏之行让我敢拿着广角镜头去对着那些藏族老乡。使我感觉到天地之大,在那儿拍小风景,镜头已经压缩不了了,只能用广角。
杨浪:这又使我对你加深一层理解,就是在进西藏拍人文地理,接触这个主题之前,你的镜头当中除了四届文代会,你并不主动瞄准人。
王苗:对,那个时候拍四届文代会现在看来就是个记录,当然,很珍贵,因为毕竟这些老艺术家们经过文革活过来的,能够出来的,在海外发了很多稿,海外特别关注谁出来了,哪个艺术家还活着,尤其在香港报纸上采用率特别高。
杨浪:但那时候你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
王苗:对,就是个记录。
杨浪:但是你说进入到西藏去以后,才开始……
王苗:有意识地创作。
杨浪:对准人的创作。
王苗:对准人的拍摄。后来我出了一本叫《西藏神秘的高原》的画册,在美国好几个地方办了我的第一个个展,就叫《我眼中的西藏》。
1986年,就在我刚刚到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同仁们就说,你这个西藏主题太好了,后来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博物馆再次展出,富士还赞助了我。
杨浪:如你所说,1985年那个时候也是中国摄影家最早进西藏的那一批。
王苗:对,是比较早。
杨浪:你又是最早的潮头弄潮儿。
王苗:那时候的西藏真的是非常原始的状态,你去拍这些藏民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一点抗拒的心态,非常自然。
杨浪:四月影会是开创性的,小诗对于丰富摄影语言是开创性的,然后进入西藏,把西藏这个主题传向海外,这好像你又是开创性的。
王苗:说不上。
到了香港以后,毕竟我在编一本《中国旅游》的杂志,这本杂志是以图片为主的画报。因为办刊,我就开始了在中国大地的行走。云南、四川,整个福建、广东,我跑遍了中国,可以说中国的30几个省、区、市,没有一个是我没去过的地方。几乎全部都是靠汽车一个一个跑过去的,走遍了中国。
那么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人文地理的探索。因为要做故事,一本画报里面要传给读者的信息是有故事的,通过画面、通过影像,要让读者看得有兴趣。所以到了香港后的第一次大活动,是在1987年选了唐僧取经的道路,跑到新疆去了。
杨浪:西游记,唐僧取经。
王苗:唐僧取经的这样一条路。
杨浪:方向是新疆。
王苗:新疆之后,跟着走了西南的丝绸古道。
杨浪:西南丝路。
王苗:那个时候印度还叫身毒国。
杨浪:茶马古道。
王苗:那个时候不叫茶马古道,我们管它叫西南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经过整个凉山地区,到宜宾,五尺道、临官道,最后到保山,从腾冲出境。这样,跟吴家林,还有冬瓜(徐晋燕),云南的冬瓜,我们也走了三四个月,一直走到云南边境上。
杨浪:我发现这又是一个特点,当你进入到人文地理拍摄,无论是西藏、新疆、云南还是哪儿,这个时候你不单是一个摄影家,你身边永远有一些当地最优秀的摄影家,被《中国旅游》所组织,具体说由你王苗组织的。
王苗:是的。
杨浪:刚才说到王苗和她的朋友们,我发现许多写这段故事的人,都是在路上跟你相识相交。比如西南丝绸之路,同行的吴家林、冬瓜他们是云南的大师。
王苗:云南的大师。然后紧跟着,1991年的时候重走马可波罗之路,并出了六七个版本的画册。
杨浪:就这本《马可波罗》。
王苗:对,这本是英文版,还有法文版。这里面的照片全部是我拍的。
你知道当年开车的是谁吗?四川的王建军。我们从帕米尔高原起步,一直走到元大都,走到北京。而且最巧的是我们到北京的最后一天,马可波罗的十六世孙刚好也到了北京。
杨浪:这是安排的吧?
王苗:没有,就那么巧,正好在开马可波罗的研讨会,他的第十六世孙正好到北京。
杨浪:所以你们计算着行程……
王苗:就是赶巧了。
杨浪:我的印象里,人文地理摄影成为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虽然这个题材许多中国摄影家都触及到了,但就空间的广度和历史的深厚度而言,你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而且你还是屈指可数的女性摄影家。
因为《中国旅游》这个重要媒体平台的存在,你组织和团结了中国一批非常优秀的摄影家。我编稿子时发现这些哥们儿全是每个省的腕儿,不少是那个时候每个省的摄影家协会主席,反正每个省的扛把子,都聚拢在苗姐周围,都是在八九十年代结识的。
王苗:是,都是我的好朋友。
杨浪:这类摄影就成为了抢救和记录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行为,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王苗:我想当时跟这么多朋友能够这么好的交往,其实是大家帮了我,因为《中国旅游》画报需要有稿件,需要有好的题材,靠我们几个记者是拍不过来的,肯定要靠当地最棒的摄影师,而在那个时候,能够拍出好故事的摄影师不多,而正是这一批人,后来都成为了大家。那么我跟他们联络,成为我们的特约记者。
杨浪:我印象里吴家林是被你们《中国旅游》画报发现、扶持起来的,可以这么说吗?
王苗: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因为吴家林他是很早就在昭通的一个文化馆里搞摄影,早期当然都是高大上的这种照片,他受影响是四月影会。知道云南有个萧敬志吗?一个老先生,他原来是新华社的老记者、老编辑,当时下放到云南,就留在云南了,他在云南带出了一大批摄影家。
杨浪:吴家林是萧敬志的……
王苗:副手,都在云南新闻图片社工作,萧敬志是云南新闻图片社的老编辑,吴家林、冬瓜他们都是云南新闻图片社的摄影师。是萧敬志把四月影会的第一届、第二届展览搬到了昆明。
杨浪:在圆通山公园。
王苗:你看,你都有印象。
杨浪:我当时在昆明军区文化部,我对我的留言都还记得,我当时写下“这是一次辉煌的日出”。
王苗:你当时在昆明?
杨浪:在昆明。
王苗:太难得了。
杨浪:非常激动,看到这个四月影会。
王苗:我最近在看关于吴家林的一篇报道,他特别讲使他开窍的是四月影会在昆明的展览,他突然发现摄影原来是这么回事,可以这么拍照,要记录平常人的生活,所以开始了转变。1980年我到云南就认识了他和冬瓜,此后我每次到云南,都跟他们同行。重走西南丝绸之路就是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弄一个破吉普车滚下来的。
杨浪:所以这本书里你们三人署名。
王苗:对,而且中间出了好多事,您不是说让我讲点有趣的故事吗?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我们中国新闻社经常要到一些侨乡去采访,1980年,我们到了福建。福建分社当时的社长是陈佐洱,后来成为港澳专家。他派了一个文字记者陪着我,沿着福建海岸线边走边拍,我现在手里有一大批1980年、1981年在福建拍的老照片,很有意思。
杨浪:40年前。
王苗:40年前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们到了莆田的湄洲岛,当地的臺办特别紧张,我们就奇怪说这是怎么了,他们说某连队要拆湄洲岛上的妈祖的祖庙,为什么?因为当时岛上驻守着解放军的一个连队,连队反映老有台湾渔民偷偷地上岛拜祖庙,祭妈祖。所以连队就说我们把庙拆了,拆了他们不就不来了嘛!台办的人知道这是个麻烦事。
杨浪:80年代初期还没有这些政策。
王苗:没有。台办的人把这事告诉了我。恰巧我回到福州的时候去见了项南。
杨浪:福建省委书记。
王苗: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可不是文化革命了,怎么能把庙给拆了,妈祖庙是台湾渔民心中的神。项南不相信,他说没有的事儿。我说你去问,他就立刻叫他的秘书去问,一问果然有这么个事儿。他虽然是福建省军区政委,但他管不了部队,所以他当时就交代我两件事:第一件,回去以后写个内参,一个报中央,一个给我;第二,你能不能把秦家骢给我请到福建来?
杨浪:这是谁?
王苗:《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非常有名,当时是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的记者,咱们的《参考消息》上有他很多文章,因为他那时候写采访中国的文章。项南对他特别有兴趣,就是说你能不能请他到福建来看看。我说好,答应了他,就回了北京。
杨浪:他是想借力打力,尽管他在部队有军职,但他没有权力。一个是你发个内参,再请一个国外媒体的记者来,聪明。
王苗:这两件事我都给他办了,回去写了内参,然后项南就拿着内参把连队给迁走了,祖庙就保下来了。现在湄洲岛的祖庙不得了,宏大的,每年办多少活动,那可是妈祖的祖庙。
杨浪:那就是说湄洲岛这个妈祖祖庙能留下来有你一个大功劳。
王苗:有我一功劳。所以我回头说吴家林和冬瓜,我们跑云南的时候,出了无数次险,有妈祖保护我就没事。你说我们开着吉普车,从一个山坡上下来,走在一个水坝上,前轮飞了,破212吉普车前轮飞了,飞到水里去了,我们的车愣是没事,停那儿了。
还有一次我们去拍马帮,在狭窄的山路上追着马帮驼子拍,我傻,我背对着马匹站在路边,被马驼子撞了一下,倒栽葱栽下去三丈,滚了好几个滚,相机还举着呢,没事儿,把吴家林他们吓死了。

2004年6月,“两岸摄影家合拍贵州24小时”启动,王苗在活动背板上签名。
杨浪:那个马道是这样的,马带着两个驼子,你以为背过去了,马也不知道,但是驼子比较宽,把你给拱下去了。
王苗:对,我就倒栽葱栽下去了,一个大石头把我绊住了,坐那儿了,手还举着相机,相机都没摔着。
杨浪:人也没事儿?
王苗:一点事儿都没有,把吴家林他们吓得,就在上面叫啊叫,然后又从旁边下去把我捞上来,没事儿,我说我有妈祖保佑着呢。
杨浪:就是把妈祖祖庙救下来以后的事。
王苗:对,以后的事,我跑西南丝绸之路的事,你看沿途多少好玩儿的。
1989年我就组织了中国大地24小时的拍摄,发动了全国500个摄影师,记录中国大地一昼夜,在《中国旅游》上出了整本画册。
杨浪:这个叫什么呢,中国24小时?
王苗:中国大地24小时。后来跟着就出《重走长征路》,在《中国旅游》上出了很多这种长的大的专题,大运河,空中看运河,当时是鲍昆拍的。
杨浪:鲍昆还玩过航拍?
王苗:有一张航拍片子特棒。而且你知道什么事呢?就去年疫情,我开始整理我所有的40多年的东西,从香港背回来了二三十个大纸箱子,一个一个整理,发现了有几百张当年鲍昆他们拍运河的135反转片,还有120的反转片,我全部还给鲍昆了,把鲍昆给激动的,说欠着苗姐,她帮我保存了这么多年。
杨浪:所以我给鲍兄打电话的时候,鲍兄说“我欠苗苗一个人情”。
王苗:你想我替他保存下来,而且我发现,这大运河是当年我跟鲍昆他们组的稿。
杨浪:当时鲍昆不是大学老师吗?
王苗:他和于志新,还有邓丽丽。你知道邓丽丽吗?他跟于志新他们一块儿采访大运河,我们出了上下两集,当时选用的这批片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我那儿。
杨浪:包括作为理论家的鲍昆,有过非常出色的摄影实践。
王苗:而且这些片子我一看,还真拍得特别棒,现在你再看看大运河,都没有当时人民老百姓生活的自然的场景了。
杨浪:他居然还是航拍的。
王苗:有航拍的,空拍的运河一条光带特别漂亮,我们做的封面。
杨浪:当时怎么解决,没有无人机怎么解决?
王苗:他们用直升机。
杨浪:这又是听到一件事,原来鲍兄还玩过航拍大运河。
王苗:我告诉他,我说这些宝贝你现在都可以出本画册,会非常精彩。
杨浪:如果在今天拿着无人机再拍一路,那就是一个厚重的对比。
搭建交流的平台
杨浪:对吧,有时间和空间厚重感的东西。也就是说苗姐你在主持《中国旅游》的过程中,当然这个平台很重要,就像文澜和延光他們自己的《中青报》和China Daily平台。那么你凭借《中国旅游》这个平台不光组织了国内的这些大家,还跟“两岸四地”包括世界华人摄影联盟的摄影家广泛合作。作为世华盟主席,你跟全球的摄影家,特别是著名的中国摄影家,都保持着紧密联系。
王苗:是。为什么呢?因为侨办是做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工作的,所以我在《中国旅游》这么多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给海外的这么多华文文化中心供图片展。
杨浪:这是很自然的业务联系。
王苗:您知道我把文澜的《长城》《自行车》、郭子的《红色中国》、陈复礼的……办了展览。我带着郭子到法国去的,我把郑云峰的《长江三峡》办到巴西去的,所以这些年我们办了几十个展。

1997年月1日,王苗在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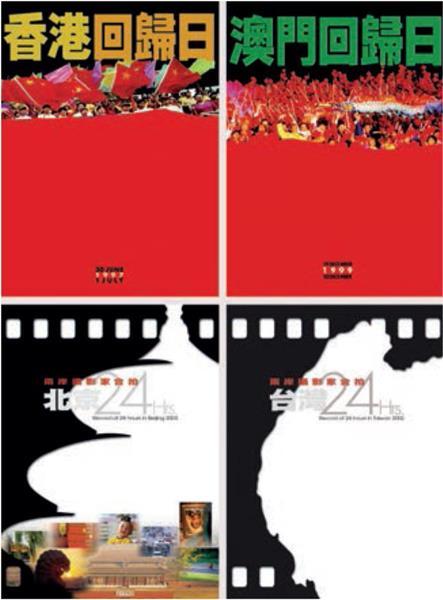
《香港回归日》《澳门回归日》画册封面。中国大地24小时拍摄系列画册封面。
杨浪:把优秀中国摄影家的作品推介到世界,同时推广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风光、中国的故事,最早讲好中国故事的摄影家和组织者。
王苗:对。
杨浪:然后再把全世界华人里面的优秀的摄影家的资源结合起来。
王苗:组合起来,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世界华人摄影联盟,大家一起讲好中国故事。在这个中间,我们不光要走出去办这些展,我们还要跟“两岸四地”的摄影家更多的交流。
所以,在2002年我带了三四十个大陆的摄影家到台湾,开始了“24小时记录”,两岸摄影家拍台湾,当时是跟《中国时报》合作的,你看转眼快20年了。
杨浪:这又是一个事件了。
王苗:对。
杨浪:数十位的大陆摄影家,到台湾去拍台湾人的生活。
王苗:对,而且打破了当时的台湾的一个禁忌。那个时候叫“团进团出”,你一拨人三十几个人只能一起进去,坐一个大巴,挨个转一圈,还不能散开。但是当时突破了,王金平给我们开镜,在台北故宫的宫门前。
杨浪:王金平当时是“行政院”……
王苗:“行政院长”,《中国时报》当时在台湾的能量还是蛮大的,遍布全台湾都有它的记者站,这次活动破了当时的一个限制,让我们这些人分散到二十几个组,每一个组配一个台湾《中国时报》当地的记者。
杨浪:沉到台湾的社会生活里面去。
王苗:我还记得我到了台南,去拍了当时台湾大地震之后的那些景象,那么后来结集就出了《两岸24小时合作拍台湾》的大型画册。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在开镜的时候,我说我们今天能够来拍台湾,我们为什么不能拍北京,不能拍上海,不能拍中国各个地方呢?所以从2003年,我们启动24小时拍中国系列活动,准备在4月拍贵州。
杨浪:把他们请来。
王苗:包括香港、澳门的摄影师,叫“两岸四地”,结果遭遇SARS。贵州的旅游局长跟我是好朋友,叫杨胜明,一个女局长,特别能干,就跟我说“来吧,没关系,我们贵州一个SARS确诊者都没有”。
杨浪:去了吗?
王苗:我说人家不敢坐飞机,台湾的飞机怎么飞过来,担心飞机上有风险,就延期了。
王苗:到11月,继台湾之后启动拍北京,100个“两岸四地”的摄影家在天坛开镜,拍摄北京。2004年6月去拍了贵州。
杨浪:是拍什么?在一个24小时之内拍。
王苗:大家分散,分成若干个组,全北京遍布我们100个摄影师。
杨浪:然后集中起来出书还是办展?
王苗:出画册、办展览,这系列的24小时北京、台湾都到了海外的文化中心……
杨浪:这是一套系列活动。
王苗:对。
杨浪:这套系列活动丰富了“两岸四地”的摄影家之间的联系,既是文化的联系,也是人民之间的联系。
王苗:对,这个持续了十几二十年,而且都出大的画册,这些画册被很多省市当做礼品送给海外。为什么?因为我们记录的都是各個省市人们真真实实的生活,而且是这24小时之内拍摄的。
杨浪:苗姐,我看有好几篇业内大家的文章管你叫“大姐大”,确实是因为你持续践行中国当代摄影,并在这里面做出突破性、开创性的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你对于中国“两岸四地”的摄影的组织,通过摄影把中国文化推出去,把中国摄影家推出去,把国外优秀的华人摄影家介绍进来,这个工作主要是你,这工作很难由别人替代,当然大家都在不同的领域协同推动。
王苗:但是我恰好是在香港这个有利的位置上,而且我本身的工作性质也需要我去做“两岸四地”的工作,我要团结香港的摄影师,所以我们没有放弃任何机会。1997年香港回归日,我们记录了48小时,6月30日一天、7月1日一天,当时大陆的摄影师、香港本地摄影记者协会的摄影师,还有台湾来的摄影师,共同记录回归日,并出了《香港回归日》。在1999年出了《澳门回归日》。
杨浪:苗姐,你做这些事其实不奇怪,咱俩聊到这儿,还有一点就是你为人谦和,热心帮人,作为一个女人你不独。
王苗:能帮干嘛不帮呢?大家都需要,因为我能够在海外,得到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杨浪:就是说你不独,对吧?有的人很强干,但他个性很突出,这其实都是好的地方。但是说你是甘愿铺平垫稳了给大家做平台,给大家串连起好多事情,这恐怕也是你做人成功的一个特征。
王苗:我在1992年出任中国旅游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之后,我自己的相机的确是放下了很多,因为我知道我的责任。在1991年、1992年之前我一直不停地跑,大量的人文地理作品都是八九十年代拍摄的。
王苗:2000年之后的,我只有在24小时召集大家一起去拍摄的这些机会上,真正地去走、去拍摄。大量的时间其实用在出版社的管理,以及相关的这些业务上。
杨浪:也就是说2000年之后,你的个人作品的绝对数量开始减少。
王苗:相对的少了很多。

《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画册封面。
走向世界
杨浪:但是也值得,因为进入新世纪,中国国际化开放提速,中国摄影迈向国际化,这里面你的组织作用又是不可替代的。
王苗:我们24小时的画册出了15本,差不多拍摄了20年。
杨浪:也是厚厚的一套。
王苗:一套系统。我们把十年拍摄的东西集结起来,在香港的天际100还办过一个展览,叫“中国大地24小时拍摄10周年”,当时董建华去给我们剪彩。
杨浪:既然都说到这儿来了,那咱们聊聊这些年出的那几本重要画册。
《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系列,我觉得又做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功德无量的用影像记史的事。
王苗:那是,我们觉得图片要经过编辑加工,才能够真正让它传下去,让它起到它应有的一个效果。2008年,时值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使命感驱动我们,就创意说我们编一本改革开放30年的画册,用影像来记录这30年的历史。
当然这也要说到《财经》,有波明的支持,还有博源基金会的支持。当然最重要的支持者还有文澜、延光、刘阳、陈小鲁、秦晓、百家等……
杨浪:还有杨浪同志。
王苗:杨浪同志的文字缺一不可的。
杨浪:这本画册是这套具有环球视野史感的第一本。
王苗:对。
杨浪:讲述中国巨变30年,然后第二本是《中美关系》吧?
王苗:第二本是《百年天安门》。
杨浪:第二本就不提它了,然后是中美……
王苗:《中美关系200年》《中日关系180年》,现在正在编的《中俄关系180年》。哪天你再去看看图片,已经收集很多了。
杨浪:手机面前的朋友们,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就是这几年苗姐和她周围的朋友们,编了一套非常重要的影像记史画册,并且是全球摄影的著作,影像著作。其中的2008年的《见证改革开放30年》,是由香港的牛津出版社出版,并且获得当年的香港图书奖,已经再版N次,是被海内外的摄影界公认的最出色的一本摄影画册。
《中俄关系180年》我到目前看过一些图片,没有看到完整的成品,也是绝对震撼的,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影像记史的著作,这又以苗姐为核心组织的。
那么也就是说在你从个人拍摄、从四月影会,然后作为摄影记者,进入香港,运用《中国旅游》的平台,开始组织中国的摄影家拍那些重大的主题,而这个主题重大到纵着记录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横着记录中国广袤的天地里的故事。
再以时间为单位,启动中国24小时的摄影活动,团结了广泛的“两岸四地”的海内外摄影家,这就是苗姐在过去40多年里面为我们编制的一部中国当代摄影记录。其中有一个为世界所公认的,我特别不喜欢用江湖上的这个词,但又好像只有这个词来定义你——叫“大姐大”。

西藏山南,摄于1985年。
王苗:没有没有,不好意思。
杨浪:因为为这本书的组稿,我跟朋友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王苗和她的朋友们,王苗和她的朋友们,再说一遍,王苗和她的朋友们,说在当代中国摄影界,能够当得起这个位置的只有苗姐。她和一批中国的摄影家,在中国历史上会永远被人记得,并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她沉甸甸的分量。
我最近老说这个话,苗姐肯定都听到过,过去2000年的中国历史多数是文字记载的,最多有个东汉画像砖,再来个敦煌壁画,片断的有影像。但是自有摄影术以来,中国的历史开始有了影像记录,在过去100年以来,中国革命史的一些重大事件虽有影像,但是大多是由外国人记录下来的 。而在过去40年里,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这个壮怀激烈的时代,这段历史是被影像彻彻底底完整地记录了,而记录它们的正是苗姐和她周围的这些朋友们。所以我说,苗姐所代表的其实是这一代中国纪实摄影家们为中国历史做的贡献。
苗姐,这话被我已经拎到这份儿上了,如果你有一两句归纳性的话,你在中国纪实摄影领域,你和你周围的朋友们,你觉得怎么评价自己和他们?
王苗:我觉得如果要评价,还是用你为这本书写在最后的那几句话,我觉得写得太好了。
杨浪:我忘了。
王苗:你忘了?你不能忘。
楊浪:写东西的人写完就忘,反正我说了关于摄影记史之类的意思。
王苗:不是,你写的那几句话太棒了,就是说我们不讲其他,只讲摄影,王苗和她的朋友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躬逢其盛,他们为中国的摄影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是不是?
杨浪:这话该由苗姐说,苗姐和她的朋友们,因为我们躬逢其盛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做了该做的事情,这话很谦虚。
王苗:不是谦虚。
杨浪:你可以谦虚,我从评论家的角度,可以把它再升华一点。
王苗:我们只是记录了,而且应该说感谢那个时代,让我们在那个时代成长。我想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想再拍那个时代的纪实影像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它已经过去了,而我们在那个时代没有缺席,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

陕西延安,摄于1987年。

香港机场三个搞怪的女孩,摄于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