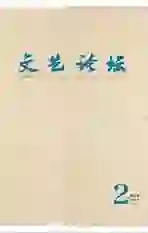论影游融合语境下《想见你》的游戏化叙事
2021-07-20张明浩
摘 要:《想见你》表现出一种游戏化叙事特质:其一,该剧中作为叙事主体的主人公具有“游戏玩家”性质,他们不仅是叙事承载者,更是叙事的生产者;其二,该剧叙事情节设置具有互动性、想象性等游戏特质,在剧集内部的人物互动性设置与剧集外部观众互动探索悬疑情节谜团的行为上都有体现;其三,该剧叙事空间内的工具、场景等都为触发游戏环节打下了基础,具有划分性、体验感、触动性、演变性、期待感等游戏化特质。该剧在颂扬真挚爱情的同时关注边缘人物,具有人文关怀与现实温情,在主题表达方面达到了一种超越游戏的美学效果。
关键词:影游融合;想象力消费;《想见你》;游戏;游戏化叙事
2020年年初,爱情、悬疑、奇幻类电视剧《想见你》在全国引起了观剧、讨论热潮,它不仅突破、颠覆了以往爱情题材类电视剧的创作模式,更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以“想见你”为IP的文化现象,成为当下影视行业的一部现象级电视剧。何种原因促使这个投资较小、无知名明星加持且在开播之初影响力、号召力均表现不佳的剧集高歌猛进?它成功的背后预示着什么?它是否具有可借鉴、可复制的地方?……种种问题之下,本文对《想见你》的成功之道进行探析,以此为今后剧集创作提供借鉴。
毋庸讳言,在当下影视行业中,青少年占据市场的主体,青年文化的潜力是惊人的,在这个“受众为王”的时代,青少年可谓是互联网的一代、游戏的一代。关于“游戏”,David Kelley认为游戏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和达到目标所允许使用的手段;Katie Salen等人认为游戏是一个让玩家进入一个人为的冲突系统,有规则限制,并有可计算的结果;Jesper Juul则提出游戏具有六个特征,即“规则、多样且可计量的结果、赋予可能出现的结果以(不同的)价值、富有挑战性、玩家依赖结果、可协商性结果”。
借此思考,虽然说《想见你》并无直接展现游戏场景或改编自游戏IP,亦或是在剧情中展现“玩游戏”的情节,但是它具有游戏化的风格及游戏特质,达到了影视与游戏的“结合”。首先,剧集中每次主人公在过去与当下之间的穿越都需要“进入游戏的钥匙”,即随身听与歌曲《Last Dance》,这便是游戏“规则”之一;其次,剧集进行到最后时,主人公黄雨萱面临着多样且可计量、可带来不同价值的结果,她依赖于结果改变命运,并且对结果进行了修改;再次,每次主人公穿越到过去后都面临挑战,并且在最后面临着“游戏体”陈韵如与“游戏玩家”黄雨萱的冲突;最后,它不仅具有游戏化特质,而且融爱情、悬疑、奇幻为一身,做到了类型融合与样式突破……所以说,《想见你》的成功离不开其游戏化的总体美学特质,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满足了当下在互联网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受众“想象力消费”的需求。或者说,《想见你》成功的背后预示着“影游融合”类剧集作品与“想象力消费”类剧集作品的巨大市场潜力与文化影响力及受众号召力。
由上可见,《想见你》的游戏化特质与风格多体现在叙事方面。美国传播学者詹金斯曾在21世纪初提出“跨媒介叙事”的概念,在影游融合语境下,“跨媒介叙事”可以形成“既影视、亦游戏”的游戏化叙事美学。此种影游融合叙事模式表现为人物设计、场景设计的游戏奇观化与“游戏线性故事”设置。美国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一书认为叙事主要包含故事和话语两个部分,故事可以分为情节、角色与场景。借如上理论进一步思考,我们也可以从角色、情节、场景等方面对《想见你》的游戏化叙事进行论述,探析其成功的内在奥秘与游戏化特性。
一、具有游戏玩家性质的主人公:叙事承载者与生产者
《想见你》具有角色扮演类游戏的特质。关于“角色扮演类游戏”,苏珊娜·托斯卡曾言,“角色扮演意味着没有剧本的表演,玩家们凭借基本的角色描述,在他们的冒险旅程中表现适当的行为和语言”;马林·C.贝茨则认为,“大型角色扮演类游戏玩家身上呈现出的不仅仅是一种身份,还有演绎和更改这种身份的方法。身份是依照软件本身、網页以及其他玩家提供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虽然在游戏中的表现让玩家可以把身份演绎到一定的程度,但是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导致只有有限的几个玩家—人物能目睹这一表现”。《想见你》中,主人公黄雨萱每次穿越到过去之后,都有一个“客体”陈韵如作为她灵魂的承载者,她不仅需要扮演好“客体”在过去的身份,如照顾家人、上学等,在穿越之后表现出符合那个时代的行为和语言,还在不断地超越着、改变着陈韵如这一原本的游戏客体的行为、心理、性格,此种剧情设置便似乎从整体上体现出了该剧的“角色扮演”类游戏性质。
更进一步来讲,剧集中黄雨萱来回在“现在—过去”之间穿梭,她所穿越回去的“客体”陈韵如(游戏设置的身份)有固定的背景身份特质,如性格内向、母亲嗜酒、父母离婚等,但是当黄雨萱担任“游戏玩家”后,陈韵如这一郁郁寡欢的游戏客体发生了改变,具有了“游戏玩家”的性格和技能,并且在她“扮演陈韵如”时,帮陈韵如赢得了家人、同学的好评,甚至帮陈韵如完成了追李子维的梦想,达到了一种“超越游戏身份设置”的效果。此外,剧集最后,在陈韵如演绎黄雨萱身份的过程中,只有黄雨萱这一人物可以目睹这一表现,也体现出角色扮演类游戏的特质。由上,不断穿越的黄雨萱可谓是角色扮演类游戏的游戏玩家,她穿越后的陈韵如,便是这场“寻找真相”的游戏客体。
主人公的游戏玩家性质还体现在她进入游戏(穿越回过去)的目的上。与以往穿越剧如《步步惊心》中主人公穿越过去的“无目的性”不同,该剧中的主人公是带着“寻找王诠胜,改变小年夜陈韵如自杀”等诉求进入游戏的。此种“游戏线性故事”的设置无疑使该剧呈现出一种游戏化特质:主人公在穿越后,她需要像游戏玩家一样完成任务,闯过关卡(关卡在这里便是阻止陈韵如小年夜自杀)达到一个结果。
主人公游戏玩家的性质亦表现在她在“游戏”中所具有的可操纵性权力方面,即自主选择权与可协商性结果权。一方面,《想见你》中的主人公可以依靠“游戏规则”即用固定的随身听播放固定磁带的歌曲,自主选择进入游戏的时间、自主操控身份表现,而且表现出在现实生活和过去生活(游戏)中共同寻找线索、现实与过去相互交融的双线叙事状态。另一方面,剧集中的主人公可以对游戏结果进行协商与更改,具有可操作性,如故事最后,当黄雨萱发现是自己进入“游戏”才导致陈韵如要自杀后,她选择了摧毁磁带(现实与过去/游戏之间的媒介),改变了结果。
此外,主人公在“游戏循环”中性格、行为的变化也呈现出游戏玩家特质。顾名思义,主人公在多次进入游戏后,会对游戏的规则、游戏的发展、游戏的结果有一定的认识,而主人公也会随之提升自己的技能,在游戏中变得越来越熟练。正如中年李子维对黄雨萱所说到的“我知道每一次循环后的王诠胜都会比上一次更勇敢”,而这个“越来越勇敢”的背后,便是“玩家”在一次次进入游戏、循环游戏、掌握规律后的技能的提升与熟练程度的提升。
值得强调的是,该剧主人公不仅仅是叙事的承载者,更是叙事的推动者与生产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大叙事在向小叙事转变,宏大叙事被无数小叙事取代,小叙事是“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特别喜欢采用的形式”,一个人就是一种叙事,或者说一个人就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同样,在该剧中,一个人或一个主要角色在“游戏循环过程中”会生成不一样的故事,进而达到生产叙事的作用。正如苏珊娜·托斯卡所总结的,角色扮演游戏可以进行叙事生产,不同的游戏玩家可以把完全一致的故事情节通过惊人的、截然不同的方式表演/讲述出来。
在该剧的循环闭环式游戏中,黄雨萱与陈韵如是一条游戏线的两个玩家,陈韵如的身体可以作为游戏角色,当黄雨萱进入此身体后,她生产了相关的叙事,如与李子维相恋、改变家庭现状、调查小年夜的杀人凶手等。而当陈韵如进入客体之后,便开始了原本属于她性格的叙事,如伪装黄雨萱等。以影片“雨中相恋”的桥段为例,当客体是玩家黄雨萱时,她肆意大笑,并且大胆向前,但当客体是玩家陈韵如时,客体则表现得唯唯诺诺、小心翼翼。再如骑摩托桥段、看日出桥段、过生日桥段等,都表现出“一致故事情节但不同讲述方式”的特征。
此外,该剧主人公对于叙事的生产还体现在他通过穿越过去或未来(进入游戏)改变游戏中其他人的思想、行为,进而促使相关叙事相互链接、交融、循环的方面。首先,我们可以对该剧剧情进行线性梳理:1. 2019年的黄雨萱寻找王诠胜,但偶然之间穿越到了1998年客体陈韵如的身体之中,从而启发了或者改变了李子维的思想;2. 在陈韵如死后,李子维因车祸穿越到未来(2010年)的王诠胜身上;3. 穿越之后的李子维(王诠胜),在2011年找到黄雨萱并且与其相恋,并使其刻骨铭心;4. 王诠胜遭遇飞机事故后去世,他里面的灵魂又穿越回车祸的李子维(2003年)身上,并且在2008年阻止好友自杀无果后,一直到2019年寄给黄雨萱CD;5. 黄雨萱因为找王诠胜而收到CD,进而穿越到1998年……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剧集是一个“莫比乌斯环”,而推动叙事、或者说生产叙事的就是主人公黄雨萱和李子维等人,正是他们进入“游戏”,促使了一系列相关故事的出现。所以说,该剧的主人公不仅是叙事的承载者,更是叙事的生产者与推动者,而叙事主体们生产、推动叙事的方式就是“进入游戏”。故,影片的总体基调于此便具有了游戏特征,表达方式也在角色设置方面表现出游戏化叙事的独特魅力。而这似乎也恰好符合马克·柯里所总结的多样化与解构主义的“后现代叙事”特征,叙事变得复杂多样,也不再具有“稳定意义和连贯设计”。
二、情节的游戏化特质:互动性与想象力
亚里士多德曾言“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大卫·波德维尔曾认为情节的成功设计“可以帮助观众对电影故事的建构”。电视剧亦是如此。《想见你》便是在情节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互动性与想象力,主人公与受众都参与到故事之中进行互动,从而呈现出一种游戏化特质。
首先,该剧情节的互动性体现在剧集内部的人物互动上。人物在处理与各种环境及其他人物的关系上会具有选择性,进而促使情节的递进与发展,而《想见你》中的互动性情节可以根据主人公是否在游戏之中(主人公是否穿越)进而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玩家们在游戏中的互动。当黄雨萱(简称游戏玩家A,她与陈韵如共同使用陈韵如的身体,陈韵如可称为游戏玩家B)进入游戏后(穿越后),B可以看到A的所有经历与行为特点、性格特点等,在剧集最后,当B回归到陈韵如身体后,她伪装成A与其他人进行交往,并试图取代A,此情节设置无疑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B在自己的身体里扮演A,化被动为主动,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促使游戏继续进行。如B为使循环继续而故意在日记本上写“他就是王诠胜”,此种由“看客变主体”的行为,具有着一种互动性质的游戏化特征。此外,故事最后,A被困在虚拟房间里时(出现游戏故障时)可以看到B的行为,并且可以与B交流,体现出一种类似游戏之中的玩家互动。如在陈韵如往日记本上写“他就是王诠胜”时,黄雨萱便对其进行了阻止,但她却说“没有这句话,我将不能与李子维相恋”;再如当陈韵如一直靠假装黄雨萱与李子维恋爱时,黄雨萱说到“现在我们应该是找到真凶啊”,但陈韵如却说“我就是黄雨萱”……这种种情节设置不仅充满着想象力,更体现着游戏的互动性——一种游戏玩家与游戏客体的互动也是一种游戏世界中两个游戏玩家的互动。
第二种是玩家们游戏外的互动及玩家与游戏外人物的互动。显然,现实生活中的游戏的互动性是不止于游戏中玩家互动的,更包含着游戏玩家与“客观者”或言游戏外人物的互动。《想见你》便有具有此种互动特质。一方面,表现为玩家们在游戏外的互动。这些互动会改变着游戏进程,促使着情节发生变化。如正是在现实生活中(游戏外)黄雨萱给谢医生表露心声(说出游戏规则)才促使谢医生在掌握规则后穿越到过去,改变了谢医生自己与哥哥的命运,进而导致了诸多悲剧情节的发生,如强奸陈韵如、杀死同学、打伤李子维、小年夜给陈韵如注射药物等等,这些情节的发生起因是二者的互动,也正是在二者不断的互动过程中,真相不断浮现、情节不断推进。另一方面,表现为游戏玩家与游戏外旁观者的互动。在游戏过程中旁观者会具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功能,他们会给玩家以建议,进而促使着玩家改进或升级技能。如具有“上帝视角”的舅舅每次在黃雨萱进入游戏前都会指导黄雨萱,两者的互动促使了剧情的不断发展。
其次,该剧的互动性与想象性还体现在剧外的受众互动与结局调整方面。该剧可谓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探案风”,剧外的受众仿佛真正变成了游戏玩家,在不停寻找真相,进而与剧集产生了高度的互动:他们针对“谁是真凶”“陈韵如为什么在最后假装黄雨萱”等诸多情节进行了互动。但该剧情节不断反转,使受众们一直处于摸索阶段,进而促使着受众不断与剧集产生互动,更促使其情节具有了超越剧集的游戏化特质,即互动性与不确定性——一种受众与受众、受众与情节、受众与结局的互动与结局(游戏结果)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该剧结局的加拍或多结局设置则在另一个角度诠释着该剧“双向互动”式的游戏特性。这就如游戏升级换代一样,当玩家们精熟于游戏规则并且可以预见到游戏结果后,游戏的创造者会对游戏的关卡、角色的皮肤、关卡的走向进行调整,而《想见你》便具有此种游戏化的互动性调整升级特质。
综上,《想见你》的情节似乎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场域,它具有的游戏化互动性特质不仅体现在文本内部主人公(游戏玩家)的互动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文本(游戏)与受众(玩家)之间的二元互动方面,也正是剧集内外的双重互动,推动着剧集的发展与情节走向,使其情节充满了想象力、互动性等游戏化特征,进而奠基了剧集总体游戏特性的美学特征。
三、叙事场景的游戏化:触动性、划分性与体验感
美国学者M.J.波特等人都曾认为“电视场景具有叙事功能”。毋庸讳言,在剧集中,不同的场景会引发不同的叙事内容,场景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促进叙事的作用。游戏中的场景亦是如此。游戏场景本身及游戏场景中的工具等都具有触发性,都为触发游戏环节或推进游戏进程打下基础。除此之外,游戏场景还具有以下几点重要的特性或作用:1. 划分性,它不但可以划分现实与游戏的界限,还可以划分关卡;2. 体验性,它可以通过奇观化、想象性的场景建构,给代入游戏之中的玩家(受众)以视听与心灵上的体验,即一种真实感与超现实感并存的体验;3. 演变性与期待性,游戏场景会跟随玩家关卡的变化而随之变化,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又给玩家以期待感,促使玩家对下一关卡及下一关卡的场景的期待。《想见你》中的场景具有着触发性、划分性等类似游戏场景的特征,进而使其拥有着游戏化的总体美学风格。
游戏场景的触发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不同的场景、同一场景内的不同工具、同一工具所处的不同时间或工具性能的变化都会触动游戏中的关卡或者使玩家产生不一样的游戏体验。《想见你》的叙事场景便具有此种触发性。
剧中随身听与歌曲《Last Dance》是玩家进入游戏的工具,或可谓进入游戏大门的钥匙,它们承担着触发游戏的作用,更承担着连接叙事的作用。它们可以让游戏玩家(主人公)跨媒介、穿越时空,而它们性能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游戏玩家的体验感,如在故事最后,黄雨萱使用坏掉的“游戏钥匙”,被困在了虚拟的房子之中,进而衍生出陈韵如扮演她(即2号玩家扮演1号玩家)的故事线。由此,从“好的随身听可以带主人公正常穿越、坏随身听会导致主人公穿越受阻”的情节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出,游戏工具性能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游戏玩家的游戏进程与游戏体验,更会直接触动到该剧的叙事走向与情节设置。
黄雨萱穿越在1998年的生活空间可以说是她作为游戏玩家所属的游戏空间,这一空间内的场景都可谓游戏场景,主人公进入到每个场景之中都会对游戏有所触动。当黄雨萱进入弟弟房间后,她便触动了“改变弟弟、教育弟弟”这一关卡,进而产生了相应的叙事;当她选择进入篮球场场景,也便意味着她触动了“受其他女性同学妒忌,赢得别人刮目相看”的关卡设置;等等。每一个场景都会给主人公(游戏玩家)以不同的关卡呈现,不同于以往剧集中主人公未知未来的设置,《想见你》中主人公知道自己身份并且扮演陈韵如身份对场景进行选择的设置是具有可控性、主观性、互动性等游戏特征的,而她在选择的过程中也便如玩家一般触动了每个场景所对应的关卡。
在同一游戏场景中往往会隐藏着多种触发关卡的工具,这也是游戏的乐趣所在。主人公触发不同的工具会进入到不同的关卡之中,进而使游戏具有了探索性,也可以保证玩家的新鲜度。陈韵如房间这一个场景便包含着日记本、相片、镜子等多个触发游戏关卡的工具:黄雨萱通过日记本确定李子维的身份,进而促使着之后“寻找之旅”的循环;通过照片确定陈韵如、李子维与莫俊杰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触动了现实与游戏的二元交汇,衍生了之后的种种情节……这与“游戏重启”后玩家回到最初场景探索同一场景中不同玩法的行为相似,也在佐证着该剧叙事场景具有触动性的游戏特质。
《想见你》中的叙事场景还具有划分性的游戏场景特性。一方面,该剧中的场景将现实生活与虚拟游戏进行了划分:整个1998年的叙事场景表现出一种诗意之美、虚幻之美,与2019年的冰冷感形成强烈对比,可以使用受众明确感受到实与虚。而1998年的唯美、虚幻、诗意恰恰也在表示着游戏的性能——一种可以使人从现实生活中解放,在虚拟中感受到美与复归的功能。另一方面,该剧的场景具有划分游戏关卡的作用。随着游戏玩家每次的穿越,游戏场景也随之向前递进,出现新的叙事场景。如在黄雨萱最后穿越时,剧集便出现了海边、日出、操场等新的场景,这预示着关卡的向前推进,也隐含着该剧演变性、期待的游戏属性。最后,场景还具有划分玩家的作用。存在于超现实空间内的小屋子将两个玩家(黄雨萱、陈韵如)划分:屋子里的为客观观看玩家,她可以看到其他玩家在游戏中的行动,甚至可以读取另一玩家的心理;而屋子外的便为游戏玩家,她知道观看玩家的存在,并且用自己的行为推动情节发展。如在黄雨萱最后穿越出现问题而被困屋子的设置中,她成了“局外人”“观看者”,整个房子外的事情就如游戏直播一般在她面前闪过,她可以看见玩家并且读取玩家内心与玩家交流,于此,玩家与玩家的身份被划分,并且推动了相应的叙事。
此外,《想见你》的叙事场景还具有体验感、演变性与期待感等游戏特性。在陈韵如进入游戏后,她在逃课、看日出等多个情节背后的场景中体验到了爱情的美妙,并沉浸于这种感觉,甚至为了让游戏继续而故意在日记本上写下“他就是王诠胜”,以此改变游戏规则,促使游戏循环。同样,受众也在剧集的叙事场景中产生体验之感,唯美的校园场景、复古的街道、淡雅的课堂等诸多场景都在使受众回到校园、回到1998年,沉浸于温馨的叙事场景之中,并于此体验到质朴的青春、爱情、友情、亲情。此外,如前文所述,该剧的叙事场景随着情节而推进、演变,新的情节產生新的场景,受众与主人公都期待新场景、新故事,于此,该剧的演变性与期待感也得以展现。
四、超越游戏的叙事主题:对至情的颂扬与对现实的关照
对于剧集而言,主题是否动人也是影响其成功关键因素。《想见你》便是达到了影游融合的“文化融合”层面,它不仅可以称为一个大型角色扮演类游戏、悬疑推理类游戏,而且表达了“至情”的主题,对现实、对边缘人物也有所关照。
首先,《想见你》以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坚守与执着颂扬了“爱情”的伟大。该剧以女主人公“寻找王诠胜”为起点,爱情贯穿全剧,奠定了该剧的主题基础。该剧开头便表达出女主对去世男主的痴恋,如自己一个人去与王诠胜所经历的所有地方,又如为寻找男友而执于“32”号,甚至坐32号公交车到天黑,等等,都直接的表现出女主对男主的爱,一种时过两年依旧记忆犹新的爱。同时,女主向已故男友不断发讯息的设置,也表现出女主的“至情”:明知对方已经去世,但是还坚持不断地给已故之人发送不会收到回复的短信。在她向天堂喊话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想以此种形式证明男友去世,进而放弃思念,但她又想通过此种形式得到男友回应,进而证明男友在世,此种矛盾的心理与对爱情的执着无不表达着女主的“至情”。此外,这种“至情”还体现在女主不断穿越寻求真相的过程中。女主为寻求真相一次次不惜影响身体、影响工作而进入“游戏”,穿越回1998年;当得知真相后,她还不惧危机再次穿越,以此改变现状……她大胆无畏、勇敢向前的行为都表现出她对爱情的执着、对情感的坚守,更表现出她对男友的“至情至爱”。这种“至情”不光体现在女主对爱情的执着上,还体验在男主对爱情、友情的坚守以及莫俊杰因友情而牺牲等方面:李子维为再见女主而不断选择登上明知要坠毁的飞机、为避免好友去世而一次次回到好友自杀的场地;女主为化解一切危机而选择破坏进入游戏的钥匙;莫俊杰因为拯救陈韵如无果而愧疚自杀;等等。主人公们都通过自己的选择与行为诠释了爱情与友情,也正是这些行为表达了该剧对“至情”的颂扬。
其次,该剧在表达爱情、友情等主题的同时还关照着现实社会中的边缘人物,表达着人文关怀。《想见你》中塑造了陳韵如、王诠胜等多个具有边缘色彩的人物,关注到了现实生活中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不理解的群体。陈韵如代表的是内向、不善言谈、甚至有点抑郁的人群,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表现出“可有可无”“存在感低”等特质,他们不知如何表达自己,更不知如何与人交流。王诠胜本体代表的不仅是抑郁人群,更代表着同性恋群体,他反映着当下同性恋群体的普遍性:他们需要面对家庭、社会、学校等多方面的压力,不但需要得到别人认可,而且还需要自己说服自己。尽管说当下社会包容、兼收、开放,但人们对这一群体的看法还是较为保守的,而且这一群体内部的人也总体表现出一种不自信的特质。或许真正使王诠胜、陈韵如自杀的不止是家庭,还有整个社会的一种偏见与压力,以及对他们这些群体的漠视。而影片也于此为大家立体、全面地展现了边缘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及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呈现出了独特的人文情怀。
此外,该剧还在关注家庭教育、孩童心理、校园生活等方面。该剧从陈韵如的遭遇上强调了家庭环境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从谢医生的变态行为上强调着儿童教育、关注儿童心理健康、注重儿童心理疏导的关键性;从女同学因嫉妒黄雨萱而孤立、暴力黄雨萱的行为中,反思了当下校园暴力问题,更强调了建设安全校园、保护学生心理健康等举措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总之,该剧在奇幻外衣下表达着人文情怀,在游戏设置中表达着至情至信,在悬疑情节中关照着社会生活,关注着边缘人物,更审视着社会问题。
立足当下,国产影视剧在近年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出现了如《微微一笑很倾城》《亲爱的,热爱的》《陪你到世界之巅》等直接展现游戏或游戏题材(如电竞题材)的“影游融合”类作品,它们融爱情、游戏等元素为一身,但似乎也难免落入以“甜宠”“高糖”等为主要情节设置的俗套之中,将游戏变为了一种噱头。《想见你》的出现无疑改变了这一风气,它讲述爱情张弛有度,既没有落入爱情剧的一般套路,又趣味十足,具有现实感、话题性及人文关怀。它以“游戏”为内在创作机制,虽并无直接表现主人公“玩游戏”的场景,但在整个剧集设置上遵循“游戏法制”,人物、情节、场景都具有游戏化特性,使主人公/受众的观赏过程变为了游戏过程,并促使受众在游戏之中感受到男女主人公们对爱情、亲情、友情的坚守执着,颂扬着主人公们的“至情至信”,更关注着现实生活中的边缘人物,反思着孩童心理、家庭教育、校园暴力等社会问题。
《想见你》的成功离不开“网生代”受众们的支撑,表达出网生代受众们的审美趋好与美学选择,即喜好具有想象力、游戏、虚拟等特性的作品,更预示着“想象力消费”类影视作品与“影游融合”类影视作品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影响力与生命活力,进而强调着发展此类作品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当然,《想见你》的成功也为今后影视剧创作尤其是爱情剧创作提供了一条可借鉴之路,即:进行游戏化叙事,设置具有游戏玩家性质的主人公;进行具有互动性、想象力等游戏特性的情节设置,并不断在线下对受众的反馈进行吸收,达到剧内剧外双向互动的效果;设置具有触发性、划分性、体验感、演变性等游戏特质的叙事场景……增加符合当下青年审美趣味的游戏、想象力等设置,走出以往爱情剧偏于固定化的“甜宠”或“唯美”设置,并将视点对焦现实生活、关照小人物或边缘群体、关注社会问题、审视社会现状。在此良性循环之下,国产爱情剧或许将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更具人文意义与历史价值,使当下良莠不齐的爱情剧创作现况有所改善。
无疑,未来将是青年一代的,未来的影视行业也将是青年一代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喜好,想象力、游戏、虚拟便是他们的文化与喜好,而创作“想象力消费”类作品与“影游融合”类作品也将会是未来影视行业的大势所趋。
注释:
据悉,《想见你》每集成本大约35万人民币、主创团队仅60人左右且没有重量级明星加盟,但是它在收官之时获得了豆瓣上近27万观众平均9.2的极高分数。
陈旭光:《新世纪华语电影研究:美学、产业与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5页。
陈旭光:《“受众为王”时代的电影新变观察》,《当代电影》2015年第12期。
Kelley , David:The Art of Reasoning,W.W.Norton &Company,
1988,P.50.
Salen , Katie &Zimmerman , Eric:Rules of Play -Game Design Fundamentals,MIT Press,2003,P.96.
[英]Jesper Juul:《游戏、玩家、世界:对游戏本质的探讨》,《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3期。
影游融合有几种重要的方式:其一,直接IP改编;其二,游戏元素被引入,整个情节和情境的设置就具有游戏的特点;其三,具有广义游戏精神或游戏风格;其四,剧情中展现‘玩游戏的情节,甚至直接以解码游戏的情节驱动电影情节的发展。参见陈旭光:《论互联网时代电影的“想象力消费”》,《当代电影》2020年第1期。
法国学者让-米歇尔·弗罗东曾把“电影与电子游戏的关系归纳为四种形态,即“评述、改编、引用与结合”。参见[法]让-米歇尔·弗罗东:《电影的不纯性——电影和电子游戏》,《世界电影》2005年第6期,第169页。这种划分对于电视剧也同样适用,《想见你》便是达到了影视与游戏的“结合”。
所谓的“想象力消费”,指受众(包括读者、观众、用户、玩家)对于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的艺术欣赏和文化消费。它顺应的是互联网哺育的一代青年人的消費需求。参见笔者近年来撰写的探讨“想象力美学”“想象力消费”,呼唤“想象力消费时代”的文章,如《“后假定美学”的崛起——试论当代影视艺术与文化的一个重要转向》(《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中国电影想象力缺失的批判》(《当代电影》2012年第11期)、《想象力的挑战与中国奇幻类电影的探索》(《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4期)、《中国科幻电影与想象力消费时代登临》(《北京青年报》2019年4月19日)、《中国电影呼唤想象力消费时代》(《南方日报》2019年5月5日)、《类型拓展“、工业美学”分层与“想象力消费”的广阔空间——论<流浪地球>的“电影工业美学”兼与<疯狂外星人>比较》(《民族艺术研究》2019 年第3期)、《论互联网时代电影的“想象力消费”》(《当代电影》2020年第1期)、陈旭光、李雨谏《论影游融合的想象力新美学与想象力消费》(《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陈旭光、张明浩《论电影“想象力消费”的意义、功能及其实现》(《现代传播》2020年第5期),等等。
[美]亨利·詹金斯著,杜永明译:《融合文化: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冲突地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23页。
陈旭光、李黎明:《从<头号玩家>看影游深度融合的电影实践及其审美趋势》,《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7期。
陈亦水:《<哪吒之魔童降世>:国漫复兴语境下中国动画的审美经验创新表达》,《当代动画》2019年第4期。
Ernest Adams:Fundamentals of Game Design(Second Edition),Peachpit Press,2010,p.155.
参见[美]西摩·查特曼著,徐强译:《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美]苏珊娜·托斯卡:《远非私人笑话:角色扮演游戏中的跨媒介戏仿》,《世界电影》2011年第1期。
[美]马林·C.贝茨:《连续世界的连续修辞:论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中自我的易变性》,《世界电影》2010年第2期。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车槿山译:《后现代状况》,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130页。
[英]马克·柯里著,宁一中译:《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第5页。
[古希腊]亚理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David Bordwell:Narration in the Fiction Film,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P.49-51.
[美]M.J.波特、[美]D.L.拉森、[美]A.哈思考克、[美]K.奈利斯:《叙事事件的重新诠释——电视叙事结构分析》,《世界电影》2020年第6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招标课题“影视剧与游戏融合发展及审美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8ZD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