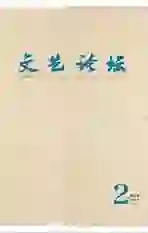论作为“影游融合”基础的“意象—身体”系统
2021-07-20李典峰耿游子民
李典峰 耿游子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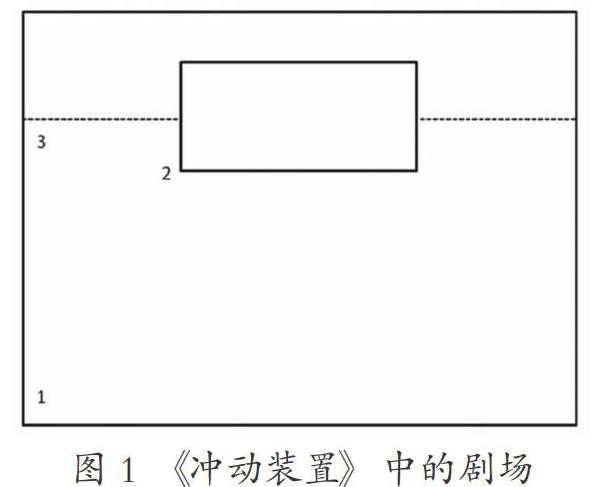
摘 要:电影与电子游戏的生产都需要人工配合计算机技术合成,而人工制作完全基于身体对图像的理解和表达。“影游融合”的出现实际上基于电子游戏的反馈循环融合电影的视听语言,形成一种电子器官以反馈调节机制形成新的“意象—身体”。数字电影与电子游戏通过CGI等数字编码技术逐渐实现从生产方式的融合到控制反馈的融合,这两组概念推进“电影—游戏”的孵化,并以“意象—身体”为基础建构新的活动常态。
关键词:影游融合;意象—身体;控制论
一、导论:“影—游融合”的物质基础
“电影”,若为保罗·维利里奥所说乃视觉的“义肢”,决定其运动的是马达和眼球的协同,那么“电子游戏”,就是想象力的义肢,决定其存在的是数字技术和身体的协同。上世纪80年代后,数字技术全方位介入电影生产领域,它同时摧毁了两个关于电影的物质本体:作为电影(Film)的物质载体——胶片,以及作为电影(movie)的机械马达。
当我们中文使用“电影”来翻译英文的film和法文的Cinema时,其在古代汉语语境中的含义和所指就被现代含义遮蔽了。然而这样又恰巧延续了新“电影”一词所指在中文里使用的寿命。当英文中film所指的胶片已慢慢作古,电影的媒介特性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中文电影的使用语境还相对更为牢固。如今,电子游戏依靠多年对电影技术的吸收,在视知觉体验上越来越接近电影。藉此,我们发现“影游”的融合实际上早在两个媒介诞生之初就已发生。
早期电影曾经被宣统年间的记者翻译为“影戏”,因其屏幕展示的很多手法与“皮影戏”类似。在今天,当我们发现电脑生成图像(Computer-generated imagery)(以下简称“CGI”)技术在创造幻想出来的角色并把它以电影的方式搬上银幕时,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当年对“影戏”一词译法的态度。
游戏和影戏,电子“游艺”和“电活动影”,“电游”和电影,对比这些词汇我们会发现“影—游融合”的基质是一种关于image和人类活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今天看来,是关于我们如何调动自己的身体和影像发生活动的认知结构。
相对滞后于早期电影发展的电子游戏,它的基质——“计算机”则托生于二战对密码机的研究。真正奠定电子游戏触控反馈机制的电子计算机概念则相对更晚。得益于凯瑟琳·海勒对维纳早期的工作的总结性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从“负反馈调节”开始,系统论如何通过控制与传播慢慢融化人与机器的界线。广义的电子游戏在今天对人文学科的贡献似乎并没有它在对军事以及传统数字科学的贡献那样多,也正是因为此,狭义的电子游戏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在今天背负了过多的人文主义论证负担,还需要通过承载传统艺术领域的叙事责任来为自己正名。
电影与电子游戏的融合,正是以作为触控反馈商品的电子游戏主动拥抱电影开始的,后者作为今天承载叙事内容的主流媒介,已经形成了一套全球范围内通行的视听语言。电子游戏作为商品化触控媒介结合传统视听语言,正慢慢孕育新的全感官身体文化产品。“影—游融合”的英文对应词汇“Film-Game Integration”精确定义了这一影像工业未来产品的存在形态,连字符如何让“电影—游戏”诞生以及具体形态如何,也是本文重点讨论的理论基础。
二、融合:控制论对“身体”的重塑
站在后人类主义的角度上,我们今天需要重新理解“身体”这一被建构的历史概念。我们今天是否还能回忆起第一波控制论浪潮之下被反复冲刷的“人”这一概念?这个最令人困扰,最具革命性后果的观念——“人类主体的各种界线不是既定的,而是被建构的”。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大量出现带有器械的游戏,从网球、击剑,到火枪射击,现代人对于“身体”极限比拼的理解已经自然地越过与古代人的界线。我们如何看待身体与球拍或者武器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身体的边界——盲人的拐杖是否是他身体不可被剥夺的一部分?控制论让我们重新审视身体被建构的某种理论边界,并把这种边界通过不同的类比形式慢慢擦除。而电子游戏的出现则建立在一种新的人机羁绊关系之上。当所有人都必须依赖电子设备维持日常生活时,围绕身体建立的游戏规则便自然滑向圍绕“自然身体+电子设备”建立的游戏规则。这便是国家在今天大力宣传电子竞技的初衷之一,因为今天人类对身体的理解,和1894年创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相比,已经不再具有同样轮廓。
二战之后,我们对控制论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认为控制论的系统是由各种信息流所构成。从这些观点看,球拍和运动员处于一个简单系统,球拍向整个比赛系统传达运动员对运动的理解——助听器之于耳背的老人,义肢之于残疾人,电子成像瞄准装置之于无人机系统中地勤控制员亦然。
一旦这种拼接的获得通过,再对这个过程设置概念上的界线判定就变得相当困难。所谓“Cyb-org”,即以连字符为基础拼接两个名词,建立一种新的概念。我们把生物同控制论装置融合在一起,就是为了颠覆人类与机器的区分。同样,“影—游融合”的理论基础,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描述“电影—游戏”正在发生的变化及建立起来的一种临时办法。
控制论对“身体”的重塑基于一个我们日用不知的事实——“正/负反馈调节机制”。我们今天使用的互联网空间也被称作“赛博空间”,这一称谓实际上和一项与互联网诞生息息相关的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维纳在1948年提出的“控制论(cybernetics)”,“cybernetics”其词根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操作之术”。在控制论的理论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是维纳和奥图罗·罗森布卢斯(Arturo Rosenblueth)、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elow)在1943年《行为、目的和目的论》(“Behavior,Purpose,and Teleology”)中提出的“负反馈理论”。反馈理论指的是将系统的输出结果返回到输入端并形成新的输出结果。如果输出端的结果和输入端的输入预期相似,那么系统偏差就会不断增大,形成正反馈;反之,如果输出端的结果和输入端的输入预期相背,那么系统偏差就会不断减小,形成负反馈,进而使得系统趋于稳定。
整个控制反馈都建立在一种可以书写的循环系统之上,这个书写包含对系统规则的书写以及对信息输入的书写。从德里达对“书写”的理解看,书写本身也作为一种身体补充的技术,我们的身体从使用绳线与棍棒开始就以工具作为补充,这也是人开始的地方。所以,“没有天然的原始身体:技术并不是简单地把自己从外部或事后添加为一个外来的身体。或者至少这种外来的或危险的补充‘最初是在‘身体和灵魂的所谓理想的内在性中起作用的”。
电子游戏实际上只是从运动的角度将Thomas Elsasser的“心智电影”从意识游戏层面推进到行为游戏层面,这些过程终究没有脱离“意象—身体”的范畴。电子游戏通过触控装置进行书写活动,这个活动相对电影来说是由身体活动重新编码为数字信息再反馈回到机器中的,“电影—游戏”的出现就是以视觉意象结合触觉活动为基础,重塑整个身体文化工业。
同样的书写机制在游戏活动中也如此。玩家每次操作都会产生相应的反馈,来调整我们对电子影像中的虚拟角色“身体”的理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对于自身运动中行为负反馈调节的一种外化,整个过程就和我们如何训练自己身体保持平衡,以适应球类比赛的机制相似。我们不会要求一个网球运动员不使用网球拍进行运动,以表现自己更强大的运动理解能力,同样我们今天也不会通过驱逐电子产品,来捍卫一个人本主义的“身体”崇拜体系,因为那样只会让个人乃至社会远离必然的全球化和赛博格化。
正如导论中所言,全球化和数码化的大趋势下,电影正在失去自己作为物质基础的“身体”,并将自己的意义通过数字编码的方式寄居到整个网络中。电子游戏则从来没有所谓基质作为身体,它是一种人类游戏活动在新“身体”中的延续。电子游戏只是以数字媒介为基质来为这一概念命名,所以早期的电子游戏(Electronic Game)和今天的电子游戏(Video Game)仍旧会出现在中文语境中的使用场景混淆。而更容易被混淆的一个概念是,我们仍用电子游戏中主题换皮和后期联合宣传这种早期的“影游联动”概念来谈论“影—游融合”。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和工具如此深度地融合在一起,维纳的“赛博格之镜”所照出的他者是每一个当代人自己的主体。
三、重构:“意象—身体”控制系统
理解图像与意象(image)在今天作为装置的关系,需要先对电子游戏中的装置做一个简单的媒介历史梳理,以此来说明为何需要将“电子游戏+玩家”看作一种抽象的装置(dispositif)。从达尼埃尔·阿拉斯的《蜗牛目光》关于图像与圣象(icon)的关系我们看到,那一只蜗牛和文章中四处可见作为“公度”的“木瓜”“苍蝇”等标识物,不只是画家在处理圣像绘画时与图像构成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它同样是一道门,这道门连接着绘画中神圣的象征世界与每一个虔诚信徒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但这道门的位置一定要处于画框的边沿,也就是图像世界的边沿,因为这个边沿位置是另一个更大型的“装置”——教堂——的内部结构。
教堂和圣像绘画通过视觉经验的传递共同作用于信徒的精神,保障了教徒们对教廷权力结构的认同与支持。这便是“装置”在前现代社会运作的一种体现,但是这个时期的图像技术对主体的控制还只是停留在使用可见的“光线”进行视觉信息输入,输入的结果是预期在主体的认识层面形成“天使报喜”的意象,主体对这个意象的反馈体现在身体膜拜等行为。
尽管前现代圣像绘画中显现的神圣世界在现代知识话语中已经不可追溯,但是前现代视觉“装置”的“光线”技术和现代语言“装置”的“发音线”却在出现了电影和电子游戏之后被整合起来。如何将生产、消费和再生产有机结合起来,我们需要给予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大众一个可以持续吸引注意力的“装置”。这个装置它是可以看的,同时又是可以读的,最后它还可以反馈信息,进行控制论的系统循环,如图1这个装置中作为中剧场舞台位置(2号)和观众位置(1号),已经被强大的编码系统封锁并重组。这个系统就是“意识—身体—图像”三层结构组成的电子游戏,当2号的观众和2号的演员变成同一个主体时,整个装置的结构便无法只通过看与被看(或读与被读)的关系来进行区分,只能通过“認识”与“行动”来重新讨论。依靠图像进行意识思考的过程就如中世纪不认识拉丁语的天主教民一样,身体活动所依据的从“图像—意识—意象”变成了一层系统。
这个新的“装置”便是20世纪后出现以电影视听语言构成叙事系统的电子游戏。当代电子游戏中使用大量与这个力比多装置同构的画面结构,形成一个“视听语言+触控反馈”的控制系统。这个系统在不断解码预装的语言程序,同时与人的身体进行连接,让我们的每一个反馈都可以及时传递进入机器,然后机器再将新的“视听语言”作为新反馈输入我们的身体。换句话说,每一次跪拜都会有神的影像与声音传递到信徒的身体。
如果我们需要我们用一个词来描述“影—游融合”这一概念存在的基础领域,我想可以使用“意象—身体”(image-body),因为这个词从第一个名词来看,它描述了电影作为影像媒介从物理层面的图像(picture)到认识层面的意象(image)的抽象化过程;从第二个名词来看,它描述了电子游戏从语言层面的数码编程到现象层面的身体认识的具象化过程。
“意象—身体”这一概念作为主体的同时,也是一个我们用来考察“影—游融合”客观媒介在和主观身体发生融合的系统。围绕着“image”我们会谈论电影和人类想象力如何发生关系,以及它的感觉逻辑。围绕着“body”我们会谈“身体—图示”、游戏活动(Ludens)以及建立在控制论之上“电子人”(Cyber-org)概念在未来文化领域的影响。
首先,在“影—游融合”中观众发生了从艺术欣赏者到艺术创造者的状态突变,这种突变并非观众精神对于文本或者观众自身的“内省”的观照,而是由身体的内在冲力出发,突破“自我”界限的一种努力。这种状态表现为一种收到及时反馈后的“紧张状态,一种构成身体内部力量关系和结构的状态。每一次操作都会带来视听的反馈,艺术创造就处于这样一个临界点,不断地生成并且毁灭,犹如湿婆的舞蹈。
其次,这种力从身体由内而外分层次的爆发运动最鲜明的表现就是“意象”的增生。这是一种高度的“表现力”,一种想要最大限度地“表现”那无限丰富的喷涌而出的意象的努力,而这种状态正是通过“表达者—表達—被表达者”对应“身体—意象—身体”来实现的,这是对尼采“身体—意象”(body-image)这种结构在发生“影—游融合”后的概念重构。因为人体和图像从相互协作到彼此融合,就像电影只有依托于电子游戏才能发生最彻底的“影—游融合”一样,最后以想象力为支撑的意象主宰了身体,并用力线封锁住被融合后的身体形成了新的“身体”。
诸如汉森和德勒兹所指出的,数字媒介正在取代电影的位置成为新一代“影像制造者”,汉森基于本雅明研究提出“神经网络”innervation已经在数字影像时代变成电子计算技术的基础系统。与其说“电影”是一种义肢,不如说它为我们的身体补充了一个额外的器官。通过电影来重现人类活动已经变成一种流行的媒介手段,然而当下,随着娱乐行业和消费主义的盛行,这种拍摄—剪辑—播放—观看的语义传达链已经断裂,在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加入了主观的想象力,并且尽量将它向“可消费的产品”进行拓展。至少大众在影院中观看的电影已经不再关于真实,电影变成了遮蔽技术和制造利润的手段。
当“电影”不以胶片和马达为介质再现客观世界的光影,我们或许会认为它所传达的信息离我们生活越来越远。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商业电影的工业生产逻辑是紧紧跟随着大众消费需求的。虚构的故事,CGI技术呈现的视觉震撼一直表达着观众内心的需求。它不过是再一次依托我们的想象力将幻象从精神世界请出,并用数字电影技术转换为外在视听现实的过程,它紧紧地贴着我们认知经验和想象幻觉的边界。同样,电子游戏还可以让玩家踏入这个边界,甚至用手指隔着机器去触摸这些视听影像与之进行交互。
其实“意象—身体”(image-body)是一个对于正在发生的影像变革的切片式表达。今天,我们丰富的文化现象仍依靠视觉为基础建构,所以我们的想象力和身体经验依然沿着视觉认知的逻辑进行分配。至于未来是否如此,尚未可知。随着对基因信息的解码技术以及神经系统的拓扑结构认识,电影作为以光为介质的媒体或许会被更为基础的神经化学信息所替代。“视听语言”是以光和空气作为介质引发我们身体发生神经反馈,如果直接传递神经反馈所需要的化学递质,那么“意象”最后终将替代“图像”“圣象”“影像”等形而下的媒介,成为承载身体想象力活动最基础的媒介。
对今天“赛博空间”日常化的我们来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传播应该被理解为需要控制,并且控制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传播形式。”将“意象—身体”作为一个控制系统向前推进的基础动力,就是“影—游融合”理论和“电影—游戏”制品研究和研究者之间的反馈回路。不同类型媒介之间的进行结构融合与信息交换,本身就需要不同类型的控制装置间进行连接,这样通过连接部分形成的控制系统,在新结构下发生更多信息交换而形成新系统。实验者、控制装置以及系统界面之间的循环只是这个建构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电影—游戏”既不是电影,也不是电子游戏,它是一种新的媒介类型。
这个建构过程不仅包括控制论系统的机械装置,还包括实验者在控制论模式下构建他们本身以及他们的装置的思维倾向。正如我们所见,维纳的控制论,植根于概然性世界观,而我们的身体理论根植于对“身体”的概然判断。意识到这一观点所产生的一个微妙的结果是,信息不是被当作事物本身而是作为这一领域各元素之间的不同关系而被构成、测量以及传播。传播关乎系统结构之间各部分的关系,而非某种结构“本质”。
这样看来,今天我们建构的“意象—身体”其实类似一个理论上的“黑箱”工程以及“电影—游戏玩家”的身体工程学或者行动反馈循环,这些类比的替换需要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严格的操控。如果没有类比,控制论就无法被建构成一门学科。当类比被用来在控制论话语中选择代理时,它是一种被重点使用的修辞方式,它把传播理解为关系,暗示对这种修辞“系统”是否具有一个本质的问题。类比并非仅仅是语言的装饰品,而且是通过关系建构意义的一种强有力的概念模式。
我们今天反而因为瘟疫的肆虐而看到,实际上客体之间的关系也都是依靠类比被构建的,比如人类政府的系统、人类与自然的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没有一个主控中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所有对这个网络系统输入信息的操作,都会让整个系统产生负反馈调节——比如一个假想的“自由主义政府”崩溃。
维纳早在二战时期就预见到了今天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某些方面。他质疑人类、动物和机器,除了作为在话语和传播领域建构他们的关系网之外,是否真的存在某种“本质性”特征。“无论我们对于在我们的自省和经验以及机械事实背后的‘现实持何种观点,这都是次要的,任何不能被转换成关于可观察物的陈述的命题都是无价值的。”
“意象—身体”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来描述文化产品的消费主体,它既是超前的,又是陈旧的。超前在于它所预言的媒介融合最终样态还没有出现,陈旧在于它来自上一个世纪人们对于媒介样态的基础传播理论。如果有一个电影或者电子游戏共同使用的技术可以有效地描述“影—游融合”理论,我想CGI技术如何生成新媒介的过程可以让我们直观地理解“意象—身体”作为一个控制系统在今天如何有效地进行生产。
四、生成:CGI孵化“电影—游戏”
电影和电子游戏通过两个层面进行具体融合。第一个是技术层面,CGI技术让电子游戏和电影拥有了同样的生产流程;第二个是认识的层面,数字编码系统以我们触觉神经和视觉神经为基础重新在信息层面对图像进行书写。从电影拷贝脱离胶片开始,到电脑特效图像大规模进入电影,电影开始通过数字技术的二进制书写取代传统的胶片光学绘图。早期胶片电影会有大量的图像噪点,这是由于胶片忠实地记录着大自然通过光影进入摄像机的图像。而到了数字编码时代,电影图像优化技术、画面渲染技术的出现,让整个电影通过人工方式添加上各种滤镜和特效。这都是因为电影的去胶片数字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从人工筛选到人工直接生产的过程。影像画面也似乎逐渐呈现了一种距离自然越来越远的感觉,变成某种意象的表达。
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更多如宗教般宏大叙事的所谓“史诗”电影,在这些电影的带领下,电影内容生产默默走向早期吸引力电影的回归之路。然后从1990年代开始,以小岛秀夫为首的一批电子游戏制作人也开始使用电影的视听语言作为交互的基礎,让玩家身体可以通过连接虚拟角色进入画面进行交互。电影从再现走向了表达,电子游戏从语言书写走向了身体交互。
今天,站在“意象—身体”被模糊的边界上,我们看到同产业以及技术结合在一起新文化商品,“影—游”在融合的历史进程中默默打造了今天巍巍壮观的视听触觉文化工业系统。而“影—游融合”的结果就是从视听中心走向以身体为中心打造更多的全感官文化产品,这一融合的阶段性成果就是“电影—游戏”。
当代电影和电子游戏中大量使用的CGI技术就是基于这种视觉图像认知反馈系统之上的开发的“意象—身体”装置。这个装置的出现从多个角度促进今天“电影—游戏”的生产,然而它只是一个实际的技术案例,未来基于对身体研究的技术会越来越全方位地加入文化生产之中,形成越来越多的“意象—身体”装置来装配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身体。
(一)CGI的完整“意象”神话
安德烈·巴赞曾论述过电影与技术的关系,在论述中,他强调“支配电影发明的神话就是实现隐隐约约地左右着19世纪从照相术到留声机的一切机械复现现实技术的神话……如果说,电影在自己的摇篮时期还没有未来‘完整电影的一切特征,这也是出于无奈,只因为它的守护女神在技术上还力不从心”。如果说传统的影视与游戏的分歧在于图形的本质差异与技术的壁垒,那么在CGI普遍应用于电子游戏与电影创作时,其便从技术层面统一了作为“承载想象力的图像”——意象(image)。这时不论游戏还是电影,都成为一组显示在屏幕上的二进制像素数据。从这点看,“电影—游戏”的所指之一,正是统一了一切物质层面意象的CGI数字编码技术。CGI技术或许在一个为图像与幽灵复魅的未来也可以翻译为“Configurable-
Genesis Image”。
1.数字生成意象:游戏的电影化
CGI技术首先推进了电子游戏开发由“游戏学(Ludology)”到“叙事学(Narratology)”的思路转向。正是由于CGI尤其是三维CGI技术的成熟,在游戏中建立模拟现实世界的三维空间成为可能。1997年,史克威尔公司推出的角色扮演游戏《最终幻想7》成为游戏史上第一个使用离线渲染CGI技术的RPG(角色扮演)游戏,其开场动画便是一段处于三维空间,具有明显镜头调度的叙事性画面。1998年,小岛秀夫监督的RPG游戏《合金装备索利德》实现了即时演算的CGI画面,并尝试使用灯光、分镜头等电影拍摄元素。而小岛秀夫的合金装备系列也成为后期互动式电影游戏的渊源。1999年,铃木裕监督的游戏《莎木》成为“沙盒式”RPG雏形,其使用日趋成熟的三维CGI技术打造了一个完整开放式的“虚拟世界”。时至今日,在CGI技术的推动下,大量电子游戏以“电影级画质”为噱头,采用电影化的叙事模式,如以交互电影为制作核心的白金工作室,制作了诸如《暴雨》《超凡双生》《底特律:化身为人》等极度接近电影制作逻辑但仍保留游戏交互性的作品。同样,在2019年底,以“影—游融合”为宣传口号的电子游戏《死亡搁浅》,利用CGI技术建立影视明星面部模型,并使用动作捕捉等技术,实现了电子游戏明星化演出。
总的来说,当代电子游戏的游戏环节+过场动画+游戏环节这一模式,便是CGI技术下“影—游融合”的最好表征。CGI技术的运用直接使电子游戏由早期游戏性为主导的发展,转移到叙事与电影化的轨道上来。
2.意象生成身体:电影的游戏化
无独有偶。在经历了《星球大战》以奇观创作为目标的猎奇时代后,游戏文化对CGI的渗透便通过1982年的《创》(又译《电子争霸》)——第一部计算机动画电影展现出来。而后,2000年基于真人CGI技术的电影《最终幻想:灵魂深处》遭遇票房滑铁卢,但其技术探索影响深远。2005年《最终幻想:圣子降临》再一次将游戏IP电影化,基于《最终幻想7》故事背景的此片,正是对8年前那部伟大作品的脚注。而后,大量游戏IP纷纷搬上银幕,且在拍摄中复用了大量游戏内容,如《生化危机4》中若干打斗桥段,其分镜头完全复制了原游戏CG片段中的分镜,在《最终幻想·王者之剑》CG电影中,大量电影场景建模与游戏《最终幻想15》复用,《头号玩家》不仅包含了大量游戏CGI元素,其基础叙事更是一个典型的游戏化叙述。
另一方面,随着CGI技术的发展,大量电影开始使用面部建模与动作捕捉技术。早在《速度与激情7》中, 便强调以CGI技术还原了保罗·沃克形象,到了《加勒比海盗5》《惊奇队长》和《金刚狼3》中,则分别重建了年轻的约翰尼·德普和萨缪尔·杰克逊,以及年老的休·杰克曼形象。至此,游戏与影视在CGI浪潮的拍打下,褪去了媒介物质性的差异,不会再有“拍不出来的画面”与“无法实现的视觉效果”,意象的边界从客观现实的藩篱挣脱,被迅速扩张到想象力的极限,继而统一了视知觉层面“电影—游戏”。
(二)以“电影—游戏”承载“意象—身体”
在《双子杀手》中,李安利用CGI技术重建威尔·史密斯20岁时的形象,正如开篇所进行的分析,CGI作为一套自生成的图像控制系统,由此生成的威尔·史密斯形象,既不是“现实”中的威尔·史密斯也不是历史中的威尔·史密斯。我们的大脑从未记录过一个4K、120FPS 下的威尔·史密斯,而由于早期的技术限制,我们也无法从历史影像资料中获得一个4K、120FPS下的威尔·史密斯。从这层意义上看,人类共同记忆与物质遗产均没有记录过《双子杀手》中如此“清晰”的青年威尔·史密斯,所以这里,由CGI所展现的“威尔·史密斯”成为一个基于威尔·史密斯身体的想象力表达。
这个想象力表达的过程非常具有控制论的反馈特征。首先电子计算机会基于演员的身体采集数据,建立一个身体空间的数据库。然后计算机图像显示技术会将这个数据库以“模型+数据”的方式呈现一个身体轮廓,再基于后期制作团队的图像工程师们对少年、青年、老年威尔·史密斯的想象,把这个身体轮廓修改成不同参数的具体身体“图像”。最后再以后期制作的方式,把一个“臆想”的身体加入电影中。整个过程其实是《双子杀手》后期工程师们的想象力游戏,游戏形式基于所有的图像技术控制系统,游戏目的就是创造一个视觉上可以接受的年轻身体。当然,这个图像生成游戏目的是否完成,还需要观众来评价。整个反馈过程其实一直在循环、修正、再输入、再循环。实际上,《双子杀手》只是导演李安为了制作他心中最理想的《马尼拉之战》而准备的一次技术试水。或者制作组可以把这些数据库做成可交互的电子游戏,实际上,今天大多数电子游戏得角色创建都用了类似的捏人系统。
总而言之,在CGI技术的指引下,图像生成与游戏活动在意象层面达成统一。巴赞在《摄影摄像的本体论》中曾说,电影艺术的背后,是人类用逼真的临摹物代替外部世界的心理愿望,是保存生命的本能,这种本能是人类对“存真”的渴望,继而形成了“木乃伊情结”。笔者认为,所谓“木乃伊情结”,就是人类渴望构建“真实记忆”,以抵达永恒的情结。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宽银幕到IMAX,再到今天到CGI、4K、120帧,笔者认为,不论电影或是电子游戏,都有一个统一的终极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寻求“永恒”。在CGI技术下,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年龄的“威尔·史密斯”,看到一个《死亡搁浅》中末日悲凉的“美利坚”。在CGI所统一的意象之下,“电影—游戏”拥有了超越“木乃伊情结”的身体,直抵理念世界,将我们身体能承载的意象用数字图像再现出来。
电子游戏经历了从人机对抗到人机协同,视觉工业体系经历从“影游竞争”到“影游联动”。电影与游戏从物质性的二分,到电子游戏系统性整合数字电影,最后融合为“电影—游戏”。
近年来,大量老电影也经历了从胶片储存到数字再版、数字储存、数字修复、数字放映的全数字化再制作的过程。新拍摄的电影除了少数艺术电影还坚持使用胶片之外,大多基本是用数字技术来进行制片。同时期,装配图像显示技术的计算机,开始使用电脑生成图像技术制作电子游戏,并使用电影的视听语言进行叙事。电影去胶片化的过程,以及电子游戏拥抱电影视听语言,让“电影—游戏”基于同一个身体进行融合。而这两者的融合,又是建立在我们的身体如何认识图像的基础上,所有计算机生成的图像背后都有人工对编程参数的调整,对图像后期的修复与润饰,也基于我们身体对世界的理解。换句话说,“电影—游戏”所有的视听语言都是人工语言,所有的人机交互都是控制系统反馈。
整个数字绘图技术是基于“意象—身体”来进行表达的,身体和机器通过控制系统建立连接,通过图像生成来将我们的视觉经验再现。当我们使用“界线”的类比来分割不同概念同时,这条线也在连接着彼此,就像从皮影戏到cinema到电影,最后以“影—游融合”形成“电影—游戏”,甚至一开始回归到它本来被误判的“影戏”。电影和电子游戏一直都是我们身体的外部延伸,它是一个与我们身体认知反馈系统同构的控制系统。当一切从影像借助视觉神经分解为化学信号之后,它才能上升到意象并被我们认识,这个过程就是图像被身体解码为信息的过程。电子游戏则借助数字编码技术,重新让这个想象力拥有可以触碰的物质载体,它通过电影视听语言配合触控输入装置生成“电影—游戏”。
“电影—游戏”甚至可能只是我们阶段性通过外部媒介理解“赛博格”(电子—器官cyb-org)的第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走向后人类模式的文化工业制成品被补充进我们更大的“身体”之中。
注释:
[法]保罗·维希留著,杨凯麟译:《消失的美学》,河南大学出版社,第149页。
天津《大公报》1905年6月16日所载题为《活动电光影戏出售》的广告为据,曰:“兹由外洋运到新式电影机器一副,并影片……。”
李铭:《电影一词的由来》,《现代电影技术》2015年第二版。
二战早期的电子计算机原型是图灵机,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机器,它有一条无限长的纸带,纸带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方格,每个方格有不同的颜色。有一个机器头在纸带上移来移去。机器头有一组内部状态,还有一些固定的程序。
[美]N.凯瑟琳·海勒著,刘宇清译:《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页、第111页、第124页。
陈旭光、李雨谏:《论影游融合的想象力新美学与想象力消费》,《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年1月 第37卷第1期。
[美]托马斯·埃尔赛瑟著,尹乐、陈剑青译:《心智游戏电影》,原载《谜题电影 :当代电影中的复杂叙事》 (《Puzzle Films: Complex Storytelling in Contemporary Cinema Edited》),沃伦·巴克兰( Warren Buckland)编,[英]布莱克威尔出版社(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9 年版。
Nietzsche, Friedrich, On Truth and Lies in a Nonmoral Sense. “Philosophy and Truth Selections from Nietzsches Notebooks of the Early 1870s”. Ed. and trans. Daniel Breazeale. published by Atlantic Highlands ,转引自姜宇辉:《德勒兹身体美学》,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9页。
[法]德勒兹著,汪民安译:《什么是dispositif?》选自《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第198页。
[法]达尼埃尔·阿拉斯著,何蒨译,董强审校:《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一部别样的绘画描述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30页。
[法]利奥塔著,李洋、于昌民译:《反电影》,选自《宽忍的灰色黎明》,2014年版,第342—343页。“因此,场面调度也在两个区域之间设定了再现或替代的关系,它必然出现场景现实的贬值,因为它只能是现实之现实的代表”。
[法]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le schema corporel)和德勒茲的图示Diagramma,“无器官身体”概念的论述这种“图式”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翻译为“图画”Picture ,在康德那里称为Schema。
[法]吉尔·德勒兹著,谢强、蔡若明、马月译:《电影2:时间—影像》,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21页。
[美]诺伯特·维纳:《观察者的作用》《“The Role of the Observer”》,刊于《科学哲学3》(《Philosophy of Science3》),1936年,第311页。
*本文系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影视剧与游戏融合发展及审美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8ZD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