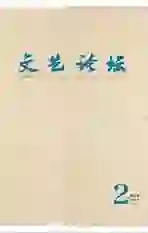当代文学史料的基础与限度
2021-07-20魏华莹
魏华莹
摘 要: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层面成绩显著,但也面临着具体研究成果跟进不足的问题。文章结合写作实践,从史料研究的基础和限度出发,讨论史料发掘的可能性与客观性,及通过新材料的发现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提升与深化,形成史料与文学史叙述的有效互动。
关键词:文学;史料;基础;限度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规范化,近年来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从方法论和实践层面推动研究。关于当代文学史料的会议和学术文章越来越多,专家学者也在不断查找问题,完善研究范式,如洪子诚突出“材料的差异性”及“众声喧哗的互证”,程光炜“抢救当代文学史料”意识及当代文学史“下沉期”的界定,吴俊“从专业学术、社会发展现状、国家政治、网络技术”的多重探讨,杨早重视“氛围性史料”的研究与使用,王秀涛讨论“当代文学史料的等级问题”,付祥喜提出的应警惕史料“窄化”问题,等等。有学者认为这是1990年代以来强调学术规范与学科建设的结果,从而让史料的发掘与呈现逐步建立起有序的、有效的过程。
近年来,笔者一直在跟随师辈做当代文学史料的研究,也在反省学界聚焦和自己遇到的种种问题。关于史料研究的合法性、方法论已提出很多,但一些具体工作仍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笔者尝试结合个体研究,就当代文学史料的基础与限度问题,谈谈浅显的认识。
其一,史料的基础问题。
许多学者多注重史料的基础工作,包括大型工具性与专题性研究史料的编撰和出版,近年来成果丰硕,如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丛书》,吴俊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程光炜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丁帆、朱晓进主编《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程光炜、吴圣刚主编《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等等,基本涵盖了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展现大量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还有当代作家的年谱写作,较为集中推出的《东吴学术》系列栏目,已经成为该刊的标识。选择的作家,多有充分的创作实绩来支撑年谱的写作。年谱的简编能够勾勒出作家基本的人生图景,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但存在的问题普遍是对作家童年、少年时期进行细密考证,不少还做了口述史,写得较为鲜活和有趣,但中年之后,随着作家声望日隆,更多成为作品年表和个人活动史,不免显得生硬、机械。虽然有“尊者讳”的成因在,但研究者史料和史观有待加强也是不争的事实。有些作家重要作品的考证也存在问题,如《毕飞宇文学年谱》中对于茅盾文学奖作品《推拿》的创作成因书写,与作家多次的创作谈出入较大,缺乏客观的考证。王尧曾指出,相关作家与文学思潮、文学事件的叙述显得单薄。在年谱中,作家是鲜明的,时代是薄弱的。
程光炜曾提出相较文学制度、会议研究,具体的作家、作品史料研究还显薄弱。近年来,他率先垂范,对莫言、路遥、贾平凹的作家作品考证,以及“干校系列”的研究等等,都是如此。作为学生,我们在后面紧追慢赶,节奏也没有完全踏对。前几年,程老师还经常会给大家发几篇主题为“好文一读”的学术文章,某大年初一早上我收到邮件还很激动,但老师也逐渐加强对我们的“同情”和“理解”。好在他自己一直扩大再生产,刷新着学术研究新视界。包括他对于路遥招工、兄弟失和、与林虹关系问题的材料发掘,在路遥的史料研究公认较为扎实和丰厚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更显敏锐和可贵。
我个人准备在写《贾平凹研究史》的时候,发现这位和新时期文学史紧密联系的作家,从1978年第一篇评论文章开始,40余年来一直与文学批评缠绕在一起;对贾平凹的研究史呈现出批评家和作家共同成长的特征,也可以发现当代批评在不同年代的方法、路径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但具体到史料研究仍很匮乏,到现在,很多还是借用贾平凹作品中的前言与后记自述,以及新作问世之初媒体记者的采访,进入学术层面的并不多,可能与作家旺盛的生产力有关。孙见喜一直做贾平凹史料的追踪研究,从1980年代就开始写传记,多年来持续在更新、接续。去年夏天,他专程到河南某縣寻访《带灯》的原型——一位女基层工作者,因对方扶贫还等了两天才得以相见。据悉,两人交谈甚欢,互赠诗画,还拍了一些仅供内部参考的照片。人物原型很是低调,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是第一次和文学圈内人讨论该作,是很大气、爽朗之人,和书中描述的有出入,和我们想象的诗性也有差异。但也有材料披露有批评家见过原型给贾平凹发的信息,优美且充满诗情。多重讲述与考证也丰富了作品研究,在序跋之外多了旁证,也许以后会成为打开这部作品的符码。孙见喜作为传记写作者一直坚持去现场查证材料,这使我想起程光炜所强调的田野调查,在开掘式的基础上才能够深入研究。这也是很多书斋里的学者需要补课的环节。如果没有孙见喜从1980年代以来持续的收集、跟进,现在的贾平凹研究会少了很多基础性的依据。
其二,史料的限度问题。
不同学者就当代文学研究的材料使用,提出很多问题,如阐释和提炼不足,有与事实出入过大的“孤证”问题,还有重文献、轻实物和口述史料的问题等,都是制约研究有效性的多重因素。我曾写过《废都》的系列文章,缘于程老师讲《废都》是座富矿,被视为知识分子大分野的标志性事件,我就想重新清理历史,在整理与研究中逐渐发现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以及该事件如何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结。2020年贾平凹本该出版的长篇小说《酱豆》,是“贾平凹”写《废都》的故事,虽因种种原因现在还没有面世,也说明作家本人在尝试解开这个心结。
其间,我倒是做了很多口述史,拜访田珍颖、费秉勋、贾平凹、孙见喜、韩鲁华等亲历者,他们对于《废都》事件做了很多的细节讲述,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帮助我打下了学术研究的基础。这个过程很愉悦,我在亲历者的讲述中彷佛回到历史现场,多重讲述可以较为客观地呈现问题,而且能够使我吸收多方面的知识。我知道田珍颖、费秉勋1990年代初都是“神秘文化学会”的骨干力量,费老师更是通天地精神的易学大师,在交谈中我很是感佩他的智慧,很想请他帮我看看且透露些玄妙的天机,但担心损耗先生内力,搁置了。
后来在长春参加《文艺争鸣》当代文学史料会议时,丁帆老师在会议茶歇时找到我,讲述他所经历的《废都》事件,很多细节让我获得新的历史认知。丁帆和贾平凹在1980年代作为批评家和作家就有良好互动,他对贾的创作很熟悉,并且是1990年代《废都》事件的在场者,他的讲述又提供了另外的角度,让我很是感动。还有学者跟我讲北京出版社相关同仁也有话要说……我才意识到《废都》仍是一个无穷尽的问题,既有的史料收集虽然还原了当时的批判话语、创作周边和大的文学场,但对知识分子内在的、表象之外具体心理状况的发掘,席卷整个知识界的众多参与力量,甚至“市场经济时代”突然到来时围绕一本书与市场的整体关系,当事人秉持的不同话语立场,等等,还有很多史料亟待收集、整理和深入研究。
在程老师的鼓励下,我还写了“二王之争”“顾准热”的文章。在读那些慷慨激昂的论辩文章中,我渐渐明白真诚捍卫人文精神和自由讨论公共话题的可贵。之后,人文知识分子经历了从广场到书斋的身份转向,迄今用近20年的时间退而结网,积沙成塔,回到学术的本心,多年的耕耘也逐渐确立起各自的学术根据地。后来,在一次厦门的学术会议上见到王彬彬老师,之后的游船活动时就端端正正坐在我对面,谈不上严肃,面色平静安详,但就是不说话,我很想请他讲讲当年“二王之争”时的风采,但没好意思,也担心旧事重提惹人不快。毕竟,王老师近年来围绕高晓声研究等做了大量史料工作。当时,同行的接待方很是厚道,带领我们驶向离台湾最近的岛屿,大家的心情都被浪花美景激荡,还要提防周围隐蔽的炮台,在家国情怀、人身安全面前,“再回首”有些不合时宜,于是搁置了,我内心还挺遗憾。这也使我意识到既有的研究仍是未尽的话题,也会随着材料的不断更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整体来说,基础和限度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体两翼,基础决定了地基的深度,限度决定搭建的高度。当代文学史料仍存在巨大的研究空间,不断挖掘、补充材料才能带来学术新发现,不断更新的发现亦会使得史料研究一直在路上。这也促使我们始终保持开放性心态,不断为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制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提供补充或改写的史料。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