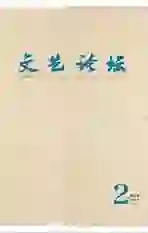《黄河东流去》创作考论
2021-07-20魏华莹
魏华莹
摘 要:《黄河东流去》是李准的茅盾文学奖作品,也是其经历新时期初《大河奔流》批评的压抑,重回农民问题的长篇巨制。文章通过考证创作过程,发现李准的写作与家史、地方史、民族史的关系,作为跨界作家和剧作家在不同文体间的吸收与借鉴,从而摆脱既有“跟政策”的批评范式,发现其如何通过不断地纠正写作方式,创作出符合不同时期文学规范的作品。
关键词:《黄河东流去》;家史;文学新人;文学改写
李准被认为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为政治服务最有成绩的作家”,1953年凭借《不能走那条路》成名,后在电影剧本、小说领域取得诸多成绩,《老兵新传》《龙马精神》《李双双》引起全国范围的轰动。“文革”后的复出之路却颇费周折,《大河奔流》经过反复修改作为1979年国庆重点献礼片,上映之后遭到诸多批评。根据《大河奔流》改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写作长期陷入困顿,上下卷的出版间隔五年之久,但还是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既有的研究多从大的历史场域考察其与“十七年”文学的转折和延续,以及新时期的复出之路等问题。本文尝试从创作本源出发,通过梳理《黄河东流去》的写作过程,发现李准的创作与个人史、地方史、民族史的关系,作为跨界作家和剧作家在不同文体间的吸收与借鉴,以及摆脱“跟政策”的批评范式,发现其对于读者接受的重视,以及如何通过不断地纠正自我写作方式,创作出符合不同时期文学规范的作品。
一、家史、村戏与《黄水传》
《黄河东流去》的写作最初动机是李准对河南黄泛区历史的熟悉。193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为阻止日本军队西进,采用“以水代兵”策略,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人为造成5.4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洪水淹没冲毁村庄3000余座,房屋数百万间,死亡民众达89万人,逃离家园达391万人,受灾人数超过1200万。至1947年堵口成功,黄河泛滥长达8年9个月,为亘古未有之人间惨剧。
李准与黄泛区难民的交集发生在1941年。因河南大旱,家境陷入贫困,读了一年初中的李准被迫辍学。13岁的他和本村几个小伙伴一起随难民步行赴西安投奔表叔,准备报考当时的国立五中。从洛阳启程,背着行李,带着干粮,挤上西去的火车。在陇海线上,李准看到从黄泛区逃出来的成千上万的难民推着小车,挑着坡筐,挎着篮子,形成一条饥饿的走廊。到处是乞丐,到处是饿死的难民尸体。他曾看到一位青年妇女,为了救活将要饿死的丈夫,自卖自身,换一点粮食给丈夫吃。临走还脱掉布衫,换了两个烧饼塞到丈夫手里。当时是李准第一次离开家,因中途没有扒上火车,和同行的四位同学失散,被留在站台上,拖着4人行李,被大雨淋透,夜间站在一个席棚下避雨,还被索要五角钱。当天夜里,李准长大了许多。第二天黎明雨停了,李准看到地上不少死尸。他向几位刚下车的逃难叔伯诉说遭遇,他们帮他挤上火车,还把4个行李递给他。到西安后,报考国立中学未遂,在西安度过近半年的流浪生涯,于秋天返回家乡。这段触目惊心的经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还谈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1949年,李准作为农村银行信贷员,到黄泛区为返乡农民发放麦种和农具,看到很多惨不忍睹的情景。有个村子在黄河决口中死绝的有28户,被黄水淹死和因旱灾饿死的有208人,还有72人找不到下落。在一所倒塌的茅屋里,一家大小5口人的骨骸堆在一起。这些历史记忆都刻在李准的心里,部分情景写入《黄河东流去》。
1969年“文革”期间,李准“被打倒”,下放到黄泛区西华县屈庄“劳动改造”。村民知道他是文化人,熟悉之后,就有人来找他写祭文。最初是所在屈庄的两兄弟要求为大哥写祭文,说大哥一辈子受苦,把两个弟弟带大,自己没有娶媳妇,却分别给弟弟娶了媳妇。大弟弟曾被抓壮丁,从军队逃回来又被抓住,按照规定,逃兵是要被枪毙的。大哥听到消息,愿意去替弟弟死,说弟弟家里老婆孩子一堆人,自己光棍没有负担,就带着钱走了门路,将弟弟换回来。后来人家出于同情,也没有枪毙他。李准听了很受感动,就把祭文写得很有感情,开追悼会那天很多人都哭了。还有村东头一位老贫农的祭文。他逃荒到陕西后,靠宰牛生活,每天把一大锅牛肉汤分给逃荒去的同乡们喝,就这样救活了100多口人。自己一辈子没有讨过老婆,却操持着三个兄弟都成了家。有个小弟弟,被他娘卖出去两次,他追去抱回两次。有一次,他找了三天,才发现弟弟的印花布小棉裤搭在一家门外绳子上晒着,就这样找到了弟弟。李准把这些事写成悼词,主持人在会上一念,很多人都哭了。以后就传出去了,都知道有个写祭文的老李。从此,三里五村不断有人找他,陆续写了几十篇,都是一部部真实感人的难民家史。
李准搬到前高大队后,村里住着一位叫留建的人,在业余剧团演过戏,在当地小有名气。当时只有几个样板戏,群众都不愿意看了。留建多年不演戏,也想唱,就鼓动李准写部戏,在村子里演。大队支书也支持他写戏。李准心有忌惮,就在大儿子的帮助下写出《榆树记》。“主角是个老太太,她孩子是生产队长,撂挑子不干,她忆苦思甜,教育儿子。”戏排好后,大年初一正式演出,村里还搭个台子,演出很成功。外大队的也请着去演出,一直唱到十五之后。《榆树记》被认为是李准创作《大河奔流》的雏形。
李准1973年“解放”后,被允许回到郑州写作。次年开始创作《大河奔流》,曾到黄泛区的通许县、中牟县、淮阳县、郑州花园口公社,收集的家史不下200家,但一直找不到写作方向,还沿黄河到济南,搜集黄河两岸人民的生活和地方风情等资料,后又到烟台、威海等地采访。为了搜集“花园口决堤”时河南逃荒难民情况,还曾赴武汉、四川、西安、咸阳、延安等地。1975年完成剧本《大河奔流》的写作。
剧本重点突出了李麥的形象,人物原型集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母亲和日常接触的陈大娘等为一体。杜凤瑞是河南方城县人,曾任云南剿匪司令员,1958年和台湾国民党空军激战时不幸牺牲,年仅25岁。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母亲作报告时,李准被打动,随即采访了她。他还曾在灵宝县发现一个老太太,丈夫是个卖豆腐的,为了十八亩地,跟地主打了一辈子官司,第三年打到了南京。李准跟她谈了三天三夜。
提及李准的黄泛区历史书写《大河奔流》与《黄河东流去》,不能忽略新中国河南第一部长篇小说《黄水传》,作者冯金堂是扶沟县崔桥镇人。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后,他靠撑船摆渡为生,后逃荒到陕西黄龙山,在外流浪八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水回归故道,才重返故里拓荒种地。冯金堂能说会唱,曾是村业余剧团的骨干分子,解放后在《翻身文艺》《人民文学艺》《长江文艺》等发表多篇作品。1957年至1959年,他以黄泛区为题材,写出了35万字的长篇小说《黄水传》,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黄水传》采用话本小说的形式,描写了黄泛区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三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画面。
早在1954年4月,冯金堂参加了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到因写《不能走那条路》而闻名全国的李准,二人成为好友。1959年初,30多万字的《黄水传》终于写出来。“为了出版此书,他根据出版社的意见,来到北京进行修改,恰巧和李准住在一起。李准在写稿改稿之余,第一个读了《黄水传》,对作品内容和表现手法都极为欣赏,同时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冯金堂“在李准帮助下将作品润色后交给了编辑部。1959年底,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黄水传》正式出版”。小说塑造了武强、黑妮、二怪、油锤等人物形象,是最早反映黄泛区历史的文学作品,为黄泛区人们谱写了家史。贺敬之专程从北京来到扶沟,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宣布接收冯金堂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冯金堂、李准是黄泛区灾民的亲历者,李准少年时期的逃难经历、冯金堂多年作为灾民的流浪生涯使得他们对这段惨痛历史有着深刻的记忆。文学书写多以个人经历为主,虽然笔法不同,但都能做到真切感人。即便李准创作于“文革”时期的《大河奔流》,不免于“三突出”痕迹,作者对于人物、故事亦是信心满满。按照历史学家的研究,“若是兼顾了幸存者的声音、他们对往事进行的文学形式的构建以及他们对自己经历的解释,我们恰恰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他们当时的反应和行为。如果我们懂得幸存者自己的回忆和叙述对他们的生活曾经起过何种作用,我们就还能看到,他们对经历和历史的不断叙述加工,本身就是历史现实的一部分”。《黄水传》以章回体小说形式,为黄河立传。《大河奔流》以电影形式,塑造李麦的英雄形象,突出新旧社会黄河岸边翻天覆地的变化。《黄河东流去》回归民间书写,讲述七户人家的流浪史,其中春义打算到黄龙山开荒种地本身就带有冯金堂逃难经历的影子。他们既讲述了黄河带来的民族苦难史,也写出了黄河孕育出的生生不息、倔强坚韧的民族品格。
二、剧本、影片与小说
1974年李准写出17万字的《大河奔流》初稿,让一些同志和朋友看了看,都说:“还是不拿出来好。因为你这个和现在流行的作品不一样!”他又拿到北京,得到谢铁骊、田方、崔嵬和很多老同志的热情肯定,而且主张拍宽银幕上下集。谢铁骊、赵丹建议李准把原稿中说教的部分全部删掉,修改本只剩下十万字左右。一方面是因为电影的长度限制,另一方面就是原稿中有不少败笔。如曾有李麦在黄泛区打游击、支援淮海战役的情节,写得比较概念,谢铁骊让删去了。赵丹初读《大河奔流》剧本时批评李准:“套话太多!”水华讲得更具体:“剧本中的黄河决口、逃荒、农民相互间的阶级感情、对土地的感情,以至于解放后重建家园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等情节,你都达到一个水平了。但是写黄泛区打游击、土改等情节,还没有超过‘文化大革命前一些作品的描写。”这些章节也都删掉了。崔嵬曾告诉李准,他不喜欢“金谷酒家”中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星文斗争的那几场戏。他说:“不是你的风格。”“我当时还舍不得去掉,总觉得有戏剧性。”“后来曹禺同志把剧本看了三遍,说:‘从整个剧本看,是他创作中一个高峰。就是‘金谷酒家那几节戏有点跳出他的风格。”在谢铁骊的建议下,李准还采访了黄委会主任等,在下集中增加了毛泽东、周恩来视察黄河的场景,也是新中国影片中第一次出现领袖形象。
《大河奔流》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问世的第一部电影剧作和影片,由谢铁骊、陈怀皑联合执导,张瑞芳、王心刚、陈强、张金玲主演,又是出自久负盛名的李准之手,业界给予很高的期望。作为国庆30周年献礼片,1979年春节隆重推出。影片在投映前就被宣扬得沸沸扬扬,电影界也试图借该片打翻身仗,激活创作空气。电影宣传海报为滔滔洪水与李麦的形象照。李麦表情肃穆庄严,眼神果敢刚毅,与背景中黄河肆虐奔流的情景互相呼应,展现出“不管惊涛骇浪,我自岿然不动”的非凡气势。
《大众电影》1979年复刊后的第一期封面就是《大河奔流》的剧照,选取的是游击队员天亮和未婚妻梁晴的剧照,还以大量篇幅刊载《一曲黄河儿女的颂歌——赞影片《<大河奔流>》,指出“是部史诗式的影片”,“是电影创作拨乱反正的新成果”。但在開始放映时,却门庭冷落。“据有关材料显示,其中一次放映,700多张票只卖出了300多张,作为一部全国重点影片,在电影仍是全民热点的时期(1979年的观众人次,是中国电影史上观众人次之最),这是十分罕见的。”在放映期间,“《大河奔流》的观众并不那么踊跃,而《三笑》的售票窗口却经常长龙一条”。《三笑》是香港影片,取材于唐伯虎点秋香的才子佳人老旧故事,但娱乐性强,影片中的民歌、小曲对于长期只能听到进行曲的观众来说,也很别致。这也反映出刚从“文革”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人们对轻松娱乐的渴望,以及对刻板说教的反感。
很快,专业评论界出现大量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大众电影》1979年4期发表多篇讨论文章,包括《影片评论要实事求是》质疑《大河奔流》作为国庆30周年献礼的重点电影,在拍摄前后,报纸和杂志一再宣传,给予极高的评价,但看了影片之后,却不免失望。李麦“非常突出”,是一位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群众领袖”,一大群黄泛区的群众靠她来保护和教导,她能在一个又一个关键时刻“扭转乾坤”。不客气地说,她很像前些年电影中出现的“一号英雄”,根本谈不上“完全跳出了‘四人帮创作的模式”。《人为的痕迹》认为影片虚假造作,缺乏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宋敏临终前能说那么多话吗?!》指出诸多细节不真实。《有些场景不真实》质疑影片不自然、不合情理,“三突出”的痕迹仍然存在。更多批评集中在李麦形象“给人半神半凡的感觉”。
也有评介杂志刊出群众来信,指出《大河奔流》拍这样的长片,国家投资大,效果不好,上座率低,得不偿失,“劳民伤财”!有的观众觉得是“看了部纪录片,不叫艺术片。没有享受到美的艺术,作家没有掌握适当的表现形式,未引起观众的共鸣,电影技巧运用得不好,形象语言不够,特别是李麦”。
这些批评意见李准始料未及,也给他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被问及如何评价在改革开放之前所写的作品,李准说:
很惭愧,很内疚,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打倒“四人帮”后也没有意识到,当时还为自己以前的作品沾沾自喜,自以为是。到了1979年春天,《大河奔流》这部电影的失败,才使我感到震惊,冷静下来,在痛苦之中反思,否定自己。我才真正意识到,《大河奔流》仍未擺脱“高大全”“三突出”的阴影,仍然沿袭了“样板戏”的创作原则,把真实的人物夸大了,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公式化了。所以啊!千万不能人为去拔高或压低小说人物,生活里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这一次彻底的反思,我可能就完了。正是因为否定得好,我才跳出了老框框,才写出了《黄河东流去》。
对197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上卷,李准做出了重大修改。“电影剧本《大河奔流》只是着重写了李麦一家人的命运,小说写了七家。几乎有四分之三的情节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我在创作上作了一些探索。”那就是“生活里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绝不再拔高或故意压低人物了。”
新时期“跟政策”的批评,对其作品的全部否定,也给李准带来很大的压力。毕竟,李准的名字是跟“十七年”文艺创作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以擅长描写农村斗争生活”的作家,新时期之后,由于评价标准不同,他的作品受到了批评和否定。因此,他对自己的创作又有了另一种总结。他说“人没死,作品已经死了,或者上半年写的,下半年就死了”,并一再检讨自己“是一个不成材的作家”,“愧对人民,第一、十年没给人民干活儿,没写一个字;第二、三十年来写了不少作品,有生命力的不多;第三、《大河奔流》写得不及格”。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河东流去》的上卷情节有了大量改动。电影剧本开篇就是“黄河滚滚奔流的雄姿”,“民族的摇篮”。小说开篇先是推出世界上伟大的河流,亚马孙河、尼罗河、密西西比河、湄公河、伏尔加河、多瑙河、泰晤士河,然后介绍中国的大江大河,再引入黄河是“祖国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人民勤劳勇敢性格的象征”。剧本重点突出李麦的英雄气质,以及领袖对黄泛区的重视,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小说则淡化政治色彩,重点写出七户人家的悲欢离合。李麦则从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成为一个朴实、热情、能干、吃过大苦、见过世面的农村女性形象。
广受称道的是小说中塑造的徐秋斋形象,作为底层农村知识分子,集中代表了中原农民狡黠的“侉气”。他懂药理,识阴阳,机智勇敢。他替王跑把被抢的驴子按价码要回来,对方感激他,给了5块钱,他只收了一块钱喝羊肉汤。在西安的破茅草屋中,他教育梁晴:“我们人穷义不穷……什么叫良心?良心就是一个人的德行,一个人的胆气,一个人的脖筋和脊梁骨,人有良心就活得仗义,活得痛快,什么都不怕,他没有亏心!”回到故土后,编着“感谢故乡土,除病又消灾”的快板,仰望星月,安然入睡。此外,小说还有长松、海老清、蓝五、王跑、春义、凤英、陈柱子、四圈、雪梅、爱爱等人物形象,写出了农民群像,且极具个性化色彩。
小说还注重描写中原风土人情。即便在灾荒面前,还有诗意的乡村风景,以及吹唢呐的蓝五的浪漫爱情。如“九尽春来”,“杨花落地了,杏花开放了”,“黄河水淹没过的荒村野摊上,土地开始变得松软起来”,“这里成了芦苇的世界。它占据了几乎所有的荒水野滩。偶尔有几株红蓼和青蒿,长在破落的荒村断垣残壁下,把这些荒村点缀得更加荒芜、凄凉”。蓝五有几出拿手好戏——《秦香莲》《二进宫》《对花枪》《穆桂英挂帅》。正是在一次白事上吹河南坠子《林冲发配》,吸引了雪梅——“蓝五那悲愤的表情,男性粗犷豪壮的声气,使这个少妇完全沉浸在八百年前的开封街头,她好像看见那个披枷带锁的落魄英雄林冲在仰天长叹”。唢呐声也吹进了雪梅的心里,引出了之后的私奔和爱情悲剧。剧本中革命加爱情的写作让位于民间并不合伦理的朴素情感。还有大量民歌的借用,烘托了作品的氛围。同时也有写作方式的变化,改变了之前常用的“白描”手法,“吸收了必要的和读者所能接受的‘心理刻画”。蓝五和雪梅在秦经理家重逢时的复杂感情等,也体现出李准对新时期多种艺术手法的吸纳和借用。
三、新人、新事与改写之路
1953年,李准凭借《不能走那条路》成名,写出了当时面临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问题,成为“写方向”的重要作家。次年,李准响应号召,带领家人来到荥阳县司马村安家落户,在一个农业合作社当了三年的副社长。其间,文化部电影局举办“电影剧本讲习班”,李准去学习三个月。在被问到解放前看过什么电影时,他说自己一部都没有看过,大家都哄地笑了。在讲习班上,蔡楚生讲了小说和电影的区别,洪深讲写剧本的方法,对李准的启发很大。1958年初,李准被下放到登封县马寺庄劳动锻炼,在生产大队担任农业试验场场长。
正因为此,他对于农村农民很是熟悉,作品充满生活气息,但对自己塑造的人物形象并不满意。曾反思《不能走那条路》东山这个新人形象没有写好。“写得比较概念”,“性格不够鲜明”,反而宋老定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物自己很熟悉,写出了落后农民在党的教育下战胜私有制,走上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发表的《灰色的帐篷》《芦花放白的时候》,被认为“有毒素”“不健康”。李准赶紧自我批评——“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和伟大业绩,甚至思想感情变质,写出有严重错误的东西”,也因积极的自我批评躲过了反右斗争。
当时的社会语境,也决定了创作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必须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承担歌颂国家和人民的使命。1956年,李准到北大荒采访了中国首个机械农场的场长周光亚,并以他为原型,创作了剧本《老兵新传》。创作动机是“毛主席最近有个讲话,大意是建国后,环境改变了,我们很多人闲起来了,一些战争中熟悉的东西忘掉了,如今全国大搞建设,工厂农村要发展,老兵要新传。李准说,看到这个指示以后写了剧本,把当前社会的思想焦点反映一下”。剧本提交给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不久,在苏联学习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拍摄方法的导演沈浮和摄影师罗从周回国,一起将剧本变成了电影。
《老兵新传》故事取材于解放初期我国在北大荒建立的第一个国营农场的故事。剧本初稿只写出一万多字。写第二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赵松筠被放到不恰当的地位,李准也自我批评“反映了我的政治水平差”,直到1958年1月写出第四稿。老兵战长河,是一位“和天斗,和地斗,和风斗,和雪斗,还得和狼斗,和自己的落后头脑斗”的英雄形象,但李准也写出他性格的多面性,如爱护青年,又粗暴干涉他们的生活——性格急躁,爱争吵,但不失为“一员亲切可爱的‘闯将”。老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找到新的战场,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影片上映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被评为建国十周年优秀影片,并在第一届(1959)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技术成就奖银质奖;1960年在英国播放后,《泰晤士报》评论该片“在某些方面使人联想到旨在向俄国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的、有关他们革命的俄国影片。但俄國影片给人的印象几乎是严肃的救世主式的,而《老兵新传》却有生气、有风趣、亲切而热情”。
影片的成功也使得李准的创作心态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想写一些农村新人物,想在农村新人的精神面貌上,新的性格形成上,进行一些摸索”。这一时期,创作出李双双(《李双双小传》)、肖淑英(《耕耘记》)、韩芒种(《两匹瘦马》)、耿良(《春笋》)、吴忠信(《三月里的春风》)、高秀贞(《两代人》)等一系列新人形象。他们在新时代的变化,正是我们新中国经过共产党的十多年的教育、劳动人民接受教育产生出来的花朵,他们是新人。李准认为文学创作“就是要积极地、热情地反映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新的精神”。
根据形势创作出来的新人形象,也因为新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不停地修修补补,如《李双双》从小说到电影,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动,将中心事件“办食堂”改为“评工记分”。李准说:“改动的目的第一是为了符合更广大群众的需要;第二是为了能够更广阔更多方面地塑造李双双的新性格和新品质。”副线为金樵当副队长之后和李双双的冲突,以及二春、桂英的婚姻问题,增添了民间的喜剧色彩。李双双虽然是“模范环境中的模范人物”,但形象亲切,有生活气息,代表了妇女解放运动以来意气风发的受益者,“有着社会主义时代所需要的所有优秀品质”。全国迅速掀起“李双双热”,成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创作《大河奔流》时,李准长时间找不到方向,“访问了很多黄泛区的地方。通许县、中牟县、淮阳县、花园口公社。收集这种家史不下二百家,我仍旧写不成一个作品。我觉得现在单是写写旧社会受的苦,有什么大意思呢”?后来,他来到了扶沟县海岗大队和通许县百里池大队。“特别是到了海岗大队,一下子激动得我几晚上没有睡着觉”,从这里,“我看到了黄泛区的变化,从前最穷的地方,变成中原大地的粮仓。从前的要饭孩子,变成公社书记、拖拉机手、农业技术员、赤脚医生”。写新的变化、新的历史成为李准的写作着力点。李准对旧人物、旧故事不感兴趣,着意写新社会的成长、光辉,却造成写作以来的最大困境和败笔。人们认为他的作品只不过是“政治运动的应时之作”,“谈不上现实主义”。
在此之前,李准一直是新中国文化生产的积极参与者,他能够将政治意识形态转化为自觉性的追求,转化成自身的使命、义务与责任,也一直是备受好评的主流文学家。作为剧作家广受观众喜爱,《李双双》曾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肯定。据李准回忆,自己写东西一直很顺利,收到的反馈多是感动、受教育之类,而写《大河奔流》却“收到不下十封骂我的信,人家说你这个作家不行,你干脆回家啃红薯吧”!“《大河奔流》给我上了重要一课。剧本是在‘四人帮时期写的,我总觉得,还是写了人物吧?还允许人物哭,还写了一点人情的东西吧?但放映的效果,很使我吃惊。当年那些看过《李双双》《老兵新传》《龙马精神》的观众,忽然没有了。这在我可说是很意外的。”新时期文学场的改变,文学观念的转轨,观众和读者审美视界的革新,使得李准既有的写作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失却了曾经的价值和意义,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从前沿阵地上被抬下来的战士”。
这期间,有人给李准推荐了赛珍珠的《大地》。小说于1928年在南京创作,较为真实地写出江苏、安徽农村,农民在水、旱、匪、蝗灾下的悲惨遭遇,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读完这部小说,李准的感情很复杂。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他对中国农民的了解,总比赛珍珠要熟悉得多,他应该写出比《大地》更为深刻、更富有社会意义、更能代表中国农民的作品。“大河”的经验,“大地”的催促,使李准全力投入到《黄河东流去》的创作,想“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
《黄河东流去》上卷于1979年出版;下卷于1984年完稿、1985年1月出版,开篇二十五到二十八章续写蓝五、雪梅的爱情、殉情,之后写春义、凤英咸阳安顿、海老清寻妻女、李麦寻女等,故事结尾写到难民的返乡,重新成为“土地的主人”,退回到《不能走那条路》的史前史。曾经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人新事、集体化道路消隐了。李准在反思历史和自己的写作,刻意规避“运动文学”的帽子,重回审美法则和历史谱系,寻找民间与土地的力量。在作品后记中,他写道:“《黄河东流去》这部小说可能会受到电影《大河奔流》给人的印象的影响,暂时不会受到广大读者注意,但这只是暂时的,我相信只要把小说读下去,读者就可以知道我不是草率地把一个电影故事变成小说,而会感觉到我是在诚实地、全力以赴地在探索,在前进。这些探索包括我对革命现实主义向前推进一步的思考,也包括我对赋予民族化以新的生命的尝试。”细究起来,这段话也是颇为中肯的。程光炜曾在《为什么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说》中指出:“研究应该具备两种视角,一个是新时期文学视角,另一个是70年代视角。它们是在一种新的辩证关系中出现的新的历史视野。”对李准的创作和评价,更是如此,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同样的经历、故事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复生”。
反观李准的写作,他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作家,“作家自己就应该属于新时代的人物”——热衷于写新人新事,自觉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积极呼应着各个时期的政策与号召。到新时期之后,他因《大河奔流》的失败重审自己的写作道路,发现读者群的变化,也对自我身份重新定位。他开始书写真正的农民故事,写出了他更为熟悉的底层人民生存史、苦难史。李准的一再转型不能仅仅归咎于个人的“跟政策”,在各个历史时期,他总在不断地调整、改写,力图创作出反映时代新貌的作品,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生产建构者。即便在新时期被甩出轨道之后,他还在重新调整写作范式,参与《牧马人》等电影编剧工作,写出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在西方现代派和本土文化之间吸收借鉴,拓展艺术审美表现空间。我们无法要求写作者都能够超越历史,毕竟任何书写都会被特定的历史境况所制约。无论从反思层面还是创作层面,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回到他所熟悉的民间生活场景,塑造出众多有光彩的农民形象,写出了民族的苦难与诗意,不失为“一部真正反映中国农民问题的小说”。
注释:
翟国胜:《说世短语书系:黄泛区往事》,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李准:《黄河东流去·后记》,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778页。
李毓梅、蒋晔:《成功者访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第366页。
董冰:《老家旧事——李准夫人自述》,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冯梅芳口述、李郁整理:《第一代“农民作家”冯金堂的凄然人生》,《纵横》2012年第10期。
[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59页。
李准:《<大河奔流>创作札记》,《十月》1978年第1期。
李准:《一个纯真见性的人——悼赵丹同志》,《电影创作》1981年第1期。
徐峰:《裂解与期望的年代——新时期初年的中国电影景观速写》,《当代电影》1998年第6期。
罗艺军:《风雨银幕》,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页。
秦裕权:《<大河奔流>——从剧本到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509页。
王铿:《关于“ 上、下集” 的一封来信》,《电影评介》1979年第10期。
《观众对影片<大河奔流>的反映》,《电影创作》1979年第4期。
李准:《黄河东流去·上》,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第148页、第45—46页。
冯牧:《在生活的激流中前进——谈李准的短篇小说》,《文艺报》1960年第3期。
《“文艺的社会功能”五人谈》,《文艺报》1980年第1期。
刘景清:《李准创作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刘认为《黄河东流去》中徐秋斋形象最成功、最有典型性。
李准:《李准谈创作》,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36頁、第25页、第74页、第149页、第133页。
李准:《我怎样写<不能走那条路>》,《长江文艺》1954年第2期。
李准:《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光明日报》1960年8月24日。
《徐桑楚回忆上影厂1959年献礼片》,《电影艺术》1999年第4期。
陈清泉:《我给李凖、叶楠当编辑》,《上海采风》2015年第5期。
1947年冬天,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派周光亚等三人到通北县赵光地区勘察荒地,白手起家,建立起通北农场,隶属东北人民政府。不到两年时间,就开垦荒地3.9万亩,有拖拉机140多台,职工队伍也发展到260多人。建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科学技术和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由农学家主持农业生产,领导干部积极学习现代化农业技术和科学管理知识。在1950年代,名扬全国的女康拜因手刘英,就是在这个农场成长起来的。张聪:《北大荒的第一批农场》,《中国农垦》1984年第2期。
李准:《我怎样写<老兵新传>》,《人民日报》1960年3月2日。农学家赵松筠最终的荧幕形象带有知识分子因循守旧、教条主义等诸多问题。
《“泰晤士报”载文谈我影片“老兵新传”》,《参考消息》1960年9月22日。
李准:《向新人物精神世界学习探索》,《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6日。
[美]唐小兵:《流动的图像: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再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页。
光明日报新闻研究所编:《中国知识分子四十年掠影1949—1989》,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吴光华:《李准和他的<黄河东流去>》,选自《黄河东流去·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89页。
程光炜:《为什么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说》,《文艺争鸣》2011年第12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国庆献礼片的视觉经验与文化审美研究”(项目编号:20BZW1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