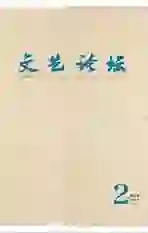从“五四”到延安
2021-07-20王珏李明晖
王珏 李明晖
摘 要: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现代中国文艺自我变革逻辑的集中体现,他的《讲话》在现代中国文艺发展史中具有转折意义。毛泽东《讲话》体现的现代中国文艺自我变革逻辑,在思想发展上,是从民主与科学的基本共识,演进到马克思主义,因为新共识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必然是从泛泛的民主科学,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实践。在形式追求上,是从平民化演进到大众化,平民化所追求的“化”是局部的变化,而大众化所追求的“化”是彻底的融入。启蒙观的发展,是从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色彩的“启蒙”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自觉,后者不是对启蒙的否定,而是对启蒙的发展与深化。
关键词:毛泽东;现代中国文艺;变革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
毛泽东在现代中国文艺发展历程中的巨大作用是不争的事实,新时期以来人们长期争论的焦点是这个作用的“意义”究竟应如何认识。本文将论证的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现代中国文艺自我变革逻辑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毛泽东之所以能以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实现“五四”以来中国文艺的又一次转捩,根本原因是其在当时的历史新局中,总结和延续了现代中国文艺的道路和经验,精确地表达了现代中国文艺本身的发展力道,解决了长期困扰现代中国文艺的方法与观念困境。可以说,只有在现代中国文艺史的全局视野中,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讲话》,而只有真正理解了毛泽东的《讲话》,才能贯通现代中国文艺的诸多根本性、规律性问题。
一、《讲话》的文艺史转捩点意义
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有一个大的文艺史语境,就是抗战时期许多年轻的进步文艺人纷纷自发地奔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奔向延安;因此,原本偏僻的边区,變成了新文艺的一个中心地带。此前,新文艺的中心都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此,这次文艺界的大迁徙,给文艺家们的创作心态、创作方式、创作主题等,都带来了新的课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少文艺家没有认清新社会与旧社会的本质区别,没有充分理解创作环境与读者群体发生的巨大变化,于是发生了创作与社会之间的脱节。体现在文艺观念上,就是囿于对暴露、批判、启蒙这些文艺观念的偏执理解之中,认为只有寻找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并进行暴露,才是最有价值的文艺,认为现代文艺家的最大使命就是对民众进行启蒙,救治民众的愚昧落后。正是针对这样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召开了这次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开了十二天,毛泽东在座谈会开始时作了一个引言,在座谈会结束时又作了一个长篇的结论,这两次讲话经过整理修订后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就是《讲话》。毛泽东这个讲话,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全面地阐释了人民文艺的思想,匡正了新文艺界在面对时代的新发展时种种迷惑、模糊乃至错误的观念,为中国新文艺的进一步发展与质的飞跃,指明了方向。
《讲话》的主题,就是文艺为群众和文艺如何为群众。文艺为群众,说的是立场,文艺如何为群众,讲的是方法,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只有运用了正确的方法,才是真正的为群众,而方法是要从实际出发的,是要因时代与社会的变化而发展的。在这样的理论脉络中,就得以辨明刚才说的一些来到延安的文艺家们创作困境的实质,而且自然地引出了突破困境的办法。
这些进步文艺家,是有着为群众创作的意识的,但是,他们此前都是在反动统治的重压下进行创作,在旧社会的环境中进行创作,在人民群众被迫处在无权利、无组织、缺少教育、一盘散沙的现实状态中进行创作。这就决定了他们为群众创作的方式:一者,主要的不是直接以群众作为目标受众,而基本上是进步知识分子们之间的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二者,强调启蒙民众的使命感;三者,推崇批判和暴露社会黑暗与国民劣根性。这在此前的创作处境中,是不得不如此的,也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但是他们机械地把这些特定处境中的方法,当成了定律、原则,不假思索地认为在延安、在边区,也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或者说遵循这些“文艺定律”,这就给自己的创作造成了瓶颈甚至是偏差。
所以,《讲话》首先厘清了理论的根基,分清了“为群众”这个立场问题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方法问题,然后,用大量的篇幅重点论述了在新的文艺创作环境中,创作应该遵循的新方法。比如,文艺家应认识到在根据地,文艺的受众是广大的干部群众,从而主动学会用广大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进行创作,而且突破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与群众的情感融合在一起。再比如,文艺家应认识到在根据地,人民群众已经获得了民主权利,已经组织起来,已经在接受着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的教育,这样文艺家们才能够实事求是地重新理解“启蒙”,而不是再用老眼光把群众看作是可怜的“愚众”;另一方面,文艺家也有了深入到群众生活之中的机会,而不是像在1930年代的上海那样必须化妆改扮之后偷偷地了解底层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在新的社会中,为了暴露和批判而紧盯着现实中的一些个别现象,然后在笔下渲染放大,这不但是劳而无功的做法,而且很容易成为有害的做法,因为会成为混淆新旧社会区别的借口。《讲话》中,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作了阐释,他说:“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又说:“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针对有的文艺家宣称的“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毛泽东顺势指出:“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并进一步反问:“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这样的反复申说,打破了文艺家们的思想桎梏,解放了文艺家们的创作力。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一批崭新风貌的作品相继问世,比如赵树理的小说、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获得国际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中国现代文艺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并随着革命的胜利而大步迈向当代文艺的阶段。
二、从民主科学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讲话》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文艺的指南针。这个观点,体现的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文艺发展的必然逻辑。中国现代文艺自我变革的思想发展脉络之起点,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展现的民主科学新共识,这个脉络的走向,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发展线索,在逻辑上是一脉贯通的,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我们从中国现代文艺的一些名作中,可以理解这个必然性,从中国现代一些著名的文艺家身上,能体会到一脉贯通的逻辑。
中国现代文艺“第一个十年”的文艺作品,整体上体现出两种情感倾向,一种是奔放喜悦的情感,一种是愁苦悲愤的情感,而后一种情感明显是压倒前一种情感的,越到这个时期的后面越明显。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两种情感倾向同时出现的原因,都在于民主科学新共识的建立。奔放喜悦的情感,是因为这种新共识带来的解放感和目标感;而愁苦抑郁的情感,则来自这种新共识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巨大对比,以及想要在现实中落实这种新共识的时候,会立刻碰到的巨大阻碍所引发的强烈挫折感、失落感。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最能明显地体现出这样的文艺现象。《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中的“凤凰更生歌”,都充满了新生的喜悦兴奋,说“充满”都不准确,在有些诗句中,尤其是在“凤凰更生歌”的原版中,简直满得都溢出来了,以至于后来诗人自己做了大篇幅的删改,就是因为写的时候情绪太热烈、太兴奋了,大概后来自己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不像样子,这就是体现着奔放喜悦的解放情感的自然流露。那些集中歌颂太阳、歌颂地球等的诗篇,也都强烈地呈现着这种情感。可是后来的诗,尤其是“归国吟”这一部分里的诗,整个情绪就变了,以读者的感觉来说,就是整个气氛变了,从万里晴空变成了愁云惨雾,从明媚变成了阴沉。但是在阴森的环境氛围之中,还有诗人的反抗力量存在着,这种力量虽然在愁云惨雾之中还很微小,却能给读者勇气和力量。那个时期的另一位著名诗人闻一多,其实也经历了和这很近似的心路历程,而且将其记录在了他的诗歌中,喊出了饱含着血泪的这句话:“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像郭沫若、闻一多诗歌名篇中呈现的这种情感,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这其实体现了一个很深刻的历史课题,那就是:新共识究竟如何在具体历史处境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落地生根?
1920年代末戴望舒写了《雨巷》,今天我们读它的时候,最感动的是它表现的爱情的甜蜜与迷茫,但是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包括对戴望舒本人来说,这首诗的感情是超越爱情的,它是寄托在爱情意象上的对于整个人生情绪的一种表达:追求“人生理想境界”历程的种种经验给他们的感觉,正像是雨巷中遇到的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正像那条“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也许我们更应该从另一个方向来说:正是因为这首诗中寄托了更深更大的感慨,所以才把爱情中的一种感受表达得这么经典。还有何其芳著名的《预言》:“我激动的歌声你竟不听,/你的脚竟不为我的颤抖暂停!/像静穆的微风飘过这黄昏里,/消失了,消失了你骄傲的足音!/啊,你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当时年轻的、怀揣着梦想而又饱经挫折打击的读者,读这首诗的时候有着比我们今天丰富得多、强烈得多的情感体验,因为这写的几乎就是他们此前的人生。
这种情感,显然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一定是要继续追寻、探索、奋斗的。这也就意味着民主科学的共识不可能再停留于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那种状态,一定要向前发展。这时候我们就要分析一下它自身发展的规律是什么样的。民主和科学,在欧洲都是基督教信仰遭到严重冲击之后生长起来的新共识,它本身就是动态生长变化的历史过程,而不是稳定不变的实体。它和资本主义几乎同时萌生成长,但却有自身的走向,并不依附或局限于资本主义,所以必然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文化发生矛盾,到中國在近代语境中接受这种新共识的时候,它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在方方面面体现出来了,它本身的发展已经呈现为多阶段、多走向并存的状态,而就其真正的发展逻辑来说,民主必然发展为人民民主的诉求,科学必然发展为变革社会的科学,而当中国的有识之士沿着这个逻辑探索的时候,就发现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资本论》是用数学和哲学的方式细致地分析纷繁现象掩盖下的现代社会本质,发现社会发展的趋向与道路,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则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勾勒了以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人民民主的方案。所以,新共识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就必然是从泛泛的民主科学,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实践。当然,这个过程中有激烈的争论,也有偏差与挫折,但是这个方向是一定的。我们刚才说过的几位诗人,郭沫若在创作《女神》之后不久就坚决地表示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闻一多后来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勇敢地牺牲了生命,戴望舒成为革命的积极宣传者和参与者,何其芳1938年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典型的例子还有鲁迅、茅盾,两人和郭沫若一样都是五四时期新文艺的巨星,后来全都成了共产主义者,成了左翼文艺的领袖。总之,从民主科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是中国现代文艺整体思想发展演进的规律,也是呈现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的事实,历史与逻辑在这里正是高度统一的。
三、从平民化到大众化
中国现代文艺在形式追求方面的自我变革趋向,是从平民化到大众化。
文艺革命从最开始就包含着平民化的意识,白话文运动本身的理论逻辑之一就是平民化,因为在古代,文言文是社会精英的书面语,就像在中世纪的欧洲,拉丁语代表着社会精英身份,在近代的沙俄,法语一度代表着社会精英身份一样。主张废除文言文这种延续数千年的精英文化符号,其实就意味着淡化甚至取消精英身份与精英意识,实现文化方面的身份平等。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之间还是有分歧的。有的人,比如胡适,比如周作人,内心里还是要保留文化上的精英身份与精英意识,而周作人这种心理尤其强,所以会暗暗地用各种新的符号来顶替文言文的身份区别功能,比如外语,比如国故,比如绅士气或名士气,等等;但是像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当时都是有着文化平民化的自觉的。
文艺平民化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方向,这两个方向在五四时期也都得到了推进。一个方向,是向平民输出,也就是文化普及、思想启蒙。当时就有许多平民夜校甚至工人夜校的创办,胡适、鲁迅这些大学者大作家,都去平民夜校讲过课;体现在文艺上,就是文艺的语言和表达追求通俗易懂,平易浅显,但也应该意识到这里有所谓“眼前景致口头语”这种古典文论传统的支撑。另一个方向,是输入。典型的体现就是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建立,这个研究会开展了在各地采集民间歌谣的活动,还印了书,虽然目的也是多元的,但是要在新文艺中引入民间文艺、民间语言的成分这个目的,也是占很大比重的。
但是这两个方向,又都没有超出传统文人意识的框架。输出的方面,用白话文、平民的语言向平民进行知识与思想普及的事,至迟从唐代的变文、俗讲就开始了,到晚清更是有很多人在做,而且是不同思想主张的人都在做。输入的方面,最有名的就是明代文艺家、出版家冯梦龙编过一本《山歌》,搜集了几百首的江南民间歌谣,而且在序言里也赞美了这些歌谣“为情真”,而且与“假诗文”进行对比,这也很有用平民的文艺来批评当时文艺界的意思了。
到了“第二个十年”,左翼文艺界就很明确地反思了此前平民化的不足,而提出了大众化这个新的主张,左联还为此进行过几次论争。大众化也可以分为输出与输入两个方向,但是与平民化的输出与输入比起来,都有很大的不同。就输出而言,左联时期的大众化已经不只是说通俗易懂、平易浅显,而且认真探索和学习各种在当时大多数群众中流行的或者可能流行的表达形式,其中不少是传统文人不屑一顾或者觉得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如连环图画、打油诗、莲花落等;就输入而言,提出了“大众语”的概念试图作为“白话文”的升级版,也就是意图直接用大众口头的语言来进行创作,当然,这里立刻就遇到一个方言的问题,其次,语法的不严密、语汇的粗糙,也都是难题,但是这种设想本身就是可贵的。而且在左联主导的大众化努力中,输入和输出实际上已经开始融合到一起了,也就是说,以大众的语言、大众的形式与大众交流的意识,已经开始形成了,残留在平民化主张与实践中的那种自居于平民之外、平民之上的意识正在有力地被克服。可以说,平民化所追求的“化”,是局部的变化,而大众化所追求的“化”,是彻底的融入。
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不允许,也由于当时左翼文艺家们本身思想认识上的不足,大众化的努力在这一时期并未获得成功。这颗种子真正开出花朵、结出果实,是在抗战时期。一方面,“文协”发起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活动,让文艺家们有了真正与大众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另一方面,在边区,文艺家和群众的关系更是得以发生彻底的变化。这时候,真正的大众化就有条件实现了,那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在这一时期崛起了一位最有代表性的大众化作家,那就是赵树理。他的文艺经历,也很能映照出刚才所说的这个从平民化到大众化的进程。赵树理出生在1906年,所以他进学校读书的时候,新文艺已经在文化界取得了主导地位。但是他意识到了所谓“平民化的新文艺”,依然是和普通民众脱节的,新文艺的刊物图书似乎很繁荣,可一般识字的平民百姓,看的还是书摊上贩卖的那些有着封建思想的小唱本。于是他立志自己要做一个新文艺的“文摊文学家”,让自己的作品也能在那些书摊上卖,“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但是从理想到成功,还是有一段长路的,他最开始走上文坛的作品,也基本没能脱离当时新文艺普遍的状态,直到他到了边区工作之后,特别是在学习了毛泽东的《讲话》之后,才真正摸索出了一条大众化的路,《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了热烈的認可。1930年代左翼文艺家们的一个文艺理想,他实现了。
四、从“启蒙”到“团结与教育”
中国现代文艺中启蒙观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从“启蒙”到“团结与教育”的发展路线。毛泽东将文艺工作的目的概括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其中,“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对应的就是五四时期所说的“启蒙”。“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理论,不是对“启蒙”的否定,而是对“启蒙”的发展与深化。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要追溯一下“启蒙”这个词的历史。在汉语里,“启蒙”的原意,就是让人从不知道变为知道,“蒙”表示一种混沌不明的、蒙昧的状态,而把这种状态打破,就是启蒙。在古代,这个词经常和另一个词连用,那个词是“发覆”,古人文章里常常说“启蒙发覆”,我们把两个词放在一起理解,其中的意思就更清楚。“覆”就是覆盖,“发”在这里表示揭开、打开。原来在古人的观念中,人本来就是具有生命智慧与道德知识的,只是被“覆盖”了,所以处于混沌蒙昧的状态,一旦把覆盖物去掉,智慧和知识就能够起作用,那么去掉覆盖物的这个行动,就叫做“启蒙发覆”。到了近代,学者用“启蒙”这个词翻译欧美特别是法、德、英等国在十七、十八世纪流行的一个概念,也是相当准确的,因为那个概念在英语里叫“Enlighten”,字面本意是照亮、照耀、使发光,引申为使人运用自己的理性,发挥人性的高贵等。而在法语、德语中,相对应的概念也同样用的是表示“光明”“照耀”等含义的词,这其实也意味着有些伟大之物本来就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淹没在了黑暗之中,而需要一个行动来把它照亮,可见在汉语中把表示这个行动的词翻译成启蒙,是非常恰当的。
但我们同时还要知道,在欧美,这个“启蒙”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当然,也有人在理论上提倡无差别的启蒙,但是影响更大的还是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启蒙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启蒙。古典主义崇尚秩序,认为真正能够“照亮”理性的是社会的精英分子;浪漫主义崇尚本能,认为真正能够“照亮”智慧的是少数的天才。至于普罗大众,他们通常认为应该用精英社会的文明成果去规范。这个传统其实来自古希腊,而文艺复兴时期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也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这个来自欧美的概念传到中国之后,一部分人也就是这样接受的,比如胡适、梁实秋等,基本上继承的是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启蒙观,而早期的郭沫若等人,继承的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启蒙观。所以,现代汉语里的“启蒙”这个词有先天不足的一面,总的来说,就是对大众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融入不到大众之中去,与大众不能交心。这其实也是让当时很多文艺家感到苦恼的一件事。苦恼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胡适等人主要体现为慨叹中国人的“贫愚弱私”,其实背后是一种无力感,而左翼文艺家像郭沫若、茅盾、田汉这些人则表现为对自己作品感到不满、遗憾,感到和普罗大众总是还隔着一层什么。不同的表现方式,体现的是不同的观念,而不同的观念又会引发不同的行动。从五四时期的邓中夏等先进知识分子,到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家们,已经在积极地思考和尝试突破当时“启蒙”观的缺陷。像鲁迅五四时期创作的小说《一件小事》和1930年代写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文章,都包含着重新“发现”民众的努力,这里说的“发现”,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新文艺家们的一种自我启蒙发覆,这次要去掉的覆盖物,就是“启蒙”这个词上沾染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因素。
这个努力在理论上的完成,就是本节开头说的《讲话》中概括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这个理论首先说“团结”,而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本质上是惧怕人民的团结的,在他们的语言里表示联合起来的“大众”的那个词(如英语里的mass)本身就带有贬义色彩。所以,“团结人民”这个表述,就表示了立场,也表示了对人民本身力量与智慧的认知与信心。这个“团结”既指以文艺作品巩固人民的团结,更指文艺工作者要与人民团结在一起,成为或者说回归为人民的一份子。以此为基础,“教育人民”,就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育,而是平等的教育,是人民的自我成长。在这个过程里,文艺作品在教育人民,人民也在教育文艺工作者,两者是融为一体的,而这正意味着,人民和作为人民的文艺工作者本身蕴涵着也创生着智慧、知识和力量,团结和教育都是为了解放和发挥这些智慧、知识和力量,这不正是启蒙发覆的本意吗?
此后,延安文艺作品中的启蒙观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以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为例:一方面,这篇小说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都有着严重的愚昧落后思想,但小说的叙事,既是在严厉批评他们,又表现了他们尤其是三仙姑精神病态的社会历史成因,更写了他们在新的社会现实中失去了固执己见的土壤,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小说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小二黑和小芹这两个青年农民,他们的原生家庭正是愚昧落后的典型,他们在人生斗争中的成长却是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再比如《李有才板话》,小说中阎家山的贫苦农民之所以那么真实生动,就是因为作家完全是在他们之中写他们的,所以无论是他们的局限不足,还是他们的精神力量与精神成长,都融于真实可感的生活细节之中。这些小说中所写的“启蒙”,就都是作为“团结与教育”的启蒙。
五、从“反传统”到“打击与消灭”
中国现代文艺斗争观念的演进,是从“反传统”,变革为“打击与消灭”。“反传统”是五四时期文艺的鲜明精神标志。关于五四的“反传统”,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理解和评价。当时新文艺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普遍有矫枉过正的心态和以偏概全的做法,辩证区分和客观看待传统文化的意识还很弱,这些都是事實。但是另一方面,从具体的论述和文艺呈现来看,他们攻击的重点还是很明确、很集中而且也相当正确的,那就是攻击僵化的家族礼教,攻击裹小脚、典妻、私刑等愚昧的现象。尤其是僵化的家族礼教,更是被他们作为传统文化弊端的集中体现,加以猛烈攻击。鲁迅自己曾说《狂人日记》的主旨就是“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此后的名家名作,如巴金的《家》《寒夜》、曹禺的《雷雨》《北京人》、老舍的《离婚》、张爱玲的《金锁记》等,都或多或少地表达着这样的批判意识。
同时,我们还会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上述这些作品中,对抗家族礼教者的结局,大部分是悲剧,即使不是悲剧,那也是不了了之。在这些作品,以及当时的其他大量作品中,我们总是能看到僵化的家族礼教对人的碾压残害,而几乎看不到人战胜家族礼教弊端。胡适早年的剧本《终身大事》可能是个例外,但这个剧本只是为了当时一群留美学生的自娱自乐而作的,后来连胡适自己都说这个剧本没什么价值。事实上,它在中国白话剧的形式方面的确有开创之功,但是故事情节编造得太生硬了,结尾年轻人的胜利怎么看怎么像是美好而幼稚的幻想,或者说选了一个最欢快的场景戛然而止,不再管后边又会发生什么了,也就是说,剧情逻辑是不成立的,是没有完成的。在当时能够做到情节有说服力的作品中,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作品,也包括一些通俗小说,人在僵化的家族礼教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家》中觉慧在目睹亲历了一场场悲剧之后,只身出走,已经算是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反抗家族礼教最有力、最成功的行动了,但他的出走并没有改变那个摧残所有美好之物的高公馆,他的出走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觉慧有一句名言,巴金说是他自己年轻时说过的话,过了多年之后都记在心里,那就是:“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这里说的“他们”,放到小说的情境中,指的是以高克安、高克定、陈姨娘等为代表的家中长辈。觉慧的这句话,在这激流三部曲中没有实现,在当时其他人的作品中也都没有实现,牺牲的都是觉慧心中的“我们”,而不会是“他们”。
总而言之,所谓“反传统”,一旦落实到人的现实生活中,就都是失败的,至少是受挫的。这个事实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反传统”这个观念本身的缺陷。
巴金的《家》中还有一个更有历史认识意义的细节,那就是觉新一度宣称的“作揖主义”。以前有不少读者简单地把“作揖主义”理解成了不反传统的意思,其实这个词来自五四时期刘半农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的一篇杂文,本身是作为一种反传统的策略提出来的,可是这种策略恰恰说明了当时反传统观念的糊涂之处。为什么呢?因为提出这种策略的理论依据就是:一切坏事坏现象都是因为传统的东西,而这些传统的坏东西之所以还存在,就是因为还有那些维护传统的旧人,但旧人最多再过几十年就会被自然规律淘汰了,所以,新人不要把宝贵的精力用在与那些旧人争论纠缠上,给他们作个揖送他们走就是了,新人应全力去建设新的东西,这样,等到将来,旧的自然消失了,新的也造好了,理想中的新社会就实现了。这一套理论从根本上就大错特错了,但在那个时期可不光是刘半农相信这个,很多人都以为真的是这样。鲁迅当时是以生物遗传的比喻来质疑这种观点的,说后代的血液里会有祖先的毒素,思想也是如此。后来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政变的时候,鲁迅在广东目睹了国民党青年如何迫害共产党青年,他们手段之毒辣残忍、心思之卑劣阴暗,比起过去的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自己说,他当时被这样的社会景象“吓得目瞪口呆”。历史的事实比任何理论主张都雄辩有力,天真乐观的“作揖主义”送不走任何坏现象,更送不走一个旧社会。文艺作品中的悲剧,映射的是现实的规律:社会若不发生根本改变,无论是愚昧落后的思想还是僵化的家族礼教都是不可能消亡的。所以,要终结高公馆中那一连串的悲剧,真正要去战胜的不是“传统”,而是别的什么。
究竟是什么呢?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于这些,必须在现实斗争中进行打击,目的是消灭它们,只有这样,文艺家控诉的那些悲剧才能不再重演。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现代文艺家都有这样的认识,但是即便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的作品只要是认真的、诚实的,就会一再有力地证明这一社会历史的事实。
所以,毛泽东《讲话》中将文艺任务的斗争方面,概括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两句话,正是代表着中国现代文艺这一方面自我变革的理论成果。
而在这种“打击和消灭”的实践正在不断取得成果的时空中,就会有《小二黑结婚》这样的作品,在那里,僵化的家族礼教符合逻辑地失败了,对抗家族礼教弊端的年轻人获得了合情合理的胜利。
总结起来,毛泽东在1942年从现代中国文艺的新坐标、新语境出发,清晰地表述了现代中国文艺自我变革的逻辑,有力地解决了现代中国文艺的“平民化”难题、“启蒙”难题和“反传统”难题,因此实现了现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性转捩。毛泽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中坚之一,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响亮地提出了“现代中国文艺之问”,那么1942年的毛泽东就为在历史风云中成熟起来的“五四”一代做出了响亮回答。
注释: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自《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1页、第872页、第873页、第851页、第848页。
参见郭沫若:《女神》,人民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8页。
闻一多:《发现》,选自白崇义、乐齐编:《现代诗百家》,宝文堂书店1984年版,第107页。
戴望舒:《雨巷》,选自白崇义、乐齐编:《现代诗百家》,宝文堂书店1984年版,第229—231页。
何其芳:《预言》,选自白崇义、乐齐编:《现代诗百家》,宝文堂书店1984年版,第178页。
冯梦龙:《序山歌》,选自郭绍虞、王文生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长江文艺》1949年第1卷第1期。
鲁迅:《<中国新文艺大系>小说二集序》,选自《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巴金:《家·后记》,摘自《巴金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
参见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选自《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鲁迅:《三闲集·序言》,选自《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