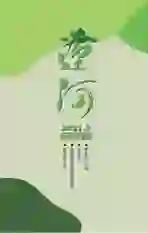草屋里那些事
2021-07-20子薇
子薇
在中院村,很多人家住的都是草屋,我们家住的也是草屋。现如今,爱好摄影的人们若是冷不丁地见到草屋,一准兴奋地把照相机镜头对准了,咔嚓咔嚓地按下快门,拍下一张又一张。对于一事一物,单纯从欣赏的角度所看到的,是距离人间烟火颇近的唯美,是距离产生美的不一般浪漫;而日复一日置身其中的人们,其艰辛和苦涩,往往是无法言传的。
我们家在村庄顶东头,门前一方空地,左侧一株三人才可合抱过来的大树,右侧一口池塘,前面一方院子,院子里种满苦楝树,还砌有一个猪圈;房子后门也有一方院子,也种满了苦楝树,里面有柴房和茅厕。房子一长溜四间,一间堂间,一间灶间,两间房间。房顶铺稻草,墙壁砌土墼,是谓草屋。雨落长了,屋顶会渗漏,家里的大盆小盆大桶小桶甚至大罐小罐一起用上了。一个狂风暴雨的日子里,草屋顶被狂风掀翻得支离不堪,雨水汹涌地落进屋子里。母亲独自一个人,顶着狂风暴雨,架好木梯,携着粗重的麻绳,奋力爬上去,将屋顶上的稻草一一整理归位后,固定好一根根麻绳的中段于屋顶的正中,再将固定好的麻绳分别从四面八方甩下去,然后爬下木梯,将麻绳的末端牢靠地拴死在之前搬来的沉甸甸的山石上。上上下下惊心动魄地好一顿忙碌后,母亲有旧伤的腰,再次被拉伤了,腰伤令她行动时剧烈疼痛,苦不堪言。
村子里有一位孤寡老人,我叫她“二娘”。逢年过节,母亲必会接她老人家来我们家吃饭,平常的日子里,若是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母亲也不会忘记送些给二娘。大约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我每次从学校回来,必会去看望二娘。那次回家,像极了我亲人的二娘难过地告诉我,你妈没被暴风雨打下屋顶摔死,真是老天爷保佑,捡回了一条命。
彼时是春天,我在读初一。从汤沟中学回到家里的父亲,看着双手叉腰艰难挪步的母亲,将我叫到他面前,开始了自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谈话。
你妈腰伤又犯了,不说地里的农活,就是去水边洗衣,去地里摘菜,去井边挑水,在家里烧火、做饭、喂猪、喂鸡、喂鸭,那都是你妈没有办法去做的事,你休学半年……
说话时,父亲的眼底隐含着些许无奈和忧伤,但他的言辞却是严肃认真的。做出这样的决定,父亲一定是思量再三了的。
那时,嫁往异地的姐姐已是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读高中的大哥正处于高考的冲刺阶段,二哥在离家百里之外的太湖师范学校读书,弟弟尚且年幼。能够照顾母亲的只剩下我这个唯一合适的人选了。
小兰,你休学半年,照顾你妈。父亲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似钉子,钉向母亲,钉向我。短暂的沉默之后,母亲的话语像是一阵惊雷似地从我耳畔滚过。休学休学,小兰半年学一休,她还有心思再上学?可是你这腰伤,不说做事了,你和成武(我弟弟)饭总要吃吧。父亲还在坚持。这事不要你管!我和成武不会饿死的,家里的猪狗鸡鸭也不会饿死的!说时,母亲皱紧了眉头,右手扶住桌拐,左手猛地叉向腰间。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发那么大的火,简直要把屋顶都冲开了。我和弟弟躲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几番争执,父亲拗不过母亲,只得妥协依从了。
母亲腰伤复发后的又一个周末,我再次从学校步行三十里路赶回家时,从医的舅舅正在用手沾上冷水全力拍打母亲的膝盖正后方,那里已经被拍打得一片紫红,皮下的淤血几乎泛滥成灾到要撑破皮肤奔流而出的地步。母亲死命地咬着牙,痛苦分明刻在脸上,嘴里却是一声不吭。
能忍得了吗?舅舅问。
没事,你只管打,打得重好得快。母亲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母亲每次腰伤发作,精通中医的舅舅都会以这样的方式为母亲治疗。
当晚,我做饭,舀木桶中的水淘米时,才发现桶底有着厚厚的沉淀物——泥土。我家在村庄顶东头,供全村人食用水的水井在村西头,距离实在太过遥远,母亲无法将清冽甘甜的井水弄回家,唯有避远求近地一手拄着棍子一手用木桶拎离家较近的池塘中浑浊的水,然后往水里和上明矾,让泥土沉淀下去。想象着母亲强忍腰部剧痛,去水边洗衣,去地里摘菜,去池塘边拎水,烧火、做饭、喂猪、喂狗、喂鸡、喂鸭……我的泪水终于如泄洪的江水,倾泻而下。
生于 1930年的母亲,原是家境殷实人家的女儿,家中四个儿女,除了舅舅,其余三个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三个女儿,都没有进过学堂。在娘家做姑娘时的母亲,吃穿不愁,农活不用沾边,每天只帮着外婆做些日常琐碎事务。自从嫁了尚且就读于“苏州师范学院”,后更名為“苏州大学”的父亲,苦日子便开始了,除了照顾年迈的公婆、种地耕田、缝补做鞋、洗衣烧饭、饲养家禽,还得收捡废品,抠啊省的、以积攒钱财供父亲上学生活等一应开支的费用。
母亲勤劳能干、人情通达。到了晚年的爷爷奶奶,身体相当糟糕,母亲端饭、递茶、抹身、洗澡,把他们服侍得很周到。姐姐六岁那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一个年头,一个年尾。父亲在绩溪中学教书,母亲捧头起水、披麻戴孝,一个人办完了老人的丧事。那时候,交通极不便利,五百多里的路程,又是倒车,又是赶船,没有三天时间是拿不下来的。父亲接到电报后,先后两次匆忙赶回家。没能见到父母最后一面的父亲,悲痛欲绝地扑在由母亲垒砌的亲人新坟上哭了个天昏地暗……
爷爷奶奶离世是因为疾病,听母亲说是蛔虫过膈。他们去世前,肚子鼓得像是卡了一口铁锅,然后便有蛔虫从嘴里爬出来。在乡村生活的人,肚子里蛔虫成灾,早年在省教育厅做秘书的爷爷,后来离开工作岗位四处云游讲学,但他终究也没能摆脱农村人易得疾病的困扰和纠缠,直至丧失性命。
大哥二哥年幼时,那年夏天,脑膜炎流行,他们俩都未能幸免,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在卫生防疫站工作的舅舅忙得无法抽身,于是,他拜托去中院村给乡亲看病的医生朋友一定别错过我们家。那位医生看到躺在堂间意识模糊的大哥二哥,给他们略微检查了一下告诉母亲,这两个孩子都得了正在流行的脑膜炎,边说,边拿出药箱里的药水给他们打针,又告诉母亲,二哥的病情轻些,大哥这种情况,只怕即使治好了,十有八九也是个孬子。当时母亲都急傻了,只是懵懂地点点头,嘴里谢了人家。那段日子,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们走村访户地忙疯了,有好些孩子因为病情太重没能治好而一命呜呼,也有好些孩子留下了后遗症。大哥二哥的屁股因为打了太多的针剂而凹陷下去,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变孬,上学后,成绩在班上遥遥领先,尤其是二哥,拿老师的话说,课堂上的内容,根本不够他吃的。
我们姊妹几个,年幼时没一个让人省心的。姐姐年少时放牛,在坡地上摔断了腿,在家瘫了好几个月;弟弟年幼时,喜欢爬高上低,经常摔得头破血流,甚至出现过短暂昏迷,除此之外,他还先后七次掉进水塘里,每次都幸运地被人救起。我呢,每到暑假,必会打一次摆子,也就是疟疾,一会儿高烧一会儿寒颤,总要吃上几天的奎宁药,才能慢慢好起來。有天夜间高烧,魇住了,那次不是患疟疾,而是因为出水痘,我半夜里睁开眼睛,看到床前的踏板上站着一个双眼赤红的人紧盯着我,因为和母亲还有弟弟睡在同一张床上,所以我并不害怕。老鼠在床头呼呼生风地窜来窜去,把装稻米的木头缸盖啃得咔嚓咔嚓响。很长时间,那人一直不走,就这么和我对视着。我对母亲说,有个红眼珠的人。母亲问,在哪儿?我说就在这,边说边朝踏板指了指。母亲抬起头,哪有什么红眼珠的人。说时,母亲摸了摸我的头和身体,说,瞎讲,睡觉。我便闭上眼睛,过一会儿睡着了。那一夜我的体温应该是非常的高。农村的孩子不娇气,想娇气也没有让你娇气的环境。从小到大,发烧于我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冻感冒了发烧,出水痘了发烧,每年暑假打一次摆子也发烧。
年轻时的父亲,一来工作忙,暑假还要批改高考卷子,二来为了尽量地节省,很少回家。大哥四岁时,父亲回家探亲,于是母亲怀上了二哥。二哥三岁满村跑时,父亲再次回家探亲,见到那个伶俐活泼、虎头虎脑的男孩,上去拍拍他的脑袋,说,这孩子,长得真漂亮,哪家的?乡邻们哄然大笑:大先生,这是你家小能啊。
母亲大字不识一箩筐,但是,母亲的敏捷与聪慧是人见人赞、人见人叹。她一生育有五个子女,父亲在我这个排行第四的孩子出生的当年,才由距家几百里地的绩溪中学调到距家三十里地的汤沟中学教书。
村子里,起早歇晚的第一人,当属母亲。即便是父亲人至中年调到离家较近的枞阳县汤沟中学后,他也是两个星期才回家一趟,虽然人回到了家里,努力帮助母亲做农活,却是力量有限,天上地下山上水里家里家外的一应事务农活,母亲咬紧牙关大包大揽着。母亲的个子不高,但她做起事来却有着一股子凌厉的狠劲儿,绣花、纺纱、缝补、做鞋、洗衣、做饭的细活,上山砍柴、下水踩蚌、割稻打麦、犁田打耙,甚至做土墼盖房子的粗活,母亲哪一样都不比别人差。她是女人,更多的时候,她俨然是个男人。
大哥第一次参加高考是在1980年,那时的他是一个英俊美少年,成绩在汤沟中学也是佼佼者。在当时不知分填志愿的情况下,不屑于大专的大哥,很自信地填报了本科。但是,成绩下来后,大哥以两分之差名落孙山。
父亲是汤沟中学的数学老师兼数学教研组组长,但父亲与大哥之间可谓惜字如金,除掉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对话,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情感交流。学校里的老师似乎都能感觉得到,他们安慰父亲,也安慰大哥,发挥失常不怕,底子好,再复读一年,一定能够如愿。那年的暑假,大哥拼命地帮母亲做农活,浑身上下晒得黑炭一般。
下半年,二哥来到父亲身边读初三。再次走进课堂的大哥,脸上没有了笑容。父亲每隔两周带大哥和二哥回一趟中院村,帮着母亲做一些田畈里的事。每次与母亲说到大哥,父亲总是愤愤的语气,说大哥木讷不懂事,母亲便护着,之后,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吵起来,然后赌上大半天的气。
这一届的高考,大哥再次失利,父亲的脸色更是冷若冰霜,母亲背着大哥时,眼睛里时常含着泪水。成绩优异、向往读高中上大学的二哥,被父亲恩威兼施地送进太湖师范。你妹妹和弟弟都在上学,他(大哥)是还要复读的,家里多困难,你都清楚。上个有生活费的师范,减轻点家里的负担吧。父亲如是说。临走的那天,虚十五岁的二哥泪水淌成了河。
大哥进入了又一轮的补习。曾经意气风发的大哥,背似乎有些佝偻了,头总是低着的,见了人,便远远地躲开。高考前的预考,大哥与之前一样,依然全校第一。但是,大哥的心理素质已经溃不成军,高考的失常发挥,在所难免。
我读小学毕业班这年,大哥去了周潭中学复读。一个狂风暴雨大作的周六早晨,大哥回来了,他的眼睛因为狂风的吹打、雨水的浸泡,血红血红的。母亲诧异地问他为啥不上课,大哥说他的脚趾昨夜被老鼠咬了,疼得厉害。母亲求村里的郎中为大哥敷了点草药。大哥在家歇了两天,周一大清早赶回学校。这一年的高考,大哥依然名落孙山。
大哥回到汤沟中学继续复读。父亲在一个风雨如晦的早晨,穿上胶靴,撑起雨伞,正要跨出家门时,大哥走到父亲跟前,说,你不要办退休,我不顶你的职。
大哥在1984年的高考失败后,参加了周潭乡政府首次对社会的公开招考,成为一名干事。心有不甘的大哥,在工作一年后,再次参加了高考,却出人意料地一举成功,成为“安徽医学院”,后更名为“安徽医科大学”的一名大学生。
姐姐出嫁后,我们家完整的劳动力,准确地说,只有母亲一个人,饶是如此,母亲种出的粮食和蔬菜还是足够我们全家人从容度日。乡村清苦的日子,被母亲一双勤劳的双手操持得温润生华。一锅稀饭,就着母亲腌制的咸菜、萝卜干、豆腐乳、黄豆酱;一锅干饭,就着自家菜园里种植的白菜、萝卜、毛豆、大蒜,沸腾于煤油炉上的梅干菜锅子,便是我们年少时的一日三餐。最开心的是,父亲每两周从汤沟中学归来时,母亲会在火锅里放上自制的豆腐、菜籽油煎炸出来的山芋粉圆子,偶尔火锅里还会加上醇厚香浓的肉和骨头,那是全家人极尽奢华的丰盛大餐。
至今每每想到那些丰盛的大餐抑或小菜,总会让我的内心被美好的旧日时光填塞得充实而温暖。
要说母亲制作的咸菜,还真有不少的话题。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吃饱饭都是奢望的年代,母亲起早摸黑地把自家的菜地种得满满当当不留一处空隙。收获季节,可以腌制的菜蔬被大篮大篮地摘回家,经过一道道工序,母亲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整齐码放到坛子里。需要久存的咸菜,母亲会把它们装进养水坛里,只要及时往坛口续水,坛子里的咸菜可以吃到第二年菜蔬大量收获的季节,色泽依然清新如初,味道依然可口如初。菜蔬淡季,那些腌制入味的咸菜便派上了大用场,一家人不说吃得多好,但至少不用强咽硬吞清淡无味的米饭。母亲还大篮大篮地拎着腌制好的咸菜送给缺盐少菜的邻居们。年少时的我,实在是想不明白,那些有一群劳动力的人家,下饭的菜蔬为什么还需要母亲的接济。
身教重于言传。多年后,回首母亲为我们这个家庭的辛勤付出,我以为确乎如此。在母亲无视自己的腰伤,咬牙撑持家中的一应事务也坚决不让我休学之后,我的成绩一跃而起,虽然身处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乡镇学校,但在初中毕业时我还是以超过省重点高中分数线的优异成绩被武汉一所中专录取,弟弟高中毕业后,以池州地区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上海交大。
我们姊妹几个,在母亲辛勤地劳作和呕心沥血的教育下,一个一个地,相继跳出“农门”。路遥《平凡的世界》,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卑微、生活的沧桑、成功的艰难、人性的坚韧,让我于书中领略了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路遥。真实的生活,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母亲的平凡却又极其的不平凡。
我们家的草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盘给了一位邻居。离开中院村,离开草屋,已有多年,但是,草屋里住过的亲人们以及与亲人们血肉交融的那些事,一直都在,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心海里,在我的血液里,汩汩流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