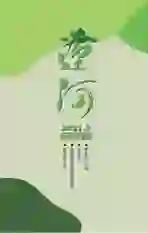南方来信
2021-07-20丛棣
丛棣
一
整条街多是干广告牌匾和房屋中介的,“沐阳心理咨询”门面不大,混在其中,很不起眼。这是我表弟牟杨干的,他是老板也是员工,是大夫也是患者。他比我小一岁,却从不管我叫哥,小时候我们总在一起玩,感觉友情大过亲情。
我常过来,一是走顺脚了,再就是来看看有没有我的东西,样报样刊什么的,偶尔也会收到邮政汇款单,上面的数额总是让人羞于启齿。我是个自由职业者,说白了就是个没正经单位的人,平时靠婚礼摄影及写点儿闲文赚些小钱,勉强过活吧,反正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的小说牟杨基本都看过,他可随意拆看我的东西,对此,我的态度是默许的,甚至是纵容的。
我什么时候过来,他都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屋里没别的人,门玻璃上一直贴张纸,招聘护士。连招呼都省了,牟杨转身去了另一间屋子,看似光洁的地面留下一串足印,有浮尘在光线里升腾闪现。他取来一副军棋,二话不说,摆上,一直都这样。这棋我俩从小下到大,不知下过多少盘,算不上瘾,就是种习惯吧,要不四目相对枯坐着,多闷啊。军棋好像有三种玩法,我们只玩“翻棋”,有点儿悬念,也拼运气,你猜不出下一个脸冲下的棋子会是多大的“长”,军师旅团营嘛,当然还有“司令”,也少不了意外,地雷和炸弹一触即发。我俩玩得云淡风轻,脸上都带笑,偶尔呵呵两声,看不出谁输谁赢。不紧不慢地下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都不怎么走心。牟杨问:大姑父身体挺好的啊?我答:还那样,天一冷就咳嗽,气管不好。我问牟杨:舅妈还出去干活吗?他答:一直干家政,闲不住。又补充了句,现在伺候一个老太太,一天给做两顿饭,一个月两千多。我说:那还不错,真不错。牟杨没有抬头,苦笑了一下,又撇了撇嘴,他的“军长”刚刚踩了我的“地雷”……
我妈和舅妈一直不对付,到后来势同水火,我知道的就有两次大的冲突,两个女人互吐口水,乱薅头发在地上翻滚,一时难分胜负。第一次姥姥还活着,在舅舅家卧床不起,妈妈领我去探望,发现姥姥的被窝里屎尿成堆,而姥姥的菜碟里只有半块腐乳,已经变黑板结。动手时,我妈在哭嚎,舅妈在尖叫,或许是我妈在尖叫,舅妈在哭嚎。其时,我和牟杨已躲进小屋,插上门,摆上军棋,难掩兴奋。第二次姥姥尸骨未寒,舅妈歇斯底里地争遗产,还要把这个小门市房过户到牟杨名下,本是来日方长需坐下好好商量的事,可她跳着脚抻长脖子指指点点只争朝夕,我妈孝敬我姥的金项链和金戒指随之暴露无遗,转瞬我妈就变身暴怒的母狮,将她扑倒并骑在身下,不光扯项链撸戒指,还薅掉了她好几绺头发。牟杨拉着我跑下楼,选个背阴的角落,两颗脑袋再次埋进棋里,也神了,那次想要什么我就会翻出什么,牟杨输得有气无力,我也赢到有气无力。
想想,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从此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真是这样,先是我妈出了车祸,后是舅舅得了癌症,这姐弟俩像商量好似的前后脚离开,撇下我们不管了,也切断了他们身后的亲情纽带。那时我和牟杨都上初中了,在一个学校,他被别人欺负了我会上,他给我买好吃的我也收,别人都以为我俩是发小,想不到还是正儿八经的兄弟,同病相怜的兄弟。牟杨越来越内向了,我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没了母亲,他没了父亲,两个少年的哀愁显而易见。只是他把狠劲儿用在了课本上,我把狠劲儿用在了课外书上,武侠、言情,也有中外名著,只要与学习无关就行。后来,我不出所料地进了技校,再后来牟杨毫无悬念地考上了大学,只是那所大学很一般,在省城,据说是舅妈的意思,她不想让儿子离她太远。我明明记得牟杨是学建筑的,怎么改学的心理学我也不大了解,只记得有年寒假回来他像傻掉了一样,舅妈红着眼睛找到我,像是找到了失散多年的骨肉,她让我领牟杨出去散散心,花多少钱她给。技校毕业后我进了工厂,没干上两年就赶上了下岗潮,舅妈找到我时,我正在本地的一家婚纱影楼上班,新兴行业,是托了好几层关系进去的。摄影助理,说白了就是学徒工,打杂的,工资少、活儿累,还没休息日,只是环境不错,看上去挺像那么回事儿。用舅妈的话说就是:在这儿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多好。我没法满足舅妈的请求,只答应抽空去看看牟杨。
牟杨又赢了一局。他好像看出了我心不在焉,问,怎么了,用不用我給你看看?我应了一声,心想,真是久病成良医啊。据我所知,这是瓦城第一家心理诊所,也极有可能是最后一家,现在它是唯一的,可有可无的。瓦城人看上去都挺阳光,为钱聒噪,为钱奔忙,没有谁需要心理疏导,更不会耗时劳神地来咨询什么,我想,如果改成“算命”,看病变看事儿,生意一定火。这话我不能说出口,怕他恼了,只好明知故问:最近活儿怎样,进人吗?牟杨叹了口气,能怎样,猫一天狗一天的呗。这话很世故很敷衍,同时也很浮夸,明明就是门可罗雀嘛,“猫狗”何解?不过,出自一个老肥宅之口倒也贴切,还有门上的那张纸也不难理解,“前台”硬要说成“护士”,只能说其心可诛啊。
我还是有点儿恍惚,他怎么如此油腻和猥琐,怎么也会说这种话了?也是在自问,答案明摆着,我们都年届不惑了,还都困在原地,像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面面相觑,也惺惺相惜。牟杨也是明知故问:有什么打算,和嫂子啥时候恢复?我挺无语,他从不叫我哥,却言之凿凿有个嫂子,而事实上他一共也没见过他嫂子几面,连我都快忘了我还有个前妻,结婚两年,离婚八年,所幸没有孩子。再说离完婚后她就回安徽老家了,从此音讯全无。她是我在厦门工作时的同事,我是摄影师,她是化妆师,没记错的话,她小我六岁。干我们这行流动性比较大,食色男女,萍水相逢,很容易擦出火花,同时诱惑和变数也多,修成正果的极少。谁都年轻过,那时她温婉可人,我潇洒不羁,两情相悦,当年她跟我坐火车一路北上,过了山海关,竟如荆轲过易水般悲壮。后来我们都后悔了,年龄差异,地域差异,性格差异……之前我好像跟牟杨说过,我们最后分开时只为一口饺子,她从不吃酸菜馅饺子,而酸菜馅饺子却是我的最爱,没有吵闹,只是崩溃,我们都觉得那不是一口饺子,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时至今日,牟杨仍对我的这段婚史感兴趣,一直在套我的话,还发自肺腑地啧啧,嫂子真漂亮啊,南方美女可惜了,可惜了。我有些哭笑不得,也想还以颜色揭揭他的疮疤:抓紧找一个吧,都多大了,再不娶老婆就得找老伴了!牟杨没恼,苦笑一声,幽幽道:哪个女的能入你舅妈的法眼啊,不找了,就算她跪地求我也不找了,这辈子就这样吧。我又想起点儿什么,话到嘴边还是咽下了,其实我想问问他记不记得那年寒假的事,当时他病了,病得不轻,差点儿被学校劝退了。他的初恋是高中同学,两人忍了三年,本想考同一所大学比翼高飞的,谁知人家女孩如愿考到了南方,他却灰头土脸地留在了北方,这也没什么,一时鸿雁往来,纸短情长……当年牟杨还是比较信任我的,给我看了女孩的照片,还有一封写给他的信,很长。照片是艺术照,信是绝交信。信上似乎还有泪痕,也不知是谁留下的。信里提及牟杨他妈也就是我舅妈……唉,我都看不下去了,你说她干的那叫啥事啊!瓦城很小,两家不光认识,还有点儿积怨,舅妈侦得消息后直接杀到人家,指天啐地,破口大骂,笑人家穷骂女孩贱,想勾搭她的宝贝儿子门儿都没有。女孩父母受此奇耻大辱,连夜给女孩打长途电话历数对方母亲的种种刁难,结果女孩又在绝交信中仔仔细细复述了一遍,连同自己的委屈,写满十页稿纸,字字力透纸背。牟杨当时还是个细高挑,经此一劫,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缕魂儿,他说,我想死。声音很小却吓我一跳,我都忘了当时是怎么劝他的,好像就是跟他比惨吧,在工厂干车床又累又危险,进影楼伺候客人横遭白眼,曾被三个丑女孩拒绝,到现在都未尝恋爱的滋味……见牟杨有所松动,我趁热打铁请了两天病假,陪他去了百里外的金沙滩。数九寒冬,杳无人迹,海冰一眼忘不到头,回来后我俩都感冒了,我比较重,连打几天吊瓶,为此还差点儿丢了工作。我想他是不会忘记的,只是时间过去太久了,懒得回忆,而且回忆起来也不那么真实了。
收拾完棋子,牟杨去泡了壶茶,一看就是有话要说。果然,他翻出来一本文学选刊,通常都是两本样刊的,我取走一本,他留一本。那是一篇名为《南方来信》的短篇小说,我改了几遍仍不理想,赌气般投了出去,谁知竟一矢中的,后来还被这家选刊选载了。不得不说,牟杨的鉴赏力还是有的,他直言不讳:这篇也能选载?文字没问题,那个年代的氛围还原得也算到位,“交笔友”的素材很好,只是前面给写成散文了,后面又变成网文了,有点儿异想天开,怎么说就是个怀旧故事,跟今天的人和事没半毛钱关系,别硬扯,二三十年的跨度,青春不死情缘不灭的,牵强不?你也真好意思虚构,多肉麻呀,再说都什么年代了……
牟杨的点评虽听着刺耳,但也算句句在理,让我不禁对他刮目相看,感觉他是让他那个强势的妈给耽误了,他骨子里不是个废柴,他不该留在瓦城,他不该继承这间小门面房,他也不该单身。也只有面对我时他才会说这么多话,小说读得也够仔细的,点评还远没结束:你是在用当下的思维揣度过去的人和事,你把人家姑娘写成“绿茶婊”了,可那时还没网络没手机没韩剧也没高铁……好,就算有,也没普及吧,那时的日子多慢啊,那时的姑娘多实诚啊,“梁爽”那个也不算撒谎耍心眼吧,信中的关系再亲密也是虚拟的,那时的“笔友”还没后来的“网友”直接呢,几乎没有变现的可能。连萍水相逢的机会都没有,你说她图你啥吧,不就是想装扮得更文艺一点儿嘛,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有故事的人,说白了就是弄巧成拙的单纯,甚至可以说是傻,傻得可爱……
二
我是九六年下的车间,实习期半年,半年后轉正。我的车床和李庆国的相邻,那是个虎头虎脑的家伙,总是眉开眼笑的,没出两天就跟我混熟了。算起来,他还是我师兄,同是厂技校出来的,比我早两年,看上去已是老油条了。没有他不知道的事,跟谁都嘻嘻哈哈,干活也风风火火,还是个热心肠,没少帮我。当时工厂的效益已经不好了,好不容易分下来一批活儿,得抻着点干。我们的友谊是从磨洋工开始的,出去抽烟,搭伴上厕所,或者就是在厂区闲逛,还算笔直的林荫道,有些杂乱的花坛,碰见球场有电工在玩篮球,我俩也会自来熟地凑上去,拍一拍,投一投。工厂的管理一直很松,到了后期已无条条框框,机器的轰鸣声再难连成一片,也无法掩盖一些杂音。有时和李庆国转着转着我就会心生错觉,阳光煦暖,鸟语花香,这不是工厂而是公园,生活真美好啊。事实上老工人早就愁容满面了,对此我们视而不见也很难理解,我们还那么年轻,都有些玩世不恭,甚至还都盼着厂子早一点儿黄呢。李庆国问我,厂子要是黄了你干什么去?我说,我哪知道啊,你呢?李庆国说:我去南方找我女朋友,她家有一大片茶园,如果那边好过我就不回来了。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唬住了我,南方?女朋友?茶园?哪一个都让我浮想联翩,哪一个都貌似美好的生活本身。我的目光在那张圆脸上多停留了几秒,他没笑场,眼神坦荡,似乎还透出一丝哀伤,看来这是真的,他没撒谎。
后来我才知道,李庆国和他女朋友还没见过面呢,他们是笔友。据他自己交代,两年前他在某杂志上登过征友启事,窄窄的一条,在某犄角旮旯,如边角余料,却不愁没人看到。你知道第一个月我收到多少封信吗?李庆国自问自答:过百了都,没错,就是一百多封,清一色小姑娘!见我一脸狐疑,李庆国赌咒发誓并现身说法:我那可是花钱登的,还有字数限制呢,关键是哥们儿词儿整得硬!身高一米八五,烟酒不沾,爱好文学,喜欢弹吉他……我打断他,怎么像征婚啊,再说,你这不骗人嘛。李庆国嘁了一声,这不叫骗,这是善意的谎言懂吗,要不谁会给你写信?好像是为了掩饰什么,他话锋一转:要不你也交个试试,挺有意思的,不用再花钱了,等我匀一个给你。当时也没太往心里去,谁知转过天李庆国真就带来了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信写得很有文采,字迹娟秀,信末还画了个简笔小人儿,俏皮可爱。照片上的女孩一袭白色连衣裙,皮肤有些黑,也许是反衬的关系或光线的原因,身后是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亚热带草木,蓊蓊郁郁的。女孩面目有些模糊,也可以说是柔和,笑起来的样子很明媚,透出一股别样的青春气息。手中的照片又冷不丁被李庆国夺回,说,看直眼了都,你说实话怎么样吧,我就是茬儿太多了顾不过来,要不才不会便宜你呢。经他这么一说,我脸腾的一下红了,感觉那个笑靥如花的女孩已转瞬变为商品,正卷入几千里外的一场交易,而她还被蒙在鼓里,一脸明媚。
李庆国交代得很清楚了,女孩叫梁爽,福建漳州的,职业她一直保密,不过收信地址是所小学,估计是个老师吧。李庆国和她通信一年多,她总是不冷不热的,无非说说那边的气象物候,问问这边的风土人情,再交流一下彼此的爱好,如蜻蜓点水一般,从不越雷池半步,这让李庆国兴味索然也失去了交往下去的耐心。他最后写的那封信主要是介绍我,转手的意思比较明显。我先过目一下,给我吹捧得有点儿过了,瞅着肉麻。不过不得不承认李庆国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字也是龙飞凤舞,很唬人。对于我的刮目相看,他摇头晃脑,哼唱起来: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又正色道:练练就有了,我是跟她不来电,没啥发挥余地,以后就看你的了兄弟!那封信发出去后如石沉大海,挺长时间李庆国见我都躲躲闪闪,有些抬不起头。有次他喊我一起去传达室,路上还碎碎念:也该到了,这都多少天了,怎么会呢,出啥问题了?我终于开眼了,厚厚一沓信件,都是李庆国的,翻来拣去没有一封是来自福建漳州某小学的。自然也没有寄给我的信,李庆国已介绍得很到位了,我是他的师弟,在同一家工厂同一个车间,同样的才华横溢。
李庆国一脸对不住地说,要不你主动写一封,人家毕竟是小姑娘,抹不开脸,你先起个头,等对上号就好了。我说,算了,顺其自然吧。也是感觉没戏,美梦提早破灭,也省却了种种麻烦。就是那张照片还时不时地在我脑袋里闪回,人不算多漂亮,但瞅着很舒服,区别于我的那些女同学和女工友,仿佛自带草木清香,新鲜又陌生。
谁知当一颗心不再悸动时却收到了信,还是直接寄给我的,让我一时手足无措。李庆国比我还兴奋,喜形于色,催我快点拆开,他也要看看。信中,梁爽称呼我“小高”,很熟的样子,她还跟我解释了没及时来信的原因,她病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医院。她这么一说,我还真就嗅到了淡淡的消毒液味儿,那是干净的味道,让周遭的铁锈味和机油味退避三舍。她说这些天那边一直在下雨,她还问我,你们那边下雨了吗?
我想,我得赶紧回信了。我要告诉她我这边艳阳高照,工厂花坛里鸡冠花串串红波斯菊开得正好,我还得问问她的身体状况,对她的病情表示关切,至于我自己……我觉得有必要让她知道,我已重拾课本准备自考,争取两年之内考上。这封信只有两页,却浪费了我一本稿纸。起首几个字写得不好看,撕掉!问候语不大合适,撕掉!某处遣词造句有问题,撕掉!有个标点符号没运用好,撕掉!最终呈现的也不是完美的状态,不过只能这样了,不能再拖了,寄信迟一天,收信就会晚一天。
我和梁爽就是这样对接上的。她夸我的文笔好,字字句句打动人心,不写文章可惜了。我问她,跟李庆国比呢?她回信道,没法比,他那是油腔滑调,你是直抒胸臆,就是不大会掩饰。我写信反夸她字写得漂亮,并坚信“字如其人”,她回信嗔怪我滑头,还说我是跟李庆国学坏了。这中间发生的事多已变成了白纸黑字,有据可查:我被迸射的铁屑烫伤了脸、她改吃中药不停地呕吐、厂庆征文我得了个二等奖,台风过境掀了她邻居家的屋顶……
三
再见牟杨我多少有了点儿底气,觉得有必要再跟他好好探讨一下小说,对,就是那篇《南方来信》。
之前我去看老爷子了,撞见了正在煎炒烹炸的郑阿姨,她如热恋中的少女般羞红了脸,嗫嚅着,提前给你爸过个生日,他啥也不会做,你回来正好,中午你们爷俩儿喝点,让他也解解馋。我冲她扯了扯嘴角,没说什么,跟我爸更没什么好说的,一直都这样。当年,我爸他们工厂倒得更早,等我正式下岗时他已在家闲了两年,还成功地把自己灌成一个酒鬼。后来,得亏碰上了郑阿姨,对他很上心,很多都是我媽生前所不能给予的。只是两人一直也没正式住在一起,扭扭捏捏的,其实一直想跟他俩说,不用考虑我,我是真心祝福他们的。我爸如今白白胖胖,喝喝茶,逗逗鸟,像个退休老干部。我给他发了个微信红包,又拿他的手机按了接收,他嘴上没说什么,但是脸上带笑眼中有光,仿佛那不是二百块而是两万块。我说,我过来找点儿东西,不用带我饭,我待会儿就走,又补充了一句,改天的,改天陪你喝两口。那个大松木箱子还在,那是我奶奶留下的,郑重其事地传给了我,只是我一直懒得搬走,太重了,里面满满的,多是日记本影集信件明信片之类的,我年轻时代的那些隐私都在这儿,史料般堆积着。那把锁头倒是不小,只是折页早就松动了,有撬动过的痕迹,我爸嫌疑最大,那些痕迹也无比陈旧了,我已有十多年没动过这个箱子,此次打开,腾出的灰尘及霉味有些呛人。梁爽写给我的信存有厚厚一摞,如果我席地而坐看下去会看到天黑。
我解释道:其实这篇小说虚构的成分很少,现实生活里她就叫梁爽,你说的狗血情节也是真实发生过的,梁爽得的是绝症,我是真心想去看她,哪怕是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要知道我从没出过远门,也从没下过那么大的决心。谁知她总回绝我,到后来都恼了,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看到她化疗后的模样,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由她姐姐代笔的,短短几句话,她让我忘了她,从此别过,她还说她舍不得我……
我说:信我都带来了,不信你可以看看……唉,你在听我说话吗?
牟杨就坐在我对面,头都没抬一下,不以为然地回着:我说的是后半段,很多年后你去南方工作,有天脑袋一热偷偷去了趟梁爽的家乡,结果发现她还活着,有老公有儿子,一家人整整齐齐快快乐乐地生活,受了刺激的你灰溜溜地跑掉了,回头直接跟那个女同事求婚,并带着她回到了生你养你的北方小城。到这里,也说得过去,见好就收也行,可你看看你后面写得都是什么呀?又过了很多年,你又收到了南方来信,还是梁爽。请告诉我,她为了什么呀,是惊讶于你真的成了一名作家?再顺便告诉你她看过你的小说,也看到了你的简介和近照,你的笔名和本名全被她掌握,她还很顺利地查询到你的通讯地址。
说这些时牟杨一直没抬头,眼睛也没在棋上,他在用一个指甲剔着另一个指甲里的黑垢,这让我很恼火,声调陡然升高:小说就是“虚构的真相”,生活素材需要艺术加工,懂吗,况且这个故事也是到此为止的,到最后也没展开那封信的内容,留着悬念呢,很多东西需要读者自己想象。
要叫我说啊,虚构得这么拧巴还不如狗血到底呢,节奏加快,再整出个一波三折,不是她死就是你亡,还是最惨烈的那种,多好。牟杨长吐一口烟雾,继续说,跟做人一样,写小说也不能太老实了,不能一撒谎就脸红,很吃亏的。
我重新打量了一下我这个表弟,觉得他这个买卖该关张了,他才是当作家的料,甚至可以去做编剧做导演,瓦城庙小水浅的,白瞎他这个人了。
牟杨终于抬起头,眼睛一亮,对了,还真有你一封信。又说,这个我可没拆啊,没准是嫂子写给你的,快打开看看啊。
看上去就是一封平信,标准信封上贴着普通邮票,字迹娟秀,收信人及地址明白无误,还特意注明“高述平亲启”。“高述平”是我的本名,我还有个亦俗亦雅的笔名,“高原”。再看底下寄信人地址,很长,开头即“广东省”,很多年没出门了,瞅着既陌生又遥远。这信让我觉着亲切,同时也疑窦丛生,仿佛这是件蒙尘的舞台道具,正穿越时空而来,还有些烫手。甭管是谁写给我的,我都想认认真真地看,舒舒服服地看,这不是一本杂志一份报纸,这是一封实实在在的信,身世待解。本不想当着牟杨的面拆开,可一转头我却发现他还在那看着我呢,确切点儿说是在盯着我手里的信,目光很复杂。此时走掉略显突兀,似乎就连把信揣起来都很难自然而然了,信封不是很厚,我对着光照了照,也是怕拆启的时候撕到了内容。
小高:
你好!好久不见,你一定不记得我是谁了。
年轻时我们经常通信的,你想起来了吗,呵呵,我是梁爽,你的一个老朋友。我记得我比你大两岁,我俩还一度以姐弟相称呢。当时我是医院里的护士,却骗你是个资深病人,开始是怪病,后来是绝症。对不起,我没有故意戏弄你的意思,当时就是琼瑶和岑凯伦的小说看多了,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平淡了,该有一个远在天边值得牵挂的人,也需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悲情的角色,谁知后来竟入戏太深出不来了。你好像也是,竟跟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一样,我说什么你都信,痴心一片,难以自拔。最多的时候,隔两天就能收到你的一封信,每一封都有四五页,我们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你说你要让我活下去,还说要照顾我一辈子,你说你想请假坐火车来看我……我害怕了,我不知该怎么圆下去,也不知该怎么面对你。想想我们那时多年轻啊,多傻啊,也多好啊……
那时我就看好你的文笔,没想到你真的成了一名作家,真替你高兴!我也一直爱好文学,只读不写,我好像除了写信什么都不会写,家里倒是订了很多文学报刊,只是能勾起我阅读欲望的文字已越来越少了。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小说,名字叫《南方来信》,我是一口气读完的,一边读一边掉眼泪。我又看了下作者,高原,不曾耳闻。好在有简介,原来“高原”本名高述平,就是你,没错。为此我又上网查询比对,还真就搜到了你的近照和通讯地址,也有电话。你的模样没怎么变,我们曾互赠过照片,你那时还留着“郭富城头”呢,呵呵,很潮的,只是没想到现在发量会变得这么少,不过,除了发型你真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帅气。我就不行了,满脸皱纹,一身肥肉,平日我自己都懒得照镜子,唉,不說也罢。
我记得我们到最后都没见着面,我“死”了嘛,“死”完就后悔了。之后很长时间我都幻想着你能从天而降,当面拆穿我,甩我两个耳光再拥我入怀。我也想过去找你,当面说清楚,可那时的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福州了,东北对我来说就像北极那么远。
一年后,我到底没忍住给你写了封长信,没过多久就给退了回来,你们的工厂已不复存在了。
小说中,时隔多年你偷偷来看我那段写得很细腻,我差点儿信以为真了。请回信告诉我,那是虚构的。还有,那篇小说看上去还没写完,此番给你写信也是为了迎合你的杜撰,但愿信的内容会带给你新的灵感。
对了,李庆国还好吗,现在在做什么?若有他的消息或联系方式请告知。
来日方长,期待你的回信。
谨祝秋安!
梁爽
2018年10月12日
这封信也把牟杨给噎住了,怔怔地看向我,嘴唇动了动终没说什么,其实他的话全都写在了脸上:怎么会这样?是啊,怎么会这样?我还想问问他呢。小说很生活,生活很小说,节外生枝,狗血淋漓,一旦铺展开来谁都无法置身事外。牟杨忽然问我,李庆国这人在哪儿,现在做什么?那样子有恨不得马上见一面的意思。我敷衍他,下一篇小说会专门写写他,你等着吧。事实上,我对李庆国的近况一无所知,我也有些年没见着他了。下岗后,他跑保险干传销还四处借钱,找到我时我差点儿没认出他,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这还是以前那个不修边幅的小胖子吗?好在有工友提前给我打过“预防针”,李庆国没白话几句就被我拆穿了,都是谎话,与其说是借钱还不如说是骗钱呢,对于他的胡搅蛮缠我很痛心,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堕落成了一个骗子呢?从此,他再没来找过我,我也没再见过这个人。有人说他跑路到南方了,还有人说他死了,让车撞死了,被人砍死了,当然是那些被他骗过的人传的。不知怎么,我又想起他曾经跟我说的话,他说工厂黄了他就去南方找他女朋友,他女朋友家有一大片茶园,要是那边好过他就不回来了。
牟杨说:我觉着梁爽和李庆国之间一定有事儿,你说……他俩后来是不是见过面呀?又说:你发现没,梁爽没给你留电话,这是等你给她回信呢。
牟杨难掩兴奋,还在自顾自地推理:她现在应该也是离异的,条件还不错,她已经从小说里看出你的婚姻状况了,时代不同了,她能主动联系你就说明有戏,她有在那边等你的意思,你应该马上给他回信。
要回你回。还有,再有她的信你直接给撇了,别让我看见。
我并不是生谁的气,就是觉得无聊,小说再蹩脚也已完成了,不会被改写,也不存在续篇。
四
半年后的一天——
我面前摆着军棋,战况惨烈,对面却空无一人。舅妈推门进来,顺手撕掉了门上的那张纸,又贴出一张,是“此房出租”。她一直肿着眼泡,眼里好像总噙着一汪浑浊的泪水,这让她看上去既苍老又愁苦。她说:述平,麻烦你了,再帮舅妈照看几天,你弟真没往这打电话吗,也没给你打吗?我没必要骗她,也不忍心骗她,我一直没接到牟杨的电话,一个都没有。
舅妈还是那个路数,哀怨过后又一惊一乍地问我:听说抑郁症可要命了,能死人的,你说,他不会想不开吧?
我像个医生一样开导她:他活得比我开心多了,他就是学心理学的,哪有看不开的事啊,再说他也老大不小了,过去那点儿破事他早就不往心里去了,您就放宽心吧,我估摸着他就是憋得慌,一个人出去散心了,在南方玩腻了就会回来的。
我的话有些多,漏洞百出,好在舅妈没怎么听,还在一边自责呢。都怨我,不该逼他相那个亲,那女的怎么说也是个二婚,还带着个孩子,你弟心气高啊。
舅妈好像是真想明白了,跟我掏心掏肺地絮叨上了,不时地抹抹眼睛。她的脸上已无当年的戾气,整个人看上去很平易近人,甚至是卑微,就是一个含辛茹苦的老母亲。她说:只要你弟平平安安地回来,他的事以后我再也不管了,他要是觉得外地好机会多,我给他钱让他出去闯闯也行,都这个岁数了,总在家跟前糗着也不是个事儿,还有你,怎么离一次婚就坐下病了?老本行也干不下去了?以前工作多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还能全国各地走,唉,你们能不能都好好点,让我们老人少操点儿心,都能让你俩愁死。
舅妈痛心疾首让我觉着很温暖,仿佛她的憔悴也有我一半原因,她真的老了,我爸也老了,他们都老得厉害。我终于还是忍住了,没有对舅妈坦陈,牟杨虽没打过电话,但来过一封信,是写给我的,上面有“高述平亲启”的字样,下面的地址开头即“广东省”。信不长——
哥:
见字如晤!一直当你是亲哥,一直也叫不出口,那就在信里称呼一回吧。
不该不辞而别的,也没留下只言片语,都这么长时间了,家里人一定急死了。不想打电话了,电话一通,念想、心情、空间感统统都没了,就算离家千里万里感觉也只是换了个房间,我也需要给我妈一点儿时间,让她好好地想一些事。
我恋爱了。对不住,是“梁爽”,你自己说的,要回信就让我回,结果我俩一直保持通信状态,已经小半年了。
我没有冒名顶替,我跟她说了,我是你表弟,还是个心理医生,我对那篇小说以及那段往事很感兴趣。很快我们就无话不谈了,很快我们就心意相通了。她跟我说,那个李庆国很无耻,某年打着你的旗号找过去,还从她手中拿走了一笔钱,说是要搭救身陷囹圄的你,其实她一眼就识破了他的把戏但没有拆穿,还说要真是那样就好了。我还跟她交代了你的情况,说你是我的病人,只有下军棋时是清醒的,写小说常常不知所云。她说,就算你没病你们也回不去了,永远都回不去了,她给你写信的目的就如同回头向暗处投一粒石子,她想听听会有什么回响传来。她说,她收获了我,这是老天对她的眷顾。对了,她很多年前就下海了,现在经营着一家很大的外贸公司。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她一直单身,从没结过婚。如果你真的去找过她,远远看到的应该是她姐姐一家,她姐姐在一所小学任教,你写给她的信都由她姐姐代转,“梁爽”实为她姐姐的名字,她另有其名,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吧,不说也罢。
我在这边很好,等我妈冷静下来了,我会回去跟她解释的,到时候把她也接过来,再也不回去了。其实早就该出来看看的,你也一样,再在瓦城待下去整个人就废了。出来散散心嘛,我给你留个这边的电话:139***7546。什么时候想过来就打给我,我和她一定好好招待你,说起来,你还是我俩的月老呢,呵呵,对不住了哥!
希望我们能在南方相聚,祝好!
牟杨
2019年3月19日
五一那天,我去看我爸了,中午还和他们一起吃了顿饺子,老爷子很开心,执意要跟我喝点儿。在他面前,我仍要装出一副不胜酒力的模样,两杯啤酒下肚就摇晃着告饶,一直都是这样。很早以前我爸就开始试探我的酒量,我一旦得意忘形后果将不堪设想,好在我心知肚明,不善饮的印象一度让他颇感欣慰。现在我的演技已臻于完美,老爷子对此深信不疑,嘿嘿着,完蛋玩意儿,一点儿都不随我。
他不知道的是,从他那出来我没直接回家,说来那都不算“家”,那只是个单身宿舍。形单影只的我直奔一家小酒馆,要了一打啤酒,喝到昏天黑地。最后摇晃着去了瓦城火车站,坐在外面的大台阶上抽烟,看出站口寥落的人影,听火车离站的长鸣。很多年前,我喜欢甩着长发东飘西荡,在厦门工作的那段时间总想去漳州看看,有次差点儿就成行了,谁知因醉酒而误了火车,醒酒后怅然若失,也从此断了念想。我已有很多年没有离开瓦城了,倒是经常晚上过来,在站前徘徊一会儿,夜深了,天冷了,就缩着脖子摇晃着回去。
或许,改天我还会过来的,在一个阳光很好的午后,穿着得体,跳上一辆南下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