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伍德·安德森的游离与附丽
2021-07-16林晓筱
林晓筱
舍伍德·安德森六岁时家道中落。拜他那位酗酒、纨绔的父亲所赐,美国中西部地区心碎家庭的故事中又添了新页。全家生活的重担随即落在了舍伍德身上,他为了生计,先后当过农夫、食品运送员、自行车装配工和报童。母亲略带苦涩地给他取了个昵称:“工作人”(Jobby)。
这本该是一份可供弗洛伊德式附会解读的童年档案,但事实上,类似的轨迹仍在继续,直至一九一二年,时年三十六岁的舍伍德·安德森突发精神崩溃,毫无征兆地离开了位于伊利里亚的办公室,此后开启了新的工种—写作。尽管日后他一再谈起这件事,企图为自己的作家生涯勾勒出传奇的起跑线,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工作人”跑过的一个弯道。他一直在转弯,一直在加速和减速,以至于特里林在评价他的“出走事件”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德森从未搞懂,所谓启蒙和皈依时刻,即‘走出去,不能仅仅用来庆贺,而必须向前发展,如此,始于意志的行为就会成长为一种智性行为。”或许自那时起,安德森身上的螺纹已被磨平,再也没有拧紧、固定在任何地方。奔波的足迹、频繁的转行、多变的婚姻,外加写作风格上的追寻,他似乎一直在游离,一直在寻找落脚点。
写作生涯并没有改变安德森的一贯状态,他并未安定下来专注于写作长篇故事,而是兜转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之中。有趣的是,他在给好友本杰明·许布希(Benjamin Huebsch)的信中曾这样解释他钟情短篇小说的理由:“我根本没有机会不受打扰地进行长时间的思考或写作,只有将构思的角色存入意识,与之共存,不得不用支离破碎的方式来构思它。于是,这些独立的故事变得清晰而浓烈起来。在我准备好将其中一篇写出来时,它就会一下子冒出来,像馏出物,像喷射物。”所谓“清晰而浓烈”是否就是他游离于短篇的原因呢?
一
一九一九年发表的《俄亥俄,温斯堡》(Winesburg, Ohio,又译《小城畸人》)成了舍伍德·安德森的代表作,也为他一生的短篇小说创作奠定了基本风格。许多评论不假思索地认为,安德森的这部代表作借鉴了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这样的论断若是给安德森召唤出引路人,倒也可以让他在写作上不再游离。但遗憾的是,这种观点并不能够成立。
舍伍德·安德森最初想要以第一篇故事《怪诞者之书》命名这部小说集,后改为《俄亥俄》,并在许布希的建议下,加入了虚构的小镇“温斯堡”。许多批评者都认为许布希才是读过《都柏林人》的那个人,由此才提出了在《俄亥俄》之中加入虚构地名的建议。而在安德森出版《俄亥俄,温斯堡》之后,第一次提出这部作品与乔伊斯有关的是《七艺》杂志的编辑、安德森的朋友沃尔多·弗兰克。他对这部作品赞不绝口,写信给安德森说:“没人会写这种好到令人叫绝的英语,除了乔伊斯……你应该读一读。”此外,从作家的回忆录和权威传记中,无法找到直接能佐证安德森在一九一九年前阅读过《都柏林人》的记录。
诚然,安德森或许会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一九二○年十二月期间,借助当时往返于欧洲和美国两地的“小杂志”—《小评论》—读到乔伊斯的作品,但这部作品是《尤利西斯》而非《都柏林人》。一九二一年,舍伍德·安德森抵达巴黎,在乔伊斯的出版人毕奇的引荐下,的确曾拜访过乔伊斯。这位爱尔兰作家给他留下了以下印象:“他长着一双我所见之人中最为纤细的手,有着能抵消忧愁的爱尔兰式的智慧和微笑。”此外,在安德森的笔记本中,他写道:“他的命运或许是最为多舛的,而《尤利西斯》无疑会是我们这一代出版的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一部。”随后,受到《尤利西斯》的影响,他创作出自己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中最有名的一部—《暗笑》。除此之外,未见他对《都柏林人》的任何评价。

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
相较于考证式的比对,文学史更为绮丽的一面在于作家基于时代的风格共鸣,安德森更多是在乔伊斯“多舛的命运”印鉴了自身的境遇。《都柏林人》和安德森的《俄亥俄,温斯堡》都是游离之后的一次重新归总。从写作风格上来说,短篇小说从惯常松散的陈列方式中游荡开去,其成书形式从“集”变成了“套”,后世批评家将这种将故事按组呈现,并要求读者在不同故事间相互借鉴,形成统一阅读经验的短篇小说创作命名为“成套短篇小说”(the short story cycle)。其次,风格上的游离不是姿态,而是一种创新,是属于在旅途中拉开距离后,对某个地方的重新审视,比如,乔伊斯正是怀着对都柏林这座城市架构“良心实验室”的愿望,借鉴阿奎那的神学理念,通过“灵光乍现”(epiphany)直抵都柏林人麻痹和瘫痪的中心。
相比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则有一套相对世俗的创作理念。他在往返于芝加哥和克莱德镇的岁月中,时常会住在寄宿公寓(boarding house)中。这种公寓在美国二十世纪初的工业化进程中十分多见,为许多类似安德森这样来自中西部的“工作人”提供了临时的住所。住在这里的人大体相似,他们沉默不语,神色黯然。安德森恰恰在这些人的木然中发现了故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房子里的人似乎都怀着强烈的渴望,却无人具备与生活搏斗的能力,反而以非常古怪的方式把我当成一件乐器。我觉得,他们不想亲口说出,而是通过我……以更为真实,更令人信服的方式将故事说出来。”
如何从沉默中生发出故事来?封闭的环境,沉默的人物,这对传统小说来说无疑折断了“行动”和“对话”这两大小说要素。文学史上也并非没有生发自类似封闭空间中的小说,比如《高老头》。一座公寓,各色人群,巴尔扎克依靠的是人物外在的经历,以主角拉斯蒂涅的成长,碰撞所有因欲望膨胀、身份陨落而凋零的人,所谓事件的冲突就来自“成长”与“凋零”的相向而遇。但舍伍德·安德森作为住客中的一员,感受到的是藏在沉默中的通病—怪诞。所谓怪诞,在安德森看来就是“所有人抓取了世上真理的一部分,成为各自的真理,并依照这个真理而活,于是人就成了怪诞之人”(《俄亥俄,溫斯堡》中的《怪诞人之书》)。这种极具寓言色彩的说理暗指安德森关注的不是事件,而是事件残余在人身上挥之不去的内心隐痛或精神伤疤,正是这两样东西不断翻滚着,变成了寄宿公寓里沉默的君王。安德森和乔伊斯一样,对人物现状的背后成因不做溯源式的追踪,却聚焦人物处在某种状态中的关键时间点。从描绘转向显现,这的确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转变。安德森曾在自传《讲故事的人的故事》(A Story Tellers Story)中向人们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拥挤的街道上,突然浮现出来一张脸。这张脸有故事要说,想要大声将自身的故事说出来,但是人们最多只能听到故事的一部分。”而艺术家的目的,就是要“在绘画、故事、诗歌中固定此刻”。因此,固定此刻(fix the moment)可以说就是安德森版本的“灵光乍现”。
“固定此刻”并不意味着人物僵住不动,毋宁说是对推动情节发展的人物行动进行降速、停滞,乃至最大限度的弃绝,从而将人物固定在作家犀利的目光下。如果说十九世纪的作家在书桌前进行的是手术般的剖析(比如,那幅著名的漫画中所描绘的福楼拜),那么在安德森面前,人物更像是固定在祭坛上进行启灵。他企图召唤出的是人物抵达“此刻”的经验压缩,并通过作家的才华将其显现出来。但是,要将这些人物真正联系在一起,还需要一个呈现的空间。表面上来看,所谓的“成套短篇小说”都有人物展开行动的场域,它可以是真实存在的“都柏林”,也可以是完全出于虚构的“温斯堡”,但安德森似乎并没有满足于发明一个地方。他在创作完《俄亥俄,温斯堡》之后,企图在人物的内心气质中再开凿出一块区域来。在这块区域里,所谓的“怪诞”才能进一步明晰起来。那应该怎样才能实现呢?幸运的是,他又经历了一次游离。
二
安德森于一九二一年踏上了短暂的欧洲之旅(5月23日至8月18日),只去了巴黎和英国。当他在“莎士比亚书店”的橱窗里看到自己的《俄亥俄,温斯堡》后喜出望外,忙不停地向店主西尔维亚·毕奇介绍起自己来。从毕奇撰写的《莎士比亚书店》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德森的自我介绍带有推销的性质,给毕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敏感的毕奇认为:“安德森充满魅力,非常讨人喜欢。我将他看成是诗人和福音传道者的混合体(但他并不布道),当然,略带一点演员的感觉。”正是凭借这种“演员的感觉”,安德森把自己塑造成了与巴黎这座城市相匹配的不羈的艺术家:“他一下子就决定放弃家庭,还有他那非常成功的油漆生意,离家出走,永远放弃了那种为了得到别人尊重而受的局限,还有为了寻求安全感而要背负的重担。”不过,这次在游离欧洲的时刻再次讲述之前的游离时刻,倒不是意味着安德森想一心融入巴黎的作家圈,乃至成为另一个来巴黎的美国人—埃兹拉·庞德。
安德森在遇见庞德之后,对后者做出了如下评价:“此人空空如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予的。”考虑到庞德为当时活跃在欧美两地的“小杂志”做出的贡献,并且安德森的创作和收入无不受益于这样的杂志,所以安德森所说的“没有什么”指的更多是精神或写作上的启示。无论是艺术追求和写作风格,他和庞德的确不是一路人。庞德身上的漂泊感以及艺术风格上的猛烈转向,对于“工作人”安德森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前者是一种漂泊他乡的精神扬弃,而后者更多是依附土地的焦虑生存。在因《暗笑》遭到海明威的讥讽,而与他一度交恶之后,安德森曾在信中对海明威说:“你说要给我来上一拳,语气多么令人遗憾,又那么温柔,听起来就像埃兹拉·庞德老叔。”从这个侧面或许可以看出他对庞德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安德森所说的“空空如也”更像是庞德身上的“美国性”(这其实是安德森的一次误判)。有关这一点,他倒是对格特鲁德·斯坦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安德森看来,这位“双腿如大理石柱般敦实”的美国女人,除了是他写作之路上的引路人之外,更是“用一种美国人的精明在讲故事,并把这一特性掷地有声地融入到了讲述方式之中”。无论是斯坦因身上的“敦实”,还是“掷地有声”的美国式精明,与上述语境中庞德或海明威式“遗憾而带温柔”的轻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安德森在与斯坦因谈论美国时曾毫不避讳地谈道:“你瞧瞧,我由衷相信我们这个大杂烩国家。奇怪了,我就是喜欢它。”在斯坦因身上,安德森确认了精神气质上美国性。弗吉尼亚·伍尔夫为这一点提供了注脚,在她看来,安德森就像一个在不断给自己施加催眠术的人,不断强调自己就是美国人。这种“被淹没的,然而却是基本的欲望”既是厄运,也是成为美国人的契机—不当英国或者欧洲人。
从欧洲再回美国,从彼岸的先锋艺术中闻到家乡的泥土气息,舍伍德·安德森是那个时代里所谓“现代主义洲际化运动”中的另类。将写作精神附丽乡愁,这种气质日后将在威廉·福克纳,乃至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身上不断闪现。这位匆匆离开“流动的盛宴”的过客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抵达纽约。

接下来,摆在安德森面前的任务无疑就成了书写美国人眼中的美国人,先前在《俄亥俄,温斯堡》中定义的怪诞,将进一步染上时代气息后变成美国式“麻痹的中心”,这块中心将持续成为他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的核心空间。换言之,安德森创作短篇小说的转向将在更为清晰的美国性中扎根下去。
此刻,在欧洲度过的夏天已成回响,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安德森说:“与我之前的远行相比,这个夏天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感受,凭借这种感受,我能够调整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再也不会离开自己的生活和所写的故事了。”所谓“再也不会离开”与他在欧洲确立的“美国性”有关,它不再仅仅是乡愁,而是掺杂的略带民族意味,对小说的全新认识:“长篇小说的形式(novel form)并不适合一个美国作家,这种形式是舶来品。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松散性(looseness)……生命就是一件松散的东西。在生命中并不存在故事情节。”这种创作思绪最终演变成《讲故事的人的故事》中,安德森最为著名的论断:
有一种观念贯穿于美国所有的故事讲述中,亦即,故事必须建立在某个情节之上,这种荒谬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观念认为,故事必须指向道德,指向高尚的人,引领人们成为更好的公民,等等。杂志上充斥着这些情节故事,我们的舞台上出演的大部分戏剧也都是情节剧。我在与朋友谈起这一点时,曾称其为“毒药般的情节”。因为在我看来,有关情节的认识,毒害了所有的故事叙述。我想要的是形式,而不是情节,一个更加难以捉摸,更难以实现的东西。
且不论这种对美国长篇小说的偏见是否正确,仅从安德森对“情节”的认识上来看,他的确处在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延长线上,这条线将直指小说中人物的内心。自这一刻起,摆放在安德森面前的那座祭坛将更具有美国中西部的气息。在安德森之后创作的短篇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地方不再是虚构的“温斯堡”,而成了实实在在的美国小镇。他不再借助虚拟的城市勾勒真实的人物状态,所谓的“怪诞”逐渐变成了人物心中的底板,他要做的是从这些底板中将真实活在时代中的人的照片冲印出来。他将借助真实的城市,书写隐藏在人物内心的真实品质,也将在游离欧洲之后,附丽美国。
三
哈罗德·布鲁姆将安德森笔下人物的境遇概括为:“无法成功进入内心隐藏的现实”和“无法在机器时代的现实以及传统场景的拘囿生活中找到个体的目的”。由此可见,一方面,安德森和乔伊斯一样,企图勾勒出个体处在成长临界点时的精神裂变;另一方面,乔伊斯笔下的人物在经历了“灵光乍现”之后就消失在幻灭的灯火、起航的船只、飘落的大雪等挥别的灰烬中,无从得知接下来的行踪,而安德森的短篇小说多数都带有回溯性,其浓重的回忆笔调将人物带回到成长的临界点,并再次经由“固定的此刻”放大人物当时的心理,给读者带来一种审视的眼光。
尽管如此,安德森所要做的事依旧很多。美国评论界一般认为,安德森的晚期小说写得较为失败。比如,特里林就认为,安德森的晚期小说“很明显试图赶上世界,可是世界发展得太快了”。不过,在他累得气喘吁吁、企图在游离之中赶上世界之前,他还有过一次重要的尝试,这一点在他的《马与人》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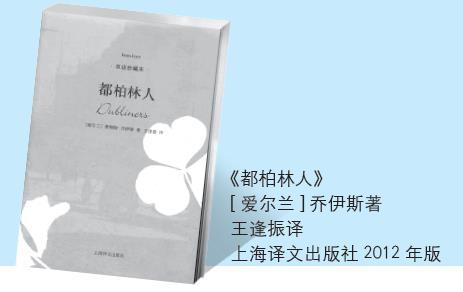
在发表于一九二三年的《马与人》中,《俄亥俄,温斯堡》的影子依稀可辨。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也是一部“成套短篇小说”(比如,其中第一篇故事中,省略号所刻意抹去的信息将在最后一篇中补全)。但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强化了《俄亥俄,温斯堡》中扑朔迷离的“怪诞”,将它放在“言说”的层面进行书写。
探索“言说自我”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安德森关注的主题。他曾在给儿子的信中指出,艺术创作是一场救赎,而“创作冲动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总是会将一个人抬得过高,进入某种醉态,随后将你摔到很低的地方。每个人身上都潜伏着一个艺术家。他就像怀孕的女人一样,即便怀上孩子之后,也要在分娩之前长时间地背负重担”。事实上,将艺术创作比作怀孕,继而将分娩视为通过文字拯救自我,这样的观点在舍伍德·安德森的私人信件中不断重复:“每个艺术家身上都隐藏着一个女人。就像女人一样,他会怀孕。他会生育。当他世界里的孩子被粗鲁地谈起,或者因他人的愚笨而不被理解时,就会产生一种伤痛,这种伤痛是那些没有怀过孕,没有生过孩子的人无法理解的。”
如此一来,艺术创作就是一场分娩,是言说内在自我的拯救行为,但关键在于,安德森也看到了这种言说拯救行为失效时会给人带来的负担。他不仅要写言说的“分娩”之痛,也要写因不能“分娩”而承受的言说“难产”之苦。这种“痛”与“苦”构成了《马与人》这部短篇小說集中,即“怪诞”主题之后,更清晰的人物空间。
《马与人》包含十一篇作品,其中严格意义上的故事只有九篇(另加一篇题记和一篇致敬西奥多·德莱塞的文字)。从题记的内容来看,安德森拿吃苹果作为隐喻,表明人们在对待实体物品时内心升起的思绪。吃下实体的苹果无疑能滋养肉身,此外,它还会激发一股思绪:“关键在于,在苹果的形状吸引了我的目光之后,我常常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触碰它了。我的双手朝我的欲念之物伸去,随后又缩了回来。”安德森强化了因欲念而生的隔阂,它构成了人内心的延宕,阻碍了人的行动。于是,“伸出又回缩”的状态就影射了人如鲠在喉的表达困境,也成了统领整部小说的内在主题。至于个中原因,安德森借助《德莱塞》这篇文字表明,作家德莱塞身上所具备的那种“看到什么就会简单而诚实地说出来”的真诚在现代作家身上已经消失。现代作家辞藻华丽,自以为能用文字击穿现实的外壳,但却在外壳之下只能构建出“美的梦境”,从而沉迷在这场梦境之中,无法抵达内心的真实。结合起来看,安德森通过肚中苹果的“饱腹感”和脑中苹果的“累赘感”之间的矛盾,意图探索的是构建言说行为与现实感知之间的隔阂问题。显然,从整体来看,安德森对此是持悲观态度的。
在小说集的《一个男人的故事》中,他借助文中那位作家的文稿揭示出的“墙”和“井”的主题,可视作整部短篇小说集的统领意象。“墙”将人们围起来,越砌越高,同时,人们在墙内不断挖“井”,且越挖越深。“墙”让人越来越封闭,“井”让人越陷越深,这个无限接近于卡夫卡式的隐喻,勾勒出的其实是人隔绝外部,又幽闭于内心的状态。当然,安德森并没有花费许多笔墨去揭示筑墙、挖井的原因,而是重点描绘了这两种状态给人物带来的影响。结合安德森有关“表达”与“生育”的隐喻来看,整部小说集可以围绕“井”和“墙”分为两组故事。其中,“墙”象征着人物用虚设的现实隔离众人,达到一种“难产之苦”;“井”则是人物沉迷于虚设的现实之中,催生全新一个虚设自我所经历的“分娩之痛”。
具体来看,《我是傻瓜》《一位现代派的胜利》《久未使用》这三篇可以视为“难产之苦”。这三篇故事中的主人公,无论出于炫耀,还是出于骗财,乃至为了躲避他人的目光,都选择了杜撰谎言。这类谎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不是对事件层面的掩盖,而是发明和重塑一个新的自我。或许,用安德森的话来说更为准确:孕育全新的自我。这些人物原本只想通过杜撰自我来躲避或接近人群,但却在构建谎言的过程中逐渐搭建起一道道的高墙,甚至还一度沉迷于不断抹去自我与重生自我的双重快感之中。安德森所描写的不是向外撒谎、骗取利益,继而自食其果的道德训诫小说,而是着重勾勒出谎言向内装点、粉饰,乃至重塑自我的诱惑。诱惑是危险的,同时也是反讽的。谎言不再是因果律上人为的逻辑作弊,也不再是对惯常生活的暂时脱轨,撒谎的人更像是迁徙于事实与虚构中的个体,他们怀着发明的快感,不断在自己身上构建世界和自我,与此同时,与外界越来越远。这种构建和躲避,原本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安宁,却给故事中的主人公带来了更为不安的心境。他们不断构建高墙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拆解自我,直至自我的碎片再也无法在虚构和现实的任何一个角落里拾起。“墙”与“谎言”是安德森小说中的空间隔绝。从小说所构建的氛围和主旨来看,这是安德森与乔伊斯最大的不同。乔伊斯的人物一闪而过,遁入“灵光”,而安德森的人物却不断让人看到落在地上的残影,他们不再隐遁在光焰之后,而是浸润在黑暗之中,用安德森自己的比喻来说,实则就是一次言说的“难产”—用内心最喧嚣的故事,言说最沉默的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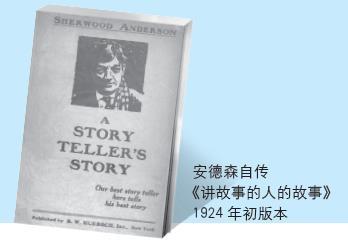
相比言说的“难产”主题,“分娩”主题更令人惊悚。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其他六篇故事都与此有关。这些故事中,主人公不再是主动选择“谎言”来建构躲避他人的堡垒,而揭示出一个古怪自我诞生于言说行为的“分娩”过程。在《成为女人的男人》这篇故事中,一直对自己的性别有所怀疑的男性主人公,在险些遭受男人误打误撞的强暴之后,躺在了一座废弃的屠宰场里,他被其中一具骇人的马的骨架包裹住。在这种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中,主人公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洗涤:
现在,我油然而生一种新的恐惧,这种感觉似乎深入到我的内心深处。我的意思是说,深入骨髓之中。我就像看见谷仓里的老鼠被狗叼着晃动一样。当你走在海滩上看见巨浪向你袭来时,就会感到类似的恐怖感。你看到它向你打来,你试图逃跑,但当你开始向岸边奔跑时,却出现了一个你无法翻越的石崖挡住了去路。就这样,海浪像山一样高,它就挡在你面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现在,它把你撞倒,或许会一遍又一遍地在你身上翻滚,直到你死去为止,从而把你冲刷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这是典型的安德森式的描写,其朴实的比喻背后隐藏着微妙的动态。海浪如山高,就像一堵堵的“墙”,同时海浪也打在人的身上,不断冲刷自我。通过不断重复的力量,强行斩断与过往的联系,从纵向上来看,也就是一个人不断向下挖井的过程,本质上是对过去自我的一次埋葬。由此可见,“井”的主题与一个人身上积攒的时间的断裂有关。通过不断努力言说自我的个体,在自身身上的连续时间中拉开一条裂隙,人们继而想要从这条裂隙中将自己挤压出来,并由此经历痛楚,这就是“分娩之痛”。
由此展开,读者可以发现,其中《芝加哥的哈姆雷特》《悲伤的号手》这两篇涉及的是儿子与父亲之间的主题,儿子身上延续着父亲所烙下的时间的影子,父亲更多代表着过往的经历,而儿子带着这种经历在面向自我时,势必就产生了在时间中诞生自我的创痛。此外,时间也呈现出“虚妄的现在”和“无尽等待中的未来”这两个维度。读者可以看到,在《牛奶瓶》以及《一个男人的故事》中,主人公所沉浸的恰恰是无限延展开去的“现在时刻”,他们对周围世界置若罔闻,乃至亲人遇害也不管不顾,只是在脑中不断构想、创作着自我的故事,这种构想不能不说是怪诞的,怪就怪在他们在孕育痛苦的同时,还不断重复着孕育的机制。“现在”只留下了机械而麻木的重復,徒有时间流过的形式,却不产出任何意义,直至如同前文提到过的“海浪”一样,将个体冲刷干净。这一股股浪潮不仅从人身上碾过,更可怕的是,它会带来未来的气息,回打在人物身上,从而改变人物从现在通往未来的途径,这一点在《俄亥俄的异教徒》这篇故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从这篇故事中不难发现,所有人都在内心深处不断与自我言说,这种言说咄咄逼人,言之灼灼,它分娩出新的个体,相比于“谎言”所带来的难产之苦,这种分娩之所以疼痛,还在于让人物自己相信并沉迷于吞噬时间的摄魂的力量。安德森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时常会中断叙事,加入离题话语,企图将读者带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么做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看清痛楚本身。
就如同整部小说集中经常会出现的“河湾”场景一样,人物起于言说,囿于言说,并最终止于言说,无数看似热闹的内心故事,最终无法抵达他人的耳畔,只能如河流般折回自身,变成一种负担。在不断酝酿的过程中,强行挤压出来的个体,又因沉迷于讲述之中,成了自我世界中的标本,他们定格在过去,虚设现在,粘连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长”是一个伪命题,毋宁说只是一具躯壳,小说展开的“过去式”的斑斓笔调,无异于蝴蝶飞回茧时展开的彩翼。

当然,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整部小说中还有一个隐藏的背景:美国禁酒令。换言之,美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似乎成了安德森笔下的另一个无处不在的“人物”。他控制着人物内心的动机与渴望,并亲手扼杀了满足渴望的可能。这种由欲望催生,并在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刻不断被苦闷消耗自身的痛楚,或许也契合了安德森这一部小说的内在精神。
四
说到底,经由《马与人》这部小说集,安德森才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作家。他笔下那些通过谎言企图躲避众人的人,那些在自我杜撰的时间里诞生并扭曲的人,他们都在欲望的时代和时代的欲望中打转。这一代的美国人,不再是马克·吐温笔下借助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从天真到经验转变的个体,而成了一个个浸润在精神堰塞湖中的“怪人”。
多年以后,福克纳指出,在安德森笔下,风格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当然,这种“目的”也回响在另一句安德森劝他勿忘本土性的教导中:“只要你能记住这个地方,但不为它感到羞愧就行了。”安德森无疑是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人。
同样,即便是对安德森创作提出诸多批评的特里林,也还是带着回忆的温度指出,安德森之所以打动他们这一代读者,是因为小说天然具有一种青春期的特质,待到成年再次阅读这些小说就会感到“痛楚与疑惑,仿佛旧日里收到或写作的信件”。关键不在于这些信件是何时写作或收到的,而在于何时将它们拆开重读。安德森在游离,从工作游离到小说,从美国游离到欧洲,他写作的小说也在游离,从经历“固定的时刻”游离到体会“分娩之痛”,这一次次的游离,其实也就是一次次的附丽,两者本意都是“离”。
或许只有不断游离,才是安德森的宿命,它不断赋予过程以起点和终点的双重使命,成就了独属于他的命定之音。读者认识这个人,阅读他的小说,就会像在某个不再痛楚、不再疑惑的成年时刻,突然收到了一封封从青春期就寄出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