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之旅,或历史的眩晕症
2021-07-16瞿瑞
瞿瑞
一九○九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间,在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局任职的弗朗茨·卡夫卡曾两次来到意大利加尔达湖畔的里瓦小镇疗养,期间共写下三个不同版本的《猎人格拉胡斯》,这部作品最终并未完成,也从未在卡夫卡生前公开发表。考虑到这个残篇遗失在历史中的巨大可能性—如果不是马克思·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意愿,决定出版卡夫卡的全部作品(包括草稿、书信、日记),以及这些作品在西方社会带来的一连串奇迹般的回应—那么近一个世纪后,另一位德語作家温弗里德·塞巴尔德的小说处女作《眩晕》,很可能完全不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样子。
历史的小径有无数分岔的可能,存在于此刻的事物,被一个个脆弱的偶然性所维持,有着极不稳定的结构。正如塞巴尔德后来在他的另一部作品《土星之环》中提到的:“燕子们成群结队在还有最后一丝光线的天空盘旋,那时我就会想,世界只是被它们从天空中穿行的轨迹捆扎起来的。”
塞巴尔德小说的美学,正是建立在对虚无的行迹的长久观察和耐心描摹之上,甚至有时,会由于人物的消失、细节无休止的蔓延,被视为随笔或旅行文学,或者某种百科全书式的跨文体写作;然而《眩晕》,作为塞巴尔德第一次从学术写作转向虚构文体的尝试,它明确的主题和精心编织的线索,完整地演示了其如何作为小说而成立,以及塞巴尔德小说美学的运行机制。
四篇故事的主人公:亨利·贝尔(司汤达)、作为历史学家的叙述者“我”、写小说的保险公司职员的弗朗茨·卡夫卡,以及阔别故乡小镇W多年的叙述者“我”(此人的经历极为接近塞巴尔德本人),虽然分散在不同的时空中生活、旅行、写作,却皆患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官能症,它表现为在特定场景中,一阵忽然而来的“眩晕”。关于眩晕作为一种不寻常的生理体验,罗马尼亚哲学家齐奥朗曾这样写道:
(眩晕症)或者具有比哲学家乃至诗人倾向于设想的更为深刻的意义。不再能直立—背离人的自然姿势—并非源于神经紊乱或血液的组织,而是因为人性现象的枯竭,也就是说人失去了伴随他的一切特征。你用尽了自身的人性?那么注定要抛弃人性据以界定自己的形式。你倒下了,但并非因此倒退到动物,更有可能是,眩晕把我们摔倒在地是为了给予我们另外的发展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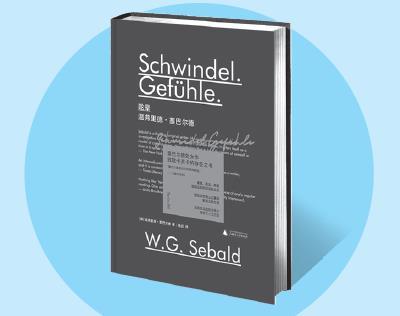
《眩晕》 [德]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著 徐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塞巴尔德的小说对于“眩晕”的展示,似乎遵循着相似的原理,眩晕不仅是一种特殊的生理感觉,一种令人迷惑的创伤体验,更是一种神秘的揭示。比如《贝尔,或爱之奇异事实》一篇中,当亨利·贝尔面对昔日的拿破仑战场时:“他感到脑海中携带的战斗画面与此刻在他眼前铺开的战争真实发生过的证据之间的差异,让它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眩晕的迷惑。”以及《海外》一篇中,历史学家“我”站在米兰大教堂的廊台上,发现:“尽管极力想自己说明这几天发生的种种是如何将我带到这个地方的,但我深知无法分辨自己在生者之地,还是已经在另一个世界。当我登上大教堂顶层的廊台,在阵阵袭来的眩晕中,遥望现在于我而言全然陌生的城市那昏蒙的全景时,记忆的麻痹依然无改。”
现实和记忆之间的差异,生者世界(正在进行)和死者世界(过去记忆)的混淆,渐渐取消了个人存在的坐标。而且随着人物的视角越来越高,俯看程度不断加深,对于记忆问题的揭示也在逐渐深入,最终在《归乡》的末尾到达了顶峰:“我的左边有一道真正令人眩晕的深渊。我走到路的边缘,意识到我从未俯看得如此深。那里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丛灌木,一棵残枝,一簇草,只有石头,云影掠过陡坡,穿过峡谷。此外无物一栋。万籁俱寂,连植物最后的生命痕迹,最后一片沙沙作响的树叶或树皮碎片也早已消失,只有岩石静止地躺在地上。这时词语作为几乎消失的回音,在令人窒息的空虚中返回。”
与其说叙述者望见了现实中的深渊,毋宁说在这一场景中,无处不在的历史黑洞最终清晰地显现,记忆吞噬了现实,只剩下一片冰冷的岩石。塞巴尔德的笔下的叙述者,具备“猎人格拉胡斯”式的幽灵属性,在看似无目的的尘世漂行中,它遇见生者也遇见死者,它望见记忆和现实—但他同时又并不拥有以上这一切—使它能够轻盈地飘升至时间和空间之上,只有历史的幽灵才可能拥有这种极致的俯瞰。写作就是这样的俯瞰,作家正是通过写作这一行为成为了历史的幽灵。
回到卡夫卡的《猎人格拉胡斯》,这则未完成的故事虽然极为短小,却有着精致的神话结构,它不仅指涉卡夫卡自身的某种困境(格拉胡斯这个名字在西班牙语意为“乌鸦”,而“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意为“寒鸦”,两者有着微妙的对应),也是现代人生存状态的一则寓言。在这则故事里,已故的猎人格拉胡斯被两个抬担架的人送到里瓦,他亲自告诉里瓦市市长萨尔瓦托雷,他摔下了悬崖,虽然已经死了,但从某种程度上他还活着。不知道是他的死亡小舟走错了航向,还是出于其他原因,他留在了人间,他的小舟从此航行在这尘世的河流上。

《土星之环》 [德]温弗里德·塞巴尔德著闵志荣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死者在尘世间游荡,取消了尘世的命运,既对未来无所依傍,也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这一历史的幽灵的形象—“两个身穿缀银深色外衣的男子,抬着一副担架,花布下显然躺着一个人”—在《眩晕》中的四个章节不断变形、复现,几乎像是一种标志性的提示。比如一八一三年,司汤达和盖拉尔迪夫人同游加尔达湖畔时,这一情形引起了盖拉尔迪夫人的不快;一九八七年,叙述者“我”在维罗纳漫游之际,匆忙间的街头一瞥;一九一三年,作为故事的关键场景,在里瓦疗养的卡夫卡的脑海中逐渐显形;以及《归乡》中,当叙述者“我”回到位于南德的故乡小镇W后,在诸多对于故乡的记忆中,提到一个摔下山崖(和格拉胡斯分享了相同命运)的猎人施拉德。而《猎人格拉胡斯》中的里瓦市市长萨尔瓦托雷变身为叙述者“我”的朋友—作家萨尔瓦托雷,此人似乎拥有超出历史的记忆力,见证着二十世纪以来,意大利维罗纳地区循环发生的恶行。
至此,人类两百年的历史,似乎呈现出漩涡形的构造,并朝着一个最终的点奔去—在《眩晕》结尾的段落,塞巴尔德于深渊之上突然调转了镜头,聚焦于伦敦大火的场景,指向人类文明覆灭的前景,甚至不无幽默地为之设置了一个期限(小说结尾那神秘的数字:2013)。四个篇章的主人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途经了同一地点(意大利里瓦),见证了历史的重叠时刻—荒诞的是,其中的线索来自一个未完成的寓言故事。在不同时代,历史的眩晕症,在四位旅人的旅途中不时闪现,就好像司汤达、卡夫卡、叙述者“我”(是否可以视为塞巴尔德本人)不过是幽灵“格拉胡斯”的不同分身,只是偶然地在灾难来临前的特殊时间点上落入历史不断重复的段落中,甚至他们追寻的事物也有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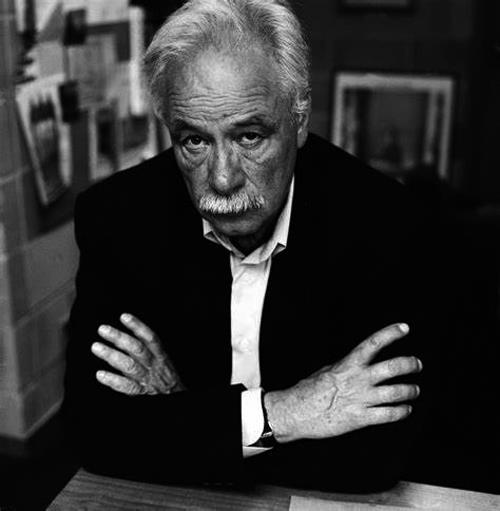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W. G. Sebald)
其中,爱的落空,如同歌剧中的咏叹调一般,是最为悲凉的乐章。比如,司汤达在纸上虚构的一场了无爱意的旅行,最终将爱情的生长比作“将死去的树枝变成一件真实奇观这一漫长的结晶过程”;比如,卡夫卡在疗养地遇到的“美人鱼”式的热那亚女孩,与她消失于船上的最后一瞥,并发展出所谓“无身之爱的碎片理论”;比如叙述者“我”在里瓦遇见的与自己同岁的旅馆老板娘卢恰娜,最终对方乘坐着“阿尔法车沿街缓缓行驶着,消失在一个拐向另一个世界的拐角处”。这些落空的爱,在第四章“我”回到故乡W之后,呈現出全然崩塌的状态,家宅、父母、邻居,并且在我童年暗恋的女孩失身于猎人施拉德这一场景中,达到了令人失语的状态。这些爱的落空,与其说是作者设计的情感线索,不如说是作为幽灵的无奈,塞巴尔德借卡夫卡之口表述了出来:“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包括渴望留住的爱人的形象。”
塞巴尔德却将对于真相的信念,转化为写作(记忆)的信念。正如叙述者“我”所热爱的画家皮萨内洛的艺术,也同样适用于塞巴尔德的作品—“其中所有的对象,无论主次,无论是天空中的飞鸟,苍翠的森林,还是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被赋予了平等而不受减损的存在权。”塞巴尔德留下的四部虚构作品,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为人类文明那不断出现又不断湮灭的细节赋形:一个人、一个地名、一座建筑、一部歌剧、一幅壁画、一片海滩、一团灰烬……这些被遗忘的事物无限地增殖、变异、消失,回望人类以及人类的所有努力留下的全部遗迹,它们都留在塞巴尔德如烟般绵延不断的长句里。
